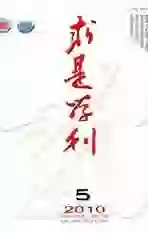明清神魔小说评点与编创之关系探析
2011-01-01纪德君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明代中后期,神魔小说产生、兴起,引起了一些文人的评点兴趣,他们从探讨《西游记》入手,提出并阐发了心性论、真幻论、趣味论与游戏论等理论主张,不仅较深入地揭示了神魔小说的编创旨趣与编创特点,而且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导、影响了神魔小说的再创作,致使神魔小说在“曼衍虚诞”的艺术描写中寓含了发人深省的“理”、耐人寻味的“真”和令人解颐的“趣”,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提升了神魔小说的艺术品位,使其具有了较丰富的审美认识价值。
关键词:神魔小说;心性论;真幻论;趣味论
作者简介:纪德君(1966—),男,安徽长丰人,文学博士,广州大学俗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教授,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明清通俗小说编创方式研究”,项目编号:05BZW023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lO)05-0107-06 收稿日期:2010-01-29
神魔小说是明清通俗小说的主要类型之一。该类小说主要描写人妖争胜、仙佛斗法与神魔争战,故事情节光怪陆离、奇谲诡异、真幻相间,而且糅合了民间的宗教信仰及处世智慧,因此颇能吸引庶众。并引起了一些文人评点的兴趣。神魔小说在“幻妄无当”的叙事中隐含了什么样的深意?它在艺术描写上有哪些特点?当时,一些文人由《西游记》人手对这些问题展开了讨论,这对神魔小说的再创作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Ⅱ向。本文试对这种影响略作考察,以期为神魔小说研究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一、《西游记》评点中的“心性论”
《西游记》这种侈谈神魔之争的小说,究竟有什么意义呢?一些评点者指出,其意义就在于它“幻中有理”,也即在“曼衍虚诞”的描写中隐含了丰富、深邃的人生哲理。如谢肇涮认为《西游记》“亦有至理存焉”。盛于斯也认为:“《西游记》作者极有深意。”吴从龙还说《西游记》是“一部定性书……勘透方有分晓”。李贽则说《西游记》“游戏之中,暗传密谛”。那么,《西游记》暗传的“密谛”是什么呢?有评点者认为它暗传的是心性修养的哲理,如陈元之《西游记序》所论:
余览其意,近斥驰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其叙以为:剥、,捌、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所以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撮魔以还理,还理以归太初,即心无可称……此其书直寓言者哉。陈氏对《西游记》原本之叙的观点甚为叹赏,认为小说中的人物皆有寓意,旨在演述“魔以心生,亦以心摄”的心性修养之道。持此说者,不乏其人。盛于斯即说《西游记》“每立一意,必有所指,即中间斜(科)诨语,亦皆关合性命真宗”。这与演述心性修养之道的认识是一致的。谢肇涮则具体地指出:“《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心猿驯伏,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书也以心性说来阐释《西游记》的内涵。其卷首《批点西游记序》云:“东,生方也,心生种种魔生;西,灭地也,心灭种种魔灭。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第十三回总评又云:“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一部《西游记》,只是如此,别无些子剩却矣。”袁于令在《西游记题词》之中也认为,这部书旨在阐发修养心性、战胜魔障之理:“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摧挫之极,而心性不惊,此《西游记》之所以作也。”
由此可见,明代人多喜欢从心性修养角度来解读、评价《西游记》。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这显然与《西游记》的思想内涵有关。《西游记》叙述孙悟空由闹三界到西天取经的传奇经历,的确宣扬了修心炼性的学问。在小说中。作者经常用“心猿”来指称“孙悟空”。孙悟空的经历,实际上就隐喻了心性修炼的过程。其中。大闹天宫是“心何足”、“意未宁”;压于两界山下,是“定心猿”;到西天取经则是“心猿归正”、“炼魔”、“魔灭尽”与“道归根”等。而妖魔则是修心的障碍,所谓“菩萨、妖精,总在一念之间”;“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取经途中的种种妖魔,即“大半起自心理或生理的现象,一方面由于感官经验的限制,导致主观意识的错误判断,因而产生种种假相,迷惑了本心;另一方面,又由于生理欲求与心理之间的矛盾,使人徘徊于满足与割舍之间,故纷纷劫难不易解脱”。如小说第十四回,写孙悟空打死了六个剪径的蟊贼:眼看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意见欲、身本忧,这实际上就是排除“六欲”对取经的干扰。第五十七至五十八回,又写了一个真假美猴王的故事,隐喻在修心的过程中,心灵有时会受两种相互冲突的意念困扰,从而迷失了方向,不知何去何从,因此只有“剪断二心”,“同心戮力”,才能修成正果。
在小说中,作者为了表现“心猿归正”的总体设计,还让孙悟空不时地向唐僧直接宣传“明心见性”的主张。例如,第二十四回唐僧问悟空何时可到西天雷音,悟空答道:“只要你见性志诚,念念回首处,即是灵山。”第八十五回,悟空还用鸟巢禅师的《多心经》提醒唐僧道:“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人人有个灵山塔,好向灵山塔下修”,顿使唐僧明了“千经万典,也只是修心”。可见《西游记》在总体上自觉地宣扬了“修心炼性”、“明心见性”的人生哲理。
当然,明代人从修心角度来认识《西游记》,也与明中叶以来儒、释、道三教合流的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当时,三教在“互借”、“互渗”中都讲求“心性之学”。禅宗讲究“即心是佛”,阳明“心学”则以“灭心中贼”为宗旨,而道教也以“心性修炼”为其主要功课。这种三教归于“心性”的文化思潮,不仅濡染了《西游记》等神魔小说的创作,而且也影响了人们对《西游记》的阐释。可以说,明人对《西游记》修心寓言的解读,既揭示了作品的思想渊源,同时也反映了作品产生时代的文化思潮。
二、“心性论”与神魔小说创作
《西游记》评点中的“心性论”,对后来的神魔小说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例如《西游记》的三部续书《续西游记》、《后西游记》、《西游补》,以及《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东度记》等小说的创作,就明显受到了明代以心性论诠释《西游记》的启发。这从这些小说的序跋与创作实际中。就可以一目了然。
清初真复居士在《续西游记序》中就从修心的角度谈论《西游记》中的佛、魔关系,认为“机心”是“魔与佛之关捩”,“机心存于中,则大道畔于外,必至之理也。前记谬悠谲诳,滑稽之雄。大概以心降魔,设七十二种变化,以究心之用”;而续书则“以荒唐毁亵为忧,兼之机变太熟,扰攘日生,理舛虚无,道乖平等,继撰是编,一归铲削。俾去来各有根因,真幻等诸正觉。起魔摄魔,近在方寸,不烦剿打扑灭,不用彼法唠叨”。
小说第三回写唐僧师徒参见如来,如来问:“为何事求经,本何心而取?”行者说是本“机变心”。如来道:“本一机变,与吾经一字也不合,怎么取得?”行者情急之下,一口气说出了奸心、盗心、邪心、淫心等许多种心。如来又道:“你说一心,便种了一心之因;种种因生,则种种怪生。”结果,在归途中,由于他们机心未断,引得妖魔纷纷赶来抢夺经卷。如第五回唐僧动了吟咏之心,遭遇蠢鱼精抢夺经担;八戒动了饥饿之心,在饿鬼林遭夺食之报;沙僧生嗟叹抱怨之心,惹出淫雨林妖魔愚弄。在作者看来,“妖魔总是机心惹”,若要除妖,还需灭掉机心。对机心的争论持续了一路。直到悟空等顿悟机心乃起魔之根,灭掉机心,路途始无妖魔。修心的主旨得到了空前的强化。
董说的《西游补》也同样演绎“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修心法则,不过,作者重在写心猿历情劫,归大道的故事。董说在《西游补答问》中即说:“悟通大道,必先空破情根,必先走人情内;走人情内,见得世界情根之虚,然后走出情外,认得道根之实。《西游补》者,情妖也;情妖者,鲭鱼精也。”“情之魔人,无形无声,不识不知……若一人而决不可出,知情是魔,便是出头地步。”小说中行者所历诸多幻梦,皆系其心动着魔人幻所致。正如董说《西游补答问》指出的:“夫迷悟空者,即悟空也。……种种幻境,皆由心造。”第十回写行者被几百条红线缠住,无法脱身,忽然眼前一亮,空中现出一个老人,帮他扯断红线。行者问其姓名,老人自称是悟空,并叙其来历。悟空恼怒:“你这六耳泼贼又来耍我么?”取棒打去,老人倏忽不见。行者方才悟得是其真神出现。这段描写即有意照应了《西游记》中真假悟空隐喻的二心之争,点出了心的主旨。正如回末评云:“救心之心,心外心也。心外有心,正是妄心,如何救得真心?盖行者迷惑情魔,心已妄矣;真心却自明白,救妄心者,正是真心。”第十一回,写悟空将其毫毛所变的沉迷女色之行者收回自身,回末批语日:“收放心一部大主意,却露在此处。”
《后西游记》也把“心即是佛”的命题和儒家的“求其放心”结合起来,依靠修心养性来破心中之魔。该书第四十回回末诗云:“前西游后后西游,要见心修性也修。”可见作者不仅认同明代人以修心观点来评论《西游记》的思路,而且还以此作为他创作《后西游记》的主导思想。《西游记》的回目中有大量的“心”字,《后西游记》亦如法炮制,诸如“心明清静法,棒喝野狐禅”、“唐长老心散着魔,小行者分身伏怪”等,全部四十个回目中有十三个回目中含有“心”字。文本中也处处强调心的作用,如第一回小石猴出生后,效仿当年孙大圣出外寻仙访道,结果发现“求来求去,无非是旁门外道。……与其在外面千山万水的流荡,莫若回头归去,到方寸地上做些工夫”,此处“方寸”即指心。第十三回唐半偈对小行者说:“我想天下那有妖魔,不过邪心妄念,自生妖魔耳。”第二十六回小行者认为“妖精虽多,却一妖一心,心多必乱”,又有诗云“万心何似一心坚”。其他如第十八、三十六、三十八、三十九回中也有类似描写。可见,作者自觉地将修心的观点贯穿到小说整个故事情节的构思与写作中,以表达其哲理意蕴。
《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则围绕着“开心迷”做文章,书中所写宗孔(儒)、宝光(释)、灵明(道)所代表的三教开化的群“迷”,如叹贫迷、做官迷、好名迷、狂妄迷、风月迷、嫉妒迷、求利迷等,名虽为妖,实由心生。“三教开迷”意在“驱邪荡秽,引善化恶,以助政教”。这与《西游记》中的祛除“六贼”,摒弃“二心”的寓意异曲同工。
《东度记》“借酒色财气、逞邪弄怪之谈”,书中所写陶情(又名“雨里雾”)、王阳(又名“云里雨”)、艾多(又名“浪里淘”)、分心魔(又名“胆里生”)四个邪魔,实即酒、色、财、气的化身;其他邪魔,亦由贪、慎、痴等七情六欲所化。这些邪魔形象地演绎了“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的哲理。
《斩鬼传》也以心术之邪正作为人鬼之分界,作者指出:“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间。方寸正的,鬼可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为鬼。”(第一回)书中所写诌鬼、假鬼、奸鬼、捣大鬼、冒失鬼、风流鬼等四十多个形形色色的鬼类,就是人世间各种心术不正之丑类的形象写照。《平鬼传》也同样把不合儒家伦常的邪心恶欲拟之为鬼,托钟馗以斩之。《精神降鬼传》则以“精神”为帅,来降服人之各种邪念恶习所化之鬼。
总之,这些神魔小说的作者均受心性论的影响,以为一切魔劫皆由心生,亦由心灭;在写法上,则有意将修心摄魔的理念具象化为小说中的神魔之争,其所写多属寓言,半皆臆造,虽不乏发人深省之处,但终不免图解概念之讥。
三、“真幻论”与神魔小说创作
在注意到神魔小说“幻中有理”的同时,不少评点者还揭示了神魔小说“幻中有真”的创作特点。表面上看,神魔小说“所述神仙鬼怪,变幻奇诡,光怪陆离,殊出于人见闻之外”,但其生命力仍在于生活的真实性,即:貌似“极幻”的故事中,蕴涵着“极真”的生活情理,妖魔之类不过是人情世故的一种幻化的反映。
李卓吾评本《西游记》第七十六回回末评语即说:“妖魔反复处极似世上人情,世上人情反复乃真妖魔也。作《西游记》不过借妖魔来画个影子耳。读者亦知此否?”袁于令《西游记题辞》则对《西游记》幻中有真的创作方法作了进一步的阐释,认为:“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意即艺术幻想当中只要蕴涵“极真”的情理,那么越奇幻就越能引人入胜。睡乡居士在《二刻拍案惊奇序》中也指出《西游记》虽说“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然据其所载,师弟四人各一性情,各一动止,试摘取其一言一事,遂使暗中摸索,亦知其出自何人,则正以幻中有真,乃为传神阿堵”。陈忱《水浒后传论略》也说:“如《西游》之说鬼说魔,皆日用平常之道,特诡其名,一新世人耳目。”其他如张无咎在《批评北宋三遂新平妖传叙》中指出该书“备人鬼之态,兼真幻之长”。锺伯敬评本《封神演义》第一百回回末评语指出:“《封神》一书,其说由来甚远,事无可稽,情有可信。”诸如此类的评点,不仅揭示了神魔小说以幻写真的创作特点,而且对神魔小说的再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
《西游记》之后的神魔小说作者,自觉秉持了以幻写真的手法,有意赋予笔下的神魔鬼怪以世俗之人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习性,致使神魔鬼怪能够“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在不同程度上折射了人情世态的某些本质方面。例如《东游记》中的八仙,聚会时就爱游乐玩耍,相互戏谑,甚至惹是生非,比如铁拐李戏放青牛,钟离权与吕洞宾弈棋斗气,吕洞宾三戏白牡丹等。《南游记》中的华光则是大孝子,他不仅未因母亲吃人而生嫌怨之心,反而为救其母,上穷碧落,下及黄泉,火烧东岳神庙,大闹阴司地府,最后三下酆都,终于救出其母。《北游记》中的玉皇大帝,身为天上的最高统治者,却贪心未泯,因想得到刘天君家的宝树而使其三魂之一投胎下凡,历经磨难。
人清以后,神魔小说中的神魔形象日益凡俗化,假托神魔以讽喻世态人情的小说比比皆是。例如《后西游记》即继承了《西游记》“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的手法,晚清张冥飞说:“《西游》之文,讽刺世人处尚少;《后西游》则处处有讽刺世人之词句,其写解脱大王、十恶大王、造化小儿、文明大王、不老婆婆等,无非骂世而已。”至于《斩鬼传》、《平鬼传》等,则无非假象见意,借鬼喻人。本来,民间即常以“酒鬼”、“穷鬼”、“风流鬼”、“饿死鬼”、“吝啬鬼”、“讨债鬼”、“冒失鬼”等讥讽现实中一些反常悖俗之人,小说不过是在此基础上予以突出、强化,以期曲尽人情,抨击世事罢了。《何典》对鬼域的描写,更是穷形尽相,虽然它“无一句不是荒荒唐唐乱说鬼,却又无一句不是痛痛切切说人情世故”。《常言道》所写亦“不过巷议街谈”,“所谓常言道俗情也”。《海游记》也是托言海外异邦,以讽喻中土的种种社会形态。作者在全书结尾自云:“紫岩句句皆真实”,“最荒唐处不荒唐”。《妆钿铲传》写遗业继承问题,主张“务本力农”。松月道士在序中谓其“语语道破俗情,句句切中时款”。
还有的神魔小说把神魔与世情打成一片,抨击世情,彰显冷暖。如李百川作《绿野仙踪》,自称是为“呕吐生活”,以之“遣愁”,既要以“笔代三挝”,作“祢衡之骂”,批判现实社会;又抱“吕纯阳欲渡尽众生之志”,“于《列仙传》内添一额外神仙”,寄托其生活理想。小说虽然受《西游记》的影响,羼杂不少神怪内容,但却广泛触及人间社会,对“官场之窳败、吏役之凶残、纨绔之纵欲、妓女之矫情、腐儒之迂鄙、帮闲之鬼蜮,以及市井细民之困窘等,都刻画入微,近于写实,人情世态,盘旋其间,带有强烈现实感”。也有的神魔小说将神魔与讲史融为一体,如《女仙外史》。清人刘廷玑在《女仙外史》第九十八回的评语中即说:“《外史》之妙,妙在有无相因,虚实相生。历览全部……在乎虚虚实实,有有无无,似虚似实之间,非有非无之际。”
需要指出的是,神魔小说采用以幻写真的创作方法,有意朝着世俗化方向迈进,这与一些评点者喜欢以写实、传信的眼光来审视、评价神魔小说也有一定的关系。不少评点者就认为神魔小说“专工虚妄”、“太无脚地”、“元虚荒渺”。再加上“世情书”的勃兴与历史演义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单凭谈神说鬼已难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因此涉笔世情,杂糅史事,也就成了神魔小说创作的必然选择。
总之,神魔小说评点中的“真幻论”,既总结了神魔小说可贵的创作经验,又有效地引导了神魔小说的再创作,致使作者在侈谈神怪的同时,能自觉地追求幻中有真,使“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从而博得了读者的广泛喜爱。
四、“趣味论”、“游戏论”与神魔小说创作
神魔小说虽然怪诞不经,“读者皆知其谬”,但仍喜闻乐见,这不仅因为它们幻中有理、幻中有真,同时还与其幻中有趣有关。一般人读神魔小说,多半是想到小说中寻求乐趣,所谓“《西游记》热闹,闷时节好看”;即使评点者也爱对神魔小说幻中有趣之处津津乐道。请看李卓吾评本《西游记》中的这些评语:
种种官名俱趣。马流崩芭,似无意义,却有谐趣。(第三回)
文字奇妙至此,真正笔歌墨舞。天花乱坠,顽石点头矣。(第七回)
老猪开口便有天趣。(第八回)
有趣,更有趣,从此后喁喁儿女语,宛然闺中枕畔问答,堪为绝倒。(第十八回)
光景如画,令人欲笑。(第二十回)
说到装天处,令人绝倒。何物文人,奇幻至此?(第三十三回)
偏有此种谐趣。(第三十四回)
趣笔、趣语。(第三十五回)
倒扯蛇,蛇没弄了,打草惊蛇,好打死蛇,都是趣。令人喷饭。(六十七回)这些兴致所到的评点,或赞叹作者笔墨之谐趣动人,或点出人物言行之滑稽可笑,或揭示作者构思之奇巧有趣,总之从不同侧面总结了《西游记》幻中有趣的创作特点。
李卓吾在评点《水浒传》所写“李逵斧劈罗真人”一节时,还明确提出了“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的观点,认为“既是趣了,何必实有是事并实有是人?若一一推究如何如何,岂不令人笑杀?”谢肇涮也说:“凡为小说及杂剧戏文,须是虚实相半,方为游戏三昧之笔。……近来作小说,稍涉怪诞,人便笑其不经……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合,不敢作矣。”以“趣为第一”、“游戏三昧”的理论视角来观照神魔小说。不仅不会轻易笑其怪诞不经,反而会觉得它们有娱人娱己的独特审美价值。后来,不少评点者即从娱乐、游戏的角度来肯定神魔小说,如褚人获评价《封神演义》说:“此书直与《水浒》、《西游》、《平妖》、《逸史》一般诡异,但觉新奇可喜,怪变不穷,以之消长夏,祛睡魔而已。……又何必究其事之有无哉?”
以上这些评论对神魔小说的创作与接受等,无疑会产生积极影响。许多神魔小说的创作,都有意无意地追求“幻中有趣”,程度不同地含有游戏、娱众的成分。例如余象斗编写的神魔小说,其“最大特点就是敢于放手地胡诌乱编,神、鬼、妖、仙,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界线,他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简直弄成了一锅粥。轮回转世也变成“玩艺账”,一个人可以投胎、投胎、再投胎,转世、转世、再转世,既不要什么合理的原因,也可以不受任何的限制。小说中的角色,神仙也好,菩萨也好,妖怪也好,都是些不守信用、心胸狭窄、喜怒无常的角色,一下子弄恼了,就翻脸不认人,为了一些琐事,就可以大动干戈。但这些小说的长处,恰恰是它的肆无忌惮,以至于一切清规戒律视同儿戏,将天上地下的秩序搅得乱七八糟,从而起到为市井细民娱心的作用”。
又如,明末潘镜若创作《三教开迷归正演义》,也是考虑到“世恐有执经义示人,召其盹睡,而终日与谈淫冶、魑魅不倦者”,故而在行文中“杂以诙谐谑浪,非故怪诞支离,以伤雅道”,实则为了“婉语求容”。
再如,清中叶江洪创作《草木春秋演义》,则别出心裁地以不同药性的草木,来比拟汉、番人物:药性温和清润的草木,拟之为汉人;药性猛烈燥热的草木,则用来拟称番邦角色。如“刘寄奴”为汉家君主,“管仲”、“杜仲”为丞相,“甘草”为国老,“金石斛”为总督,黄连、木通等为各地总兵;“巴豆大黄”则充当番邦郎主,“高良姜”为军师,“天雄”为元帅,等等。据此,作者敷演了一出番汉交战的战争游戏,书中广涉神仙灵怪之事,读之奇趣横生。清《斩鬼传·兼修堂跋》即称该书为“无中生有,才人游戏之笔”。作者也自称该书“半属游戏”,“盖任其笔而为之耳”。
至于刘璋作《斩鬼传》,也是受《草木春秋演绎》“才人游戏之笔”的启发。仅看第十回结末一段,钟馗斩尽群鬼,归庙受享,因灵应异常,县尹上报,龙颜大悦,钦赐一匾,“士大夫争来观看,果然写得整齐;盆样大的五个字写道:‘哪有这样事…。游戏意味昭然。像这种信笔挥洒,涉笔成趣的情形,在神魔小说创作中几随处可见。
其他如《飞跎全传》、《常言道》、《何典》等,其“游戏”特征更为明显。一笑翁在《飞跎全传序》中说:“已趣斋主人负性英奇,寄情诗酒,往往乘醉放舟,与诸同人袭曼倩之诙谐,学庄周之隐语,一时闻者无不哑然失笑。此《飞跎全传》之所以作也。”观《飞跎全传》,也确是“一味荒唐玄虚,莫名其妙”,“似用意唯在谑浪”。张南庄作《何典》,也是以文为戏,他自嘲该书乃“逢场作戏,随口喷蛆”。小说结尾诗云:“文章自古无凭据,花样重新做出来。拾得篮中就是菜,得开怀处且开怀。”这也表现了他以游戏为怀,不拘一格的创作旨趣。海上餐霞客也指出“是书特先生游戏笔墨耳”。
总起来看,趣味论、游戏论以及前文所述的心性论、真幻论等,确实从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引导、影响了神魔小说编创,致使神魔小说在“曼衍虚诞”的艺术幻想中寓含了发人深省的“理”、耐人寻味的“真”和令人解颐的“趣”,三者相辅相成,共同维系了神魔小说编创的基本艺术品位,使神魔小说具有了一定的审美认识价值。
参考文献
[1]谢肇涮,五杂俎[M],上海:上海书店,2001
[2]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3]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第十九回总评[M],中州书画社1983年影印明刊本
[4]吴璧雍,从民俗趣味到文人意识的参与[A],意象的流变[c],北京:三联书店,1992
[5]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
[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7]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选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
[8]刘复.重印《何典》序[A].何典[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松月道士.妆钿铲传序[A].古典小说集成[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影印本
[10]李百川.绿野仙踪自序[A].绿野仙踪[c].北京:中华书局,2001
[11]张俊.清代小说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
[12]吕熊.女仙外史[M].济南:齐鲁书社,1985
[13]刘荫柏.西游记研究资料[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4]金圣叹.读第五才子书法[A].水浒传(会评本)[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
[15]李卓吾评《水浒传》,第五十三回回末总评[z].明容与堂刊本
[16]欧阳健.中国神怪小说通史[M].苏州: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17]潘镜若三教开迷归正演义·凡例[A].三教开迷归正演义[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古本小说集成本
[18]刘璋.斩鬼传[z].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9
[19]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20]海上餐霞客.何典跋[A].何典[z],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杜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