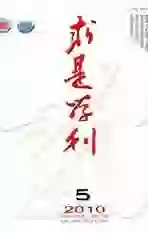民间组织兴起:转型期法治进程的新兴动力
2011-01-01马长山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民间组织迅速崛起,并呈现出特殊的发展路径,具有复杂深刻的社会背景。数量巨大的民间组织不仅成为克服传统中国“两极化”关系模式和思维定式的重要力量,也在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中承担着重要使命,形成了“柔性”的纵向权力分割分解机制、组织化和群体化的权利保护机制、自主平衡的民间秩序生成机制、立足“草根”的公民性塑造机制等。尽管我国的民间组织发展还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问题,但是,其重要作用和功能却不可低估,其发展前景不可小觑。
关键词:社会转型;“两极化”关系模式;民间组织;法治进程
作者简介:马长山(1964—),男,黑龙江肇东人,黑龙江大学法学理论与法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法学理论和法治发展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建设法治国家的公民文化基础研究”,项目编号:10AFX002:黑龙江省教育厅重大项目“公共舆论的法治价值及其实现”
中图分类号:D922.5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70-06 收稿日期:2009-12-15
众所周知,中国正经历着重大的社会转型。也即由农业社会转向商业社会、由等级社会转向大众社会、由礼俗社会转向法理社会、由集权社会转向民主社会。在这一整体转型中,民间组织悄然兴起,并成为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的新兴动力。
一、传统中国“两极化”的关系模式和思维定式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具有几千年封建社会传统的国家,但是,中国的封建社会与西欧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却有很大的差异。西欧封建社会虽然整体上是一种君权神授、等级身份、宗教禁欲的状态,然而它毕竟建立在王权、教权、贵族权和市民权的多元权力斗争与整合基础上,并且形成了领主分封的契约关系、世袭权利和相对自由精神。它打破了大多数古代文明的显著单一性,使得多种社会组织形式、多种精神和原则、多种利益要求在其中同时并存着,相互制约和抗衡,任何单一的权力、组织或者原则都不能征服、驾驭和控制其他力量,也就是说,这种多样性防止了单一性和独断性,从而大大消解了专制主义滋生的基础。虽然14—15世纪进入了专制主义时代,但随后便遭遇了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最后按照启蒙精神和原则,社会公众与国家“订立”了民主契约,建立起宪政体制和权利保障机制,民间组织日益发达并承担着自主自治、民主管理的职责,以此来抵御国家权力的不当干预、建立自由平等的社会联系和组织自己丰富个性的私人生活。可见,西方社会具有一种“社会自主性”的历史传统,这成为西方走向民主法治的一份重要历史资源和现实动力。
在传统中国,则是另一幅迥然不同的景象。皇帝是绝对的、单一的、不容置疑的至高权力中心,国家和社会则是皇权王室的放大、扩展与延伸,广大社会成员生活在皇权等级、儒法宗族的封建关系网中。在这里,皇权、特权和宗族权威无所不在,形成了国家权力深入社会、管控一切的“国家主义”价值体系和生活模式,民间组织及其自治管理也就很难形成气候。这一方面导致了“公共生活与私生活‘两无’的社会格局”,同时也形成了皇权奴化民众、民众“官逼民反”的状态和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两极化”关系模式和思维定式。在这种模式下,国家权力为了建立“统一秩序”就必须进行全面监控、严密管理,而这必然导致社会发展的僵死阻滞、甚至危及政权的存在;为了缓解这一危机,就又必须放权给社会,而一旦放松管制,社会就会因缺少自律力量、自律意识、自律习惯和自律机制,出现放任不羁、混乱和动荡的“无政府”状态,于是,国家权力就要“卷土重来”,重新进行严厉管制,以恢复“统一秩序”。这样,就形成了“一统即死、一放即乱”的历史怪圈,进而在“专制”和“无政府”的两极状态中徘徊,人们在心态上也是尊崇皇权与造反心理二者同时并存,造反成功者也最终都当了皇帝。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大大推进了社会的发展进程,但是,受“极左”思潮和封建残余的影响,推行了“一大二公”的中央集权体制。这无疑仍然是国家控制、吞噬一切的管理模式和运行状态,一方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管的国家权力,而另一方面则是被动服从、分散无为的“人民群众”,社会自律机制、自律力量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仍没有建立起来。
毋庸置疑,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一直是农业文明的历史。历史上著名的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人的社会变革。都只是封建体制内部的变革,尤其是都未能改变农业文明的性质。即便是蒙古族、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外来“入侵”中原所建立起来的元、清等王朝,也导致了“征服者被征服”的结果。虽然形成了民族大融合,但农业文明的性质依旧。然而,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与历史上所有的社会变革都不同,它使得中国几千年的农业文明发生了断裂,开始转向商业文明,并融入了全球化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说,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涉及中国文明性质转变的伟大历史变革。在这一进程中,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一统天下”、国家权力高度统合监管社会的状况发生了重大改变。随着多元利益崛起和权利诉求日增,国家也不断回缩放权,出现了“民进官退”的发展趋势,这就为社会的多元化、自主化、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平台。于是,传统中央集权的政治化控制,就让位于民主化、法治化、市场化管理。在国家权力回撤后所形成的巨大社会空间中,如果没有相应的自律力量填充、替代,那就必然还会出现控制盲点和行为失序,“一统即死、一放即乱”的历史怪圈还会“卷土重来”。当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广泛兴起,就承担起了这一职责。它横亘在国家和社会之间,成为二者之间的缓冲平台,既制约国家权力,又进行自主管理,既推进民主,又建立自律秩序,从而防止传统中国那种集权专断与“无政府”的两极交替状态,对转型期的中国法治进程具有重要意义。
二、中国民间组织的悄然崛起
中国法学界关于民间组织与法治的研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但是,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实际上从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了。由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经济背景,民间组织的成长展现着特殊的路径。
1、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路径
由于诸多历史和社会现实因素的影响,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有着特殊的路径。简言之,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政府来推动的,但主要立足于经济和社会变革,而政治体制改革却相对滞后(这与俄罗斯相反)。这样,政治改革既是民间组织的推动力量,同时又是民间组织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力量。这无疑就决定了民间组织与政府既依赖、又抗争的复杂关系和发展路径。目前,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主要分为五种类型:一是原来就具有行政性质和职能的民间社会组织(如工会、妇联、共青团等);二是由政府职能部门转化为民间社会组织(1993年政府机构改革。纺织行业总会、轻工业总会等);三是政府支持的社会组织(如各种行业协会、学会等);四是民间自发形成的社会组织(如立足民间需要而兴起的一些民间组织:青岛船东协会、温州服装商会、齐齐哈尔塑料门窗协会等);五是尚未登记但仍活跃于社会上的各种民间组织(如各种同学会、同乡会等)。相关调查显示,目前全国性行业协会全都是基于行政手段而组建的,国家经贸委直管的15家行业协会,有9家是由其直管的国家工业局直接转制而来;北京行业协会的领导层80%具有行政级别,1/3协会的主要负责人由业务主管部门推荐或决定产生。而青岛有53.5%的社团仍由党政领导干部兼任其领导职务,52%的社团人事任免权归于业务主管部门。可见。中国民间组织的成长在总体上还是具有较重的行政化和较强的依赖性。
2、民间组织兴起的社会背景
改革开放后,政府机构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主要取向是精简机构、简政放权。改革分为五次:1982年的改革,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100个减到61个,人员编制减少25%;1988年的改革,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72个减到68个,人员编制减少20%:1993年的改革,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86个减少到59个,人员编制减少20%;1998年的改革,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61个减少到52个,人员编制减少47.5%;2008年的改革,国务院的工作部门由31个减少到27个,人员编制未增加。从上可以看出,政府机构改革的导向是越来越趋向于宏观调控,机构和人员越来越精简,从而放松了社会管制范围和幅度,为民间组织成长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基本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内生产总值中公有制所占比重为99%,经过30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1978年。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24.0%,工业总产值中占77.63%,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数量占76.0%,工业总产值中占2237%。随着市场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到2007年,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数量仅占6.1%,工业总产值占29.5%,集体企业数量占3.9%,工业总产值占2.5%。
伴随着国有企业的转制,私有经济飞速发展。2007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741.5万户,私营企业551.3万家,分别比1992年增长0.8倍和39.1倍。在规模以上工业中,非公企业数量达到30.3万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的90%(其中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占总数的20%),总产值所占比重为68%。在改革开放初,几乎所有城镇从业人员都集中在公有制企业,而到2007年,城镇国有和集体单位从业人员则只占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24.3%。从上可以看出,私营经济获得了迅猛发展,民间组织的经济基础日渐厚重,而且,随着经济的多元化,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也日益世俗化、多元化、自主化(婚恋、择业、理想、追求、权利等)。
3、民间组织的发展态势
1988年全国有登记注册的各类民间组织4446个,1993年达到167506个,1997年达到181318个;1998年是165600个,1999年是142665(含民非5901),2001年210939个(含民非82134),2004年289432(含民非135181)。
2005年登记注册社团171150个,基金会975个,民非147637个,总计319762个;2006年登记注册的社团191946个,基金会1144个,民非161303个,总计354393个。职工人数4199000人,其中,社会团体2654722人;2007年登记注册的社团211661个,基金会1340个,民非173915个。总计386916个。职工人数4568515人,其中社会团体2885287人。
2008年登记注册的社会团体23万个,比上年增长8.5%:就业人数475.8万人,比上年增长4.2%;形成固定资产805.8亿元,比上年增长18.2%;各类费用支出964.8亿元,比上年增长7.2%:社会组织增加值372.4亿元,比上年增加21.1%,占第三产业(服务业)增加值比重0.31%;接收社会捐赠103.4亿元(接收捐赠实物折价26.1亿元)。基金会1597个,民非18.2万个,总计约41.4万个。这些民间组织活跃于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舞台,在参政议政、自律管理、利益代表、权利主张、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功能和作用,成为中国民间组织的主导力量。
三、民间组织的法治使命
改革开放30余年来,民间组织获得了飞速发展。最新数据显示,到2009年6月底,我国各类民间组织已达41.16万个,其中社会团体22.8万个,民非18.2万个,基金会1622个。这些民间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负有重要的法治使命。
1、形成了“柔性”的纵向权力分割分解机制
权力分立制约是防止权力独断的根本手段,因而是近代以来法治运行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但是,随着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和交织,行政权力急剧扩张。传统的三权分立机制发生了动摇。于是,如何重建国家权力的制约机制就成为亟须解决的时代课题。为此,“超越左和右”的“第三条道路”开始兴起,它致力于探索国家与社会的新型合作关系和“治理”机制,“全球社团革命”就成为从“统治”走向“治理”的基本动力。这就是说,逐渐崛起的民间组织构成了国家与社会合作的关键平台和新的权力制约分割机制,成为当代法治的重要支撑力量。
在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民主法治进程。然而,中国既没有“三权分立”的传统,也没有现实存在的制度空间。因此,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更多的只能走纵向分割分解的道路,而且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不能采取对抗式的激进分权,只能采取非对抗的“柔性”分权,这样才能更好地避免“两极化”关系模式和行为定式的重演,在和谐有序的环境中推进民主和法治。改革开放后民间组织的兴起,正是国家简政放权、鼓励培育环境下的当然结果,它以组织化形式和群体化力量。来进行利益表达、反映呼声、自主管理和民主参与,既与国家权力合作,又分解国家权力,从而形成了“柔性”的、纵向的国家权力分割分解机制,在一定意义上构筑了一道抵御国家权力扩张和滥用的堤坝。也促进了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多元化和民主化,从而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2、形成了组织化、群体化的权利保护机制
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个体权利面对国家权力时都是弱不禁风的。而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公司权力的扩张、对个体权利的侵蚀也并不比国家权力逊色太多。这就意味着,个体权利与自由面临着国家权力和公司权力的双重威胁。因此,要想使个体权利和自由获得可靠保障,社会成员就必须联合起来,形成社会组织,并以组织化形式和群体化力量来表达愿望、主张权利、捍卫自由。特别在中国,官本位浓重,垄断企业势力庞大,加之个体自由和权利的保护渠道不健全、不完善,个体的力量更显脆弱。因此,民间组织就成为保护个体权利和自由的重要后盾和屏障。如1997—1998年间海南省企业协会就以自,身组织力量。促进了海口狮子楼大酒店董事长雷献强受非法拘禁案的解决,保护了个体权利和自由。如果没有海南省企业协会的介入,单凭雷献强的个体力量恐怕很难取得这样的效果。
3、形成了自主平衡的民间秩序生成机制
西方经历了几个世纪的民主法治演进历程,而中国民主法治进程才短短30年。这30年间,社会呈现出日益高涨的多元化、世俗化和自由化发展势头,众多的自由和权利得到了快速释放。与此同时,中国又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和习惯,对自由和权利的心理承受力不足,因此,多元化自由和权利之间的摩擦、冲突也就在所难免,社会秩序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近年来的道德滑坡、假冒伪劣、恶性竞争、行为失范等就可见一斑。面对这一情况。不可能再用国家一统天下、规划社会的办法来解决,而只能用社会自律的办法来化解。民间组织正是立足不同群体利益主张和权利诉求的社会自组织力量,它们能够在多元利益、多元权利和多元自由的冲突与合作中。进行理性对话和自主协调,从而促进多元和谐秩序。如2001年劳动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国企业联合会联合组成的协调劳动关系“三方机制”、中国消费者协会对四大银行“借记卡收费”的交涉对话、温州烟具业行业协会对恶性竞争的“行业治理”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促进了自主平衡的民间秩序的形成。
4、形成了立足“草根”的公民性塑造机制
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传统。“臣民意识”、“草民意识”浓重,而公民意识匮乏。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表明,推进民主法治进程,一个很大的问题并不是制度构建,而是人的问题。现代的制度在传统的人面前,往往是废纸一张,民主机制很难运行,社会秩序也很难建立。因此,培养社会成员的公民性品格和民主技能就显得十分关键。在目前的社会体制下,人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制度、听证制度等都能提供一定的公民性品格和民主生活技能的培养机制,但是,它的容量是十分有限的。对大多数社会成员而言,还得靠日常生活中的相应机制来培育。这一机制的最好平台就是民间组织,它通过行业治理、自主管理、民主参与、公益服务、社区矫正等“民间治理”活动,能够推动公民参与的热情,搭建民主参与的公共平台。能够培养公民的民主意识、法律观念、公共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塑造适于民主法治需要的公民性品格和民主生活技能,从而构成了推进民主法治进程、建立和谐秩序的新兴动力。
四、民间组织的发展困境与对策
尽管中国“民间治理”的兴起具有重要的民主意义和法治价值,但这并不是说它是理想化的。恰恰相反。它存在一定的困境和问题。
首先,是行政依附性问题。尽管这一问题在其他国家也会出现,但中国可能更为突出和典型。我们知道,中国具有“国家主义”的雄厚基础和邻里密切互惠的传统,而缺少民间自治的意识、习惯和传统。在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及其“民间治理”就难免产生一定程度的行政依附效应。据笔者对黑龙江省民间组织情况的调查(黑龙江省与东、西部相比地理位置居中,又是大省,有一定代表性),官办34.0%,官民合办41.8%,合计75.8%;民办24.2%,其中省级占其总数的16.1%,市级占其总数的9.9%,县级占其总数的29.1%。由此看来,民办数量总体较少,基层远离权力中心,其依附性反而较弱。
这样,一方面,国家对民间组织的管理、扶持和鼓励,在相当意义上是令其成为政府行政职能的实际延伸和助手,力图借此更好地实施社会管理和维持社会秩序,因而要在人、财、物等各方面来控制或制约着民间组织,甚至使其成为机构改革的重要分流渠道:而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民间组织也出于风险、收益和绩效考虑,往往主动靠近政府,甚至热衷于向政府要编制、要经费、争职能,以寻求其合法性、权威性,而不是在服务性和代表性上下工夫。这样,在很多时候民间组织就成为政府的“雇员”,而不是合作的“伙伴”,缺少社会性和自主性,因而也就很难充分发挥其“民间治理”的功能。
其次、是动员能力和公信力问题。尽管中国的民间组织在近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它们的动员能力和公信力一直不理想。这里面自然包括政府对民间组织的资源控制、市场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等因素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民间组织的覆盖范围不大,在对黑龙江省民间组织的调查中笔者发现,覆盖率能达到80%以上的,省级民间组织占其总数的31.2%,市级民间组织占其总数的27.0%,县级民间组织占其总数的31.5%。即使发展较好的上海行业协会的平均覆盖率也只有50.7%,而全国性行业协会的覆盖率一般不超过40%,因而代表性差。领导层和工作人员老龄化、“非精英化”,如几年前的调查数据显示,北京行业协会中年龄超过60岁的会长就超过了40%,因而业务活动的组织能力和服务能力差。领导机构行政附庸化,因而对成员的权益主张和维护的能力差,甚至可能会出现与政府的某种“共谋”。这样,就使得成员对其缺少认同感、归依感和“家园感”,加之人们普遍缺少通过自组织力量解决问题、谋求发展的信念和习惯,因而,民间组织在收缴会费、自治管理及其他业务活动中,往往得不到成员和社会应有的信任和支持。这样,就呈现出明显的动员能力不足和公信力缺乏。而这种不足和缺乏又反过来抑制了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及其“民间治理”功能的充分发挥,从而降低其动员能力和公信力。
再次,是民主空间问题。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取得了重要成就,“民间治理”也开始兴起,但仍不能满足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仍需进一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民间组织在“民间治理”活动中,缺少应有的制度保障:国家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对民间组织的开放度还不够;民间组织也未能进入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体制内”平台,等等,因而民主空间尚需大力拓展。
基于这些困境和问题,我们认为,民主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主流,但是通向民主的道路却不能只有一条;法治也不仅仅是权力制约和自由保障,它在很多时候是一种多种要素和力量的平衡。无疑,中国要走向民主法治,就必须大力培育民间组织,推动多元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分割制衡,促进自由、平等、权利和多元价值的实现,这样法治秩序才能建立起来。但是,中国的民间组织发展却不宜有太多与国家对抗的性质。这就意味着,采取渐进主义策略,并建立民间组织与国家的互动合作机制,才是中国更为现实的选择,也才能避免传统中国那种集权与“无政府”的“两极”交替状态的重演,从而推进社会转型与和谐稳定。因此,充分发掘“民间治理”的功能和潜力,就成为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促进和谐秩序的重要环节。
其一,拓展开通民间组织在“体制内”的民主参与渠道。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的民主法治进程不断加快,但是,民主参政议政的空间还需要进一步拓展。目前,在“体制内”的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等还没有民间组织的界别,这无疑是民间组织民主参与的一个重要瓶颈。因此,有必要把民间组织纳入“体制内”民主参与渠道,使民间组织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更大的作为,并为“民间治理”提供更好的宏观环境和民主条件。
其二,开放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目前中国的民间组织更多地致力于自身利益的代表和权利维护,而在“公共政治”中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发挥。因此,政府和相关公共服务部门应进一步开放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积极挖掘民间组织的潜力,在基层自治和社区治理(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居委村委自治、环境整治工程、市场自治管理等)中。更多动员和发挥民间组织的力量和作用。同时,民间组织也应更积极主动地投身于“公共政治”。这样,才能形成政府、公共部门、相关单位和个人、民间组织等共同动手、互动支撑的“多中心、多向度”的治理结构,从而培育民主法治的社会根基和多元和谐秩序。
其三,提高民间组织的公信力和动员能力。由于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人过多相信政府,而对民间组织信任度不够,公民参与度也就不高。因此,就需要政府继续缩小行政干预和职能辐射范围,让民间组织拥有更广阔的发展参与空间。特别是在当下社会转型期和民间组织的成长期。政府应该在政策导向、经费筹集、授权委托、业务活动等方面给予民间组织以大力支持和帮助。同时,民间组织也应该积极组织立竿见影的业务活动,广泛吸纳并动员公民参与,从而扩大影响和提升动员能力,更充分地展现民间组织的“民间治理”功能。
其四,提高公民的民主法治意识和参与精神。只有公民对民间组织的信任依赖和广泛参与,民间组织才有良好基础,也才会为“民间治理”注入生机和活力。因此,公民民主法治意识的高低,就成为“民间治理”兴衰的关键因素。事实表明,西方较为成熟的民主法治国家,也十分注重公民教育和民主法治精神的培养。因此,在中国集权专制文化浓重、缺少民主法治传统及公民传统的情况下,更需要进行必要的民主法治精神“启蒙”,特别是应把它纳入公民教育和普法规划,以强化民主参与意识和公民精神,进而促进“民间治理”的蓬勃发展,为民主法治进程提供重要而持续的社会动力。
参考文献
[1]刘泽华,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与社会整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2]翟鸿祥,行业协会发展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
[3]吴玉章,社会团体的法律问题[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4]沈荣华,积极稳妥地探索实行职能有机统一的大部门体制[N],光明日报,2008-02-28
[5]马长山,法治进程中的“民间治理”——民间组织与法治秩序关系的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6]余晖,转型时期行业协会的发展不足及其阻因(EB/OL],http://www.finance.sina.com.cn
[责任编辑 李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