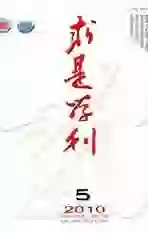先秦儒\\道“通”\\“异”论
2011-01-01普慧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儒、道两家都以“道”作为追求和向往的对象。所不同的是,前者之“道”为“天道”和“先王之道”的结合,是一种典型的尊天明神的“神道设教”信仰;后者之“道”则表现出对现实的超越性,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的理想。但二者所崇之“道”,都具有“言说”的性质和特点。“道”体现于社会,则表现出了对理想社会的回归:老子的“小国寡民”与孔子的“大同社会”似无本质区别。而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治理,孔、老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和策略。二者的主要不同在于对待“礼”的态度:儒要奉礼,道要毁礼。
关键词:“道”;儒家;道家;“无为而治”
作者简介:普慧(1959—),本名张弘,陕西榆林人,西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南开大学985创新基地研究人员,从事中国文学思想、宗教思想、佛教文化等研究。
基金项目:南开大学“国家985工程二期‘中国思想与社会研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支柱课题“中国宗教思想史研究”,项目编号:105212200400012
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42-06 收稿日期:2010-02-12
儒、道两家是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两派,也是最为显赫、最具影响力的学派。以往学者多从两派“异”处着眼,对其“通”处则很少言及。本文拟就儒、道两家“通”、“异”之处作一梳理、比较,力求言他人之未言。
一
一般认为,作为学术思想的儒、道两家的出现几乎是同时的。尽管道家创始人老子其人、其时仍在探讨之中,但老、孔同时的认识,已为学界普遍接受。儒、道两家的产生,都是对“道”的一种追求和向往。“道”,《说文》:“道,所行道也。从辵(chòu),从首。一达谓之道。”“道”的原意是指人所行走的道路。但是,人们所行之路并非随意创辟,而是恒常行定的。若不按此路行走,人们就会误入歧途,无法抵达正确的目的。于是,上天是神明,其所指道路,即为“天道”。“天”,《说文》:“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王国维云:“古文天字本像人形。……本为人颠顶,故像人形。”“天”又谓“首”。《山海经》:“形天与帝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山海经,海外西经》)袁珂谓:“刑天亦作‘形天’……刑天即断首之义。”由此可知,“道”乃为上天所行之路,盖非凡人所走之路。在原始崇拜的观念里,天帝所行之路自然是最为正确、最为快捷、最为坦荡的,它是一切世俗道路的根本、根源。这样,“道”就在原始崇拜的观念体系当中,不仅具备了超越世俗的超验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始具有了现象界的经验实践价值。所以,当传统的自发宗教崇拜信仰的大厦行将坍塌、理性主义高潮席卷而来之际,春秋时期的思想家们便自觉地以“道”作为追求的目标和方向。
《论语》中记载了孔子关于追求“道”的一系列论述:
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孔子明确提出了对“道”的向往,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他还用“道”来教化天下,故先秦称“道教”者,实乃指儒家。据先秦儒家的一系列论述来看,儒家之“道”实为“天道”和“先王之道”的结合,即一种典型的尊天明神的宗教信仰。所谓“天道”,最初是指将神化了的日月星辰等天体运行过程与推测吉凶福祸相结合的知识、观念、信仰,即早期的自发宗教崇拜;所谓“先王之道”,是指尧舜以来以“天道”治理现实社会的经验范式。先王之道的核心是“礼”。而其“道教”。则是教化的“神道设教”,即所谓的“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易·观·彖》);“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庸》第1章);“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中府》第16章)。所以,《墨子》谓:“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而儒者以为道教,是贱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据此,先秦所谓“道教”者,乃以儒家为对象,与东汉末以后的道教实无关系。
除了儒家论道外,被后人誉为道家、道教的创始人老子也提出了对“道”的理解和体认:
道,可道,非常道。(《道德经》第1章)
道生一,一生=,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不改,周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目大。……故道大,天大,地大,王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与孔子不同的是,老子所追求的“道”更具有对现实的超越性。在老子看来,道意味着一种不一般的秩序,一种循环往复的过程,它不仅具有宇宙万有的根源和本源性质,按照一定轨迹运行,还通过不断变化显现恒常,在过程中显现恒常。这种恒常使世界在一定程度上处在不断更新的状态而不可预知。老子的道论,似乎缺少西方本体论式的“存在”范畴。因此,对于老子的“道”,集中于本体论和宇宙论上的探察,显然是偏离了轨迹。因为在老子的道论中,似乎并没有存在与非存在、多与一、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的截然对立。就是说,在老子的“道”中,“无数的存在者(‘万物’或‘万有’)的背后无存在,多后面无一,现象后面无本质”。这一点。老子的后继者庄子讲得更为具体:“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魏礼(Arthur Waley)在英译《论语》和《老子》的“道”时,用的是同一个词Way。而Way在英文中主要是指道路及其引申出的轨迹、规律、法则等。但实际上,无论是孔子还是老子,其“道”义还有另一层语义,即“道”的言说性质。孔子的“朝闻道”和老子的“道可道”。皆昭示了道是可以言说的。海德格尔注意到老子的“道说”之义,即“道路是道说,反之亦然,道说是道路”,却忽略了孔子道的言说性。孔、老之道所不同的是,孔子虽然将其作为最高的信仰,但并未将它神秘化;而老子从一开始就将道指向了神秘主义和神圣意义的终极境地。所谓道又是不可言说的,即要求超越语言和知识,以“诺斯”(gnosis)来理解“人类意义世界的根源”。这样,在表面上,老子似乎与宗教信仰关系不够密切,可实际上,老子将“道”神秘化、神圣化后,为后来的道教寻找一个具有根源性的、能够与人格神合二为一的抽象之道提供了宗教信仰上的神学依据。
孔、老之后,属老子一系的《列子》,也有关于“道”的论述:
无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虽终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虽未终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无用而生谓之道,用道得终谓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谓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谓之常。季梁之死,杨朱望其门而歌。随梧之死,杨朱抚其尸而哭。隶人之生。隶人之死,众人且歌,众人且哭。
关尹喜曰:“在己无居,形物其著,其动若水,其静若镜,其应若响。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违道。道不违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视听形智以求之,弗当矣。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用之弥满,六虚废之。莫知其所。亦非有心者所能得远,亦非无心者所能得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为,真知真能也。发无知,何能情?发不能,何能为?聚块也,积尘也,虽无为而非理也。”(《列子·仲尼》)《列子》发展了老子的“道论”,强调了道与常的辩证关系。在《列子》看来,常是道的形式特征,道是常的本质属性。道和常有两重关系。其一是无为无用的,但却潜存于宇宙万物,是为道;体现道而终其世者,是为常。其二是有所作为而死者,也可称之为道;充分运用道得死者亦可称之为常。这样,道和常的关系就变得十分复杂了。这比起老子的道论,更具有社会现实的参与性。
纵观春秋、战国思想文化,其全部的共性特征就是对“道”的体认和追求。因此,史华兹(Baniamin I.Schwartz)在对雅斯贝尔斯轴心说的中国特点作出更为详细的说明后,便深刻地指出“道”的观念是先秦诸家的根本主题。
二
孔、老除了在形上意义上追求和向往“道”外,还将“道”的思想直接运用于现象界的层面。这首先表现于他们应时治世的政治理想与形而上的“大道”相结合的追求上。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执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礼记·礼运》)孔子所谓“大道”,主要体现在应时治世。孔子的理想社会结构有两个层次:一是“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二是“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显然,这两个社会历史分界是以大禹为标志的。据考古学研究,黄帝是中国上古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转型的起始人物,大禹则是这种转型完成的代表人物。大禹之前为“大同社会”,大禹以后则为“小康社会”。在考古学上,大同社会相当于旧石器晚期至新石器时代,即母系社会;小康社会则相当于青铜时代。即父系社会。在中国,青铜时代起源于大禹,传说中的禹铸九鼎,正好印证了父系社会的正式开始。一般来说,老子向往母系社会,而孔子则盛赞三代以来的父系社会。但是,《礼记·礼运》里记载的孔子这段话却明显地与孔子的其他言论有差异。故对此“大同社会”的思想,或以为道家思想,或以为墨家、农家思想,或以为后来儒家思想。其实,细而察之,其所述大同社会,虽为母系社会,而就具体结构特征言之,仍然反映出孔子以来儒家一贯倡导的社会模式。如“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男有分,女有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货不藏己,力不为己”;“盗贼不作,外户不闭”等。正是历代儒家所追求的理想社会。从孔子对“道”的追求来看,他完全有可能向往“大同社会”。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礼运》所示的“大同社会”的理想受到道家影响的可能性。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礼运》所示的孔子“大同社会”的理想,在形成、发展的过程中,注入了一些道家的思想,而老子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在原始母系氏族社会特征上。与孔子的“大同社会”似无本质区别。对于这种理想社会的治理,孔、老都主张采取“无为而治”的态度和策略:
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公》)
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道德经》第37章)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57章)孔子盛赞的舜帝即受禅于尧帝而采取了无为而治的国家策略,致使氏族联盟兴旺发达。这在孔子看来,舜是顺应了“天道”,并不是舜帝本人人为所做的功业。老子认为,治理国家的世俗王侯若能坚守“无为而无不为”的恒常之道,那么。万物将会按照它自己应有的规律来生化,而王侯则可坐享其成。
这种道的原则体现在“德”上,则表现出了“中和”之美的根本特征。如: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来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庸》)再如道家: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道德经》第4章)
天地之间,其犹橐橐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教穷,不如守中。(《道德经》第5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道德经》第42章)
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日常,知常日明,益生日祥,心使气日强。(《道德经》第55章)
游心乎德之和。(《庄子·内篇·德充符》)“中”,英文常译为mean(中间)或right(正)。其汉字本义即指上下通,表示能贯通一切,容纳一切。《说文》:“中,和也。从口、丨,上下通。”考其字源,则与吃饭有关,即用筷子(短细树枝或竹枝等)往口中进食。因筷子置于口中间,故引申为中正、不偏不倚之意。《周礼·地官·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疏:使得中正也。”(《周礼注疏》卷十,十三经注疏本)“和”英文通常翻译为“harmony”。“和”最早写作“咊”,说文释“咊”为“相腐(yìng)也。从口,禾声。”“咊”字字源又与吃饭有关:即口吃那些将“禾”类的各种谷物一起熬煮而成的调和味美的粥。故“和是一种结合和调和的艺术,这是将两种或更多的食物合在一起加工,在烧出来的食品中它们既不失去各自的特殊味道,又相得益彰,新增滋味,而且构成了一种无缺憾的整体。这种和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容忍种种特殊成分,以及和谐的美容性(cosmetic nature)。这是一种秩序,它是在细小之物水乳交融、相互协同作用中产生的,这种秩序使这些成分的相互促进、相辅相成显得美妙无比”。《老子》中的“冲”,当为“中”。长沙马王堆《老子帛书》小篆做“中气以为和”。《文选》张华《鹪鹩赋》注引字书曰:“冲。中也。”故知中古以前“冲”、“中”通用。由此,中和之道、中和之美不单为儒家所独有,道家亦在竭力倡导。道家从事物之规律、事物之变化以及空间、时间等四个方面“皆突出了道学的中和之德”。
三
儒、道两家的相“通”毕竟是有限的。二家既然分立,自然是求异之处、冲突之处更多。庄子就借孔子之口明确区分了儒、道二家为方内与方外:“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内者也。外内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吊之,丘则陋矣。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疯溃痈,夫若然者,又恶知死生先后之所在!假于异物,托于同体;忘其肝胆,遗其耳目;反复终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尘垢之外,逍遥乎无为之业。彼叉恶能愦愦然为世俗之礼,以观众人之耳目哉!’”(《庄子·内篇·大宗师》)二家既不同,则必然会有“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现象。道家思想偏于宇宙论,儒家思想偏于道德论,一玄远,一具体;一超越,一现实。事实上,“孔子到底是先秦诸子中最早而最重要的思想家;其它儒家及诸子百家,或推波助澜,或变异责难,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孔子的思想在辩论”。道家则是最典型地在批评儒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首先老子批评了儒家标榜的礼教体系,认为这乃是自然之道堕落的产物: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道德经》第18章)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道德经》第38章)宋翔凤《过庭录》卷13将“乱”训为“治”,认为“老子言礼,故孔子问礼”,“黄、老之学与孔子之传,相为表里”。朱谦之则认为宋说“未明学术源流……老子盖知礼而反礼者也”。显然,“礼”是导致儒、道两家不同的论辩核心范畴。一要奉礼,一要毁礼,火水不容。老子的后继者庄子对儒家之礼批评得更为猛烈:
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为也,义可亏也,礼相伪也。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庄子·外篇·知北游》)老、庄都认为,“礼”是导致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由“礼”而体现的“道”,实质上就是“伪道”。这样,儒、道两家的分野由此而形成。马克斯·韦伯引述了德·葛路特(de Groot)的观点:
庄子尖锐化了老子的论点,借此突出其与儒教徒相异之处。1、追求“智能”,是执着于外在事物;2、追求“理性”,是执着于声音(话语);3、追求“人间之爱”,是混乱一己德性的修炼;4、追求尽一已之义务,是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全能的道);5、固执于“礼”(规则),是执着外在;6、喜好音乐,是沉溺于恶习;7、固执于神圣性,是耍弄伎俩;8、追求知识,是穿凿附会。韦伯本人则还注意到了儒、道的对立不仅是在思想上的,还在于其现实社会的地位差异。
半传说性的传统说法里,描述了孔子与老子个人之间的对立。然而关于“学派的对立”,尤其是关于这两位敌对者的明白分野。都还未曾有个清楚的分说。诚然,在气性(Naturen)、生活样式以及态度上,尤其是对于实际的国家问题(官职)的态度上,两者存在着尖锐的差异。然而学派的对立显然一方面是由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另一方面是由于庄子的尖锐论争,才清楚明朗起来。可以确定并且为专家们所强调的是,神秘主义者为了自身或者一般人的幸福而拒斥理性的知识,在理论上乃是一个最重要的命题,可是却无法为儒教徒、甚或其夫子所接受。
孔子与老子的信徒之分裂,自子思的攻击后就已存在。不过双方反目之加剧,是由于学派的发展,以及彼此竞争俸禄与权势所造成。据班固的考察,“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汉书·艺文志》)。司徒者,相传少吴始置,唐虞因之,周为六卿之一,日地官大司徒,掌管国家土地及人民教化。汉哀帝刘欣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改丞相为大司徒,与大司马、大司空并列三公。史官者,在王左右,执掌祭祀、星历、卜筮、记事记言等职。夏、殷和周前期,由于原始宗教崇拜信仰的盛行,史在国家官僚制度体系中的实际权限、地位要高于司徒。西周后期,随着理性主义和人文思潮的兴起,司徒的地位和权力得到了提高和扩大,而史官则渐趋下滑。班固指出儒家出身司徒,盖因孔子担任过司徒;道家出身史官,亦盖因其祖师爷老子曾为周柱下史。在孔、老及其以后的时代,司徒官职远远高于史官,故儒家虽屡遭诸子批评,但其社会地位和官方待遇均高于道家。
先秦道家尽管批评儒家甚为激烈,但由于各诸侯国的治国策略大多离不开儒家的政治学、社会学、道德学的思想,特别是儒家之“礼”,孔子及其弟子乃至学派的社会影响依然与日俱增。所以,庄子一面不遗余力地攻击儒家,一面却又不得不借孔子及其门人的言论来表达自己的主张。例如:庄子著名的心理学思想“心斋”、“坐忘”,就是借孔子及其弟子颜回两人的对话来表述的。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暤天不宜。”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矣。”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日:“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而后也。”(《庄子·大宗师》)道家如此重要的一些修行术不是自己直接言说,而是借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和弟子的对话来宣传。庄子的用意,昭然若揭:一方面,庄子通过孔子在春秋、战国时期的威望扩大了他自己思想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借孔、颜师徒间的对话有意抬高颜回的境界,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孔子。此种现象在《庄子》一书中屡见不鲜。
从儒、道思想的相通与立异、融会与冲突、借鉴与批评来看,作为后来道教的思想主要来源的道家,其思想的发展并不是单一线条的,而是大量吸收了儒家以及兵家、墨家、法家等各家思想。(《史记》卷130《太史公自序》:“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同样,儒家在发展过程中,也积极吸收了道家的黄老道、老庄道的思想。例如,汉代大儒董仲舒(一个从带有浓重神秘主义的燕、齐之地出来的儒士)就将先秦的原始鬼神崇拜、太极,尤其是燕、齐之地盛行的阴阳、五行、神仙、方术、房中等先秦非儒家的思想因素,杂糅进了儒学之中,对“通过五行的媒介发挥作用的天、地、人三界的一元性质作了新的强调”,使之贯穿于社会的政治统治和人们的精神生活方面,实现了大一统帝国的国教神学化的思想整合。因此,儒道互补不只是两种对立思想在社会进程和个体生存中的相互补充,它实际上还包含儒道两种思想的某些融合。
参考文献
[1]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袁珂,中国神话传说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
[3]郝大维,安乐哲,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施忠连洋[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4]莱茵哈德·梅依,海德格尔与东亚思想,张志强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5]本杰明·史华兹,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程钢译[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6]胡孚琛,吕锡琛,道学通论——道家、道教、丹道[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7]许悼云,论雅斯贝尔斯枢轴时代的背景[A],许倬云,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C],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8]朱谦之,老子校释·老子德经[z],北京:中华书局,1984
[9]马克斯·韦伯,中国的宗教——儒教与道教,康乐,简惠美译[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崔瑞德,鲁惟一,剑桥中国秦议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 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