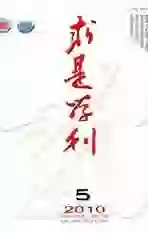卡西尔與文化哲学的进路
2011-01-01王立志
求是学刊 2011年5期
摘要:卡西尔是新康德主义的殿军,他的思想仍未偏离康德哲学的重心——人的问题,他通过创造性地思考和解答康德提出的问题,把“回到康德去”这一目标推进到了一个新层次。卡西尔把康德的先验图式转化为对符号的劳作,赋予先验图式以存在论的意义,从而把人类的自我认识看做理解和阐释人类“创造物”的构造原理,揭示人类的精神形式的过程。洞察神话、宗教、艺术、科学的思维和表达形式,探究其中隐藏着的人类精神得以统摄的法则是文化哲学的任务。
关键词:先验图式;符号形式;功能性统一
作者简介:王立志(1972—),男,河北冀州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哲学與文化研究所、哲学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从事过程哲学、科学思想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B516.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0)05-0013-05 收稿日期:2009-09-12
作为康德先验原则的体现者,卡西尔从两个方面发展了康德的理论:一方面他把康德的先天形式发展为生成着的符号形式:另一方面他把康德哲学的逻辑结构與人类文化领域结合起来,把康德的先验原则运用到人类的一切活动中,从而把康德的理性批判变成文化批判。卡西尔的《实体、函数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是最早对相对论作出哲学反应的著作之一。经过现代科学的洗礼,在卡西尔那里,认识的先验条件转化为一种时空观念,一种符号形式。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使客观地起作用的创造力被主观地发现了,卡西尔符号形式哲学赋予了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以存在论的意义。卡西尔的哲学以文化为研究领域和基点,从符号形式方面对人类经验予以科学的、现象的分析,这不仅扩大了康德哲学的知识论原则,也为德国的人文主义传统找到了知识的、科学的、现象学的表现形式。卡西尔开辟的文化哲学研究为我们理解人的完整性,理解多样的世界奠定了新的方法论基础。在文化哲学成为显学的今天,重新审视卡西尔这位唯一在中国哲学文化中有现实影响的新康德主义思想家的思想进路,对于克服传统的唯理智主义对文化哲学研究造成的困惑,走出“纯观念的王国”,清理文化哲学研究的地基,回答“真正的人的科学如何可能”都有重要的意义。
一、康德的先验图式與文化哲学的奠基
康德在1793年致卡尔•弗里德里希•司徒林的信中说:“很久以来,在纯粹哲学的领域中,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学)3、我应该希望什么?(宗教学)接着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二十年来我每年都讲授一遍。)”如果把《实用人类学》放入康德整个批判哲学的脉络中,我们就会产生一种新的看待康德哲学的视角:他的批判哲学(《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是建立先验人类学的努力。康德的先验哲学(他称做先验唯心主义和批判唯心主义)对人类的各种能力(知、情、意)的先天原则进行批判的考察只是为真正的、实用的人类学奠基。康德的真正目标是建立融会人的知识、情感和道德为一体的,体现出人的自由能动性的、人的崇高性的人性论或人类学。这样一来。康德哲学就可以被看做两种人类学的合一。即由三大批判构成的先验人类学和经验性的实用人IoZ430GuWain2MgKmjNNDw==类学的合一,后一种人类学是前一种人类学的归宿。这两部分都JzYL+yZnVMhgYoh7KFKafA==以关于“人的知识”和如何运用“人的知识”为己任。
关于“人的知识”只能到人的创造物中去寻找。维柯的“真理與创造物相互转化”这一新科学的第一原理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8世纪,数学、力学、天文学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在康德看来,关于“人的知识”隐藏在人类最伟大的创造物——数学自然科学知识中。关于“人的知识”是其他一切知识的前提,这个前提是先于经验的(先验的),是隐而不显的。如何从人类的“知识库”中发掘出那个深藏着的先验原理是康德知识论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康德的工作也可以叫做“知识考古学”。知识是人类的“制作”。先天知识是制作的依据,先验哲学只研究先天知识被运用的那一部分。只有这一部分是可以把握的。至于先天成分中没有被运用的部分只能是潜在的,不是现实的,因此不在先验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先验哲学是面向“现实”的,它是关于“人的知识”的现象学。
康德对纯粹理性的批判旨在厘清为自然科学提供基础的、独立于经验之外的“纯粹部分”(理性)。这个“纯粹部分”决定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它是人自身的界限和本质,也是人认识外部世界的方式、尺度和界限。人是凭借着这个“纯粹部分”为自然立法的。人是靠着这个“纯粹部分”、这个“天分”與世界打交道的。人应该充分地利用这个“天分”(理性)。康德通过追问“科学知识如何可能”和“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走向经验世界的深层,走向那个纯粹的领域,洞彻经验的逻辑结构和规律,它的普遍原则和条件,即先验的形式结构及其发挥作用的机制,去追寻知识制造的过程。康德称人类创造知识的能力为知性,指引知性发挥作用的是“先验图式”。用他的话说,就是一种“限制知性概念使用”的形式和条件。康德特别强调了图式的形式特征无论是可能性条件还是普遍性条件,都蕴涵着一种超越具体经验对象的形式规定。通过先验图式,感性和理性在先验想象力中融为一体。在康德那里,图式是作为方法而不是作为实体的。在通往纯粹知识这一片晦暗不明的领域的途中,《纯粹理性批判》点燃了一把火炬,不过,它所指向的不是那超乎感性世界之外的未知领域,而是照亮着我们自身理解活动这片漆黑的区域。康德的先验方法并不发展为超验的、超感性的,而是把我们引回到理性的深度,使我们认识和把握理性的前提及其基本力量。这一基本精神贯穿于三大批判的始终。
关于“人的知识”不仅要到人类认识的成果——科学知识——中寻找,也要到人类行动的创造中去寻找。人不但为自然划界,也为自己划界。在那个纯粹的领域里,不但蕴藏着人类的认识原则,也蕴藏着人行动的原则,即人行动的先验条件。在“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这一命题背后回响着的“人的自由如何可能”这一更深层、更重要的命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了解决。人凭借着实践理性这一天赋的能力从自己出发,在现象世界,在可感的、物理的、必然的世界中创造出了一个“事件的世界”来。这个行动的、实践的领域具有原创性,人的主动性在这个领域得到了体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持否定态度的“超越”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得到了妥善的安置。
在活生生的经验中,人是一个完整的整体。“生命”不可以真的分割为“理论”和“实践”两大块,如何在“同一的理性”中理解人的完整性?理性规定下的意志(纯粹意志)怎样才能创造出“作品”来?这是人实现“不朽”的最关键的问题。必然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都有自己的内在规律,这两个世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可是这两个世界靠什么联系在一起?人的行动是自由的,是“从心所欲”的,但不是毫无顾忌、任意妄为的,它受到必然世界的限制,受到目的的引导。人鉴别完美的能力(康德称为审美鉴赏力)把必然世界和自由世界连接起来。人的这一天赋的能力在人“当机立断”之际显现,相机而动。意志是自由的,它可以不受可感世界的摆置,自行其是。因为意志是“自由”的,所以它可以不计利害行事。理性存在物在不计利害的前提下进行创造,他需要“材料”,他在处理这些“材料”时需要“通盘考虑”,行动要及时,判断在当下。这就要求这种“通盘的考虑”在瞬间完成。审美判断需要人在感觉到事物时,“感而遂通”。显然,理智不能担当此任,因为概念推理是延迟的,所以判断不能依凭概念。同时,它也不能违背理智的规则。审美判断是一个“情通而理达”的状态,理即形式。“通情达理”的审美判断的先验条件是想象力利用知性提供的材料构制的蓝图,这个蓝图即主观形式,它如影随形,无时不在,它是当机立断(鉴赏判断)的依据。康德首先在人的审美心理上寻找一般鉴赏判断的普遍有效的先天条件,然后在人类审美的经验事实即艺术和艺术史中,寻找鉴赏判断及审美愉快普遍传达的先天条件。就审美鉴赏的对象和认识的对象而言,它们是同一个对象:就内容而言,却是不同的。鉴赏的内容是自由的,认识的内容是必然的。在人的创造过程中,自由和必然统一起来。
在人的创造物中,纯粹形式的、没有感性直观的、不在时空之内的道德自由具有了可感的内容,有了“不确定”的时空直观形式,这种形式不是必然知识的图式,而是自由世界的象征。因为这个形式是主观的、自由的,所以它不显示对象的客观属性而是显示那最隐秘的“本体”、“人自身”。在这自由的时空中,不可感的、在必然的时空中隐而不显的“物自身”显现出来。“我”从内部给所有行为和关系分派了质和形式,这个物的世界因为“我”而有了生命。先验哲学向人们提示:人有一个向世界的实际构造敞开着的结构。人可以凭借这个已有的结构建立起與实在的日益丰富的关系;人可以凭借这个结构塑造自己,通过“尽(显)物之性”,而“尽(显)人之性”。康德哲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为自然立法和为自由立法的问题。而是要考察人类整个文化实践生活所赖以成立的理性的先决条件,考察人类精神能力的本性、功能、界限和范围,以及人类的天职、希望和历史的未来方向,探究人类文化在其先天意义上究竟如何可能。
二、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與文化的统一性
知性的先验图式在康德哲学体系中占有重要位置,离开它康德的其余理论框架就无法理解。卡西尔对先天的看法基于康德的范导性原理,他把康德哲学看做一种引导、一种哲学方法,而不是一个完成了的体系。卡西尔接受了康德先验哲学的基本原理,即现象的实在性不是来源于感官和心灵的被动接受,而是来自于精神把先验形式赋予感性杂多所产生的影响和结果。先验图式到底是什么?它是與生俱来的,还是生成变化的?如果是生成的,它的生成机制又是什么?康德的先验图式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在卡西尔看来,康德并未提出一种数理一自然科学知识的理论,他的贡献在于形而上学之所以可能的条件:康德的“科学知识如何可能”这一命题构成了一个物理世界的可能性,然而,人不仅是科学这一种类型的世界的构造者。人还构成了语言、神话、历史、宗教、艺术的世界。科学只是人性圆周的一个扇面。如何理解不同类型的世界的创造者?如何对人作整体性的理解?这是卡西尔关心的问题。卡西尔认为完整的人存在于“人文化成的世界”里,他把人看做符号的动物。符号的世界、“人文化成的世界”只有通过其起源和普遍有效的立法形式才能成为可理解的。
在这一思想的道路上,黑格尔是卡西尔从康德的先验图式过渡到符号形式的桥梁。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的领域有自己的规律,这规律要到“历史”中去寻找,即通过对艺术史、神话史、宗教史的经验知识的“回忆”,抵达精神世界的深层。规律潜藏在过程中,事物的本质在“大全”里。对于那个变动着的“精神”,把握它的唯一方式是通过它的效用性去考察,也就是去把握意识的诸形态,精神变化的诸环节。黑格尔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概念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的形式,是自己确知自己的精神的形态。黑格尔的概念是一个关系的集合,因为“事物只有在关系中,只有通过我以及它與我的关系,才有意义”。对于变化着的意识、精神而言,形式就是自我自己,因为形式包含行动着的自身确定的精神,自我是在履行着绝对精神的生活。黑格尔的形式是有内容的,诸形式是那活生生的精神的自我确定的方式。形式、概念描绘了精神的变化过程,这个过程以自由的、偶然的事件的形式呈现出来。“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揭示了时间的转换和精神上原初生长得以展开的过程。”卡西尔由此看出了自身的问题和方法——批判唯心主义的方法:不把自己限制在纯粹事实的范围中,依照普遍原则去规整这些事实。这些原则不是先验的思维方式推衍出来的,而是通过询问具体科学获得的。只有接受具体科学提供的素材,分析和理解在语言、神话、艺术、宗教、科学中的那些基本感知、表象、想象、描述方式,才能保持精神的生机與活力。艺术與神话、科学和语言都是朝向存在的创造,它们不是对已经存在的实在的简单摹写,它们表达了精神运动、理想过程的伟大路线。
卡西尔把这种精神的创造看做对符号的劳作。符号是人的创造物,人栖身于符号中,并在这个自己创造的世界中创造。对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个体而言,符号世界是被给予的、是先天的。符号是人“文化”自然的结果也是人成为自己的前提条件。人是在这个结构中实现知、情、意的统一,完成自我认同的。人自身的谜藏在这个新的实在之维中。先验图式、人之为人的依据不再是隐藏在人自己内部的什么东西,而是由生活世界的形式给予的,这些形式是一种活生生的力量,一种沉浸在我们生活世界的经久不衰的能量之流,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着的人成为独特的自己的根源,符号是潜藏着的形式得以显现的中介。因此研究符号、符号世界的结构和生成过程就是在研究人自身。康德的先验图式转变成了符号形式的生成过程。符号形式成了组织思想和表达情感的方式和媒介。康德曾以研究“人类心灵的建筑术”为自己的目标。一个人天生就是一位杰出的建筑师。他从外部摄取材料构筑自己的身体,同时也从外部摄取材料构筑自己的“心体”。构成身体和“心体”的材料是不同的。人通过摄取物质材料(蛋白质)构筑自己的身体,通过摄取符号构筑自己的“心体”。研究人的“心体的建筑术”是卡西尔符号哲学的目标。
符号既是人的创造结果,又是创造人的条件。人是通过摄取饱含情感的符号、符号之间的关系以及关系模式成为自己的。科学、艺术、宗教、文学各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符号系统,从具体的形态上看它们是不同的,而从形式和模式的角度来看。它们却有相同之处。卡尔所要探究的是“整个现象所依凭的不同函数的本性”。这是一个崭新的思考维度。
三、符号形式的功能性统一
20世纪初,关于时空、物质和运动的科学思维打破了过去实体性的思维方式。当我们不再把现代物理学的语言看做外在事物的直接图像和对应物,而把它们看做符号,即看做康德所说的那种其唯一目的“在于说明现象以便使它们有可能作为经验被人所理解的符号,我们就会看出,用不同的符号去说明现象不仅是可能而且是必需的”。卡西尔从符号学角度评价了玻尔的互补原理。他写道:“玻尔为了解释和论证他的原理,不得不回到理论物理所运用的符号的本性,并以一种明白无误的方式反省这些符号。为了建构他的新的原子模型,他不得不放弃光的电磁理论中的放射律,这看似悖谬。然而,它却是我们基本的物理概念所具有的符号特性的最清晰、最鲜明的证明。”如果我们不满足于各种记号的物理属性,而是重视对简单材料的形式的思考,那么这些材料就有了变化的新生命。科学理论是人的创造物,它是一种融人类生命和自然物理事件为一体的创造物,对这些符号体系本性的研究成为审视人类自身之谜的途径之一。
卡西尔要研究科学的语法、艺术的语法、神话的语法、宗教思维的语法。这种探究是对活生生的思维和表达方式的探究。符号具有感性的性质,是一种抽象化了的感性,是有一定形式的感性,它们不仅是感性的物理存在,更是我们人类精神活动的标记。在现代物理学所展示的自然宇宙里,整体先于部分;在精神宇宙里,意义先于符号。符号的作用首先是把意义固定下来。语言、神话、理论认识在这里都被当做“客观精神”的基本形态,这种“客观精神”的存在必须能够纯粹作为自身被指示和理解,而独立于它的“生成”问题。卡西尔把符号世界当成“文化事实”看待,他要把握和描述的是文化事实的结构。在这种意义上,卡西尔的“符号形式”與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一致的。这與他们把现代数学物理学看做符号意义指示功能发展的最高程度密切相关。
依据康德的观点,空间是外经验的形式,时间是内经验的形式,时间比空间更具本源性。“我们的各种表象,不管它们来自何处,无论它们是外物影响的,还是内因造成的,是先天地产生的,还是有经验产生的现象,总之都是内心的变形,都是属于内感官的,因此我们的一切认识全部依从内感官的形式条件,即时间,它们全都必须在时间中加以整理、联结,纳入关系。”时间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程序,它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规整的、被纳入关系的不是物质实体。而是代表着特定关系和情感的符号形式;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东西会以完全相同的形态重新发生,它们相互渗透,并强化着自身。时间作为内感官的形式条件也随着符号世界的变化而改变。人的生活世界(精神宇宙)不是“机械的建构”。“空间和时间是一切实在與之相关联的架构。我们只有在空间和时间的条件下才能设想任何真实的事物。”在这种意义上说,时空观是“人文化成的世界”的尺度。人的时空观念、思考和行为的尺度是怎样获得的呢?在卡西尔看来,人是通过符号塑造自己的。“抽象的空间观念为人开辟了通向新的知识领域的道路,而且开辟了人的文化生活的新方向。”当天文学取代了占星术,几何学的空间取代神话和魔术的空间,近代科学的符号系统确立起来,人就生活在一个完全崭新的世界里了。“近代哲学最初和最困难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理解这种符号系统的真正意义和全部重要性。”
时间上的瞬间、空间的点、事物和它的属性只有在意识的形式结构里,在一个关系系统内才存在。在卡西尔那里,康德的自我意识的统一性变成了主体内部经验的三种统一性:时间统一性、空间统一性、客观综合统一性。康德的先验图式变成了符号制作。这种符号制作是遵循着一定的函数关系进行的,科学理论这个“人的创造物”是形式化了的感性符号在功能上的统一。我们生活在语言中,生活在诗歌和造型艺术的形式中,生活在音乐的形式中,生活在宗教表象和宗教信仰的结构中。只有在这些形式中,我们才能彼此认识,才能自我认同。文化科学的目标不是定律的普遍性、事实和现象的个别性,而是人生实现于其中的形式整体。符号形式的哲学把“文化意义”的统一性和客观性当做理性任务。符号是包含着精神意义的载体,它用内在于自己的形式追求、探索、捕捉、摄取外在于自己的事物。现代科学提供的宇宙图景只不过是“一个由符号体系所标示的世界”。科学和其他的文化模式(语言、神话、宗教、艺术)一样,通过为自己创造一种确定的可感觉的根据,构造自己的对象,从而发展它特有的构造模式和理解模式,揭示实在。科学体现了人类精神的一种组织原则,这种原则是开放的、可变的,因为符号世界的结构在变化,符号形式始终处于生成的过程中,符号系统具有开放性和可变性。在那可感的、具体的形式结构中蕴藏着一个变化不息的、由自然事件构成的、由人的意识所把握的意义世界。物理的宇宙是一个必然的世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世界,只有在符号的宇宙里人才是自由的。生活在自己创造的世界里,就要和自已的创造物打交道。
符号的多样性象征着世界的多样性。通过符号的多样性理解世界的多样性,通过符号的功能性统一认识人與世界的统一性,进而发现自由得以实现的方式和途径。在这种意义上,卡西尔开辟了理解自由、认识人自身的新维度。卡西尔强调抽象的关系结构,同时他又强调符号蕴涵着情感;他把科学看做符号劳作的最高表现,又强调原始的世界表达形式即神话世界观的相对独立性;他用符号形式的关系模式取代了先验的图式,展示了符号形式的生成性、过程性和象征性,同时他又强调符号世界的客观性、有效性和可交流性。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在构思和涵盖范围上是惊人的,他处理哲学问题的方法从根本上是综合的和调和的,他融合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努力虽然由于深层的系统性的困难未能实现,但他所昭示的方法和思考路线对于科学地研究“人文化成的世界”却是不可绕过的里程碑。
参考文献
[I]卡西尔,符号、神话、文化,李小兵译[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8
[2]康德,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3]邓晓芒,康德哲学诸问题[M]上海:三联书店,2006
[4]江怡,康德的“罔式”概念及其在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演变[J],哲学研究,2004,(6)
[5]张慎,西方哲学史[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
[6]范进,康德的文化哲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7]卡西尔,人论,甘阳译[M],上海:上海泽文出版社,2007
[8]迈克尔一弗里德曼,分道而行——卜尔那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 李小娟 付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