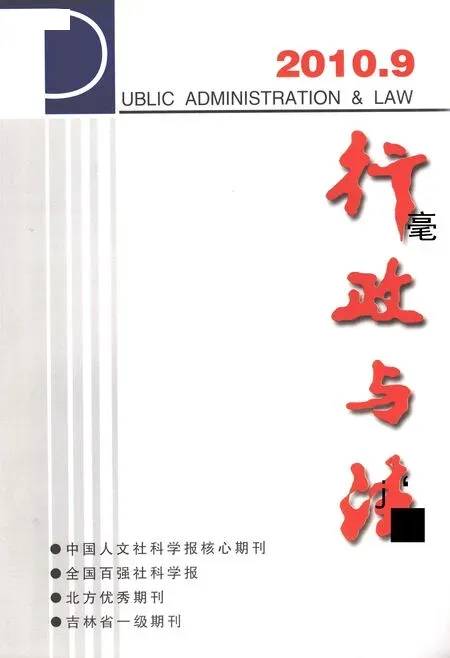不动产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理论反思
2010-12-26□孙潇
□孙 潇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不动产善意取得适用范围的理论反思
□孙 潇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88)
在中国语境下,“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问题之争主要不是法律效果争议,而是制度安排争论。在比较法视野中,“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之争是实质的规范效果的问题。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并不意味必然构建囊括动产与不动产相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不动产善意取得最终在法典上与动产善意取得区分设计,在“登记公信力”的制度安排下实现“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不动产善意取得;登记公信力;善意
一、争议的总结与梳理
对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或者说善意取得适用对象的范围是否应扩大至不动产这一问题,我国学界历来争议颇大,可谓“见仁见智”。现梳理如下:
(一)不动产善意取得的否定论
以梁慧星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不动产是以登记为其公示方法,交易中不至于误认占有人为所有人,故不发生善意取得之问题。基于物权登记的公信力,即使登记错误或有遗漏,因相信登记正确与登记名义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其所得利益仍受法律保护。[1](p94、218)
以孙宪忠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因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又因为不动产登记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任何人已经无法在不动产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者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动产物权法公认的原则。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领域内已经无法适用。国际上凡是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在法理与实践上均有这样的效果。[2](p303)
以王利明为代表的学者认为,不动产的转移因为有登记过户制度,故而权利归属十分明显,不必以善意取得而对交易安全加以特殊保护。如果不动产发生错误登记,第三人因为信赖登记而与登记记载的权利人发生交易,此种情况一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而应适用公信原则。[3](p280)
中国政法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指出,由于不动产的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是登记,因而在不动产交易中,双方当事人必须依照规定变更所有权登记。不存在无权处分人处分不动产所有权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必要前提,故各国立法均规定只有动产交易适用善意取得制度。[4]
(二)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肯定论
以叶金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动产善意取得、不动产善意取得,具有相同的价值基础及逻辑结构,没有偏废之理。而且在具体的构成要件及法律效果上,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均具有基本相同的架构。公信力强弱不应成为否定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理由,登记之较强的公信力倒是应该使第三人物权的善意取得更为肯定。[5](p187)
以常鹏翱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动产占有和不动产登记作为权利的外观是同质的,它们在推定和拟制之法律技术的构建下,最终通向便于交易的归宿。既然目标一致、基础相同、结构类似,将动产善意取得进行一体化的结构设计,自无不可。[6]
(三)争议观点的总结分析
综合以上观点,持不动产善意取得否定论的学者大都认为,在不动产领域,不动产登记制度使得不动产的交易以登记簿公示内容为准据,第三人不得因信赖“占有”的公示方式而实现类似于动产的善意取得。同时,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已经发挥了保护交易中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的功能,因此,“无需”也“不必”再建立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此外,大多数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国外立法中,只认可动产的善意取得,而不存在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立法例。而持不动产善意取得肯定论的学者则认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以动产占有的公信力为逻辑前提的,与之相对应,建立在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基础之上,也应该存在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否则法律逻辑就欠缺一致性。同时,不少学者认为国外立法中,善意取得的适用范围已扩至不动产。[7]
二、善意取得适用对象比较法上的考察
(一)肯定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立法模式考察
⒈德国法。《德国民法典》第932条规定:⑴即使物不属于让与人,取得人也应依照第929条所为的让与而成为所有人,但是取得人在依照该条的规定本来会取得所有权时非为善意的除外。但在第929条第2句的情形,仅在取得人已从让与人处取得占有时,才适用前句的规定。⑵取得人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该物不属于让与人的,非为善意。这是德国法对动产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具体规定。该法第892条规定:“为以法律行为取得土地上的某项权利或此种权利上的某项权利人的利益,土地登记簿的内容视为正确,但对正确性的异议已经被登记或者不正确性为取得人所知道的除外。”按照体系解释方法,该条文是继891条土地登记的推定力之后,对土地登记簿公信力的规定。土地登记簿公信力的结果,按照M·沃尔夫的解释,是善意取得人取得权利,好像土地登记簿中登记的法律状况就是实际的法律状况一样。善意取得人因此而取得被登记的权利,尽管该权利在实际中不存在。[8](p228)
从法律效果上分析,该条文事实上承认“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效果;从构成要件上分析,同样要求第三人为“善意”,取得人在明知登记簿不正确时为非善意,因重大过失不知并不排除善意取得效果的发生。该条文尽管采用了“登记簿公信力”,而不像规定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第932条直接采用“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但透过这些词语的迷雾,在法律制度体系化的视角里,同属于善意取得的范畴。[9]在鲍尔/施蒂尔纳的物权法教科书中,将该条文称之为“自无权利人处之取得:土地登记簿之公信力”,[10](p488)德国学者M·沃尔夫直接把该条文称之为“土地权利的善意取得”。[11](p220)可见,在德国物权法的立法体系和学术体系中,承认土地权利的善意取得,只不过在制度构造作为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的效果而存在。或者说,在德国法上不动产善意取得是通过登记簿公信力的制度予以表达的。
⒉瑞士法、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瑞士民法典》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典都采用了与《德国民法典》几乎一致的立法模式。《瑞士民法典》就动产所有权善意取得制度的一般规定体现在该法典第714条第2款:“以所有权转移为目的的善意取得动产,依照占有的规定,其占有受保护的,即使该动产的出让人没有出让权,依然是该物的所有权人。”与之对应,在不动产登记簿公开性中区分了对善意第三人和恶意第三人的效力。第973条规定:“出于善意而信赖不动产登记簿的登记,因而取得所有权或者其他权利的人,均受保护。”第974条规定:“物权登记簿不正当的,该登记对于知悉或者应当知悉该瑕疵的第三人无效”。可见,瑞士法上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效果也是在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制度框架下实现的。
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第801条规定了动产的善意取得,该条规定:“动产之受让人占有动产,而受关于占有规定之保护者,纵让与人无转移所有权之权利,受让人仍得取得其所有权”。但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没有对土地等不动产登记效力作出规定,《土地法》第43条“依照本法所为的登记有绝对效力”的规定也不甚清晰。依照“司法院”的解释,所谓“绝对效力”系为保护第三人起见,将登记事项赋予真实的公信力,因此第三人信赖登记而取得土地权利时,不因为登记无效或者撤销而被追夺。同时,需第三人信赖登记而取得登记权利,才有本条的适用。[12](p48)另外,“民法物权编修正草案”增设759条之一规定,因信赖不动产登记之善意第三人,已依法律行为为物权变动登记者,其变动之效力,不因原登记有无效或撤销之原因受影响。该条文的增设恰恰是为了弥补原有条文的含糊规定,直接效法德国与瑞士的立法模式。可见,我国台湾地区在司法和学理上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
(二)否定不动产善意取得的立法模式考察
⒈法国法。《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规定:“对于动产,自主占有具有与权利证书相等的效力。”法国民法在善意取得制度上深受罗马法的影响,认为动产善意取得制度的法律依据为即时时效或瞬间时效。因此,法国物权法称善意取得为即时取得,且将其置于“时效”一章中作为若干特别时效的一种加以规定。法国学者马洛里和埃勒斯认为,第2279条规定具有两种不同含义:⑴动产的自主占有与所有权的证书是等值的,占有如同权利证书,当事人可用以证明其所有权的存在;⑵自主占有是一项所有权的证书:当占有人未被予以真正所有人的同等对待时,自主占有使占有人成为所有人。如果将法国民法典第2279条第1款的规定理解为同时具有上述两种含义的话,则必然导致以下结论:自主占有不仅是对所有权的一种推定,而且尤其是对属于他人的动产的一种即时取得的方式。[13]显然,法国法上的即时取得制度仅仅适用于动产,而排除了不动产的适用。
与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相对应,法国法是否有通过登记公信力的制度安排来实现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呢?法国不动产登记为物权与债权的混合登记,不动产公示仅为一种“宣告”,此种宣告在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不能发挥任何作用,亦即公示的作用仅在于对抗从同一出让人处取得同一权利的第三人。[14]法国的不动产登记作为登记对抗主义立法模式的典型,是没有公信力的。在登记对抗主义下,登记这一公示方法所表彰的权利状态,第三人仅能信赖“不存在与公示所表现出来的权利相反的权利”,即未发生相反的物权变动,而不能信赖“存在与公示一致的权利”,如果登记簿的记载有错误,错误地将无权利人记载于登记簿,即使是信赖登记簿的第三人,其所为的交易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15]
⒉日本法。《日本民法典》第192条规定:“通过交易行为平稳且公然开始占有动产的人,在善意且无过失时,即时取得可在该动产上行使的权利”。该条即为日本民法上动产善意取得的实证规范。关于不动产的登记,《日本民法典》第177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取得,丧失及变更,除非依登记法规定进行登记,不得以之对抗第三人。日本的登记模式也是采取登记对抗主义,在法典上没有正面承认登记的公信力。日本学者我妻荣先生认为,日本民法对于动产物权的变动虽然采取了公信原则,但关于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并未采取公信原则。当甲将其所有的物卖给乙并进行了登记,乙进而卖给丙并进行登记后,甲试图主张甲、乙之间的买卖因错误而无效,则乙不能取得所有权。但是,丙的立场则因买卖标的物为动产还是不动产而有所不同。若标的物为动产,乙误信且无过失,可以取得所有权;但是若标的物为不动产,即使丙对登记信赖且无过失,也不能取得不动产所有权。(丙对于乙取得追究出卖人责任的请求权)。[16](p219)可见,在日本法上,不可依善意取得获得不动产所有权。
尽管动产善意取得在各国立法上存在体系安排、制度构造上的差异,但是,各国对其基本持肯定态度,而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则存在较大差别。总体来说,《德国民法典》、《瑞士民法典》、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典属于同一模式,在不动产交易中,承认“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尽管在制度表达上,通常称之为“不动产(土地)登记簿的公信力”;与之相对应的,《法国民法典》、《日本民法典》对于不动产或者土地并不承认“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法律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德国、瑞士、我国台湾地区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而日本、法国则不予承认。
三、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的原因解析
从比较法的角度看,是否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与各国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及登记审查制度密切相关。物权具有对世性,物权的得丧变更必须通过一定公示来完成,动产为交付,不动产为登记。尽管现代各国都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方式,但在公示方式的效力上有两种不同的立法模式:一为公示生效要件主义,一为公示对抗要件主义。公示生效要件主义认为,单纯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意思,不能引起物权变动的效果。无论对于第三人,还是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物权变动如果没有进行登记,都将确定地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公示对抗要件主义认为,当事人一旦达成了引起物权变动的合意,就发生物权变动的效果。只不过在未经登记以前,已发生的物权变动不能对抗第三人,第三人可以以当事人没有进行登记为由,否认物权变动的效果。
德国、瑞士以及我国台湾地区,采行公示生效要件主义,不动产登记具有决定不动产物权变动是否成立的效力,并对其不动产登记采取严格的管理。在德国,登记官吏虽然没有审查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的权限,但是依照《德国土地法》第19条的规定,登记官吏需对登记承诺严格审查。承诺人要么亲自出席于土地登记所陈述登记承诺,要么以公证证书证明有登记承诺。同时,登记官有疑义时,可以主动审查原因行为,并把所发现的疑点告知当事人。在瑞士,土地物权变动的登记的要件除需要“申请”和“登记承诺”外,还需要证明“登记簿册的处分权和法律原因”。[17](p152-153)这样通过严格规定登记要件,赋予登记官吏严格的审查义务,尽可能减少甚至杜绝登记簿册的记载同真实的权利关系不一致情况的出现。在此基础上法律赋予不动产登记以极强的公信力,即使登记簿册记载有错误或者遗漏,因信赖登记正确而与登记簿上记载的无权人进行交易的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也受到法律的保护,即发生“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的效果。
与之相反,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采行公示对抗要件主义,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完全维系于债权意思,其不动产的登记不能表征不动产物权变动和归属。物权变动可以公示,也可以不公示,即使不公示也可以产生物权变动的效果,这就无法保证登记的连续性,在制度设计上就不能保证法律上的权利人和真正权利人的一致性。登记簿册中记载的权利人可能是真正的权利人,也有可能不是。例如甲为一宗不动产的所有人,甲和乙之间订立了不动产的买卖合同,但是未办理登记手续。这样,乙就是这宗不动产的真正所有人,而甲则是登记簿中的名义所有人。如果在制度设计上强行赋予该登记以公信力,这样虽然有效地保护了善意第三人,消除了第三人的心理顾虑,但也势必会给名义权利人提供恶意转让的可乘之机,真正的权利人势必会因此遭受风险。[18]基于此,采公示对抗要件主义的国家在法律逻辑和交易实践中无法赋予登记簿册以公信力。
同时法国和日本的登记审查制度并不能在相当程度上保证登记的权利人与真正的权利人的一致性。在法国,抵押登记员就当事人交由登记的行为效力进行评价,仅在抵押权注销的情形,行为已经严重至不可挽救,此时方可审核行为是否具有可公示性。[19]在日本,《不动产登记法》第49条规定的驳回登记申请的限制性条款,除了标示登记之外大多是形式性的,不涉及对于导致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真实性和效力的审查,只要登记申请与这些条款不抵触,登记机关就必须受理。[20](p263)同时,日本不动产登记簿相当不完备,“地图制作和土地测量极不完全,且由于‘宗’相当错综复杂,因而登记之记载不慎明朗”,构成不实记载的可能性非常大。由于以上的原因,日本在不动产交易方面,理论上的观点是不采用公信原则的,也就无法有效保护那些在无过失情形下信赖公示的人。而在动产交易方面采用了公信原则,所以在动产物权变动中承认了动产的即时制度。[21](p31)
综上所述,在以德国、瑞士为代表的国家,通过严格登记审查确保实体法律关系的真实性,登记被赋予有公信力,以此为支撑,承认了“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而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国家,登记审查是不涉及实体权利内容的形式审查,登记不具有公信力,这使得第三人不可能仅凭对登记簿的信赖而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诚如学者所言,将“善意取得只适用于动产所有权”这一说法加以普遍化是片面的,事实上,该判断仅对法国、日本等不动产物权公示对抗主义的国家有效,其原因在于此类国家未赋予不动产物权变动以公信力,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便失去了逻辑支撑。反之,在不动产物权公示公信主义的德国、瑞士及我国台湾地区等立法例中,善意取得制度同样适用于不动产物权变动领域。[22]
四、善意取得制度构造的影响要素
(一)动产与不动产的二元划分的立法技术影响
德国、瑞士采用了“登记公信力制度”来实现保护不动产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与之相对应采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动产交易中的善意第三人。这种立法体例与动产不动产二元划分密切相关。
动产和不动产的划分对整个《德国民法典》,尤其是对德国民法物权法体系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德国民法典》尤其是物权编没有按照物权的种类来编制其物权编的结构,而是按照动产与不动产的划分来设计了它的物权编。这样,该法典物权编事实上建立在对不动产和动产区别对待的法律规范上面。拉伦茨认为,这种对物的区别不仅在物权法中和债法中具有重要意义,在实体法上进行区别对待的规定也影响到诉讼法,法院在强制执行中对地产的强制执行所依据的法律规定也是完全不同于对动产的强制执行的规定的。[23](p382)同时,《德国民法典》的编纂也充分体现了德意志民族喜爱抽象思维的特点,因为该法典到处都留下了立法者从具体制度中概括出一般原则的烙印,德国人将这种方法叫做“提取公因式”。比如总则编、债务关系的一般原则、不动产法的一般原则等。凡是能够抽象出一般规则的地方,《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无不乐而为之、善而为之。[24](p9-11)
可以说,动产法律制度与不动产法律制度分别设计,是德国民事实体法和程序法所秉持的一项重要原则。将动产的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分别规定正是这一立法思想的体现。但是,德国立法者在物权编没有放弃“提取公因式”的努力,他们尽可能地归纳二者的共性,统一予以规定,比如占有法、所有权内容、所有权种类以及所有权的保护。而将一系列被法律所许可的特殊权利种类和所有权与限制物权之设立、转让以及废止各自区分予以规定。[25](p19)可见,在《德国民法典》的立法者看来,动产的善意取得与不动产的善意取尚没有充足的共通性作为依据,用“提取公因式”的技术来将其一体构造,而是遵循动产与不动产区分规定的原则。
(二)制度的体系性因素的制约
在德国与瑞士的民法典中,不动产善意取得是作为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的法律效果规定的。然而,登记簿的公信力的外延远远大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德国不动产登记实行法规定,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主要内容有:关于不动产状态的文字的描述,关于不动产四临界址的表述,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记载。其中,重点部分是关于不动产物权的记载。这也是发生公信力的内容。法律规定这一部分必须包括的内容有:⑴所有权,记载不动产的来源及其变更;⑵用益物权及其他权利限制,记载不动产负担的用益物权以及根据民法典对不动产所有权的处分限制、异议抗辩以及预告登记等;⑶担保性权利,记载抵押权、土地债务、定期金土地债务以及这些变价权的预告登记等。[26](p146)《瑞士民法典》第958条规定,下列权利应在不动产登记簿上登记:⑴所有权;⑵地役权及土地负担,⑶担保物权。可见,登记簿几乎是按照不动产物权体系设立的。那么登记簿的公信力就是依照这些记载发挥其作用的。一般来说,登记簿的公信力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登记名义人处取得所有权的人,即使登记名义人不是真正的所有权人,取得人仍会确定的取得其名义下登记的所有权;其二,自登记名义人处取得所有权的人,如果该不动产上存在没有登记的抵押权,则该不动产视作不存在抵押权的财产;其三,抵押权名义人实际上并不享有抵押权,但由登记名义人处受让抵押权的,可以真正地取得抵押权;其四,自处分权受限制的登记名义人处受让物权的人,如果所受限制并未记载,受让人取得的为没有限制的物权。其五,向登记名义人履行给付义务,如登记名义人并不是真正的权利人第三人履行有效,真正权利人不得在要求第三人履行给付义务。[27](p160-161)
动产善意取得,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一个前提是正当的占有状态,即作为权利外观载体的特定的占有状态。这种状态应必须使取得人有理由在出让人身上发现所有权人的特征。[28](p395)可见动产善意取得只为第三人提供了一种积极的信赖保护。而建立在不动产登记簿基础上的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则既包括积极信赖保护,也包括消极的信赖保护。[29](p125)如果在承认不动产登记簿上述所有效力的前提下,将其积极信赖保护“提取”与动产善意取得一体规定,势必会分割不动产登记簿公信力的保护体系,使得与登记簿记载内容密切关联的不动产公信力的“支离破碎”。如果将整个保护体系一体“提取”,结果将打乱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体系安排。因为不动产登记簿的效力,实属不动产登记制度项下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不动产登记簿的公信力与登记的权利正确性推定规则和异议登记制度密切关联。前者是登记的善意保护效力的逻辑前提,后者是旨在破除登记的公信力,为推翻登记程序运行的结果奠定基础。如果将登记公信力的保护体系与动产善意取得一体规范,则很有可能割断登记制度的内在逻辑的关联性。另外,一体构造的立法模式,单从条文上看似乎是节约了立法资源,但条文过分的原则性和笼统性,将会给法律的解释和适用带来更多的工作量。
同时,动产的善意取得制度也形成了其本身的特别规范,这些规范在不动产领域是没有适用的空间的。一般来说,动产善意取得将标的物区分为“占有脱离物”和“占有委托物”,二者在善意取得上有不同的效果。“占有脱离物”是指非出于动产所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占有委托物”是基于真实权利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的物。前者无条件地发生善意取得,而后者在一定条件下发生善意取得的效果或者根本不发生。这种区分在不动产善意取得中是没有意义的。
(三)“善意”判断标准对制度构造的影响
善意取得中“善意”与“取得”为两个核心要素,在“取得”上动产与不动产没有实质性差别:都可发生从无权利人处取得权利的法律效果,但在“善意”这一核心要素上的异同却不可不察。
对于动产善意取得,《德国民法典》第932规定,取得人知道或者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该物不属于让与人的,非为善意。也就是说,善意是指取得人不知道并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道。对于不动产善意取得,《德国民法典》第892条规定:“为以法律行为取得土地上的某项权利或此种权利上的某项权利人的利益,土地登记簿的内容视为正确”,但“不正确性为取得人所知道的除外”。该条中的善意,仅要求取得人不知道。可见,法律对“善意”设定了不同的衡量标准。在动产方面,鉴于官方编制的土地登记簿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仅在实际知道时才予以排除善意取得,重大疏忽并不排除善意取得。[30](p226)而在不动产方面,“已知”和“由于重大过失而不知”都排除在善意取得之外。根据通常的表述,在取得人“根据整体情况以一种不寻常的重大程度违反了必要的谨慎,而且未注意到在该案中任何一个人都本应该弄清楚的东西时”,他就有重大过失。[31](p413)一言以蔽之,二者之差异在于是否有额外审查的注意义务。
动产善意取得与不动产善意取得在主观“善意”标准上存在实质差别,也使得善意取得制度难以用“提取公因式”的方法一体规范。在制度安排上,不动产的善意取得在强大的登记公信力下得以实现
在中国语境下,“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问题之争主要不是法律效果差异的争议,而是制度安排的争论。反对“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观点大都认可不动产登记的公信力;主张“不动产善意取得”的观点,亦是以不动产登记公信力作为逻辑前提。而不动产登记公信力就包含了不动产所有权“从无权利人处取得”的法律效果。这一点可以从比较法的视野中得以证实:以法国、日本为代表的物权变动公示对抗主义的国家,没有赋予登记以公信力,不承认不动产的善意取得;而以德国、瑞士和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物权变动公示要件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承认登记公信力,认可不动产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并以登记公信力作为其制度表达方式。因此,比较法视野中“不动产是否适用善意取得”之争是实质的规范效果的问题。承认不动产善意取得,并不意味着在立法上构建囊括动产与不动产相统一的善意取得制度。由于立法技术、体系架构以及公信力强弱差异等因素的影响,在以德国为代表的国家,不动产善意取得最终在法典上与动产善意取得区分设计,在“登记公信力”的制度安排下实现“从无权利人处善意取得”的法律效果。
[1]梁慧星,陈华彬.物权法(第三版)[M].法律出版社,2005.
[2]孙宪忠.中国物权法总论[M].法律出版社,2003.
[3]王利明.物权法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4]中国政法大学物权立法课题组.关于《民法草案物权编》制定若干问题的意见[J].政法论坛,2003,(01).
[5]叶金强.公信力的法律构造[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常鹏翱.善意取得的中国问题[J].中德私法研究,2006,(02).
[7]参见朱庆育.寻求民法的体系方法——以物权追及力理论为个案[J].比较法研究,2002,(02);陈永强.论德国法上不动产物权善意取得制度[J].比较法研究,2005,(03);董万成.不动产善意取得制度[J].河南省政法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5,(05);周铁朋.国外不动产善意取得法制的考察[J].中南大学学报,2006,(05).
[8][11][30](德)M·沃尔夫.物权法[M].吴越,李大雪译.法律出版社,2004.
[9]常鹏翱.善意取得仅仅适用于动产物权吗?——一种功能主义视角[J].中国法学,2006,(06).
[10][31](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下册)[M].申卫星,王洪亮译.法律出版社,2004.
[12]史尚宽.物权法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3]尹田.法国物权法上动产的即时取得制度[J].现代法学,1997,(01).
[14][19]尹田.法国不动产公示制度[J].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C].2000,(01).
[15]肖厚国著.物权变动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282;于海涌.不动产登记论[M].法律出版社,2007.
[16](日)我妻荣著.我妻荣民法讲义ⅱ新订物权法[M].有泉亨补订.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
[17]陈华彬.外国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4.
[18]于海涌.法国不动产登记对抗中的利益平衡——兼论我国物权立法中不动产物权变动模式之选择[J].法学,2006,(02).
[20]李昊.不动产登记程序的制度构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21](日)田山辉明.物权法(增订本)[M].陆庆胜译.齐乃宽,李康民审校.法律出版社,2001.
[22]朱庆育.寻找民法的体系方法——以物权追及力理论为个案[J].比较法研究,2000,(02).
[23](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M].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
[24][26]孙宪忠著.德国当代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1997.
[25][28](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M].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
[27]参见《德国物权法》第892条第1款,陈华彬著.物权法[M].法律出版社,2004.
[29]王泽鉴.民法物权(1)通则·所有权[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
(责任编辑:张雅光)
The Theory of Reflection of Scope of Bona Fide Acquisition
Sun Xiao
In China,most of the scholars believe the immovable property can be acquired in good faith,although they hold different views 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However,there are controversies in foreign countries in 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immovable property.In Germany,bona fide acquisition of movable and immovable property are regulated separately,which immovable property can be acquired in good faith by registration.
Bona Fide Acquisition;Registration Credibility;Bona Fide
D923.2
A
1007-8207(2010)09-0121-05
2010-07-02
孙潇(1984—),男,山东人,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