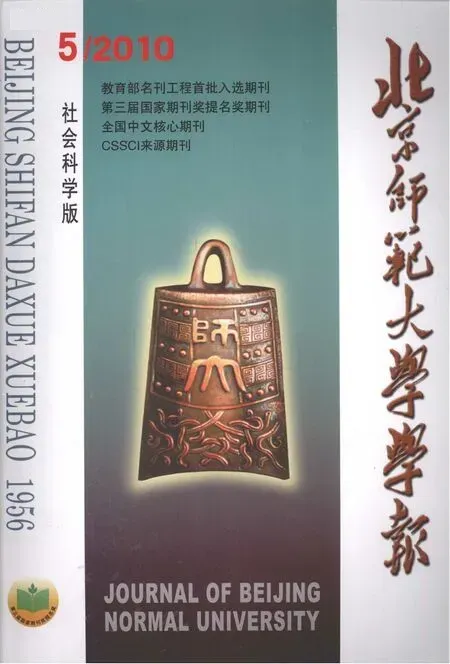重温几个黎氏语法学术语
2010-12-04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100732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重温几个黎氏语法学术语
刘丹青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北京 100732)
黎锦熙语法体系中所用的一些曾经沉寂的术语,近年来又重现于学术著作,并具有其他术语难以替代的作用。“补足语”在当代语言学中作为一个重要术语指包括宾语在内的一类重要句法成分,与黎氏语法中的补足语有相通之处。而汉语语法现有的“补语”虽然英译相同,却不是一个通用的语法概念,无法代替补足语的作用。名词的“位”是词类与句法成分之间的中间层次,近于“论元”这类当代语言学的中间层次术语,对刻画语法规则富有作用,不是所谓的多余层次。“代名词”、“指示形容词”等术语带有明确词类属性,比含义笼统的代词更便于用来阐述语法规则。这些黎氏术语比一些汉语特色的后起术语更适合进行跨语言对比和语言共性的研究。
黎氏语法学术语;补足语;名词的位;代名词;指示形容词
黎锦熙先生是创建现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第一人,他在系列著作《新著国语文法》、《比较文法》、《汉语语法教材》(与刘世儒先生合著)中所用的语法学术语,曾在学术界和教育界产生过广泛影响。不过,其中有一些术语,随着其他汉语语法学体系包括教学语法体系中相关术语的通行而逐渐淡出汉语语法学界,一度几成历史名词。但是,在时隔数十年之后,随着语法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深化,这些曾经淡出的黎氏语法学术语却又出现重归语法论著、再焕学术光辉的迹象,其学术价值值得重新估量。笔者所编著的《语法调查研究手册》就采用了一些一度沉寂的黎氏术语。而一些曾经取代这些黎氏术语的后起术语,则在学术发展中显露出某些不足,尤其是在跨语言比较和构建普遍性语法理论时显得捉襟见肘①刘丹青:《语法学术语的象似性及其利弊》,《燕赵学术》2007春之卷(创刊号)。。学术的历史,呈现出有趣的轮回,值得深思。
我们曾在《新著国语文法》出版60周年之际撰文②张拱贵、刘宁生、刘丹青:《〈新著国语文法〉对汉语语法学理论的贡献》,《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6期。,论述黎锦熙先生的这部开创性著作在汉语语法学史上的地位。二十多年过去了,汉语语法研究在黎先生离世后依然快速发展,而黎先生语法学说的理论价值则在此过程中不隐反显,本文就想通过讨论黎氏语法学术语的学术价值来说明这一点。
术语合理与否,不单单是一个名称问题,更是实质性的概念化问题。关键在于,该术语所提炼概括的现象,是不是一个具有科学性和内部一致性因而值得整合提取的概念,是不是一个有助于发现和提炼科学规则的概念。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重温几个隐而复现的黎氏语法学术语,探求这份学术遗产的内在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体会黎先生在众人逐渐抛却这些术语时仍坚守这些术语的用意。
本文重点重温的黎氏术语有:补足语、(实体词的)位、代名词、指示形容词等。
一、补足语
黎氏的“补足语”来自英文传统语法,原文应为comp lement。在传统语法中,补足语主要指由特定动词类别所带出的一些非宾语性的成分,尤其是表语性成分。《新著国语文法》将补足语分为三大类:同动词(即系词)所带的补足语、表示变化的内动词(变了、成了、现出)所带的补足语、外动词所带的宾语后的补足语。前两类都有表语性,最后一类相当于某些兼语句式中的后一谓语(工人请我报告|我爱他们诚实|工人推举张同志作代表)或作用相同但不带动词的名词(他们叫我老哥)。正如吕叔湘先生所说,补足语不同于后来所说的“补语”。可是两者使用同样的英文翻译——comp lement,这是造成很多术语理解障碍的要害。
“补语”是一个内部缺乏统一语法属性、与状语等无法区分的混杂概念①刘丹青:《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汉语史学报》,2005年第5期。,在语法规则的描写中无法进行统一的概括,更是很难与其他语言和普通语言学沟通。与其他后起的语法体系以“补语”为六大成分之一不同,黎先生体系本身没有“补语”的概念。在《新著》中完全未见此语,后来则是将其作为后加的副词附加语(简称“副附”)在其他语法体系中的用语②黎锦熙,刘世儒:《汉语语法教材》(第2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310页。,即看作状语的一种,不是一种与状语有别的句法成分。这种“轻视”补语的态度,与吕叔湘先生对“补语”的态度颇为相近。吕先生早期也不用“补语”一词,后来在《现代汉语八百词》等著作中虽然起用此词,但“补语”的使用范围极其有限,仅指动词后某些带“得”的情状成分。至于结果补语和趋向补语,吕先生在《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中明确认为动趋式、动结式“实质上是一种复合动词,只能作为一个造句单位,构成句子成分,不该分成两个成分”。到了晚年,吕先生在他的《现代汉语语法(提纲)》中(生前未正式发表,收入《吕叔湘全集》③吕叔湘:《吕叔湘全集》(第13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更是完全抛弃“补语”的国内通行含义、重新将“补语”用于类似补足语的含义,这实际上已经回归补足语的时代。
在补语被确认为六大成分之一的大势中,黎、吕两位学者始终未“重用”通行的补语概念,而钟情“补足语”或等同于补足语的“补语”,大概都是看到了“补语”概念的弊端和补足语概念的必要。
“补足语”在当代语言学兴起后重新成为常用语法术语,其所指虽然与英语传统语法和黎氏所指有所参差,但其共同点都是指动词特定小类所要求的以名词性成分为原型的句法成分,与内地通行的补语含意无关。当代语言学尤其是形式语法所指的补足语,是动词、介词等所支配的论元性成分,主要指的是直接宾语或间接宾语,包括宾语从句。例如Give him a book中的a book和him都是give的补足语,on the table中the table是on的补足语。当代句法学有个常用概念comp lementizer,直译是“补足语化标记”,实际指的就是用来引出宾语从句的关系代词一类成分,其作用就是让一个小句能充当宾语等论元成分,即补足语化,所以可以简译为“标句词”。在生成语法中,就指小句做动词介词所支配的宾语类论元;在类型学描写中,则泛指小句做动词的主语、宾语等各种论元成分。如:
(1)That Eliot entered the room annoyed Floyd.
(2)Zeke remembered that Nell lef t.④Shopen,Timothy: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2nd Editio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Vol.2:p.52.
斜体部分就是补足语化(即充当主宾语)的小句,这两个小句分别是句子谓语动词的补足语,而that就是使之能充当主宾语的语法标记,即标句词。
标句词这个概念在生成语法中经过理论再发展,成为高于VP(动词短语)和IP(屈折短语)的CP(标句词短语comp lementizer phrase)的核心。即使是一个母句,也被假设有一个形式为零的标明句子功能的标句词,使得CP成为句子最高层结构的代称。而一般的名词性宾语,因为无需标记,所以不会需要comp lementizer,这使得这个词只用于标注小句作宾语,所以有标句词的译法。
换言之,complement在当代语言中主要指宾语,同样译为complement的“补语”则主要指动词后的一切非宾语,就排斥宾语。两种含义完全对立。
有些译者、作者没有刻意去分辨上述含义的根本对立,在翻译外文语言学文献或借用现代语言学观念时,就照着字面将comp lement译为补语, comp lementization称为补语化(例如黄成龙⑤黄成龙:《蒲溪羌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第209页。,指的就是小句做宾语),标句词comp lementizer译为“补语化标记”,让国内只熟悉六大成分的读者很容易误解为与通行的补语有关。可谓差以毫厘、失之千里。其根本原因是汉语学界将一个缺乏严格定义的“补语”概念用comp lement来翻译。
此外,在当代语言学中,形容词、名词如果具有所支配的成分(要求其同现的成分),也都叫补足语,例如Iam fond of classic m usic(我喜爱古典音乐)中的of classic m usic就是形容词fond的补足语(classic music则是of的补足语)。It is not the case that he likes this(并不是他喜欢这个)中that从句就是名词case的补足语。汉语“我们去杭州旅游的计划”中的“我们去杭州旅游”是“计划”的补足语从句,区别于关系从句,同样,“主队必胜的信念”中“主队必胜”是“信念”的补足语从句。换言之,补足语是主语、宾语等的上位词,是特定动词(或形容词、名词)小类所要求的结构完形成分。黎氏语法术语所说的补足语,是传统语法所说的补足语,在当代语言学中,虽然不是其最原型的补足语——宾语,但大多仍属于某种补足语,例如系词的补足语。它们与当代其他补足语的共同点在于都是由特定动词小类所支配的成分。吕叔湘晚年《现代汉语语法(提纲)》所说的“补语”,则更接近当代语言学补足语的概念。而国内通行的汉语语法所说的“补语”,则大部分不属于当代语言学所说的补足语,而属于状语性的修饰成分(只是后置于谓语核心)或次级谓语的成分(参看金立鑫①金立鑫:《解决汉语补语问题的一个可行性方案》,《中国语文》,2009年第5期。)。
下面来看一些当代中文语言学文献所用的“补足语”的用例:
石定栩②石定栩:《乔姆斯基的形式句法》,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84页。:上面说的是核心词如何向补足语分配格,适用于动词宾语、形容词宾语以及介词宾语取得格的情况。该书术语索引列明“补足语”对应comp lement。这里所说的“补足语”,就指动词、形容词、介词所带的宾语。而形容词所带“宾语”实际大多仍要通过介词实现,如上举fond之例。
沈阳、何元建、顾阳在《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中说③沈阳、何元建、顾阳:《生成语法理论与汉语语法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11页。:某一论元必须指派至某一结构位置,如(7)所示,处所论元在动词的限定语位,而客事论元在动词的补足语位。这里的例(7)句是“屋里跑进来一只狗”,占据“补足语位”的“客事论元”就是指句中的存现宾语“一条狗”。
同上书(P406)以(41a)(“我们叫他老汪”)为例:“他”和“老汪”并不是两个论元,而是指同一个被称为“老汪”的人,所以动词“叫”只是一个单宾动词,“他”为宾语名词组,“老汪”是谓语动词“叫”的补足语,与“叫”共同构成复合谓语(comp lex p redicate)。此处将“补足语”与宾语对立,否认补足语的论元性,与上引同书411页将论元与补足语联系的用法并不一致。这与该书由几位作者合著有关,不同作者所用术语并未完全统一。但是,此处“补足语”的用法,恰好与黎氏术语“补足语”的含义更加一致,而与国内通行的“补语”概念无关,也没有其他通行术语可以表达。
以上这些“补足语”如果直接由英文comp lement翻译过来,有时就被译为“补语”,从而导致国内读者的误解。
由此可见,当代语言学在进行语法分析时,时常需要用到补足语的概念,虽然其含义在宽严程度上仍有些参差,但核心意义都是指动词等特定词语类别所支配或要求同现的成分,以名词性成分为典型(及物动词宾语后的补足语则为谓语性的),其他成分如小句等充当补足语则需要标句词等标记的帮助。黎氏术语中的补足语与当代语言学的补足语,虽然所指也有点参差,但具有同样的渊源,体现了术语的理论生命力。而通行汉语语法术语系统取消了补足语的概念,就无法表达上述论著所需要阐述的现象和规则。同样译为comp lement的“补语”一词对此并无用处。这大概也是吕先生晚年要将“补语”一词重新用于“补足语”含义的原因。
二、实体词的“位”
黎氏语法体系继承发展《马氏文通》“次”的概念,为实体词(名词性词类)设立了七个位:主位、呼位、宾位、副位、补位、领位、同位。表面上看,“位”由西方语言的“格”的概念类比而来,因而被指为在无格的语言中没有必要,是多余的概念。评论者多认为汉语由词类成分直接充当句法成分,在词类概念和句法成分概念之间不需要插入“位”这一类中介概念。如邵敬敏在评述《新著》的七位说时认为:
其实,不论是“格”还是“位”、“次”,对缺乏形态变化的汉语来说,显然是不很必要的。④邵敬敏:《汉语语法学史稿》,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89页。陈昌来在评论《新著》时也说:
“位”重在说明实体词在用法上的多样性或变化,是为了分析句子设立的一套辅助术语,其实多与句子成分重复,汉语的名代词无格的变化,同一个词处于不同位置并无形式上的标志,因而设立“位”的概念并无多大必要。①陈昌来:《二十世纪的汉语语法学》,太原:书海出版社,2002年版,第72页。
实际上,除了《文通》的“次/词”二元系统(主次、宾次、正次、偏次和起词、止词、转词、语词)和黎先生的“位/语”二元系统(主位、宾位等和主语、宾语等),早期其他学者的语法体系也在句法中设立二元或三元系统,如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有“词/语”二元系统(起词、止词、补词等和主语、宾语、加语、端语等),王力先生借鉴“三品说”的“语/位/品”的三元系统(主位、目的位、关系位;主语、谓语等;首品、次品、末品)。这些多元系统难道都只是简单摹仿形态的格而没有用处吗?黎先生并非不知道汉语没有形态上的“格”,但他直到后期仍坚持设立名词七位,是因为看到了用这个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的中介概念有益于说明很多语法规则。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语法学各家理论,都在词类和句法成分之间设立一个中介层次,称为论元、配价、格等等,不仅形态语言需要,而且非形态型语言同样需要。这是因为,作为句子核心的动词,常根据小类的属性而有相当稳定的同现关系模式,如论元结构等。单及物结构、双及物结构、作格动词(非宾格动词)结构、宾格动词(非作格动词)结构,等等,都是这种模式的具体表现形式,而同一模式的表层句法实现却有多种可能,须在更大的层面上选择。例如,“洗”这样一个单及物结构,可以形成动宾句(他洗了衣服)、把字处置句(他把衣服洗了)、受事话题句(衣服他洗了)、被动句(衣服被他洗了)、宾语省略句(衣服呢?——他洗了)等多种形式,在种种关系中,“洗”和“衣服”的语义关系并未改变。有些语法规则,有些词语的句法功能,只要求在论元结构这一类中间层次上叙述,不需要一一具体化为更细分的句法实现层次,这时,中介层次的概念就很重要。例如,指出“洗”这样一个动词要带受事论元/宾位,比指出它要带宾语更加准确,因为受事论元/宾位可以实现为宾语,也可以实现为宾语以外的成分,反而是说它要求有一个词充当宾语并不准确,因为该受事成分并不一定充当宾语。用黎氏术语来说,该动词需要由一个名词性成分“在宾位”。在黎氏语法体系中,“在宾位”的典型表现是做宾语,但不是只能做宾语,也可能转作其他句法成分,黎先生称为“变式的宾位”。在以七位为纲的《比较文法》中,第三章“宾位”的第三节就是“变式的宾位”,里面总结了“宾在动前”、“宾在句首”、“反宾为主”三种情况,这里的“宾”,指的都是宾位,而不是宾语。看黎先生的论述:
“(一)宾在动前 宾位倒置在外动词前者,其法又有三:(甲)特介提宾;宾在动前;反宾为主。
(甲)特介提宾——用特别介词提宾位与外动词前者(引按:指“把”字处置句等)……”②黎锦熙:《比较文法》,上海: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19页。
这里黎先生明确说倒置、提前的是“宾位”,而不是宾语。“宾位”在此的用处是很明显的。假如说“把”等介词提的是宾语,则介词的性质与宾语的性质是矛盾的,带了介词就是状语性成分而不再是宾语性成分。提的是宾位,就没有这个矛盾,宾位置于介词支配下,句法上就可以是状语了。在以“位”为纲的《比较语法》一书中,对各个位的说明,基本上都是讲变式的位远远多于讲常式的位,因为常式虽然是更常规的现象,但它能够用简单的话语说明,不像变式需要很多具体规则来控制。变式的大量存在,正说明位和句法位置的关系不是简单对应的,更不是重复的。后来的一些语法学体系,取消了位的层次,直接由词类通到句法成分,并且纯粹根据语序定成分,取消了提宾之类的说法,看起来固然是简洁了,但却在系统上割裂了一般动宾句和处置式、受事话题句等的内在联系,难以区分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句子和没有内在联系的不同句子。所以,引进当代语言学后,重新设立了论元结构/配价之类层次,实际上就是在一定意义上回归到“位”这种中介层次。我们曾经在分析双及物结构的时候指出(刘丹青③刘丹青:《汉语给予类双及物结构的类型学研究》,《中国语文》,2001年第5期。),双及物结构是某些动词所要求的一种论元结构,而双宾语结构是一种句法结构,双及物结构可以实现为双宾语结构,也可以实现为其他句法结构。实际上,也可以用“位”的观念来阐述,某些动词是双宾位动词,他们可以实现为双宾语结构,如“送他一本书”,但也可以实现为只有一个宾语的其他句法结构,如“送一本书给他”。
“位”的理论一方面便于揭示同在一位的成分做不同句法成分的情况,并有“常”和“变”之别;另一方面,也能揭示同一个句法成分容纳不同位成分的情况,也有常和变的区别。例如,宾语是一种句法位置,其典型的情况是容纳宾位名词。但是,也有些情况下宾语位置上出现的不是宾位功能的成分,而是其他成分,例如“副位”。《新著》97页在举到“在、往、到、上、下、出、入、进、过、回、离”等动词(后来学界称为“趋向动词”者)时,指出,“这种内动词,叫做关系内动词,常带副词性的宾语,即副位”。
也就是说,这些动词所带的成分,句法上是宾语,而位次上是“副位”,区别于作为宾语典型的宾位宾语。如果取消“位”的层次,我们就只能简单地将这些动词所带的成分称为宾语,无法揭示宾语和宾语之间的重要差别。例如,如该书98页[注3]所示,这类动词可以用在另一个动词之后起“介出副位”的“应看作‘介词’”的作用,如“送进一个光明、空阔、透气的地方”、“投入别一个世界了”,“副位”一说,实际上提醒人们注意宾语和副位宾语的区别。后者不表示真正的受事,却表示空间趋向范畴,其动词有类似介词的作用。而其他的普通宾位并没有这样的语义和句法属性。
由此可见,黎氏术语中的“位”,像当代语言学中的“论元”(argument)、“加接语”(adjunct)等概念一样,其实质就是词类和句法层次之间的中介层次,其必要性在黎氏语法学著作中和在当代语法学理论中都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决不是无事生非造出的多余概念。虽然“位”作为术语不一定要在当代复生,但是它实际上已托生在“论元”、“配价”这类新概念中获得了重生。
三、代名词、指示形容词等等
代名词,是p ronoun的准确翻译,它有稳定的含义,就是能代替名词的词,典型的代名词就是人称代词,如“你、我、他、她、你们、他们”等。而后来通行的“代词”,却包括了各种具有替代作用的词,其词性分别可归入名词、形容词、副词等,代词不再有真正的词性含义,它是这些词共同的语用功能而非句法功能的汇合,其立类的依据,不像其他词类那样是根据句法功能,而是根据语用功能,这就使它在句法分析中的作用不可避免地受限。
在国际语法学文献中,p ronoun至今不能泛指非名词性的代替性词语,需要泛指不同词性的替代形式时,有些当代语言学文献会用p ro-form(意为“替代形式”)来表示,如Shopen就用Pronouns and other p ro-form s(代名词和其他代词形式)作为节名①Shopen,Timothy: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Vol.1:§2.1.。而国内在翻译p ronoun时往往就用“代词”一词,其实并不准确,应当用“代名词”,因为适合p ronoun的规则未必适合非名词性的代词。例如说英语的主语可以由名词和p ronouns担任,这个p ronouns就不包括形容词性、副词性的代词such,so,there和疑问代词中的how,w here。在描写汉语时,有时也是“代名词”比“代词”更加准确,因为某些位置例如领属定语,就只允许名词性成分充当,则只有代名词才适合,其他词性的代词并不合适。再如,在“代名词可以加‘的’做定语”这一条规则中,“代名词”也不能换用通常所用“代词”,因为指示词“这、那、这么、那么”和疑问代词“哪”等都不能加“的”。汉语可以说“我的书、他们的书”,但是不能说“这的书、那的书”等。“这样的书、那样的书”可以说,但是这不是领属结构,“的”与形容词后的“的”地位相当。
与此紧密相关的就是“指示形容词”。现在通行术语将指示词统归代词大类,这在普通话内部也只是勉强可行,实际上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有些指示词相当于形容词或副词,如“这/那样”、“这/那么”,不是真正的p ronoun(代名词)。即使是相当于地点名词的指示词,其词类功能也不完全等同于普通的名词,它们比一般名词更容易做状语,如“我这儿忙着呢”。从跨方言跨语言视角看,将指示词统统称为指示代词会遇到更大的问题。在普通话和英语中,指示词恰好是具有名词性——能独立担当论元的词类,如“这是钢笔”、That is a book(那是一本书)、I like this(我喜欢这个)。而在吴语、粤语等很多南方方言中,相当于“这、那”的基本指示词是粘着成分,不具备名词性,只能作为定语去限定量词或名词,甚至只能限定量词而不能限定名词。试看下列苏州吴语和广州粤语的例子:
(3)a.〈苏州〉埃*(只)是酒杯,喂*(只)是茶杯‘这只是酒杯,那只是茶杯’
b.〈苏州〉埃*(只)杯子是酒杯,喂*(只)杯子是茶杯。
c.〈苏州〉我拿仔埃*(只),弗是喂*(只)。
(4)a.〈广州〉呢*(只)係酒杯,嗰*(只)係茶杯。‘这只是酒杯,那只是茶杯’
b.〈广州〉呢*(只)杯係酒杯,嗰*(只)杯係茶杯。
c.〈广州〉我攞咗呢*(只),唔係嗰*(只)。
括号外打星号表示括号内的成分不能省略。以上例句显示,苏州话指示词“埃、喂”和广州话指示词“呢、嗰”无论是做主语、限定名词还是做宾语,都离不开量词。指示词本身既没有单独做论元的功能,也没有单独限制名词的作用。其惟一的直接组合的句法功能就是限制量词,其他功能都是由指示词和量词的组合来发挥的。这样的指示词,根本只指不代,不能代替任何名词独立充当论元,不具有任何p ronoun的功能,无论在语用上还是句法上都称不上代词。既然其惟一的功能就是做定语,称为指示形容词很是准确。而普通话中的“这”、“那”类指示词,因为可以做名词用,所以《新著》放在“指示代名词”里头。而只能做状语的指示词,则适合称为指示副词。黎氏术语中虽然没有“指示副词”一名,但实际上将它们划归“表样式”的副词,如“如此、这么、这样、那么”等①黎锦熙:《新著国语文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第134页。。当然,从系统性上来说,还是归为“指示副词”为好,分别与“指示形容词”及“疑问副词”相配。
笼统的“指示代词”的说法,掩盖了指示词的词性多样性和基本功能。所以在Com rie与Smith (1977)的语法调查问卷中,仍然使用了“指示‘形容词’”这样的术语(§1.2.5.2.5,见刘丹青②刘丹青:《语法调查研究手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 Shopen则认为传统的指示形容词现在可以称为指示修饰词(demonstrative modifier)③④ Shopen,Timothy: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2nd Edi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Vol.2:p.162.。总之,对于有指示(尤其是直指)功能的词,可以用“指示词”(demonstratives)来概括,其中的基本指示词可以根据是否能代替名词单做论元、是否能限定名词这两方面而细分为几类:
1.指示代名词(demonstrative p ronouns):只能单独充当论元,不能限定名词。例如Awa Pit语(厄瓜多尔和哥伦比亚边境地区)就有不能限定名词的独立指示词ana(这)、suna(那)(Shopen④)。
2.指示形容词(demonstrative adjective或demonstrative modifier),只能限定名词,不能单独充当论元,如Awa Pit语中的an(这)、sun(那),苏州吴语、广州粤语的上引指示词。
3.指示代名词兼指示形容词(简称指示词),如普通话的“这”、“那”和英语的this,that。假如有其他功能的指示词,则还有指示时地代词、指示副词等。
对于疑问代词,黎氏语法学也是按此方法分类的,有:
疑问代名词:“谁”、“什么”等
疑问形容词:“什么”、“何”等
疑问副词:“几时”、“多早晚”、“多久”、“多”等
这与指示词的内部分类是一致的。国际当代语言学也不用笼统的interrogative p ronoun(疑问代名词)来概括这一类疑问词,而借用英语此类词的开头字母w h(w ho,w hat,w here,w hich,w hen)称为W h-words,就是为了避免词性不同的疑问代词使用单一词性的术语。当然,假如我们用“代词”来代表广义的p ro-fo rm,则“疑问代词”仍可以保留作为一个统称,但在叙述具体的语法规则时,还是不妨使用疑问代名词、疑问形容词、疑问副词这样的黎氏术语,以使规则的表述更加精确。
四、小结及余论
黎氏语法体系中的一些术语在经历了多年沉寂之后居然在语法研究快速发展的今天重显学术价值和魅力。我们的思考先要从这些术语的沉寂开始。
学界对黎氏语法的批评集中在其语法体系对英语语法的模仿,而作为对这种模仿的反动,就是努力探索汉语自身的特点。正是在这种探索中,人们更倾向选择或创造汉语自身的一些术语,同时抛弃一些从英语等国外语法理论中借鉴过来的术语。富有汉语特色含意的补语、代词,以及处置式、连动式、兼语式、主谓谓语句,等等,还有把“系词+表语”结构分析成动宾结构之类,都是这类有汉语特色的术语和概念系统。与此同时,黎氏术语中借鉴西方而造的一些术语受到了冷落。
这一阶段的探索和新概念的创造,大大推进了汉语语法的研究,尤其是汉语语法事实和特点的挖掘获得了长足的进展,也正好符合结构主义阶段对语种个性的强调。但是,这一阶段的汉语研究也有其局限:基本局限在汉语内部,很少有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深入比较,甚至缺少古今汉语和汉语方言之间的比较,更缺少与国际理论新进展的沟通,尤其对大规模跨语言比较的语言共性和类型研究了解不多。
而黎氏语法体系的形成发展,远不只是一种模仿,而是始终伴随着一种很强的语言对比意识,这与跨语言比较和语言共性的探求是更加吻合的思路。如黎先生的实体词七位说,正是在《比较文法》这一古今中外对比语言学力作中得到了更系统深入的阐发,也正是在这种比较中,黎氏语法术语的价值得到了更好的展示。设想假如不用七位说,而采用句法成分的单元说,《比较文法》很难取得对比研究的如此广度和深度。黎氏术语在其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而黎锦熙、刘世儒合著的《汉语语法教材》继承了这种古今中外对比的眼光。虽然面对批评,黎先生适度调整了自己的体系,在新版《新著国语文法》的自我批注中也坦率批评了早期版本某些模仿英语之处,但是对于本文所分析的这些黎氏语法术语,黎先生在后期著作中仍然坚守不弃,体现了一种学术的自信。历史也证明了这种自信背后的学术力量。
那些为汉语专造的术语,有的已被证明体现了汉语某些重要的类型特征,非常必要,如“连动式、兼语式”等(参看高增霞①高增霞:《现代汉语连动式的语法化视角》,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2006年版。),有的可以引导我们对其做进一步的分析解构;有可能需要给出更合理的科学定位,如“主谓谓语句”等;而另外有一些术语,则逐渐显示出难以与其他语言沟通比较、甚至无法与古汉语和汉语方言事实沟通比较的局限(参看刘丹青②③刘丹青:《从所谓“补语”谈古代汉语语法学体系的参照系》,《汉语史学报》,2005年第5期,第37-49页。)。某些术语对汉语的适应,有时也只表现在对特定历史时期对汉语认识水平的适应。随着汉语研究走向深入、走向理论、走向国际,它们的不适应性也逐渐表现出来。在这个时候,重温黎氏术语的学术价值及其深层原因,继承发扬黎锦熙先生语法学说的科学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责任编辑 宋媛 责任校对 宋媛 刘伟)
Some Grammatical Terms Used by L IJin-xi
L IU Dan-qing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732,China)
The paper review s some of L IJinxi’s grammatical term s that have not been used fo r long,but recently reappeared and played an irrep laceable role.“Complement”,for examp le,asan important term in contemporary linguistics,isan syntactic element that includes object;it hasmuch similarity w ith the same term used by L IJinxi.Nevertheless,the currently existing concep tof“comp lement”in the Chinese Grammar,though translated from English,is not a general grammatical concep t,and can not rep lace the role of the“comp lement”mentioned above.The“apposition”of nouns is the intermediate-level between words and syntactic components.It is similar to the intermediate-level term“argument”in contempo rary linguistics,and contributes to describing the rules of grammar.It is not the so-called“unnecessary level”.Terms such as“p ronoun”and“demonstrative adjective”have specific p roperties of the classification of words;that is,they are more convenient than simply theonly term“p ronoun”in the general sense w hen elabo rating the rulesof grammar.These grammatical terms used by Li Jinxi are mo re suitable for cross-linguistic comparison and the research of language universals than some later-coming terms that havemo r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L IJin-xi’s grammatical term s;complement;apposition of nouns;p ronoun;demonstrative adjective
H146
A
1002-0209(2010)05-0059-07
2010-06-24
刘丹青,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