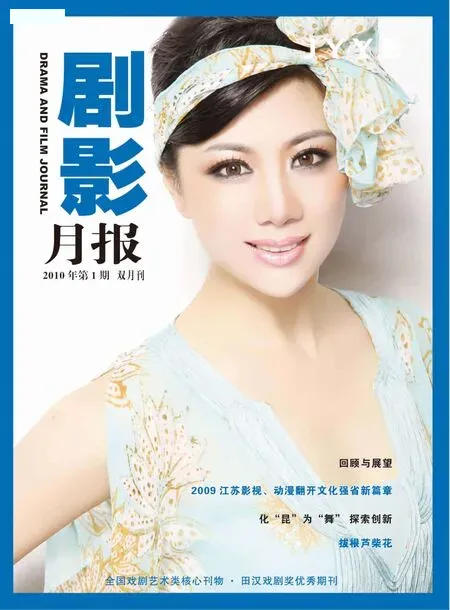戏剧创作中的“悬念与惊奇”
2010-11-16夏海滨
■夏海滨
阿契尔曾提出戏剧理论的矛盾在于:“一方面剧作者要使写出来的剧本久演不衰、家喻户晓,因而任何一场演出中的颇多观众会事先知道剧情;而另一方面又要考虑如何才能唤起和保持第一次看戏、对剧情毫无所知的人会有观赏兴趣。”看起来,这似乎是一种矛盾,而且事实上观众的“观赏兴趣”也是广泛多样,尤其是在后现代文化的今天,戏剧艺术拥有越来越多的观众,他们的喜好和欣赏趣味也是千奇百怪、大相径庭。有人喜欢悲剧、有人喜欢喜剧,更有人偏爱流行时尚的情节剧。那么剧作者面对观众如此广泛多样的欣赏趣味最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引发、调动和保持观众看戏时的“兴趣”?于是,“戏剧悬念”这一问题被提出来了。
所谓“悬念”,是根据观众看戏时情绪需要得到伸展的心理特点,编剧或导演对剧情作悬而未决和结局难料的安排,以引起大家对剧中人物的命运、情节的发展变化的一种迫切期待心情。它是戏剧创作中使情节引人入胜,维持并不断增强观众兴趣的一种主要手法。“悬念”理论,源自心理学中人们由持续性的疑虑不安而产生的期待心理。在西方编剧理论中最早提及是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在中国戏曲理论著作中虽无悬念一词,但李渔在《闲情偶寄》词曲部格局一章中提出的有关“收煞”的要求,内涵与悬念基本相似,主张“令人揣摩下文,不知此事如何结果”。综观各艺术门类,小说、电影、故事、评书、绘画也都是各有悬念。如我国古典长篇小说中,几乎每一回的结尾都要重复这样的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为了这句话具有实实在在的作用,作者常在这句话之前来一个惊人伏笔,使读者看到此处不忍释卷,急欲知道后事如何,这也就是造成悬念。悬念的内容丰富多样,造成的效果也是多样多种。诚如传统戏曲可以依靠唱腔、武功吸引观众,歌剧、音乐剧可以用优美的音乐和精彩的场面羸得观赏兴趣,由此,与剧本的戏剧性和思想意义恰当适合的悬念在话剧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如何制造悬念,如何保持悬念,让观众由始至终处于有所期待的心情之中是剧作者应该掌握的一种基本技巧。
莎士比亚的《奥赛罗》第一幕的结尾处是埃古的一段独白:“……我恨那摩尔人,有人说他和我的妻子私通,我不知道这句话是真是假,可是在这种事情上,即使不过是嫌疑,我也要把他当作实有其事一样看待。凯西奥是一个俊美的男子;让我想想看:夺到他的位置,实现我的一举两得的阴谋;怎么?怎么?让我看:等过了一些时候,在奥赛罗的耳边捏造一些鬼话,让他跟他的妻子看上去太亲热了。我可以把他像一头驴子一般牵着鼻子跑。有了,我的计策已经产生……”埃古把自己将要施展的诡计在这里合盘托出,由此观众的期待也因此产生。埃古将怎样行动?奥赛罗会不会落入这个阴谋家挖掘的陷井?奥赛罗、苔丝德蒙娜的命运如何?—这将是全剧的总悬念。可是,如果让埃古把这些见不得人的诡计藏于心间,是否观众会在悲剧突发时更感到意外呢?由此,“惊奇”这一问题被提了出来。贝克在《戏剧技巧》中认为,使人“惊奇”并不是真正的戏剧悬念。他引用莱辛的一段话给“悬念”和“惊奇”划出了界限。“……把一个重大事件向观众隐瞒起来,直到它出现为止,如果这样做有过一次是得到效果的,那么,就有十次或者十次以上是适得其反。利用对观众保守秘密,剧作者可以收到短暂的惊奇效果;但是如果他不把惊奇看成秘密,那么他使得我们很久地忧虑不安的程度该是多么大!如果我期待着这个打击,亲眼看见暴风雨即将到来的咄咄逼人之势。并在我心里和剧中人心里盘旋一个相当时间,那该如何有力呢?依我之见,剧中人物不必彼此了解这个情势,而观众则需要了解一切……假使人物们的情况没有交待出来,观众就不会比剧中人更生动地对剧中行动发生兴趣……”同样,阿契尔也反对剧作者把一切都瞒住观众。他认为,剧场在实质上是这样一个地方:在这里,我们有权解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束缚,带着微笑或者衔着眼泪,来观赏我们邻人们的盲目的游戏。由此可以这么说,在“吃惊”的运用上,剧作者几乎完全依靠戏剧情节取胜;“悬念”则是用剧中人物的性格刻划来使戏剧情节复杂多变。换言之,“吃惊”是由戏剧情节造成的,而“悬念”是用人物性格产生的。中国戏曲的很多优秀剧目,大都不依靠对观众保密去取得戏剧效果,而是善于用简练的方法把人物身份、面目以及他们要做什么事、潜在的意图等等向观众交待清楚,而剧中人物毫不知情。这样,就能迅速造成悬念,引起观众兴趣,因而常演不衰、源远流长。昆曲剧本《十五贯》在运用戏剧悬念方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在这个剧本中,冲突内容的明确、全剧悬念的形成和剧作中心思想的揭示,三者有机统一。在剧本前几场,先是屠户尤葫芦借钱而归,酒醉之中和养女开了一句玩笑就睡去了,养女视戏言为真,深夜出走投奔姨母;娄阿鼠潜入行窃,并将尤杀死;邻人发现,追赶苏素娟时,正碰上苏与熊友兰结伴同行,且在熊身上搜得十五贯钱,便把苏、熊扭送官府;过于执主观判案,造成冤狱;况钟监斩时发现冤情……至此,戏剧冲突明确,全剧悬念形成,观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况钟怎样查明真相、捕获真凶、平反冤狱,而全剧反对主观主义、提倡调查研究的思想主题正寄寓在这个行动过程之中。反之,如若改编者在“谁是杀人犯”这个基点上制造悬念,用凶杀疑团去吸引观众的注意,可能会使剧情更具传奇色彩,但也背离了原剧的主题思想,降低了剧本的审美格调。
话剧因其表现手法的局限性,使剧作者要迅速明确冲突、造成悬念,要比戏曲作者困难不少。正因如此,不少话剧剧本为了必要的交待,出场人物东拉西扯,迟迟不能明确冲突,悬念不能集中,使观众产生厌烦。在这里,我们不妨以《雷雨》为例。这出戏人物不多,但人物关系相当复杂,且时间跨度也很大。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中确立全剧的戏剧冲突?剧作家曹禺在此方面很见工力,作为全剧总悬念的关键之处周朴园和鲁侍萍的关系,剧作家并没有就此开场,而是从容不迫、有条不紊地交待、展开其他人物的关系,造成一个又一个悬念;并在交待、展开这些错综的人物关系时,为推出周、鲁关系作好准备,为造成全剧的总悬念酝酿外在、内在的力量。在戏剧运动过程中,剧作家在动作中交待剧情,开场后迅速引出悬念,却又不急于把悬念集中;人物关系在动作中逐渐展现,多条线索逐渐扭结,悬念也逐渐凝聚,终于集成焦点,每个场面都有各自的悬念,然后又把各个分悬念聚焦成总悬念,让它愈来愈紧张,直至延缓到高潮。从这个意义上说,悬念是一部剧作中的“指路标”。剧作家的才华在于,不仅要用这块“指路标”吸引广大观众的注意力,激发观众的兴趣;而且能够用它诱导观众沿着自己预定的方向一步步走下去,直到剧本的结局。
总起说来,善于营造正确的悬念,善于让观众自始至终保持强烈的观赏兴趣,是剧作者应该掌握的一种基本技巧,至于在剧本创作过程中出现的“悬念等同与惊奇”的错误观点更是剧作者应该予以重视的问题。诚如阿契尔所说:“好奇心是一种偶然的美味,它只能保持一个晚上的吸引力;戏剧的根本的、恒久不变的乐趣在于预知。对戏中的人物而言,观众就像是知道一切过去和未来的上帝那样。我们以清澈的目光注视着那些愚昧的凡人在盲目地探寻幸福,我们为他们的挫折、他们的疏忽、他们的无益追求、枉自欢喜和无谓惊恐而莞尔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