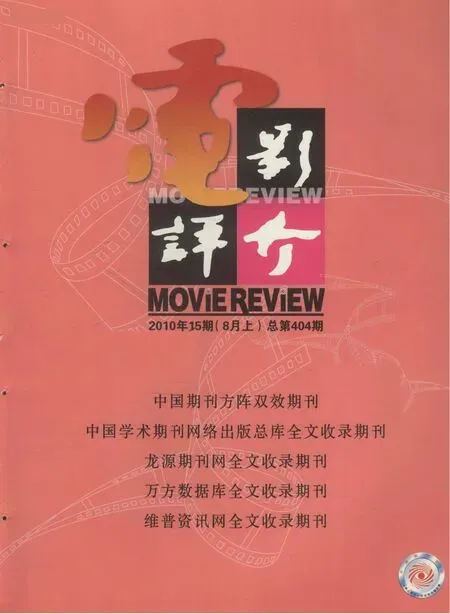从“诗言志”说谈“诗缘情”的兴起
2010-11-16侯卓均
《尚书•尧典》最早提出“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提出了“诗言志”的命题。《诗大序》在倡导儒家的“风教”之后,对“诗言志”作了如下诠释:“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些论述概括了先秦以来儒家对诗的本质的基本认识。
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序》将古人四个批评意念(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分为纲领和细目两类,认为纲领是“告诉人如何理解诗,如何受用诗”,即关涉何谓诗歌的根本性观念,细目是关于理解诗歌方法论的,是隶属于纲领的,他说“诗言志”和“诗教”是纲领,其中“诗言志”产生最早,更是“开山的纲领”,“比兴”是介于纲领和细目之间 ,“正变”是理解诗歌史的方法论。在诗论上,我们有三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即“诗言志”、“比兴”、“温柔敦厚”的诗教,后世论诗都以这三者为金科玉律,其中“诗言志”更是首要的纲领,重要性最突出。
“诗言志”是中国诗歌史上一种深刻、悠久的传统,朱自清《诗言志》一文由“献诗陈志”、“赋诗言志”、“教诗明志”、“作诗言志”四部分构成,他指出,“献诗陈志”是“由下而上”传述讽旨;“赋诗言志”是“在上位的人”互相称颂“表德”。这是诗乐不分家的时代,只着重听歌的人,只有诗,无诗人,也无“诗缘情”的意念。《诗经》所录原来全是乐歌,乐歌重在歌、颂,这也是春秋之前“诗以声为用”的原故所在,但“诗经”中也有很多非讽非颂的“缘情”之作,乐工保存它们只为了他们的声调,为了他们可以供歌唱,比如《左传》录声伯《梦歌》,便为记梦的预兆,如此说来,《诗经》对于促进“缘情”诗的发展也有十分积极的影响。
“教诗明志”是指统治者利用诗歌自上而下对人民实施教化,引导风俗,诗以读为主,以义为用,论诗之人渐渐意识到作诗人的存在,他们虽然还不承认“诗缘情”的价值,却已发现诗的这种作用。
“作诗言志”是诗人表达个人的想法,为自己写诗,然而言个人的穷通出处或人生义理,是“诗言志”的引申义,“诗言志”谓表现怀抱,其本义是讽颂,反映的是一种政教意识,与“文载道”是一致的。朱自清认为,“言志”跟“缘情”是不能混为一谈的,他所理解的“情”质地比较单纯,指感性的、个人的含义,这正是我们对“情”的狭隘理解的一面,诗人纯粹为表现个人感情、无关政治教化而创作诗歌,这才形成了“诗缘情”观念。他认为,中国诗歌史上“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是屈原为首的辞赋作者,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夫》,包括宋玉的《九辩》,以歌一己之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地位。汉兴以来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有讽谕之义”(《汉书.司马相如传赞》引杨雄语),能帮助发挥“缘情”作用,东汉赋才真正走上“屈原赋”之路,因为到东汉五言诗逐渐发达,抱这种态度的诗人更多,五言诗出于乐府诗,乐府诗“言志”的少,“缘情”的多,无论是“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还是建安诗人,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都促进了“缘情”诗的进展。沈约还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那却是“缘情”的赋,不能称为“言志”了。正始(魏齐王芳)时代,阮籍才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之外迫切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赋缘情而绮靡”这一新语,他还说“赋体物而浏亮”,“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有意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陆机的"缘情说"是艺术社会学走向审美心理学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先秦、两汉时期,经儒家规范了的"诗言志"占主导地位."诗缘情"出现后,它对儒家的"诗言志"是个巨大的挑战.言情文学日益兴起,促进了我国五言诗发展,他用“情”代替“志”,被认为是古代文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表达。
东晋的“玄言诗”抄袭《老》、《庄》文句,专歌咏人生义理,钻入狭隘“言志”犄角里,最终衰灭,出现陶渊明、谢灵运等兼包“缘情”、“示志”两义的作品,不够他们志在田园、山水之间,更趋向歌咏人生的“缘情”之作。
六朝人论诗,少直用“言志”这词组,他们一方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一面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只得将“诗言志”这句话改头换面,来影射“诗缘情”那句话,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其中,“志动于中”就是《诗大序》的“情动于中”,“刚柔”是性,“喜愠”明说是情,一般的性情便是他所谓的“志”。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七情”便是“志”,“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缘情”作用也就包含在其中。钟嵘《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里说“性情”、“心灵”、“长歌骋情”、“幽居靡闷”是“缘情”的表现,“陈诗展义”、“穷贱易安”是不忘传统“言志”的表现。
六朝诗学影响唐人,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诗大序》里“诗者,志之所在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几句时说:“此又解作诗所由。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万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这里“所以舒心之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言悦豫之志”、“忧愁之志”,都是“言志”和“缘情”两可含混的话。很多诗人在言个人的穷通出处或隐逸之志时,都似乎不离政教。“诗缘情”的传统掩在“言志”的影子里,不能出头露面。白居易继承了陈子昂的观点,加以总结和发展,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作为创作目的并付之于实践。他还认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对“情”作了精辟论述,提出了新的见解。
明代李贽提出要求恢复人的自由自觉本性的“童心说”,强调作家保持未被假道学熏染过的真见解、真感情和独立人格。公安派袁宏道从自然人性论出发,说诗“以抒发性灵为主”,强调自然天真和自然趣味。以锺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又紧接其后,崛起于江汉平原。他们在理论上接受了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口号,主张“有真情,方有真诗”(《钟谭二先生评明诗归》)。
直到清代,纪昀论诗,受陆机“缘情”影响,干脆提出“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钱谦益说:“诗者,志之所之也,陶冶性灵,流连景物,各言其所欲言者而已。如人之有眉目焉,或清而扬,或深而秀,分寸之间而标致各异。”他还将“志”、“气”、“情”并提,特别强调“志盈于情”。清代另一位诗论家叶燮认为诗离不开感情,是发愤之作,必须有所感而发,同时,对诗之“志”的理解是“才”、“识”、“胆”、“力”的载体。他还说:“惟不可名状之理,不可施见之事,不可径达之情,则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方为理至、事至、情至之语。”对“情”与“理”作了独到的分析。袁枚论诗以性灵为主,他将“诗缘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了。
实际上,这些“歌咏自己”的诗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讲述个人的穷通出处,其实都没有离开政教。这也引来了文学批评史上的“言志”和“言情”是否对立的争辩。杨明《言志与缘情辨》一文指出,言志与缘情二语无根本区别,言志也可以表现一般的生活意趣、抒发一般的想法怀抱,“志”、“情”都可以指所谓偏于理性的思想和偏于感性的情感,未必一定与政教有关,所以《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又说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吟咏情性”实质上是志、情并用,意味相同。
况且,检阅整个文学史,对“诗言志”中“志”的内涵的理解的主流实质上却是情志并重。从《毛诗序》到刘勰、孔颖达、白居易,直至清代的叶燮、王夫之,都是如此。他们强调诗歌既应反映现实,为教化服务,重视其社会作用;又应感物吟志,情物交融,突出其抒情性;情志并重,功利性与艺术性两不偏废。我想这应该是对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言志”、“缘情”两个主张的关系的更符合实际的说明,也是对“诗言志”和“诗缘情”说在本质上相生相依的最好注解。
[1]朱自清《诗言志辨》【M】湖南:凤凰出版社 邬国平讲评
[2]洪湛侯《诗经学史》(上下册)【M】北京: 中华书局 2004年9月
[3]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诗性特征研究》【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
[4]《诗“缘情”说的演进》乔武涛 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J】 2006,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