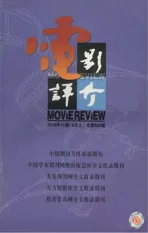浅析张艺谋电影《英雄》中的暴力美学运用
2010-11-16孙方园
“暴力美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表现手段和风格在近年来的很多国产商业大片中都有表现,而张艺谋的电影《英雄》更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在影视艺术中,所谓“暴力美学”,指的是对于暴力的表现不再执着于暴力内容本身的真实展现,而更讲究一种形式上的追求,也就是赋予暴力内容以形式的美感。
一、“暴力美学”溯源
“暴力美学”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出现的一个词汇,它起源于美国,但作为一个固有名词最初出现在对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的电影评论中。吴宇森的电影经常表现江湖恩怨、黑帮和警察之间的厮杀,但对这种场面的描写并不是充满血腥和残忍,而是常常代之以黑道英雄双手持枪,火焰中翻滚,教堂中的十字架,惊起的白鸽等意象加之以升格镜头的表现,使这些厮杀场面剥离了内容的血腥,具有了一种形式上的仪式感,充满了悲剧性的壮美色彩,令人动容。影评人将这种对暴力的形式美感的追求称之为“暴力美学”,后来这种电影的表现手法在很多导演的电影中得到运用,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特定的电影表现手段和风格。
二、《英雄》中“暴力美学”具体表现
电影《英雄》可以说是张艺谋的一个转型之作,与他前期粗犷豪放的《红高粱》和充满现实主义色彩的《秋菊打官司》相比,《英雄》无疑是一部完全商业化的电影。从影片故事内容上讲,它是空洞贫乏的,但它宏大的场景,精致的画面,强大的演员阵容,加上庞大的宣传攻势,使得这部影片赚取了巨额的票房,并开启了中国内地电影真正的商业大片时代。影片的故事是围绕“刺秦”展开的,有多段精彩的武打场面,但在表现这些场面时,影片并没有采取真实再现杀戮场景的方法,而是把这些原本残忍、血腥的场面处理得空灵、飘逸,富有诗情画意,充满了形式上的美感,使这些暴力场面不再让观众感到厌恶,而是具有了一种可观赏性。下面我们将选取一些典型打斗段落进行分析。
(一)无名战长空
在无名向秦王讲述的故事里,无名首战长空,将其杀死。这本是一场高手之间的决斗,但在影片的表现中我们感受不到惨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空灵的美感。两人的打斗伴着一位白发老人的琴声进行,紧和着琴声的节奏。两人在空中飞跃,交战。屋檐上的水滴缓缓落下,显出一种空灵、寂静。在双方对视的时候,交战则在意念中进行,这也体现出中国传统美学的虚实合一的境界。最后,无名一剑刺死长空,但镜头并没有渲染长空死时的痛苦,没有血流如注的表现,只有一把宝剑落地,溅起了地上的水珠。
这一段落,本应是生死对决,充满血腥和痛苦,可影片的处理方法让我们看到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美感,高手过招的空灵飘逸,这样就消解了观众对死亡的恐惧。
(二)飞雪战如月
同样是在无名向秦王讲述的故事里,飞雪因嫉妒杀死了残剑,如月为报残剑之仇与飞雪决战。决战在一片枫叶林进行,黄色的枫叶,飞雪,如月红色的长裙,色彩饱满,画面极富美感。风吹起满地的黄叶,漫天飞舞,两人不时腾空、飞起,红色的裙衫,黑色的长发也随风舞动。伴着柔美的音乐,这场决斗不像是充满恨意的决战,更像是两个女子的一场绝美的舞蹈。最后,如月中箭,影片依然没有正面表现她临时的惨状,而是表现了一把箭插在树上,落下一滴鲜红的如宝石般透亮的血珠。随后,以如月的视角表现了一片黄色的枫叶林慢慢被整片的鲜红浸透,我们可以清楚知道这是一种对死亡的描述,但感觉到的仍然是一种浓烈色彩带来的美感。
这一段落可以说是“暴力美学”的一个经典段落,这场厮杀,原本是充满仇恨和血腥的,但张艺谋用浓烈的色彩、黄叶、红衣等意象构建的影像留给我们最大的感受还是视觉上的美感冲击,充满飘逸、灵动之感。
(三)秦军攻赵之“书馆箭雨”
在无名的讲述中有一段秦军攻赵的场景,也是影片中暴力美学的典型场景。秦国军队的阵营用两种色彩表现,一种是鲜艳的红色,战士的红铠甲,飞舞的红色军旗,一种是灰色,战士的灰色铠甲,灰色的盾牌,这种大块的色彩表现军队,伴着整齐的“大风,大风”的口号,气势恢宏。赵国书馆内的颜色也是一片鲜艳的红色,红色的陈设,赵人红色的裙衫,极富视觉冲击力。随后,秦军箭阵齐发,密密麻麻,像密集的雨点落在书馆,射在赵人身上。赵人在白发老者的带领下,集体练习书法,纹丝不动。
这个场景表现的内容实质上是一场集体杀戮,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影片对相似场景的表现往往是惨绝人寰,百姓凄苦的喊叫,尸横遍野,血流成河,一片阴郁的色彩。但《英雄》中的处理方法并没有让我们感觉到这是一场残忍的杀戮,更像是一种集体的表演,极具形式化。我们在震撼于影像中场面的宏大之时,对惨遭屠杀的赵人并没有多少怜悯、同情之感。
由对以上几个段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电影《英雄》中,武打场面已在很大程度上剥离了内容的残忍和血腥,而形式作为一种外在的东西在影片中却成了这些场面的主角。《英雄》把暴力打斗场面处理成了一种空灵、飘逸,极富视觉美感的外在形式的展现,色彩浓烈的裙衫,整齐的军队,如画的风景,漫天的黄叶,这些完全形式化的意象成为吸引观众的主要手段。原本表现生死肉搏的视听符号已被转化成了极具形式美的表演,暴力打斗本身已被解构。
三、从《英雄》看“暴力美学”的审美特征
(一)形式之美超越暴力内容本身而成为主角
审美价值是所有艺术存在的前提与基础,电影艺术也不例外。“暴力美学”在电影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让暴力本身所具有的伤害性内容退居其后,首先让形式上的美感上前,成为主角,打动观众。事实上,形式之美也确实是最先作用于我们感官的审美要素。对形式之美的重视古来有之。古希腊的哲学家就把形式作为美与艺术的本质。中世纪的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认为,美首先在于形式,它是可感的,只涉及形式,无涉内容,不关联欲念,没有外在的实用目的。近代的克莱夫•贝尔认为,一切视觉艺术都必然具有某种共同性质,没有它,艺术就不称其为艺术,而艺术的这种“共同的性质”就是“有意味的形式”,真正的艺术在于创造这种“有意味的形式”。可见,“形式”是美和艺术的一个重要的要素。[1]电影中“暴力美学”的运用也在于把原本血腥暴力的影像转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之美。
电影《英雄》的所创造的镜头语言被有些学者称为“明信片美学”,意在指出影片形式的华美至极和内容的相对空洞。在《英雄》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剑客们过招的时候,动作和背景都是经过非常精心的设计,剑客们的服装或是艳丽的红,或是飘逸的白,或是纯粹的蓝,这些和红色的书馆、黄色的枫叶林和大漠、黑色的秦宫布置相配,在视觉上给我们以强烈的冲击。在人物的动作设计上,所有武打场面都被赋予了舞蹈般的空灵、优美的姿态。原本是一场场生死对决,在电影中观众感受到的却只是这些形式上的美感。
(二)摒弃社会道德价值判断,只做单纯的审美判断
暴力在现实生活中总是伴随着罪恶和伤害,是为法律和道德所不容的,在人们现实的价值判断中也是被否定的。但在影片《英雄》中,暴力场面本身的残酷性已被大大弱化,由于受到来自形式的视觉震撼,人们已经忽略了暴力内容本身的是非善恶,无法引起对施暴者的否定情绪和对弱者的同情,而只是单纯从外在形式上感受到一种暴力场面所带来的酣畅淋漓的美感。片中,原本代表战争的军队让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整齐的颜色,感受到的是一种恢宏的气势,我们在这时候就不会想到战争给当时百姓带来的苦难,而是感受到了一种美学上所谓的“崇高感”,大而壮美。在最有代表意义的“书馆箭雨”一段,秦军的万箭齐发,无数赵人被屠杀,其实是血淋淋的。但在观影的过程中,我们感受不到赵人的痛苦,心中也没有怜悯与同情,我们看到的只是赵人群体着红衣,在红色的书馆内写字,然后中箭倒下,仿佛机械一般。在这样的影像中,我们无法对屠杀者进行道德的批判,而只是感受到一种形式,夺取众多生命的箭,被赋予密集的雨点般的视觉感受,我们只是震撼于这样的视觉奇观,而无暇判断这实质上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屠杀。相比其它一些表现战争的电影,这就有很大的不同了。比如在美国电影《拯救大兵瑞恩》中,战争场面表现的极为真实和震撼,到处是尸横遍野,断掉的手臂,流出的内脏都被清晰地表现出来,令人触目惊心,观众对战争的恐惧和否定情绪也就由此被调动起来。《英雄》这样的处理方式弱化乃至取消了观众对暴力的合理性或者合法性的追问,就电影社会学和心理学来说,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把美学选择和道德判断还给观众的电影观。[2]
(三)充满东方审美意味的“诗意暴力美学”
“暴力美学”有很多种类型,有以香港导演吴宇森作品为代表的充满浪漫情怀的诗意暴力美学,以日本导演北野武作品为代表的残酷的静态暴力美学,有以美国导演昆汀•塔伦蒂诺作品为代表的戏谑的娱乐暴力美学。所谓的“诗意暴力美学”,指的是把暴力镜头诗化,用极端修饰的诗意化的动作和慢镜头来渲染暴力场面、营造悲情氛围,把血淋淋的暴力场面诗化为唯美的镜头语言,强调暴力的形式美而忽略内容,是一种极富东方韵味的艺术表现手法,《英雄》中的暴力美学就属于这类范畴。影片从中国的舞蹈和绘画中获得灵感,充满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所谓的虚实相生、天人合一的思想,无名与残剑在湖上一战,将这种诗意的东方美学体现到了极致。九寨沟如画的风景,侠客们飘逸的身姿,宝剑划过水面泛起的白色的水波,充满古韵的音乐,这场交战我们丝毫感受不到残忍和激烈,唯有一种空灵、宁静的东方审美体验。这就是“诗意暴力美学”的一种体现,这种浪漫手法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镜头的绚烂感,使观众的审美愉悦得以进一步地提高,另一方面,在这种整体充满浪漫诗意的氛围中,暴力的血腥性被大大冲淡。
结语
从对电影《英雄》“暴力美学”运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种对形式美的强调,其极致的镜头语言极大地愉悦了观众的感官,这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影片的内容是空洞的,其中的暴力场景往往为形式而形式,只是为了单纯地增加影片的视听美感,并没有和影片整体融为一体,没有很好地为影片内容服务,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1]刑鹏.暴力美学的审美价值[D].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2009.
[2]郝建.“暴力美学”的形式感营造及其心理机制和社会认识.北京电影学院学报[J],2005年0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