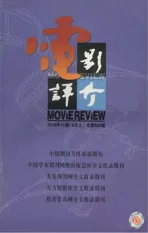论新世纪抗战题材电影中人物形象的重塑
2010-11-16宋娟
抗日战争因其在中国历史上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已成为中国电影中一个常写常新的题材。
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人获得了空前地解放,使这一时期抗战题材电影充斥着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电影以二元对立和夸张的艺术手法刻画智慧团结的抗日军民和凶狠残暴的日本敌人,利用镜头的俯仰来塑造人物形象。人物之间的关系壁垒分明——非友即敌,人物形象具有脸谱化和概念化的特征。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经典作品,成为后来此类作品模仿和超越的对象。
新世纪以来,由于人们的眼界进一步开阔,能够用更新的眼光和更平和的心态去审视抗日战争,这带来了抗战题材影片的新发展,在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有突出的表现。战争的双方——中国人,包括中国的军队和平民,和日本人都出现了新的特征,他们开始丰满起来,成为有血有肉的“人”,这是经典影视观照中所没有的。本文主要论述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在国民党、平民和日本人等人物的塑造上出现的新特点。
一、国民党:抗战硝烟中的忠魂
对于国民党人形象的塑造,一直是政治上的敏感问题,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控制。1949年,国民党败走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处于紧张的对峙状态。由于国家统治的需要,必须从根本上肃清国民党在一切领域的影响。在电影方面表现为竭力抹杀国民党在抗战中的作用, 所以从建国初到文革结束的银幕上只有共产党在敌后抗击日军的场景,没有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血战疆场的画面。因此,在经典战争影片中的国民党人被塑造成思想上顽固不化、在阵前不堪一击,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的形象。
《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和“一国两制”的提出,使台海关系出现了缓和的状况。新世纪以来,台海联系越加频繁,彼此了解加深,政治环境愈显宽松。近些年抗日战争的历史研究取得了巨大进步,史学上极大地肯定了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对抗战胜利作出的贡献。由此导致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出现了一批表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浴血奋战的影片,刻画了一系列国民党人的形象——上至高级统帅,下至普通士兵。影片努力淡化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图表现和还原历史真实。影片一改十七年电影对国民党军人的塑造,虽然在他们身上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在不完美中更突显了他们热血报国奋勇杀敌的精神和行动。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有志男儿,精忠报国;血性汉子,驰骋疆场,这在国民党人的身上得到了很好地体现。他们是抗战烽火中走出的民族英雄,是硝烟中出现的国家忠魂。“在战争影片的叙述范式中,个体生命的彼此对抗与较量,所隐喻象征的往往是某一团体、民族和国家的彼此对抗与较量”。[1]国民党人在抗战中的表现,是国民党政治集团在抗日战争中态度的最佳诠释。
《太行山上》与经典抗战片比较,它的重大突破就是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国民党将领形象:七七事变后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第一位军长——郝梦龄。“将有必死之心,士无偷生之意”,他破釜沉舟,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激昂的音乐声中步伐坚定地走向硝烟弥漫、战火燃烧和横尸遍野的战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身边的士兵一个个战死沙场,他也毫无退缩之意,最终战死疆场。“占领太行山,就是斩断了中国的脊梁”,虽然这场保卫太行的抗战失败了,但中华民族的脊梁未断,它就是那些像郝梦龄一样的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的中华儿女;还有主张积极抗日的国民党内民主派卫立煌、抵御外侮同时不忘反共的顽固派朱怀冰和在国民党、共产党和日本“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老谋深算的阎锡山。影片勾勒出了在民族告急、国家危急的关头国民党政治集团的浮世绘。
相较于《太行山上》刻画国民党内对待抗日不同态度的高级军官,《铁血》则反映了国民党从高级将帅到普通士兵在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上的表现,“气薄云天,血染厚土”,“青山埋忠骨”。影片着重刻画了国民党的一个普通士官——董监官的形象。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形象:在专业上军事技术过硬,在战场上作战英勇;对待部下,积极督促,为救助部下而战死沙场,但又有严重的军阀思想,用苛刻的方式要求战士附和服从自己;对待烟花女子桂花,侮辱调戏,但又有真情。影片在表现他具有军人的刚强之气的同时,不忘刻画他内心感情世界。有情有义,刚柔并济,智勇双全,虽有缺点但仍不失为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血肉丰满的立体人物形象。
二、平民:无端卷入战争的冤魂
平民是战争中最无辜的人,没有称霸四方的雄心壮志,只想有一方安身立命之所,苟活于乱世,他们不愿却又不得不卷入战争。“在战争片中,整个社会(通过代表性的缩图来表明的)被迫服役,来抵抗武装侵略和残酷暴行。”[2]所以,在十七年电影中总是会有舍身为国宁死不屈的共产党抗日战士,再者就是团结一致拥护抗战的群众,他们代表着整个中华民族的抗日力量和热情。影片中“民”和“兵”是同位一体水乳交融,群众都具有很高的思想觉悟,自觉并完全认同共产党即国家的任何抗日行动,即使有自己的声音也会在党的教育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任何个人都只是群众这个群体的代表而已,在不同的影片中起到相同的作用。
新世纪以来抗战题材电影再次发现了“平民”,试图把以前电影中出现的平民英雄还原成平凡而又真实生动的“人”,揭秘普通人在抗日战争中的心路历程,描写平民在生死一线之间爆发出来的人之本性。战争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的不幸,但生活还在继续,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仍艰难而又顽强地生存着,他们的身上每天都在上演着一出出悲喜剧,不同以往的是多了战争的加入,生活中的不确定性增加了。人往往在特殊情境中才能表现出真实的本性,战争这一特殊的事件更是人性的炼狱,生死存亡之间更暴露出人性的光辉或丑陋。
经典抗战片从国家或民族的角度描写战争和其中的人和事,但《鬼子来了》试图从民间立场上剖析在抗战中的人性、人情,旨在发现战争中真正的“人”。战争年代,挂甲台的人们并没有对侵略者产生刻骨的仇恨,却和日本人相处融洽,安安分分地当着“亡国奴”、“顺民”。日本人的进驻除了带来生活上的一些不方便外,毫不影响普通人日复一日的生活。马大三和他的村民们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由生存本能出发,无关乎国家和民族。作为抗日力量代表的“我”的出现,把马大三强行拉入到战争的纷争中去,把社会使命强加到自然生命中去。导演同样以超然的姿态刻画日本人,如同对马大三既不过分拔高也不极力贬低,剥去矫饰的光环的态度一样,以一个自然生命个体“人”而存在。被俘的花屋小三郎并不是一个不惧死亡的武士,他并没有在被俘后自裁了断,而是为挽救自己的生命绞尽脑汁,褪下那身军装,他就是另一个马大三,一个普通的农民。马大三和花屋小三郎,他们都是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强行拉进到战争中去的普通人。在花屋小三郎向马大三行刑时,马大三失去了生命,却看到了世界的本质,鲜血染红的世界鲜艳夺目却又倾斜失衡;花屋小三郎苏醒的人性也彻底消亡,成为行尸走肉虽生犹死,两个国家的“人”都在同一刻“消失”,成为战争中的冤魂。
不同于《鬼子来了》致力于电影在艺术上的突破和思想上的颠覆,管虎的抗战喜剧《斗牛》偏重于商业价值的获取。同马大三相似,牛二也是在不愿而又被逼的情况下接受照顾“八路牛”的任务,不同的是对于牛二的逼迫中又包含了金钱和美女的诱惑,使得这项任务更像是一场交易。牛二并没有因为牛是八路军的而像村民那样对其顶礼膜拜,而是从牛的身上“捞些油水”。牛二是自私的,在危急关头想弃牛而逃;他是懦弱的,全村人惨遭杀戮他选择逃跑而不是报仇;牛二是善良的,救助饥民和伤重的日本兵;他是勇敢的,在枪火纷飞的战场奋力救下奶牛。牛二是一个真实的人,在战争年代他没有所谓的政治信仰,他行事准则是自身的利益和情感。但在影片的最后,他发现自己几经生死努力救下的奶牛却被抛弃了,曾经具有伟大意义的任务成为一种荒诞,在寂寞中,只有牛陪他走完孤独的一生。
三、日本人:人性与兽性撕扯下的灵魂
日本既是战争的发动者——视人命如草芥,杀人如麻,嗜血如狂,凶狠残暴;同时又是战争的失败者——形象丑陋,愚不可及,不堪一击。这两个身份给予创作者无限的创作空间,十七年电影就是以此为出发点进行电影的制作,又运用夸张的艺术手法进行加工,导致了电影中日本人的形象失真。日本人的形象只是为了衬托中国抗日军民的大智大勇而生,并没有对其本身的个性进行观照。
新世纪以来的抗战电影对十七年电影中出现的片面化、脸谱化和概念化的日本人形象进行了改造,日本人不仅仅是杀人机器、战争狂和野心家的代名词,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人,有喜有乐,有爱有愁,经历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创作者运用摄像机去审视日本人身上的人性,包括人性的劣根性、弱点和光彩,试图突破前人的桎梏。在镜头中表现他们在军国主义思想与人之本性之间的苦苦挣扎,审视他们矛盾痛苦的灵魂。其中代表作品有《葵花劫》和《南京!南京!》。
《葵花劫》中的菊地浩太郎,出身高门大户,为国征程奥运,为“圣战”血战疆场,是国家的骄傲、民族的英雄。他失去了在战场上冲锋陷阵的资本,就被他所效忠的天皇和所奉献的国家抛弃了,被他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所遗忘。在小站里,由于国家、民族之间的敌对,人们对他这个陌生的闯入者的态度是冷漠、反抗和畏惧。他被排斥在人群之外,心灵承受着孤单寂寞的啃食。唯一的安慰就是那如同妹妹的化身的向日葵,但也被无情地折断;他渴望回到家乡,但唯一的亲人缠绵于病榻可能将不久于人世。战争让他失去了挚爱的亲人、健康的体魄和昔日的荣耀,被抛弃在人们遗忘的角落。恰是他的征讨对象、敌对者尚有些许温情和关心付之于他。他的生活信仰和生命支柱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灵魂在困惑迷茫痛苦中徘徊,战争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在重返战场的前夜,他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释放了挣扎的灵魂。
《南京!南京》以日本人角川的视角观照和记录日本人进入南京后的所作所为。角川曾经在教会学校里学习,教会教导要用仁慈和博爱去对待世人。他在战争中恐慌害怕,可以对慰安妇付出真诚的关心和真挚的感情,向被自己误杀的女孩们跪地谢罪。战争的鼓吹者宣称为了缔造繁荣、推进文明而来,但结果出现的却是满目疮痍的古城,无辜惨死的平民,惨遭蹂躏的女子,获得的是中国军人的顽强反抗,人们眼中的强烈恨意。没有和平和昌盛,只有杀戮和毁灭。信仰、良心和忠君、爱国在他的内心进行残酷的搏斗。哈姆雷特曾追问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角川的回答是在战争年代,生存比死亡更艰难,所以他选择用死亡来结束灵魂战场上的厮杀,逃避残酷的现实。
战争是人类竞争中最血腥残酷的表现,“在战争中整个民族被动员起来,在集体情况中经历着一种新鲜的激情的活动”。[3]在抗战题材电影中观照中日两个国家的命运,从中透视战争中每一个独立个体的命运和选择。
如同新历史主义所说:历史是一种叙述。十七年时期的抗战题材电影是在战争刚结束,人们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的狂热中,用积极乐观和夸张的语言对抗战历史的“叙述”。影片只要求突出战争的残酷、取得胜利的艰苦和积极团结的军民、凶狠狡诈的敌人,所以在人物塑造上难免出现概念化和片面化的弊病。新世纪以来,由于国外战争影片的拍摄观念和自身要求突破以求发展等原因,电影界运用新的叙事手法去“叙述”抗日战争的历史,把人作为焦点,把战争变成表现人物的背景,凸显“人性”淡化“战争”, 正视国民党人在抗战中的贡献,表现平民试图在战争中苟活却不得不卷入不可知的命运,审视日本人在战争与人性之间拉锯的痛苦挣扎的灵魂。
[1]范志忠:《世界电影思潮》,第57页,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2]托马斯.沙兹:《旧好莱坞/新好莱坞:仪式、艺术与工业》,第89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
[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 第12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