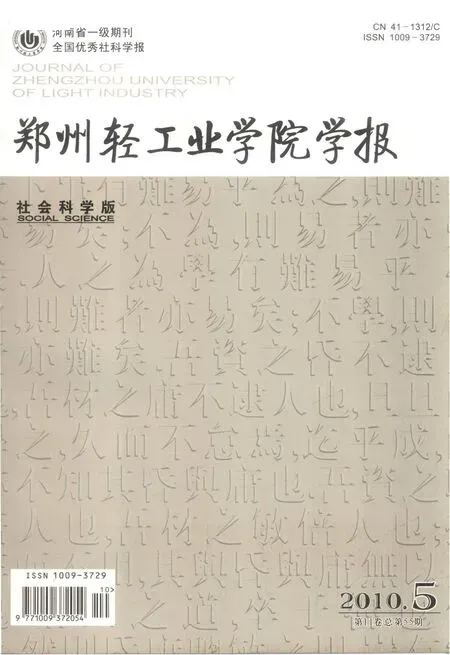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
2010-09-15行红芳
行红芳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
行红芳
(郑州轻工业学院政法学院,河南郑州 450002)
艾滋病是一种具备严重污名化特征的疾病,艾滋病人及其家庭成员会受到与此有关的污名歧视。艾滋病人通常采取隐瞒或暴露的策略进行污名控制,这会造成个人压力增加、妨碍病人获得治疗等。在社会工作职业化的背景下,认真开展并切实做好一对一的个别化工作、家庭护理小组工作、社区教育、制定和完善相关社会政策等实务,可降低污名并取得良好效果。
艾滋病;社会支持;污名控制
当前,我国正处在急剧的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经济利益结构的调整,部分社会成员因健康、性别、身份、地域等原因受到污名和歧视对待,导致社会不公平等诸多社会问题的出现。如果不采取强有力的干预措施,社会矛盾和不良情绪容易进一步积累成突出的社会问题。因此,关注污名及污名控制策略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在各种类型的污名中,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最严重也最引人关注。从艾滋病流行至今,全世界大约已有 6 000万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2 500万人死于艾滋病或相关疾病。中国自 1985年发现首例艾滋病后,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毒携带者的数量急剧增加。目前中国艾滋病的流行趋势处于世界第 14位,在亚洲排名第 2位。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每年以 40%的速度递增,据我国卫生部公布的 2009年度法定传染病疫情报告,我国艾滋病感染 13 281人,死亡 6 596人。[1]
社会科学界对于艾滋病的关注始于近年,与国外大量的艾滋病研究成果相比,国内社会科学界对于艾滋病及其相关社会问题的研究开展较晚,成果较少,质量也有待提高。从现实情况来看,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与歧视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2],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已充分认识到艾滋病的强烈污名化特征,其 2007年的报告即以降低污名与歧视为主题。因此,从艾滋病、污名与污名控制的角度对已有的国外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可以为中国制定相关政策、开展实务工作提供借鉴。本文将在对已有的污名理论回顾的基础上,探讨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探讨社会工作介入的策略与方式。
一、艾滋病污名的理论研究
从污名理论出现至今的 40多年时间里,国外学者将污名应用于多个群体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成果。关于艾滋病污名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1.艾滋病与污名
疾病与污名关系密切。美国社会学家伊坦·戈夫曼解释了高度污名化疾病的特征:一是感染疾病的人本身有过错,责备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二是疾病是累积的和无法治愈的;三是公众对这种疾病缺乏了解;四是症状无法被隐瞒。艾滋病符合这些标准,因此成为污名化最为严重的疾病之一,这将它与其他的周期性和危及生命的疾病如癌症及多发性硬化症区别开来,成为污名程度最严重的疾病之一。后来学者们将艾滋病人受到歧视的原因归结为疾病的传染性、无法识别性和致死性。[3-4]另一个与此有关的污名来源是那些感染艾滋病的人大多来自被污名化的群体[3],他们由于自己的行为偏差而得病,因此被认为是有“原罪”的。[5]艾滋病因此被社会定义为边缘化群体的传染性疾病,从而形成污名的叠加。[6]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穷人往往是艾滋病的高发群体,种族、民族、贫困与艾滋病联系在一起,使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问题更为复杂。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对污名与责任推断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学者们认为:有污名的人一般被认为对生理问题没有责任,而对行为或心理问题有责任。同样的疾病,如果其得病原因是个人无法控制的,例如孩子由于母婴传播而得艾滋病或个人由于输血原因而得艾滋病,社会成员会认为其本身无过错而给予更多的同情,这种情况下污名程度相对较轻;相反,如果由于个人可控而失控的原因得病的,例如由于个人吸毒或者不良性行为而得艾滋病,则其污名程度更严重。由此,美国学者伯纳德·维纳[7]提出“原因推断→情感反应→行为反应”的动机序列,使得许多观察到的事实可以整合到一起。这有利于揭示不同感染途径得病者的污名程度不同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制订合理的干预策略,促进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
2.艾滋病污名的后果
从微观层面上看,污名对个人选择产生严重影响,不仅阻碍人们进行测试,而且阻碍人们获得艾滋病方面的治疗。[8]与艾滋病有关的高度歧视与低参与意愿相联系[9],直接或间接影响性传播感染者在公共健康机构接受治疗的意愿[10],这不利于对艾滋病的监测、控制和预防。与艾滋病有关的污名延迟了社会成员寻求健康的行为,还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生活满意度、社会参与,造成社会排斥。个人主观感觉到的污名可能增加失落感,加重照顾者的心理负担[11],对其康复产生负面影响。从中观层面和宏观层面来看,污名将具有某些特质的人区别开来,形成“我群”与“他群”。污名实际上是社会强势群体加之于弱势群体身上的否定性评价和随之采取的孤立性行为。它导致了社会排斥和群体冲突:改变了被污名化群体的个人认同,改变了他人看待个人的方式和个人看待自己的方式;被污名化的个人通常被认为是无信用的,他们接受和内化这样的观点——他们是偏离的、不同的、无价值的,从而感觉自我厌恶和羞耻;污名也使得被污名化群体的不满情绪进一步积累,如果得不到合理释放,可能会形成一些反社会行为,对社会稳定与和谐造成负面影响。
二、艾滋病污名控制策略分析
在被污名的情况下,被污名化的个体可能采取各种策略进行污名控制,以保护自己的利益。污名控制策略成为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热点。
1.艾滋病污名控制策略种类
处于艾滋病污名状态的个人可能向智者或自己人求助,他们与其居住在一起,知道其病状。[12]情况相似的人往往组成自助组织或小团体,在互相取得信息、物质或情感支持的同时进行污名抵制来保护自己的权益。Corrigan[13]提出了抗议、教育和接触三种污名抵制策略,Stanley[14]将污名控制策略分为避免污名和控制污名两种。也有学者认为污名控制策略的维度是污名抵制,包括将艾滋病称为另外一种疾病、通过宣传或日常谈话谈论艾滋病、已经知道其感染艾滋病而继续对其提供照顾等。在农村照顾感染艾滋病的成年子女的父母常常采用两种策略进行污名控制:不对他人暴露和对孩子的疾病撒谎。[15]抚养感染艾滋病孩子的父母采用许多策略控制污名,如对学校及其他社会联系进行选择性暴露、隐瞒艾滋病的症状、控制孩子的社会生活等。[16]
2.艾滋病污名控制策略选取的影响因素
如果将艾滋病污名控制策略看做一个从完全不暴露、有选择地暴露到完全暴露的连续谱,病人及其照顾者的选择往往处于这个连续谱中的某一点上,暴露者的特征、对象、时间、情境等因素成为近年来污名控制策略研究的热点内容。研究者认为,照顾者一般会有选择地暴露污名,他们往往对家人和朋友采取暴露策略,而不对家庭外人员暴露。[17]这种策略使感染者在受到一定保护的同时,也加重了照顾者的负担。在暴露对象方面,由于母子 (女)间的亲密关系,对母亲暴露其真实情况往往是艾滋病感染者采取暴露策略控制其疾病状况的第一步。研究者也对暴露者的基本情况进行了研究,认为通过同性接触得病的人最有可能暴露他们的真实情况;已经有艾滋病或身体出现严重症状的人更有可能对他们的母亲暴露其真实情况;年龄和教育程度是两个重要的影响因素,年龄更大和教育程度更高的艾滋病感染者更不可能对他们的母亲暴露其真实情况。[18]暴露程度也成为污名控制策略的一个重要指标,其范围涉及不暴露、谈论某人有病/有重病/有HIV /有AIDS/可能死亡等。父母对自己疾病状况的暴露往往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上:暴露对孩子和将来的照顾者是最佳选择,暴露的目的是为了公开交流,让孩子为其父母的死亡做准备,以便制订出一个看管计划。[19]
3.艾滋病污名控制策略引发的不同后果
隐瞒与暴露是被污名化的艾滋病人基于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对现实情况分析判断的基础上所选择的策略。但不管是隐瞒还是暴露,都有正负两方面的后果 (见表1)。

表1 污名控制策略的后果
艾滋病的暴露导致紧张,但它也是一种人们处置疾病、减轻紧张的机制。[20]对于疾病信息的暴露也能给病人减轻负担,带来安慰。Pennebuker等[21]通过有控制的临床研究,证明了在说出长期隐瞒的秘密或创伤经历后,研究对象免疫系统的功能会显著改善。同时,由于艾滋病与污名联系在一起,非常少的人愿意暴露他们的病情。但隐瞒产生的压力对个人身体健康有负面影响,对重要他人隐瞒病情提高了个人的焦虑和压力[22],会引起心理上的隔离与沮丧。对以有益形式做出回应的他人暴露艾滋病有助于改善个人的心理状况。但在现实生活中,研究发现,病人暴露其状况极端困难,需要家庭的支持、辅导人员的鼓励和帮助,即便如此,也仅有一半的人肯暴露他们的状况。[23]
个人的选择实际上是对其暴露后果的理性预期。在其他因素大致相同的情况下,个人预期得到的社会支持越多,越有可能采取暴露策略,以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反之,个人越有可能采取隐瞒策略,以控制污名,减少社会排斥。这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涉及时间序列的因素,即个体对其前段时间暴露 /隐瞒策略效果的总体评价影响其后续行为:如果个人采取暴露策略后得到较多的社会支持,可能继续采取暴露策略,即对更多的人在更大范围内暴露;如果个体得到的社会排斥超过社会支持或者超过其心理预期,则以后可能采取隐瞒策略,即不再对其他人暴露自己的真实情况。同时,从总体上看,个人的污名控制策略执行得好,会得到更大的社会支持;执行得不好,则带来社会排斥。
个体的污名控制策略是在一定的社会情境中发生的,还受到诸多外在因素尤其是社会情境因素的影响。现代都市社会是一个陌生人的社会,人际间的沟通与互动频繁,但关系的持久性相对缺乏,由于社会成员彼此疏离,被污名化的个人或群体有更大的可能进行污名控制;传统的乡土社会是熟人社会,彼此熟悉,个体很难隐瞒自己的疾病,信息往往通过口耳相传的形式成为整个社区共有的秘密。[24]
三、积极的社会工作是降低艾滋病污名的正确途径
探讨降低污名的策略有助于促进被污名化群体的社会融入。在去污名化的过程中,专业人士由于特定的“卡理斯玛”权威,其意见可以受到更多的关注与重视,其行为可以在促进平等对待的过程中起到更大的作用。其中,社会工作者可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社会工作者秉承尊重、平等、接纳、同理心等价值理念,采用一系列的专业技巧与手法,对于改变被污名化群体的低自尊与低自我评价、促进其社会参与起着重要作用。同时,社会工作者直接与被污名化个体 /群体发生互动,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公众加入进来,从而促进社会公众与被污名化群体的接触与交流,切实起到降低污名的作用。从目前情况来看,社会工作者在降低艾滋病污名的过程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降低个体的艾滋病污名
对于降低个体层面的艾滋病污名,最为适用的是个案工作手法。因为个案工作是在接纳、平等、尊重等社会工作伦理和价值观的基础上,通过一对一的个别化工作方式,采取专业手法进行干预,以达到助人自助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社会工作者往往采用生理、心理与社会的多维视角开展工作,这更符合被污名化个体的现状,看待问题也更为全面,可以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同时,心理社会治疗模式、危机干预模式、理性情绪治疗模式等个案工作模式应用于被污名化个体,可以起到应有的作用。
2.降低群体的艾滋病污名
污名往往是社会通过类型化和区隔,将不同性状的人区分开来,然后采取不当的孤立、歧视等手段,使相关群体承受污名,进而有可能产生一系列不良后果。社会工作者可以将小组工作手法运用于降低群体污名的层面。如将被污名化群体集中起来,通过小组活动来促进小组成员之间的社会支持,实现个人增权和集体增权,达到去污名化的目标。据介绍,在艾滋病护理领域,家庭护理小组的工作取得了积极的成果。此类工作小组会探望那些根据常规检查而被怀疑患有艾滋病的人,训练专职护理人员辅导病人怎样减轻艾滋病不适症状。
3.降低社会环境的艾滋病污名
(1)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可以将社区工作的方式纳入其中,通过社区教育、社区动员等方式,普及与艾滋病相关的预防、治疗知识,增加社会公众对于疾病的了解,从而促使他们与被污名化群体的接触,达到降低污名的目的。
(2)通过制定和修改相关的社会政策,尤其是教育、卫生、住房等公共领域的社会政策,同时规定相关的法律责任,使被污名化群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这对维护被污名化群体的合法权益、降低与其有关的污名有着重要作用。
[1]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2009年我国卫生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10-03-29)[2010-04-03].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 wgkzt/pgb/201006/47783.htm.
[2]Yang Hongmei,Li Xiaoming,Stanton Bonita,et al.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HIV /STD prevention activities among Chinese rural-to-urban migrants[J].A I DS Education and Prevention,2004,16(6):557.
[3]Crandall,Coleman.A I DS-related stigmatization and the disruption of social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1992(9):163.
[4]Malcolm,Aggleton,Bronfman,et al.HIV -related stigmatization and discri mination:its for ms and context[J].Critical Public Health,1998(8):347.
[5]SiminoffL A,Erlen J A,LidzCW.Stigma,A I DS and quality of nursing care:state of the science[J].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1991(16):262.
[6]Herek GM,Glunt E K.An epidemic of stigma:public reaction to A I DS[J].American Psychologist,1988(43):51.
[7][美]维纳 B.责任推断:社会行为的理论基础 [M].张爱卿,郑葳,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83-110.
[8]Gill Green.Social Support and HIV :A Review,in Robert Bor and Jonathan Elford,the Family and HIV [M].New York:Cassell,1994:83-84.
[9]Fortenberry J D,McFarlane M,Bleakley A,et al.Relationships of stigma and shame to gonorrhea and HIV screening[J].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2002(92):378.
[10]Bronwen Lichtenstein.Stigma as a barrier to treatment of sexually transmitted infection in the American Deep South:issues of race,gender and poverty[J].Social Science andMedicine,2003,57(12):2435.
[11]DemiA,Bakerman R,Sowell R,et al.Effects of resources and stressors on burden and depression of familymembers who provide care to an HIV -infected woman[J].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1997,11(1):35.
[12]Bruce G Link,Jo C Phelan.Conceptualizing stigma[J].Annu Rev Social,2001(27):363.
[13]Corrigan P.How stigma interfereswith mental health care[J].Am Psychol,2004,59(7):614.
[14]Stanley L D.Transforming A I DS:the moral management of stigmatized identity[J].Anthropology and Medicine,1999,6(1):103.
[15]McGinn F.The plightof ruralparents caring for adult children with HIV [J].Families in Society,1996,77(5):269.
[16]Rehm R S,FranckL S.Long-ter m goals and nor malization strategies of children and families affected by HIV /A I DS[J].Advances in Nursing Science,2000(23):69.
[17]Caliandro G,Hughes C.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 grandmother who is the primary caregiver for her HIV positive grandchild[J].Nursing Research,1998,47(2):107.
[18]Constance L Sheha,Constance R Uphold,Patrick Bradshaw,et al.To tell or not to tell:men’s disclosure of their HIV -positive status to their mothers[J].Family Relations,2005(54):184.
[19]Draimin B H,Gamble I,Shire A,et al.Improving permanency planning in families with HIV disease[J].Child Welfare,1998(77):180.
[20]Holt R,Court P,Vedhara K,et al.The role of disclosure in coping with HIV infection[J].A I DS Care,1998(10):49.
[21]Pennebuker J,Kiecolt-glaser R.Disclosure of traumas and immune function health implication for psychotherapy[J].F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1988,56(2):239.
[22]Mansergh G,Marks G,Simoni J M.Self-disclosure of HIV infection among men who vary in time since seropositive and symptomatic status[J].A I DS,1995(9):639.
[23]Hays R,Mckusick L,Pollack L,et al.Disclosing HIV seropositivity to significant others[J].A I DS,1993,7(3):425.
[24]行红芳.熟人社会的污名与污名控制策略——以艾滋病为例 [J].青年研究,2007(2):37.
C916
A
1009-3729(2010)05-0076-04
2010-08-06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08BSH007);郑州轻工业学院博士科研基金项目 (000450)
行红芳 (1972— ),女,河南省孟州市人,郑州轻工业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社会政策、社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