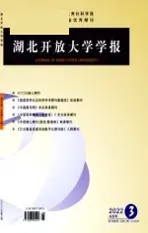试析英国讽刺文学中的理性主义
2010-08-15赵芳
赵 芳
(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试析英国讽刺文学中的理性主义
赵 芳
(江西财经大学 现代经济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32)
在 19世纪讽刺小说经典《埃里汪奇游记》中,在对现实社会与虚幻世界、理性与非理性的交融、对照中,体现了作者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讽刺和批评。在表面荒诞的情节下,影射的是一个非理性的维多利亚社会。作为一部奇特的乌托邦作品,《埃里汪奇游记》实现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世界构思的巧妙融合,其意义深远。
讽刺文学;乌托邦;理性主义;批判现实
在英国文坛,讽刺文学因其针贬时政、并以独特方式体现时代精神和大众需求而经久不衰。继乔叟、斯威夫特之后,19世纪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将讽刺手法运用至炉火纯青,其1972年创作的Erewhon (译为《埃里汪奇游记》),被认为是与《格列佛游记》齐名的一部经典讽刺作品。塞缪尔·巴特勒本人被肖伯纳称为“在他的本行内(in his own department)是19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这里所谓“本行”,有人认为即指讽刺文学而言。[1]作为一部反维多利亚的讽刺小说,《埃里汪奇游记》深刻披露了维多利亚社会的病态和非理性,其警世意义如同古希腊阿波罗神庙所刻的格言“认识你自己”所昭示的,对认识和反省维多利亚社会具有深远的意义;而且该游记体讽刺小说对后世作家的创作都有直接的影响。在该作品中,塞缪尔·巴特勒以哲人博大精深的智慧为人们展示了一个充满理性和非理性悖论的乌托邦世界。
一
《埃里汪奇游记》以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了一名英国旅行者在埃里汪的见闻。塞缪尔·巴特勒从头至尾隐去了主人公姓名,似乎有意让读者推测这位主人公仅仅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个典型人物,《埃里汪奇游记》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叙述自我和经验自我相结合的叙述视角使该作品不仅有引人入胜的内容,而且能令读者对“我”(希格斯)的立场一目了然。
然而,在书中对埃里汪人非理性成分一一列数的同时,这位领衔担纲的希格斯也并非是全然理性的。例如:我们所认为不幸的事情之所以会引起他们的愤怒,也就在于他们把这些事情看作是一切灾难和罪行的根源,而不是结果;现实的时序令他们不安,所以他们认为有必要生活在一个假设的世界里。但在刻画埃里汪奇异的浮士绘的同时,塞缪尔·巴特勒又掺杂了一些对19世纪欧洲人情世故的描写,正是这些描写使人们不禁对文明世界所谓的文明和理性划上一个问号。例如,在嘲讽埃里汪人混淆道德败坏和不幸时,书中说到:“确实,这种观点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可是,即使在十九世纪的英国,也能找到某些类似的地方。如果一个人患了脓肿,医生会说里面有‘致病’的物质,而一般人说他们的手或指头‘坏’了,说他们全身都‘坏’了时,意思不过是‘生了病’。”(p62)[2]而下面的一则例子则更有具讽刺意味:“意大利人使用同一个字来表示‘耻辱’与‘不幸’,我有一次听到一位意大利妇女谈到她的一位青年朋友,说得象是天下第一完人,却又惊呼到:‘ma,povero disgraziato,ha ammazzato suo zio’(可怜而不幸的人,谋杀了他的叔叔。)”(P62)[3]如此看来,在混淆概念方面,埃里汪人并不是始作俑者,19世纪的欧洲与埃里汪有一脉相承的嫌疑。
塞缪尔·巴特勒并不着意于性格刻划,而是精心运用了多种讽刺手法,刻意对维多利亚英国地非理性因素进行破坏性挖掘。在书中,最常见的手法是颠倒逻辑,例如国名Erewhon是乌有乡(nowhere)的倒拼外,富商Nosnibor是笛福笔下《鲁滨逊漂流记》中主人公(Robinson)名字的倒拼,看守的女儿Yram 的名字倒拼为Mary等等 。此外,塞缪尔·巴特勒还用了指东说西的手法,如将英国教会比作音乐银行,外表华丽而光顾者寥寥无几;将英国大学比做荒唐学院,讽刺英国教育体制中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荒唐成分。总而言之,塞缪尔·巴特勒对维多利亚社会非理性因素的讽刺以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方式贯穿作品始终,读者必须对其变幻的手法和视角足够敏感,若偶一疏忽,反倒要陷于迷宫不能自拔了。
二
作为英国最富有独创性和涉及面最广的作家之一,塞缪尔·巴特勒曾以各种形式对维多利亚社会的弊端予以深刻揭露和批评,在批判维多利亚时代的母题下,这些作品呈现出各异的写作手法和艺术风格,而《埃里汪奇游记》则通过游记小说的框架,将严肃的哲理与冒险故事、对社会的批评与娱乐消遣相结合,从而最大限度地将维多利亚社会非理性的种种内涵充分发掘出来。
在《埃里汪奇游记》对维多利亚时代的科技、宗教、教育、伦理道德等方面进行的批评中,围绕述埃里汪人对机器的畏惧而对科技展开的嘲讽成为该作品的点睛之处。在书中,希格斯因入境时带了一块表而招致企图引进机器的嫌疑,不仅为此入狱数月,且始终摆脱不了对他的非难。关于这点,希格斯了解到:“大约在四百年前,他们的机械知识远远超过我们,而且发展速度惊人,直到后来,一位很有学问的假设学教授,写出一本很不寻常的书……,证明这些机器最终要取代人类,而且会变得充满着与动物不同而又比动物优越的生命力,就如同动物的生命与蔬菜的生命一样。”(p57)[4]原来埃里汪的过去有着辉煌的文明和领先于欧洲的技术,却因一本陈述机器最后将主宰人类的书,而引发他们荒谬地封杀机器、禁止发明。在《埃里汪奇游记》中,塞缪尔·巴特勒不惜重墨,详尽地介绍了这本《机器的书》,那位埃里汪教授的观点渐渐为国人接受之后,由此引发的便是一场革命和一切机器被封杀。
为何塞缪尔·巴特勒要大力渲染埃里汪人不理性地对对待机器呢?细读之下,我们便会发现,借助对埃里汪人非理性的嘲讽,塞缪尔·巴特勒讽刺了机械达尔文进化论,并把这种理论归结为荒谬。塞缪尔·巴特勒曾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拥护者,从拥护到背离达尔文的理论,主要缘于他对达尔文进化论中“自然选择”(natural selection)存在歧义。塞缪尔·巴特勒认为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没有将人的意志考虑进去,否认目的性,似乎将人降至一种单纯的机械生物。既然人象机器,没有自由意志,机器的发展就必然会对人产生威胁。因此,埃里汪人及时捣毁了那些自己创造出来又将反过来毁灭自己的机器。此外,塞缪尔·巴特勒还表达了对维多利亚时代工人工作状况的深切同情。塞缪尔·巴特勒所处的时期正是工业革命之后资本主义工商业迅猛发展之际,曾经作为工业革命原动力的自然科学,已以科学的名义成功地扩展到诸多学科研究领域。然而在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工业文明高涨局面的冲击下,整个西方社会的文明生活行成了两大对立的方面:一方面是工业文明促进了社会的商业繁荣,使西方人对未来生活必将更加昌盛富强充满希望;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对人力资源和矿物资源的野蛮掠夺,给劳苦大众带来一系列的灾难——超常劳动时间、恶劣的劳动条件、人为工业机器所奴役的异化感受、处于悲惨生活境地的工人家庭等等。[5]通过《埃里汪奇游记》,塞缪尔·巴特勒不但反映了当时工人为机器物化的悲惨现状,更实现了对人类未来幻想的破灭。埃里汪的文明本已领先一步,经过历史的曲折,却走向衰弱和凋零,并走向理性的反面,那么人类的未来又如何呢?
无独有偶,在另一部经典讽刺作品《格列佛游记》中,斯威夫特也对当时一些荒唐的科学行为进行了辛辣的讽刺。例如,在拉各多的大学院中,科学家们或从事“从黄瓜中提取阳关的课题研究”,或“把粪便还原成原来的食物”或“忙着把冰烧成灰制成火药”等等。[6]不同的是,斯威夫特认为当时科学家们的行为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荒唐成分,其初衷在于倡导科学要满足实际需要。而塞缪尔·巴特勒通过对科技中非理性成分的抨击,以达到对维多利亚时期永恒进步的批判和未来世界的理性思考。但两部作品同样促使人们理性对待科技的发展趋势。
由于科学成果的应用体现出高度民主的实用价值,科学在十九世纪进入它的黄金时代,以致“概念只要贴上科学的标签,通常就足以赢得人们特殊的信任。”[7]虽然在对达尔文进化论的质疑和对技术的抨击中,塞缪尔·巴特勒的某些观点仍待历史的论证,其无疑促进了人们对理性和本真的追求。
三
作为一部既是游记,又是针贬时事、反映作者乌托邦思想的讽喻文学,《埃里汪奇游记》将对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世界的构思巧妙融合在一起,以唤起人们对现实境况和社会前景的普遍关注。
塞缪尔·巴特勒以离奇的冒险故事为线索,运用诙谐的笔调对维多利亚时代所谓的正统观念进行了否定和颠覆。一些人们习以为常的事物被塞缪尔·巴特勒颠倒和夸张加以讽刺,沾沾自喜的维多利亚人实际上“逆来顺受,长期受苦,轻而易举地被牵着鼻子走,并且会很快地把常识奉献在逻辑的神殿上”(p187)[8]。《埃里汪奇游记》体现的是理性与非理性的悖论。这种超常的写作手法足以给当时英国读者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冲击。处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维多利亚英国国力鼎盛,并在海外拥有广袤的殖民地,号称日不落帝国。而塞缪尔·巴特勒却在维多利亚人对未来无限憧憬之时给国人泼了一盆冷水。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精神的原动力——新教伦理中的禁欲主义已经丧失,物质主义抬头。基于对人类未来前途的担忧,学者们对美好世界的热忱期望已开始回归理性。塞缪尔·巴特勒放弃对永恒进步神话的希冀,他笔下的埃里汪经历文明走向衰败,也正是对乌托邦幻想的逆转和猛烈的批评。
王尔德(Oscar Wilde )曾说过,一张没有乌托邦的世界地图是丝毫不值得一顾的。然而,《埃里汪奇游记》所描述的这种乌托邦却不同于以往那种美好、自由和富足的社会。起源时期的乌托邦文学中描绘的“理想国”、“黄金时代”、“伊甸园”、“阿特兰蒂斯”这些带有浓厚传说色彩的乌托邦胜地,大多是渺不可及,无法坐实的地方。其文学空间始终想让读者明白,这个乌托邦是与现实、现世相区别的。[9]但是,塞缪尔·巴特勒笔下的偏远国度埃里汪与英国的距离似乎仅一步之遥。事实上,《埃里汪奇游记》穿行于现实与虚构之间,目的就是将维多利亚社会中的制度弊病、文明弊病予以放大、夸张、变形,以达到讽刺和批判目的。
对于如何拯救这个非理性的维多利亚社会,塞缪尔·巴特勒并没有开出一剂良方,在《埃里汪奇游记》中,他更多地是通过理性和非理性的交融、维多利亚人和埃里汪人的比照,尽力发掘和批判和与维多利亚社会息息相关的非理性因素,并寄希望于读者在体验埃里汪带来的亦虚亦实、亦真亦幻之感后,在惊诧、震撼之余,能清醒对待盲目乐观主义和绝对的社会进化论,并且对自身生存境况和人类社会发展前景进行理性思考。
[1] 塞缪尔·巴特勒. 众生之路[M]. 黄雨石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2][3][4][8] 塞缪尔·巴特勒. 埃里汪奇游记[M]. 彭世勇,龚韶忍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5][7] 喻天舒. 西方文学概观[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6] 斯威夫特. 格列佛游记[M]. 史晓丽,王林译.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
[9] 姚建斌. 乌托邦文学论纲[J]. 文艺理论与批评,2004,2.
Analysis of rationalism in English satirical literature
ZHAO Fang
In Erewhon, which is one of the greatest satirical works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author satirizes and criticizes the Victorian Age through blending and contrasting the realistic society with visionary world and the rational with the irrational. Under the seemingly absurd plot, the mockery alludes to the irrational Victorian society. As a unique utopian work, Erewhon succeeds in combing the criticism of reality with the design of future world, and has far-reaching effects.
Satirical literature; Utopia; Rationalism; Criticism
I106
A
1008-7427(2010)05-0049-02
2010-03-27
作者系江西财经大学现代经济管理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