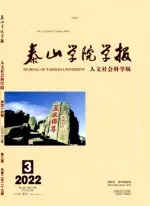论西南硕儒郑珍诗歌中的“不俗”精神
2010-08-15陈蕾
陈 蕾
(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院,上海 200062)
郑珍历来被视为道咸宋诗派的杰出代表,而其诗集《巢经巢诗钞》又被清末同光体尊为宗祖①。从道咸宋诗派到同光体,无论论人还是论诗,“不俗”始终是其一脉相承的品评标准和理论主张。其中,何绍基、陈衍、陈三立等人的“不俗论”是学界常常称引的材料。如何绍基《与汪菊士论诗》中“不依傍前人,不将就俗目”,陈衍《石遗室诗话》中“诗最患浅俗”等;何绍基曾力引黄庭坚语为“不俗”作界定:“戒俗之言多矣,莫善于涪翁之言曰:‘临大节而不可夺,谓之不俗。’欲学为人,学为诗文,举不外斯旨。”[1]这是从人品与诗品的角度立论。又如陈衍最有名的论断:“诗最患浅俗。何谓浅?人人能道语是也。何谓俗?人人所喜语是也。”[2]而陈三立论诗,同样也是“最恶熟恶俗,常评某也纱帽气,某也馆阁气”。[3]这又是从诗的措辞属对、风格气象上立论。因此,“不俗论”可以说是清末宗宋诗人所达成的一种共识。
相比之下,郑珍的“不俗”思想却历来鲜有论者,即或偶有言及之人,也仅以《论诗示诸生》一篇诗歌一笔带过。事实上,郑珍的“不俗”思想内涵深广、层次丰富,只因其散见于诗集之中,形式上莫如诗论、诗话等散文体那样容易发现和考证,而一直蒙尘至今。故本文欲专从诗歌释读的方式入手,重现郑珍生命中的“不俗”世界。
一、脱俗的歌诗
与何绍基、陈衍、陈三立等人一样,郑珍最明显的“不俗论”体现在其诗文主张上。常为人称道的是 1845年所作的论诗诗《论诗示诸生时代者将至》。盖因此诗是先生难得的系统性“文论”,它于是也成为后人论述先生诗学思想时最常引用的作品。诗中有这样两句:“从来立言人,绝非随俗士。君看入品花,枝干必先异。”这首诗之所以很重要,原因有三:一是因为它旗帜鲜明地打出先生的诗学理想——“不俗”。中国之士人,向来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为人生抱负之标尺。而先生的人生理想与诗学目标就是“立言士”和“入品花”。二是在于它指出了通往“不俗”的途径,在于人。郑珍论诗,首先注重的是人。他认为凡能立言者,其品行必不尘下。就好比名花异草,其姿态也必有不同凡响之处。因此,唯有不与世沉浮、品行卓异的高士,才有资格立言。而第三个原因需细细涵咏《巢经巢诗钞》全集方能发现:即这首诗乃是《诗钞》中高扬“不俗”精神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正是从这一年起,经巢诗中才开始时时闪现出睥睨时俗的清光。写作此诗时,诗人正好四十岁。假如人生“四十而不惑”,那么经历了科场失意、丧母之痛的郑子尹,也正是在他四十岁时真正迎来了人生与诗艺的成熟期。诗人洞见“不俗”与其生命的成熟之间,那微妙的联系耐人寻味。
除这首《论诗示诸生》之外,郑珍的确鲜有正面构建“不俗”诗学的尝试。但却不乏“反证”之作。如咸丰十一年 (1861),五十六岁的他写下这首《吉堂老兄示作 <鹿山诗草 >,题赠》。其中他这样论诗:“兹事诚小技,亦从学养化。世有昆岷源,江河自输写。俗论故不尔,只解摘嫣姹。……然诗之佳恶,意殊不争价。”“争价”二字典出《文心雕龙·明诗篇》中的“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刘勰笔锋所扫,乃是南朝宋初诗坛上的一股“新时尚”,即崇尚雕藻的山水诗风。而郑珍此处巧妙地反用其典,针对道咸诗坛“只解嫣姹”的“俗论”提出针砭。用笔洗练却涵括深广,包括了诗歌本体论(小技)、创作论 (学养)以及风格论 (不以辞害意)等等丰富的命题。但这里只着重强调两点:一是不随行就市、针砭时弊的矫俗精神;二是以学养人,人立诗立的“脱俗”之道。
时隔一年,时兼绥阳、桐梓、遵义三县职任的县令于钟岳与郑珍交往,对先生的诗学造诣推崇备至。于是郑珍写下《赠于伯英钟岳大令》一首,诗以赠答。此诗对当时海内诗风之抨击力度更猛,同时,在自谦之中,也可见出其对自己迄今为止诗学创作的总评价:“海内论诗至今日,浅狭未免难为篙。乾坤大气镇常在,必有一手牵六鳌。小诗耳耳竟何有,差觉不为时俗臊。此事如何漫推我,可怜甚爱忘訾謷。”斥海内论诗为浅狭,以时俗诗风为羞臊,此番言语从谦逊淳厚的经巢翁嘴里道出,其实也并不奇怪。因为,郑子尹性格中固然有徇徇大儒的一面,温柔敦厚,口不訾人;但人们也往往忽略了他耿介不群的一面(后文将对此有具体论述)。此其一。而五十七岁的他,此时将自己诗作的第一精神归结为“自立不俗”,以为惟有这一点还值得一提,可见在其诗学观念中,“不俗”二字占据着多么重要的位置。此其二。郑珍逝世时,享年六十四岁,之后的七年几乎都是在漫天战火的颠沛流离中度过的。平心而论,不论评价客观与否,此诗均可视为其 (现今已发现诗文中)对自己平生诗学的一个最后总结。
二、抗俗的生命
前文说到,郑珍的诗学理想及其自矜之处皆可归结为“不俗”二字。但若沿波讨源,你便会发现,诗学上的不俗追求背后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清末宗宋潮流的另一特征便是“性情第一”。如郑珍的恩师,主张以性情学问为一体的程恩泽便把性情置于学问之上②。郑珍秉承师训,也是一个以性情为根本的学人兼诗人。故其诗学上之见解首先必源于其人格上之要求。
道光二十五年 (1845),就在写作《与诸生论诗》的同一年,四十岁的郑珍携子知同,往权黎平府古州厅训导,兼掌榕城书院。到任后立即辞却了黎平府开泰县训导余芝为其庆生的邀请,于生日当天单独造访城南何忠诚公的故宅,传诗两首。其中后一首《神鱼井(并序)》中末尾有这样四句:“惨淡春风吹故井,满目凡鳞厌投饼。游人诧说飞上天,不道神鱼今未瞑。”诗中的神鱼,指的是明末护国大将何腾蛟。何氏为明季忠臣,明朝覆亡后,他为南明弘光、永历政权立下过汗马功劳。但明朝大势毕竟已去,何公终为清军所俘。被俘后他绝食七日而不死,终自缢殉国。乾隆帝赐谥“忠诚”。相传在他家,有一口井,“素无鱼,腾蛟生,鱼忽满井,五色巨鳞,大者至尺余,居人异之,后腾蛟死,井忽无鱼”。郑珍访其故居,见此井后,太息再三,因以神鱼为喻,盛赞何氏忠义靖节之精神。郑珍素来对忠臣义士十分敬重,这是他诗中时有流露的一种情绪 (如《题朱烈愍公 <守莱图册 >并序》、《闻新化邹叔绩汉勋以贰守从徽抚江忠烈忠源死难庐州二首》等)。但此诗“神鱼”与“凡鳞”的对举结构,加之联系上句“信知天惜神鱼死”的“惜”字与下句“厌投饼”的“厌”字,我们不难看出,郑珍心目中除了包含对神鱼 (高义之士)的钦敬外,还隐藏着对庸吏俗客的厌恶与轻视。明乎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拒绝同僚上司俗宴应酬的举动了。
1860年,六十岁的郑珍在《晓峰闻予将归,寄二诗至,中云“寇退君有家,君归我无友。”咏之凄然,以此十字为韵,酬之》(其三)中,夫子自道,为自己画了生前最后一幅自画像:“自性非傲物,懒拙难群世。城中近千家,往还惟有君。”又在组诗的第九首中明确宣布自己的处世原则:“乱世治文墨,宜皆笑其迂。不迂亦不拙,人乐非我娱。”两首诗合而观之,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这是一个世人眼里懒拙迂腐的老学究,一个友人心里举世独立的亲切长者。他是耿介的,但那并不等同于傲物,他和陶渊明杜甫一样,与乡村父老也有着亲切的交往:“我今忘我混谈笑,不论樵妇与牧儿。朝来邻叟约过酌,晴腊无事真良时。”[4]甚至邻舍少年遇事也会跑来向其哭诉和求助[5]。对于与他同样挣扎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们,郑珍是恫瘝在抱的。但他毕竟是一个大儒,无法泯灭胸中天下为公的良心,很难与周围竞新丽、争富贵、牟私利的浑浊世道鱼水交融;同时他又是一个学者,深厚的学养以及由此学养而培育出的精神气象使其在贵州这片山野蛮荒之地上更加知音难觅。所以,他与乡人们谈笑归谈笑,中间毕竟还是“隔”着一层清醒的自觉,那就是知识分子的“自我意识”和“责任意识”。也只有在觥筹交错的“忘我”之时,他才能与这俗世相交接。但人生的常态中,“忘我”又能占几时呢?对于这个无时不刻包裹着他的这个世俗世界、底层人生,他的态度或可以“怒其不争而又哀其不幸”来概括,而在这其中传统儒家“士”的观念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对忠臣义士的钦仰、对自身品格的持守,使郑珍自然而然地在自己与世俗之间划出了一道界限。他的诗中,时常隐隐流露出对当时日益卑下的世风的忧虑。四十五岁时所作的《游南洞》诗,中有四句:“天生两洞为先生,渡艇当门尤巧设。世惟富贵天不知,此意难与俗人说。”表达了对唯知富贵的浅薄世风的不满和鄙夷。但其中还潜藏着更深的一层涵义:俗人无法理解上天造物的美意,则此番美意似专为我一人而设。然天公的本意又岂是单单眷顾我一人呢,他实不知自己的美意会被世人所辜负啊!这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在“俗人难说”、“天公不知”的悖论中显得更加孤独和悲凉,仿佛自己成了苍天与俗世间茕茕孑立的一个醒客。而在另一首《中元节·食子行宅》中,郑珍轻时俗、重情义的性情再一次表露无疑:“盂兰俗节世所重,买肉尝鲜世所共。穷来说食真膏肓,昨饱季家今饱仲。”诗人一开头便大声宣布盂兰节是俗人的节日,自己并不看重。但弟弟们轮番宴请的盛情却让自己在大饱口福之余又深感不安(先生性节俭)。接着,诗人便由时俗想到了那良俗美序的上古时代:“周公为民制嘉礼,首曰饮食亲兄弟。笑杀邻家比屋居,叔侄终年不相视。”而再看看自己家,“疏疏微雨过竹间,雏孙泥膝催祖还。男迎女送踏歌去,月似车轮上远山。”这是何等其乐融融的家庭场面啊。由俗节而遥想嘉礼,又由嘉礼而陶醉于亲情,盂兰在世人那里是祭祖先、拜鬼神的盛会,而到先生那里,却成了置家宴、享天伦的契机。可见,先生不仅有着屈子般“众人皆醉而我独醒”的抗俗精神,更有着“返俗归淳”的醇儒性情。
三、绝俗的审美
除了在论诗、性情上持守“脱俗”、“抗俗”的精神之外,先生在审美情趣上也处处体现出相同的旨趣。如在论书法时,他就对当时盛行的字体甚是不满:“俗书两行镌墓前,知是康熙庚辰年。”“万古收藏正气地,岂是牧儿刍竖场?”[6]这是抨击低劣的时尚与墓主人超迈品行间的不对称 (墓主人正是前文提到过的何腾蛟)。而当女婿赵廷璜求教书法时,他给出的六句真言是:“要之书家止在书,毛颖自是任人使。多闻择善圣所教,少见生怪俗之鄙。学古未可一路求,论字须识笔外意。”此六句不仅适合于论书法,更可推而广之,应用到诗,到画,到一切学问艺术乃至做人上。先生由批评俗人眼光狭隘,少见多怪,而提出多闻善择、不拘一路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也可视为其追求“不俗”的方法论总纲。又如谈到绘画,他对某位画师的评价是:“吾知画师非俗工,直以浩气还太空。”[7]俗与不俗,也成了衡量画手技艺与境界的第一标准。再如,论及文物收藏,身为西南著名金石家的他,曾为汉代卢丰碑费尽心思、考镜源流,并亲自挑选健者“三往三复”前取此碑而不得,最终连亲弟弟都派上了。可见他绝非一般的“金石发烧友”。而如此劳师动众的理由,在《腊月二日遣子俞季弟之綦江吹角坝,取汉“卢丰碑”石,歌以送之》一诗中有过明确的解释:“委閟夷村世莫识,时有野衲来焚香。数年敲火已剜角,不即收拾愁毁伤。定武石易薛道祖,《熹平经》攟龙图张。子云俗楷一‘萧’字,尚有竭产夸珍藏。况兹隶古又完物,蛮叟岂足传芬芳。”一言以蔽之,保护文物古迹不为俗世所蒙覆、所毁坏,既是士大夫之传统,也是其责任所在。换言之,士大夫的责任即在于发现、保护和传承一切蒙尘蔽俗的美好事物。
提到审美情趣,最后不得不提的是郑珍对梅一如既往的欣赏:“自怜此花极似我,众人未醒先开门。何异桃李方熟睡,汝独笑与冰雪言。”[8]这首诗也许道出了他喜欢梅的最大理由:性情相似。据笔者统计,《巢经巢诗钞》中以梅为题或间接提到梅花的作品有十七首。先生以梅寄托爱情、友情、母子情、师生情乃至象征家运 (房前那一棵祖梅),一朵梅在他笔下涵义无穷。而众所周知,高标逸韵的梅,在宋诗、宋词、宋画中都是极重要的描写对象,可说是宋人不俗精神的一种集体象征。先生如此喜爱梅,一生咏梅不辍、甚至亲手莳梅,当然也撇不开对不俗精神的认同与继承这一层因素。除了梅,他还栽竹咏竹,即使被人误解也毫不介怀:“清绝王子猷,所在辄莳竹。世人黄金目,此君那肯瞩。前日负三个,自家种阶足。道远瘁其叶,紫玉自森肃。悠悠栽植心,取笑任时俗。”[9]竹和梅一样,也是宋人世界中不俗的代表。诗中的王子猷,和苏东坡不都是“何可一日无此君”吗。当然,作为园艺能手,郑珍的花草世界里还有许多其他品种,但无一例外都故意绕开了时下的流行。如世人喜盆花而厌桃李,先生偏以崇尚自然而力捧后者:“世喜盆花卑且樛,可惜根株一生囚。当年若出置平地,至今观之皆仰头。世喜奇花竞新丽,桃李寻常不省记,岂知香色随水空,何似冰盘荐圆脆。”[10]此外,他还一针见血地道破那隐藏在世俗流行背后的大众审美心理:“世间随事失真朴,时尚草木纷如麻。……喜奇厌正自俗态,庄丽久已输夭斜。”[11]可见,在郑珍的审美眼光中,庄丽与俗艳,真朴与时尚,乃是雅俗之判、云泥之判。
四、结语
上文通过诗歌释读,从诗学、性情与审美三方面发掘郑珍精神世界中“不俗”的丰富内涵,概言之可归结为以下四点特征:诗学理想尚自立、厌庸俗;人格建构崇高义、哂庸俗;世风批判喜真朴、恶浇薄;以及审美旨趣重庄丽、轻时俗。就内涵而言,这已然溢出道咸、同光宗宋诗人的论域之外,以性情为根本,辐散到思想、道德、情趣等各个方面;就形式而言,郑珍的不俗观也因其诗性的载体而显得冰水浑溶,不落窠臼,比起别家的诗论诗话诗序来,更显气韵丰满、耐人寻味。当然,需要指出的一点是,郑珍从未有意要构建某种文学观念,或为某种思想派别张目,处于近代化前夜的他仍只是一个传统学人、一介古典诗人。更何况诗在他的实际生活中还只是“余事”,这也就决定了他的诗学思想、人文精神大多散落在其众多篇什之中,如清晨荷叶晨露,如草蛇灰线,需要人们的细细品读和悉心整理,这与后世文论家们连篇累牍、随心挥洒出来的文学宣言是很不相同的。
明乎此,我们不禁又要问,郑珍的不俗精神,究竟源自何处?众所周知,郑珍一生困守西南穷乡僻壤之间,除了几次赴京赶考的经历外,鲜有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如此闭塞的环境是如何造就如此自立不俗的精神气象的呢?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三。首先要归功于郑珍之师程恩泽。程恩泽对郑珍最大的影响是他取法昌黎、山谷,融汇唐宋,合性情学问于一体的诗学倾向和他“以学为诗”并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于一体”的“学人之诗”。而其中“性情第一”与“宗宋”的取向为郑珍的不俗世界奠立础基。宋代士林有一种普遍的群体性自觉,一种建立道德人格主体的共识。“不俗”乃宋人时代精神标志之一。何绍基的不俗论即从宋人黄山谷出:“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12]这是人格上的不俗论。而以不俗论诗亦自宋人始。起初是指言语上的浅俗。《六一诗话》引梅圣俞语:“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其后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甚至论诗主唐的严羽等人都有过论述。③明人诗话中偶有涉及但所论泛泛,至清代宗宋诗风渐兴时又被再次挖掘出来,且在清末被同光体抬到诗学纲领的位置上。可见,郑珍的“不俗”观正出于这一支脉络,直接导源是宗宋恩师程恩泽。其次,从郑珍个人经历与性格起伏蜕变的过程来看,“不俗”精神也是其走向成熟的必然。随着早年出仕热情的屡屡受挫,随着对社会官场黑暗实相的体会加深,其人生取向也逐渐由庙堂而山林,尤其是其母亲黎孺人死后,郑珍更是绝意仕进。再加上贵州蛮荒之地,文化水平普遍低于京师、江南、中原地区,知音的匮乏,文人圈子的狭小,也在客观上加深了郑珍内心的孤寂感。而独来独往、直起直落的不俗精神恰可以助他砥砺气节,葆存勇气,以免被地域和文化上的边缘感以及时代的世俗化浪潮所吞没。这也是他为何四十岁始为“不俗”之论,其后又一发不可收拾的原因。最后,不得不指出的是,包括郑珍在内道咸宋诗派和同光体诗人们之所以高举不俗大旗,也是出于末世文人张扬个性的需要,出于一种宏观的文化关怀与社会意识。诗人在政坛的污泥浊水与诗坛的陈腐空气中如何重扬士大夫的人格精神,不与世沉浮,不苟营利禄,“不俗”的精神确乎可以成为保持文化清醒、寻找学术自由的一方宝剑。
[注 释]
①同光体诗论家陈衍把《巢经巢诗钞》尊为“生涩奥衍”一派之弁冕;汪辟疆认为:“故同光诗人之宗宋者,辄奉郑氏为不祧之宗。”(《汪辟疆说近代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 25页。)而钱仲联先生也说过:“同光体诗人,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之帜,力尊《巢经巢诗》为宗祖。”(《论近代诗四十家》,《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 408页。)
②程恩泽《金石题咏汇编序》:“或曰,诗以到性情,至咏物则性情绌,咏物至金石则性情尤绌。虽不作可也。解之曰:诗骚之原,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费。世有俊才洒洒,倾倒一世,一遇鸿章巨制,则瞢然无所措,无它,学问浅也。学问浅则性情焉得厚?”《程侍郎遗集·卷七》,《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 143页。
③如苏轼《于潜僧录筠轩》:“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黄庭坚《题意可诗后》:“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宁用字不工,而不使语俗。”陈师道《后山诗话》:“宁拙勿巧,宁朴勿华,宁粗勿弱,宁僻勿俗,诗文皆然。”即便力主唐诗的严羽也在《沧浪诗话·诗法》中大力反俗:“学诗先除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
[1]何绍基.东洲草堂文钞 (卷三)[A].近代中国史料丛刊[M].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
[2][3]陈衍.石遗室诗话[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99,314.
[4][5][6][7][8][9][10][11]郑珍.巢经巢诗钞[M].
[12]黄庭坚.山谷别集 (卷十)[A].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3]程恩泽.程侍郎遗集(卷七)[A].丛书集成初编[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5.
[14]汪辟疆.汪辟疆说近代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5]钱仲联.论近代诗四十家[A].当代学者自选文库·钱仲联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