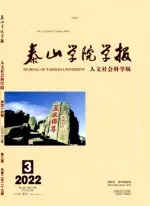赵沛霖《诗经》研究述评
2010-08-15林祥征
林祥征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赵沛霖(1938-),中国诗经学会副会长、原天津社科院文学所所长。有关《诗经》的专著有《兴的源起——历史积淀与诗歌艺术》(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诗经研究反思》(天津教育出版社,1988年);《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研究——20世纪诗经研究史》(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6年)。另有《八代三朝诗新选》、《追寻祖先的起源——漫话图腾》、《屈赋研究论衡》、《先秦神话史论》等。他是当代先秦文学研究大家,《诗经》研究的成绩更为卓著。21世纪《诗经》未来的发展方向在哪里?人们正在摸索与探讨,赵氏的研究可提供有益的经验。遗憾的是,当代学界“明察秋毫而不见舆薪”,对他的评论很少,形成《诗经》研究的一个盲点,本文希望对这种缺憾有所弥补。
一、对《诗经》学史建构模式的超越
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诗经》学进入 20世纪,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走上了现代《诗经》学的历史新阶段,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也存在着不足与问题。面对 20世纪《诗经》研究的反思与总结,就成为学界的重要课题,同时也是 21世纪《诗经》学的迫切要求。赵氏出于学术的责任感,及时推出《现代学术文化思潮与诗经——20世纪诗经研究史》(以下简称《思潮与诗经》),率先从史的角度对 20世纪《诗经》研究进行全面科学地总结:该书由 1.绪论 2.《诗经》学的传统与转型3.疑古辨伪思潮与《诗经》研究 4.唯物史观与《诗经》研究 5.极“左”思潮干扰下的《诗经》研究 6.文化意识与《诗经》研究 7.《诗经》学术史的勃兴8.文化人类学与《诗经》研究 9.20世纪考古发现与《诗经》研究 10.现代学术意识与《诗经》传注训诂 11.大众化意识与《诗经》白话文翻译 12.开放意识与《诗经》的海内外学术交流 13.现代《诗经》学的学科建设等专题组成。英国作家福斯特有篇小说叫《带风景的房间》,13个专题犹如 13个“带风景的房间”,从中可以窥见 20世纪《诗经》学的不同的“景观”及其发展脉络,同时也可以看到对《诗经》学史建构模式的超越。
所谓传统学术史的建构模式也称“列传式”建构模式,它以学者为基本单元,以学者的生平简介,加论著分析评论为研究重点,以学者及其论著的时间顺序排列形成学术史的历程,并通过不同时代,不同学者学术观点之间的渊源关系来梳理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由于这种模式如同古代史书中记叙人物行迹的列传,因而可称为“列传式”的学术史建构模式。从现存学术史看,不论是古代、近代、还是现代,不论是研究对象、内容、性质和特征的不同,通通采用这种模式,导致研究模式的僵化,而且很难反映 20世纪《诗经》研究的特殊路程。20世纪的《诗经》学与传统《诗经》学有着显著的不同的特点,即它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联系更加密切,我国现代历史上出现的重要的学术文化思潮总是很快地被《诗经》学所采纳,并在新的研究成果中表现出来,《诗经》学成为 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中一个最为开放最为活跃的学科。赵氏正是根据这个新特点,在学术史的建构模式上采用新的开放的模式,与传统模式区别开来。它在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大视野下,把握《诗经》学在现代条件下的嬗变过程。“列传式”模式所写的只是一个个学者,即一个个的点。由点到点的跳跃的历史难以连点成线,犹如词条的解释或内容提要,难以清理复杂的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和内在理路。赵氏从学术传统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对话”的视角,把握学术史的发展,可以抓住学术史的发展动力。例如 20世纪《诗经》研究的重担为何落在顾颉刚为首的历史家的肩上?离开当时的“疑古辨伪”思潮讲不清;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诗经》研究造成数千年研究史上空前未有的学术堕落,正是由于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所造成的恶果。20世纪后期的《诗经》“文化热”也与改革开放的“文化意识”有直接关系。唐人刘知几论写史要有“三才”,即史才、史学、史识。而“史识”是史书的灵魂,没有灵魂只能是一堆材料的堆砌。赵氏正是凭借其“史识”完成其学术史建构的超越的。
如果说《思潮与诗经》是一部反映 20世纪的《诗经》学史,那么《诗经研究反思》则是一部从先秦到现代的《诗经》学史,论述自汉代至 20世纪80年代的《诗经》学术进程,论述各家对《诗经》各类作品(如祭祀诗、宴饮诗、史诗、农事诗、战争诗、怨刺诗和情诗等)和基本问题(如《诗经》分类,诗乐关系、《诗序》的作者、比兴及艺术成就等)的观点和见解,追踪学术发展脉络,评断问题争端,力求为《诗经》研究找出具有时代高度的新起点。这部对《诗经》进行文学分类基础上的《诗经》文学学术史,从建构模式看,也与以学者为基点的“列传式”学术史区别开来。英国著名哲学家培根谈到学术史的重要时说,学术中如果没有学术史,“那就如同波利菲穆 (独眼巨怪)没有眼睛一样,这就缺乏那种最足以代表人类精神和生命的东西。”[1]赵氏的两部《诗经》学术史也具有这样的价值,他为《诗经》学带来一双雪亮的眼睛,更好地认识现实,更清楚地展望未来①。
二、《诗经》研究的深化与开拓
创新是学术的原动力、火车头。在先秦文学研究领域,赵氏是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它不仅表现在学术史的建构上,也表现在诸多有创造性的学术成果上。《兴的源起》——书从发生学的观点研究“兴”的起源与原始宗教的关系,及对我国诗歌艺术发展的影响。指出《诗经》中鸟的兴象具有祖先观念的意义;树木兴象具有宗族乡里观念的意义;龙、凤、麒麟等兴象具有国祚安危祸福等观念意义。并在此基础上,论证了作为形式范畴的“兴”起源的本质。迄今为止,学者对《诗经》中的“比兴”作了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从发生学的角度研究“兴”的起源,始终无人问津,《兴的源起》正好填补了这一空白。诗歌的起源与发生学的研究属于艺术起源的研究,是艺术学和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西方自 19世纪以来即开始了艰苦的探索,却很少有真正价值的研究成果。毕生从事于艺术起源研究的德国著名学者格罗塞曾把这一课题称之为艰难的“远征”。在这种情况下,利用《诗经》中的原始文化因素,和古代文献进行诗歌艺术发生研究,比用当代的原始诗歌去以古证今的作法更为可靠,它对人类艺术史、美学史和原始文化研究都有重大意义。难怪该书被李泽厚收入《美学丛书》之中,同时也彰显《诗经》作为民族文化原典的宝贵价值。
赵氏的学术目光明澈而深邃,善于在司空见惯的地方发现新的成长点。谁也没能像他那样发现屈原放逐江南,创作了宗教神话诗《九歌》,使他“于两千多年前即已走上了现代学者引以自豪的文化人类学研究道路”,从而使屈原成为杰出的神话采集、保存和加工者的新结论。[2]在一般研究者的眼中,《诗经》属于现实主义的作品,不可能有神话学的价值,但在他的《先秦神话思想史论》中,从《诗经》的神话学潜在价值、《诗经》的神话学文献价值、《诗经》的神话思想价值等方面,论证了《诗经》神话学价值,有理有据,令人耳目一新。由于人们认识的片面性,以为极“左”思潮干扰下的《诗经》研究充满着谬误和荒诞,没有学术价值可言,造成了学术界对这一段在《诗经》学术史上肆虐一时、危害巨大的错误观点及其发展历程始终保持缄默,赵氏指出“错误的东西有错误的价值,可以从反面为我们提供借鉴,把学术史上一切错误的东西都排除掉,学术史也就不成为学术史了。”由此他在《思潮与诗经》一书中列专章加以评析,收到好的效果。古人说,授人鱼不如授之以渔。赵氏很注意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与推介,在《思潮与诗经》中,对王国维开创的“两重证据法”的发生、发展及其价值作了深入的论述,对海外学者科学研究方法的总结也是该书又一个亮点,为我们送来一股清新的异域之风②。
三、可贵的学术品格
(一)严谨求真的现代科学精神
进入 20世纪,以科学观念和科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学术意识逐渐取代传统学术意识而成为研究的主导,并使《诗经》研究发生了全面深刻变化。赵氏自觉地把现代学术意识贯彻于研究之中,首先表现着严谨求真的现代科学精神。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概括学术史的四个基本条件,其中第一条是:“叙一个时代的学术,须把那时代重要各派全部网罗,不可爱憎去取”。在《思潮与诗经》一书中,不光把国内的相关资料全部网罗,而且把海外的有关著述也纳入视野之中,而且列专章加以讨论,并由此得出现代《诗经》学已是世界性学术的新结论。这使我们在看到赵氏成功的同时也看到一位求实的学者在资料搜集整理和分析上所付出的艰辛,以及开放的心态,世界的眼光。对胡适所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向来多持批判态度,赵氏则认为“它实际是一种依据大量证据研究具体现象,并以求真为目的的实证研究方法”。他的说法不仅有理,而且让我们看到不随风转舵,坚持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20世纪《诗经》白话文翻译盛况空前,构成了 20世纪《诗经》学园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然而由于学界对大众化读物重视不够,使之边缘化。赵氏慧眼独具,列专章加以讨论,填补了20世纪《诗经》学史的一段空白。正是得力于这种优良的学术品格,才使我们看到一部能够反映20世纪《诗经》发展全貌的具有科学精神的学术史。
(二)真诚的理性的批判精神
一般说来,学术史的任务有三:1.揭示学术观点的源流变化;2.总结学术研究的发展规律;3.对学术成果得失进行评估。赵氏的批判精神主要表现在第三方面,在《思潮与诗经》一书的每一章里,总有“存在问题与不足”这一栏。对研究的问题进行清理,对错误进行批判。在肯定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用唯物史观观照,才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林按:指《诗经》的思想内容)如此丰富和广大”之后,指出该书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把学术研究用于政治斗争服务的始作俑者”,批评其“套用现成理论,忽视特殊性的研究”等缺点,提出了一个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研究对象如何“对话”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批判“四人帮”文化虚无主义和专制主义所造成的祸害时指出:“极左”思潮支配的《诗经》研究,目的就是要毁灭《诗经》及其研究!“文化”的存在竟以毁灭自己为目的,只能证明它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敌人。言辞不可谓不激烈,但很深刻。在中国历史上,对当代的最高领袖的错误敢于直面批评的,除了司马迁,很少有人敢于这样做。在该书里,我们看到赵氏也是这样做的,不为尊者讳,不为爱者讳,表现了极大的学术勇气和锋芒。赵氏的研究表明,有良知的学者是社会科学的批评家和领路人。在新世纪,应该强化批评意识,应该带着一种觉醒的独立人格和历史感走进各自的领域,完成历史赋予的使命。
(三)丰厚的理论素养
读赵氏的书,就像听一位睿智哲人的谈话,他分析问题高屋建瓴而又鞭辟入里,又如小李飞刀,很少虚发,原因何在?早在“五四”时期,刘半农就指出:“处于现在的时代,非富于新知,具有远大的眼光,断断没有研究旧学的资格”。(《复王敬轩书》)所谓“远大的眼光”,就是宏观的视野,落实到赵氏就是具有世界的眼光,把《诗经》研究放到世界学术的体系中,从世界学术的高度认识《诗经》学的发展;所谓“新知”,就是新的科学理论知识。在赵氏的知识储备库里,哲学、史学、文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神话学等都相当丰厚,《思潮与诗经》里批评有的学者把甲骨文“斤”(斧子)误释为男性阳具,有理有据,没有深厚的甲骨文学、古文字学的修养是做不到的。没有丰厚的理论思维,《兴的源起》、《先秦神话思想史论》等著作也没法写。恩格斯说:“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研究的最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正是凭借理论思维,才使赵氏的研究具有前沿性和科学性的特征,才使赵氏成为当代《诗经》学的引路人。
(四)两点反思
西方有句谚语:每个人都是上帝咬一口的苹果。意思是每个人都有局限,不可能完美无缺。对于学术问题也应作如是观。《思潮与诗经》采用的是开放型的建构模式,只能把每一个学术精英及其著作分属于不同的专题,不可能像列传式的建构模式那样构筑一个人物谱系。梁启超说:“我们读《明儒学案》,每读完一案,便觉得这个人的面目活现纸上”。(《中国三百年学术史》)这是开放型学术史建构模式难以达到的。由于该范型着重于《诗经》研究与时代学术文化思潮的对话,对以审美为中心的内部研究较为薄弱。这就提出一个能否把两种模式结合起来的问题。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被誉为“开放型”建构模式的滥觞,但它既有学者的专论,又顾及文化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影响,可供借鉴。其次,《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诗中的“鸿”字,闻一多于1935年 7月,发表《诗新台鸿字说》(《新华学报》1935年 7月)一文,释“鸿”为“蟾蜍”,哄动一时。但闻一多先生后在《说鱼》中用“仍以训为鸟名为妥”加以修正。然而,夏传才先生《诗经研究史概要》认为闻一多“自我否定并不正确”。赵氏在《思潮与诗经》中也对闻先生的新说给予高度评价:“闻一多对‘鸿’的训释更体现致密和周严的现代科学精神的突出例证。”那么,到底是闻一多的新释对呢,还是他的修正对呢?对这一桩小小公案,我们认为还是闻一多的修正是正确的,因为诗中“鱼网之设,鸿则离之”是种颠倒错乱之象,比喻目的与效果的不一致。这种意象在《楚辞》中也常见。须知比喻只取一点不及其余,了解这个特征,闻先生的修正就好理解。何况闻先生也把“籧篨”、“戚施”的意象都释为“蟾蜍”岂不重复?也不合《诗经》的诗例,因为一首短诗的一个意象不可能用三个异名。
[注 释]
①杜书瀛在《文艺创作美学纲要》中指出;一位真正的杰出的作家“总是表现前所未有的‘第一次’的性质,是在这之前世界上从未出现过的,甚至连他的语言和表现手法也是未曾见过的。总之,这一切都是作家的精神创造物,是他第一次带到这世界上来的,为这世界增加了新的精神因子”。(辽宁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 20页)这里讲的是创作,但也适合于学术研究,赵氏正是凭借许多学术成果的“第一次”,为现代《诗经》学增添了新的“精神因子”,并成为当代《诗经》学界主流学术的代表人物。
②中国学术史有一个特殊的规律;许多新的学说、新的思想产生于对经典的诠释之中,从而使学术得以发展。赵先生通过对《诗经》的诠释,提出许多新的思想,推动了《诗经》研究的发展,更可贵的是,他的研究已经形成一个学派,即“学术文化思潮派、”,这个学派滥觞于梁启超,完成于赵沛霖。它以时代学术文化思潮为切入点,以现代的、开放的、世界意识为其主要学术特征,从而与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以夏传才为首的“唯物史观派”区别开来。它是《诗经》园地里,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而盛开的花朵。
[1]培根.论学术的进展[A].哈鲁滨孙.新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
[2]赵沛霖.先秦神话思想史论[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