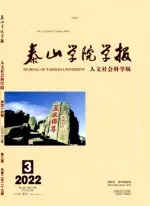“红色经典”视域中的俄苏文学
2010-08-15田承良
田承良
(泰山学院汉语言文学院山东泰安 271021)
回眸 20世纪的历史天空,物换星移,波谲云诡,“红色”被放大成为“无产者”政治革命的一个标志,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激情和理想的鲜明的记忆。在文学温情的目光注视下,“红色叙事”形成了革命理想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的史诗性追求。作为红色政权生成的最早的苏维埃国家——前苏联,不仅成了红色革命的策源地,也成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红色经典”最直接的借鉴范本。
一、当代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弥合与疏离
中国与俄罗斯有着长长的边境线接壤,历史文化也有着深远的渊薮关系。早在清末民初,梁启超、王国维、辜鸿铭、鲁迅、周作人等人就从不同角度对俄罗斯文学进行了绍介,尽管这些绍介缺少学理性的梳理和提升。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对中国这个古老的“积潭”产生了一种冲击。1918年,李大钊写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热烈欢呼新的革命政权的诞生。同时,布哈林的著作《共产主义 ABC》英译本和其他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和报道传入中国,加深了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对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认识。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郑振铎的《俄国文学史略》、蒋光慈和瞿秋白合著的《俄罗斯文学》①两本俄国文学史著作。瞿秋白是最早去苏维埃俄国的人。为了全面、真实地介绍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真相,1920年秋,他以北京《晨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前往莫斯科。1921—1922年,他写了很多通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维埃俄国作了热情、真实的报道。这些作品分别收入《俄乡纪程》(又名《新俄国游记》)和《赤都心史》两本书中。192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的俄罗斯文学研究著作明显增多,涉及的学术领域比较宽广,并出现了一批系统性、学理性较强的文章。
20世纪 30年代,贝灵著、梁镇译的《俄罗斯文学》,由商务印书馆发行,中华民国二十年四月初版。1947年 12月,晋察冀新华书局印订了《苏联文艺问题》,重点介绍了苏联文艺的观念和创作的目标任务。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与俄苏的关系时好时坏,在文化文学的交流上也是微妙多变。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有着割舍不断的联系,红色的政治谱系决定了两国的文学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会淡出相互的视野。1950年代以来的一代代中国青年,从保尔·柯察金的英雄行为中吸取了无尽的力量。富尔曼诺夫的《夏伯阳》(《恰巴耶夫》)、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科斯捷米扬斯卡娅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等苏联红色作品,同样对中国青年起到了巨大的教育作用。
1950年代,俄苏文学研究在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中居于前沿或热门,但这时的研究侧重于苏联当局当时认可的文艺理论和作家作品,多采用政治划线与阶级分析的方法,政治热情代替了文本分析,理论描述附着于社会批评话语,没能进入文学审美性特质的分析。
1950年代中期,中国文论界提出的“干预生活”的文学主张是对“歌颂与暴露”禁区的一次突围。“干预生活”思潮的产生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它显然是 1950年代苏联文艺思潮影响和刺激下的产物,也与 195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文化政策的一次短暂调整有关。当时,文艺创作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因建国初期几次大的文艺批判运动——政治对文艺的干预导致文艺创作与批评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粉饰生活,回避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重大矛盾。针对这一现象,1956年,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为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科学与文化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为中国文学接受苏联“干预生活”文学思潮提供了较为宽松的气氛。“干预生活”是在 1956年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上一些同志提出的,倡导者认为:作家不能也难以无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阴暗面,“干预生活”就是要研究生活,思索和解释生活,对生活有所行动。即作家应该以主人翁的姿态,勇敢地去探索现实生活里的问题,把它们揭示出来,给腐朽、落后的事物以狠狠鞭挞,并且呼唤与鼓舞人民与种种阻碍我们事业前进的丑恶现象作斗争,以推动历史前进。周扬在中国作协理事会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中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必须克服创作上的公式主义、自然主义及其他一切脱离现实主义的倾向。”“主张作家要积极参与社会生活,有政治和艺术的勇气表现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某种意义上,周扬为“干预生活”概念的流行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许可证。“干预生活”概念出现在 1956年是一个必然的文学事件,它本身也是“双百方针”的一项积极的成果。于是一大批“干预生活”的文学评论与作品在 1956年这个极其短暂的“百花”时代里绽放了。
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李国文的《改选》,耿简的《爬在旗杆上的人》,李准的《芦花放白的时候》,刘绍棠的《西苑草》,方之的《杨妇道》等。需要提到的一个细节是,王蒙的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中,主人公林震到区委组织部报到时,口袋里装着的一本书,就是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由此可见,这类作品和人物受到了俄苏“干预生活”的影响。这些作品突破了只准“歌颂”不准“暴露”的禁区,在一定程度上大胆触及了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诸如官僚作风、教条主义、形式主义以及社会生活的各种矛盾冲突,从而体现了现实主义直面人生的精神,加强了文学创作反映现实生活的广度和深度。可是,由于“反右”扩大化,这批作品被错误地当成毒草批判,这批作家被错误地定为“右派”,口号被一些批评家指斥为修正主义理论,变成“揭露生活阴暗面”、“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同义语。
在中国,“干预生活”的文学评论与作品被打成“毒草”,作家们也被打为“右派”或“反革命”,直到 1979年,才得以平反,作品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以《重放的鲜花》为集子名出版。而在俄苏,“干预生活”的作品出现较早,延续较长,到 1957年,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发表,被看成是苏联五十年代中后期解冻文学的信号。这部小说是在苏共党报《真理报》上发表的,体现了政府对作家的支持。从此,苏联开始大面积出现反思社会黑暗的、反对官僚主义的作品。这种思潮持续到 1958年,后来以苏联另外一个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格医生》(参见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7年 1月版本)事件”为标志,苏联文坛又出现了冰封时期,但是,地下的解冻文学仍继续发展。直到苏联解体,意识形态冰块全面消融。中国与俄苏“干预生活”的作品命运可谓殊途同归。
1960年代,中国文学与俄苏文学的交流与研究迅速降温,政治领域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同时,文艺界也开始清算所谓的“人道主义”、“人性”等,肖洛霍夫的作品首当其中。“文革”十年,整个中国文化文艺沙漠化,中国与俄苏自然已没有正常的交流途径和学术研究。
中国文学进入新时期以来,拂去了历史的尘埃,纠正了政治上的悖谬,消除了意识形态话语的隔阂,中国文学艺术界对俄苏文学的研究全方位展开,以科学、严谨的态度与理性审视的目光,建构了俄苏文学研究的新的理论平台,涌现出了一大批具有广度和深度的综合性成果。
1980年代以来,在中国翻译出版了大约 300部苏联文学作品。如帕斯捷尔纳克、瓦西里耶夫、阿布拉莫夫、格拉宁、阿赫马杜林娜、杰缅蒂耶夫、沃兹涅先斯基、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兹宾、艾特马托夫、维索茨基等人的诗歌,别洛夫、贝科夫、杜姆巴泽、科列斯尼科夫、拉斯普金、特里丰诺夫、舒克申等人的散文。格拉宁的《奇怪的生活》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推荐为中国青年必读书籍。另外,中国文艺界还创办了《苏联文学》、《当代苏联文学》、《俄苏文学》等文艺刊物,专门发表苏联作家的作品,进一步扩大了俄苏文学在中国的地位和影响。
几十年来,热心于俄国和苏联文学介绍研究的不计其数。瞿秋白、鲁迅、郭沫若、茅盾、夏衍、郑振铎、巴金等是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热爱者和积极宣传者,也翻译了许多作品。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从事文化领导工作,也翻译了一些作品。曹靖华、戈宝权、赵洵、萧三、汝龙等很早就开始俄国和苏联文学作品的翻译。1987年 3月 31日和1988年 6月 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分别授予曹靖华、戈宝权“各国人民友谊勋章”。另外,中国对苏联文艺的介绍极为宽泛,包括根据俄苏文学作品改编的许多影视剧②。为中国全面了解俄苏文学艺术的发展动态提供了多维的参照。
总之,由于地理环境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原因,中国文学界和苏联汉学界在整个 20世纪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文学六十年中,相互介绍和研究了大量的两国的经典文学作品以及相关理论著作。在互动的学术交流和创作活动中,推动了两国文学事业的发展③。从这个意义上说,俄苏文学是中国当代“红色经典”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和一个重要研究视点。
二、俄苏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对当代中国“红色经典”的标本意义——以《静静的顿河》为例
俄苏“红色经典”是指在俄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史上,一批在特定时代出现的、具有政治革命色彩的俄苏文学名著。这些作品从 20世纪 20年代末起被译介到中国,对左翼文化运动、延安革命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并在 1950——1960年代“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意识形态背景中被经典化、被工具化。
俄苏具有强烈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一向对中国读者有很大的吸引力。抗战时期,以萧军、萧红、舒群、李辉英、端木蕻良、罗烽、白朗等为代表的东北“流亡作家”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接受了左翼绍介的俄苏战争文学的影响,渲染了一种民族抗争的悲壮和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这类“抗战小说”的代表作品有萧红的《生死场》、《呼兰河传》,萧军的《八月的乡村》、《第三代》,李辉英的《最后一课》、《松花江上》,舒群的《没有祖国的孩子》,罗烽的《呼兰河边》、《归来》,端木蕻良的《乡愁》、《大地的海》、《科尔沁旗草原》等。最富代表性的是《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等。
在整个 20世纪 ,肖洛霍夫是惟一获得价值评价标准大相径庭的斯大林文学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在苏联和中国,肖洛霍夫头上也有过许多顶或褒或贬的帽子,诸如:无产阶级作家,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杰出代表,人道主义者,乡土作家,富农阶级的代言人,苏维埃时代农民情绪的表达者,等等,构成了一个多面的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是肖洛霍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共分为四部,从 1926年开始直至 1940年,共用了 14年的时间才创作完成。这部作品一经问世,立刻受到国内外的瞩目,被人称作“令人惊奇的佳作”。此书于 1941年获斯大林奖金,1965年肖洛霍夫因此书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苏联作家。《静静的顿河》自问世以来,众语喧哗,莫衷一是,有过多种多样甚至完全相反的解读。这源于作品本身就是一种悖论性结构,叙述存在着多重话语:如“人道主义”话语、“真理”话语、“乡土”话语。这些话语常常相互置换,构成一种“对话”文本关系。各种声音杂然并存,使小说获得了丰富的的阐释空间。
在《静静的顿河》中,肖洛霍夫隐含着一个人道主义的主题,一方面葛利高里在痛苦地抗拒战争对他的人性的磨蚀和扭曲,另一方面,他在混乱的战争中一直在思考和寻找着战争的意义,身上有着超常的人格力量。肖洛霍夫对战争中戕害人性的残酷行为大加挞伐,不管其祸首是白军还是红军。葛利高里在历史的漩涡里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在个人与历史的对峙中,终于走向人生悲剧的终点。
这一形象后来在中国当代抒情诗人闻捷的叙事长诗《复仇的火焰》里——一个巴哈尔的维族青年身上得到了延续,在政党、民族、宗教的历史大背景下,巴哈尔也是一个性格多变的人物,比较中国当代文学十七年流行的二元对立的人物模式,有一定的突破,但因作品主题绾结于和平、团结,人物的丰富性、复杂性还是受到了限制,而且,巴哈尔最后归来,来自于爱情和正义的化身——美丽的女友苏丽亚的呼唤,作品在艺术追求上,没能走得更远。
肖洛霍夫后来又写了一部反映苏联 1930年农业全盘集体化这一巨大社会变革的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于 1930年动笔,1932年出版。这部作品尽量地反映了正在发生、发展着的生活现实的本来面貌,真实地再现了急遽变化着的伟大历史运动。第二部完成于 1960年,描写的时代虽然仍旧是 1930年的农业集体化时代,但是却更注意了对历史嬗变时期劳动人民的内心世界的细腻的刻画,有着叙述的精神维度。
《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最早是由周立波介绍到中国的,1949年,周立波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苏联的文学是战斗的,健康的。它号召我们斗争,它使被压迫的工农和革命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自己解放的前途和人类光明的远景,看到了灾难深重的自己民族的出路。十月革命及其以后的辛苦的和成功的建设,就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榜样。从苏联文学中,我们看到了这些情形的忠实而生动的反映,使我们读者,学习了很多的东西……我们遵照了毛主席的指示,把苏联文学当做我们的最好的先生。”[1](P713)他对作者作品的深刻了解也影响到他本人的创作,如他的获得斯大林和平奖金三等奖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既可以看出土地革命战争这一主题的延续,也可看出人物塑造上的隐形影响,如老孙头的形象,与《被开垦的处女地》中的西奚卡,显然有相似之处。以至于他在 1959年创作的反映合作化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给人印象较深的亭面糊老倌子仍不能摆脱西奚卡的影子。
《暴风骤雨》中的老孙头最有代表性。他走南闯北,见多识广,既开朗、诙谐,说话风趣,喜欢卖弄自己天南海北的知识,又喜欢打自己的小算盘;他渴望翻身解放,喜欢出头露面,可一旦遇到风险,又胆小怕事,畏畏缩缩。但他仍然属于农民中的正面形象。惟有从这个真实、生动的人物身上,人们才可以了解老一辈农民的典型性格特征。相对而言,小说塑造的地主形象韩老六、杜善人和唐抓子等形象就有些脸谱化了,凶恶成了他们的本质化特点。
更重要的是,由于主题的先行和受制于政策的观点,作家有意“省略”掉土改工作中发生的偏向,周立波认为,根据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点不适宜在艺术上表现”。[2]所以事实上作品给读者提供的土改运动的面貌必然是经过修饰了的“局部现实”。但周立波按照政策来“过滤”生活和他对革命现实主义典型化的理解却逐渐被奉为正宗。这就与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有了明显的区别。《静静的顿河》里,描写得最细致的是彭楚克在顿河革命军事委员会革命法庭当执法队队长期间,每天半夜到城外去处决犯人。由于在工作中执行了极左的政策,革命军事法庭往往草菅人命,被处决的人当中有很多是无辜的哥萨克劳动者,枪毙一些手上长满老茧的劳动者,这使彭楚克非常痛苦,干了一段时间后,他身心疲惫,精神恍惚,甚至丧失了性功能。有一次他歇斯底里地对女友安娜说:“所有的人都想走进灿烂的花园去,但是要知道,在种花和种树以前,先要清除垃圾!先要上肥料,先要把手弄脏!要清除垃圾,可是谁都讨厌这种工作!”后来彭楚克离开了执法队,他的精神和肉体才恢复了正常。作品对人性的深思使文本获得了凝重的品格。
俄苏“红色时代”的作品共同演绎着走集体化道路的时代主题,其中落后人物的被改造,更是中国作家奉为圭臬的叙事范本。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在反映波澜壮阔的土地改革运动时,就不同程度地受到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一类作品的影响,场面宏大,细节生动,尤其在西奚卡一类人物塑造上,可以看出创作上的异质同构现象。也因为如此,这类作品被从广泛意义上命名为“红色经典”。
三、俄苏“红色经典”对当代中国“红色经典”叙事精神的影响
(一)成长意义的教科书
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还有:《铁流》、《毁灭》、《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俄苏优秀文学作品。长篇小说《铁流》,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绥拉菲靡维奇(1863-1949)在1921-1924年间写成,小说以十月革命后的 1918年内战为题材,叙述了古班的红军——达曼军,带领被古班的哥萨克富农和白匪军残害的红军家属和被迫害的群众,突破叛乱者和白匪军的包围,进行英勇转移的事迹,反映了士兵群众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中,由乌合之众成长为一支纪律严明的“铁流”的过程。
前苏联作家协会主席法捷耶夫的《毁灭》(1927年)、《青年近卫军》(1945年,同名电影《青年近卫军》1948年)影响同样深广。《毁灭》是早期苏联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它同富尔曼诺夫的《恰巴耶夫》、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一起被称为苏联 1920年代文学中三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毁灭》不仅描述了游击队的战斗事迹,而且着重描绘了游击队员精神上的成长和性格的形成,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深刻性与浪漫主义的理想性。
《铁流》和《毁灭》、《青年近卫军》的出版,教育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走上红色道路,坚定了胜利的信心。至今,奥列格、邬丽娅式的英雄主义与理想主义并未消失。一代代中国人在重读俄苏文学经典中,汲取了精神的清泉,获得了成长的精神抚慰。中国的当代“红色经典”,大都有一个“成长”的主题,如《青春之歌》、《三家巷》、《小城春秋》、《战斗的青春》、《战斗里成长》等,青春的激情与成长的诉求构成红色叙事的突出特征。
同样的作品,还有《卓娅和舒拉的故事》,也是一个英雄成长的主题。教人如何在残酷的环境中变得坚强、善良和勇敢。作者柳·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是卓娅和舒拉的母亲,她用朴实的语言、流畅的文笔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姐弟俩从出生到牺牲的一幕幕生活场景。
(二)“成长”中的英雄——“夏伯阳”
在“红色经典”的叙述中,往往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演绎——那就是改造与救赎。改造是指对散漫的工人、农民的无组织、无纪律的游击习气和小生产者的自私狭隘作风意识的教育与改造,救赎则是指在这种教育与改造中的党政思想政治工作。“它的斗争,它的胜利……正在经过一条鲜红的血路,克服着一切可能的错误和失败,锻炼着绝对新式的干部。”[3](P166)这里面也隐含着“成长”的主题,只不过被改造者往往是“成长中的英雄”。这类形象影响最大的就是“夏伯阳”了。
《夏伯阳》是前苏联著名作家富尔曼诺夫的代表作,夏伯阳是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传奇式的英雄人物,根据俄罗斯国内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红军指挥员夏伯阳的事迹写成。小说描写的是1919年 1月至 8月在苏联东线上的战事。当时在东线战场上作战的,大多是由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夏伯阳师就是其中的一支。穿上军装的农民在夏伯阳的指挥下英勇善战,屡建奇功,可他们的作风却自由散漫。夏伯阳足智多谋、视死如归、战功赫赫,但政治觉悟需不断提高,对党的方针政策理解也不够。政委克雷奇科夫到任后,把夏伯阳引上了正确的道路,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成为一名富有传奇色彩的优秀军事将领。
小说后来改编成同名影片,中文片名为《恰巴耶夫》,由前苏联列宁格勒电影制片厂 1934年出品。1941年荣获斯大林奖金。
夏伯阳的形象在中国也是深入人心,当代中国十七年文学中,冯德英创作的长篇小说《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就是一个“中国的夏伯阳”;刘知侠的长篇小说《铁道游击队》中,游击习气的大队长刘洪也是在政委李正的帮助下才逐渐成熟起来的。可以列举的例子还有梁斌的《播火记》中的李霸沺。近年来,阅读率和收视率较高的长篇小说《亮剑》以及同名电视连续剧中的李云龙,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中的梁大牙以及同名电视连续剧中的姜大牙,也都有夏伯阳的影子。
(三)改造、成长与救赎——“父亲”符号的多重意义
拉康理论中的“父亲”,是文化的代言人和秩序的象征。在中国传统文化叙事中,作为独特的原型符号,“父亲”有着广泛、深刻的文化象征意义。几千年来,作为宗法制度、伦理秩序色彩浓厚的中国社会,家族成为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父亲”具有绝对的支配地位和话语权力。五四时代的“呐喊”声中,个性、人性的解放首先是摆脱父亲的解放,高蹈的青年用“反抗”与“出走”演绎着反封建的主题,“娜拉”们以后怎么生存是暂时可以不管的事;十七年时期,“父亲”成了旧的私有经济体制的落后代表,属于被改造的对象,如《创业史》中的“梁三老汉”形象,正当的个人利益被高悬的政治理念口号所漠视,“父亲”成为被审视和改造的对象,作品的主题往往是显示社会主义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围绕这一主题的滥觞,在其它当代文学主流叙事的作品中,也出现了一大批“梁三老汉”。如赵树理笔下的《李有才板话》中的“老秦”、《登记》中的“张木匠”、《小二黑结婚》中的“二诸葛”等,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中想买贫农张栓的地发家致富的翻身贫农父亲“宋老定”,梁兴晨的短篇小说《合家》中单独居住在果园里的父亲黄胡子,周立波的长篇小说《山乡巨变》中的不肯入社的老倌子陈先晋,等等,都是被激进的新生力量所审视、所改造的旧式农民父亲的代表。
当然,中国作家对苏联文学的创作观念的接受,不是一味照搬,也根据国情和时代的需要,作了潜性改造。这里试比较一下肖洛霍夫的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与梁斌的长篇小说《红旗谱》。
《一个人的遭遇》发表于 1956年底最后一天与 1957年的第一天的苏联的党报《真理报》上,是一部结构复杂的独特作品。小说作者立足于人本主义的立场,采用回忆中套回忆的叙述方式。小说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写索科洛在战争中的悲惨遭遇,而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写他战前的美满幸福和战后的孤独凄苦,这种鲜明的衬托和对比突出表现了战争和人的悲剧冲突,强调了战争和个人幸福之间的不可调和性,从而有力地表达出 1950年代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时代最强音。由此可见,小说表现的“人与战争”的冲突,层面上看,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深层看,却是个人幸福和民族利益之间的悖论。小说表现了长期被禁锢的人性、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反映了被长期忽视的非“英雄”的普通人的悲剧命运。
《红旗谱》酝酿于战争年代,1932年作者梁斌在二师学潮中参与护校运动。曾以其故乡发生的“高蠡暴动”为素材写过短篇小说《夜之交流》, 1942年创作短篇小说《三个布尔什维克的爸爸》及据此扩充成中篇小说的《父亲》。1957年出版长篇小说《红旗谱》,恰是肖洛霍夫发表小说《一个人的遭遇》的第二年。主人公就是作品一以贯之的“父亲”形象。但不同于肖洛霍夫作品的是,小说逐渐过滤了人道主义的悲悯之情,代之以高亢的砥砺发奋斗志和英勇牺牲精神,但作品的艺术韵味和文本内涵也因此被遮蔽或流失了。这类“父亲”形象不再是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作品中被审视、被改造的对象,而是在政治革命的进程中成长的“革命英雄”,“在血雨腥风的斗争中成为革命力量中坚”,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是新的社会秩序的代表权威与“正史”的合法叙述者。当然,“父亲”的形象最终也走向扁平化,类型化。
另外,充当引路人的在“红色经典”的叙述中也往往被隐喻为“父亲”——“精神教父”的形象。《红旗谱》中的贾湘农,在小说中即是一位更高意义上的“父亲”形象,如同电影中《红色娘子军》的洪常青,小说《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杨晓东,《青春之歌》中的江华、卢嘉川等,都担当了革命历史征程中的“指路人”或“救赎者”的角色。这在俄苏文学里也可以找到相应的参照,如《夏伯阳》里的政委克雷奇科夫,《青年近卫军》里的老布尔什维克——伏罗希洛夫州党委书记普罗庆柯和克拉斯诺顿地下区委书记刘季柯夫。但前者显得更为“纯正”,后者显得更为“本真”。人物符号意义并不完全相等。
结合以上例子来考察,“红色经典”叙事话语中的“父亲”的形象成了一个复合的符号,即“被改造者”——“成长中的英雄”——“革命的引路人”。中国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在参差对照中,获得了广泛的话语空间。
(四)血色中的浪漫
这些作品,往往在故事的结局中展示血色中的浪漫。如《毁灭》小说的末尾,作者描绘了一幅寓意性的画面。莱奋生的部队在又一次摆脱敌人的追击后走出森林,在他们眼前“呈现出大片高高的青天和阳光照耀着、四面都是一望无际的、收割过的、鲜明的棕黄色的田野”。远处打麦场上,劳动的人群在快乐、热闹地忙碌着。这个画面象征着革命的光明远景。打麦场上的人们将是革命的生力军。因此,小说没有给人留下凄惨的形象,却使人对革命的前途充满信心。同样,在中国当代“红色经典”作品“三红”中,作者同样渲染了流血牺牲中的光明前景,弱化了人本主义的悲悯同情。如《红岩》的结尾:
齐晓东仿佛看见了无数金星闪闪的红旗在眼前招展回旋,渐渐溶成一片光亮、鲜红……
炮声隆隆,震撼天地,
星光闪闪,迎接黎明。
林间群鸟争鸣,天将破晓。
东方地平线上,渐渐透出一派红光,闪烁在碧绿的嘉陵江上;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绚丽的朝露,放射出万道光芒。
如《红日》的结尾:
军首长们,许多指挥员们,红旗排,红旗班的英雄战士们,屹立在巍然独立的沂蒙山孟良崮峰巅的最高处,睁大着他们鹰一般的光亮、炯炯的眼睛,俯瞰着群山四野,构成了一个伟大的、崇高的、集体英雄形象。
又如《红旗谱》的结尾,写帮助张嘉庆逃到农村去的朱老忠:
他弯腰走上山岗,倒背着手,仰起头看着空中。辽阔的天上,涌起一大团一大团的浓云,风云变幻,心里在憧憬着一个伟大的理想,笑着说:“天爷!象是放虎归山呀”。
这句话预示:在冀中平原上,将要掀起波澜壮阔的风暴啊!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对中国的影响跨越了半个世纪,作品中保尔·柯察金的形象就教育和帮助了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走上革命的道路。1950年代,战争时期因研制兵工武器而多次负伤的残疾军人吴运铎,以自己的峥嵘经历写了一篇长篇报告文学《把一切献给党》,被誉为“中国当代的保尔”。1980年代,山东姑娘张海迪也被誉为女“保尔”。1999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被中国编导搬上荧屏,这类作品是按红色经典的系列作品拍摄的,它在主流文化和大众文化的互动中,吸引着老中青三代观众,并取得较高的收视率。由此可以看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怎样赓续了中国几代人的精神联系。
前苏联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着“崇高的英雄气概和浓郁的悲剧气氛相结合的结局和尾声”,[4](P128)用大量的细节和场面,描写了一群散发着青春气息的女兵,在战争绞肉机的威胁下,还怎样细腻深情地回味着青春的芳香、甜蜜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让人对浪漫和美好的毁灭产生无限的惆怅、绝望。爱情在战争巨大的阴影下,显出脆弱、扑朔和无奈;她必然是铁蹄下没有怜惜、没有呵护的娇弱的花朵。2005年 5月 6日,苏联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日。为了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60周年,改编自前苏联红色经典的 19集电视连续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于当天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档推出。在红色记忆中,复活的不仅是革命战争的壮丽画面,更有对人性的反思。剧作着重刻画正面形象,突出战争对人性的压抑,表现侵略战争对女性美的毁灭,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进一步探讨战争如何改变着人们对青春、对生命的理解。在对前苏联文化、时代背景等大前提的合理把握下,重新唤起一种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精神。将战争的残酷与生活的梦想,青春的绽放与生命的陨落交织在一起来写,延展了对血与火的战争的人道主义的思考。作品里,端庄刚毅的丽达,单纯浪漫的索妮亚,热情而稳重的李莎,富于幻想却轻浮怯弱的嘉丽亚、美丽机灵又清爽勇敢的冉卡……这些生动的形象让人们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
“红色”的战争文学跨越时空,在 21世纪仍凝聚与绵延着人类的人文主义的思考。
毛泽东曾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俄苏不仅对中国的政治革命产生过积极深远的影响,也对中国文化文学的演进时时产生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俄苏的革命和建设成为中国革命的参照范式,反映俄苏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也更易于在中国读者和观众当中产生共鸣。中苏 (俄)两国在现当代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中具有某种相似性或一致性,两国在文学观念、文学思潮以及艺术审美标准等方面也呈现出某种对应性。这种相似性和对应性,使中国人在接受俄苏文学时有一种心理上的亲近和时势上的认同,因而作为俄苏文学一个特殊组成部分的“红色经典”,在当代中国的接受中就必然产生超越文学意义之外的长期影响。“红色经典”视域中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将会不断成为信仰滑坡下的言说主体。
[注 释]
①195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契诃夫独幕剧集》。1960年,又出版了《契河夫戏剧集》。1950年代,我国剧院上演了《大雷雨》、《复活》、《万尼亚舅舅》、《三姊妹》、《带枪的人》等等。1960年代初,曾上演《以革命的名义》和当代著名导演奥·叶甫莫列夫执导的《永生的人们》、《我们一定胜利》等剧。1981年至 1987年,,先后上演过埃·布拉金斯基和埃·梁赞诺夫的讽刺喜剧《命运的拨弄》、盖利曼写的《家丑外扬》、《伊尔库茨克的故事》等作品。1991年,契诃夫的名作《海鸥》在北京公演。
②1930年代,由俄国文学名著改编的影片,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和屠格涅夫的《木木》,还有《生路》、《夏伯阳》等新片。新中国,东北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译制了大量苏联影片,如《夏伯阳》、《女政府委员》、《马克辛三部曲》、《普通一兵》、《乡村女教师》、《伟大的公民》、《彼得大帝》、《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攻克柏林》、《风从东方来》等。1980年代,苏联电影《合法婚姻》、《稻草人》、《这里黎明静悄悄》、《办公室的故事》、《两个人的车站》等影片在中国成功放映。
③参见山东泰山学院宋绍香教授所著的《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苏联汉学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译介与研究》一文 (原载《前苏联学者论中国现代文学》,新华出版社 1994年版;后转载于《岱宗学刊》2000年第 1期)。原文还列举了许多重要的俄苏汉学家的卓越成就。
[1]周立波.我们珍爱苏联的文学 [A].周立波文集(第 5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
[2]周立波.现在想到的几点[N].生活报,1949-06 -21.
[3]瞿秋白.俄国文学史及其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
[4]陈敬泳.当代苏联战争文学评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