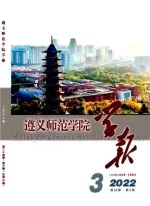论黔北仡佬族傩戏的语言风格
2010-08-15任正霞
任正霞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论黔北仡佬族傩戏的语言风格
任正霞
(遵义师范学院,贵州遵义563002)
黔北仡佬族傩戏是贵州傩戏的代表之一,其剧本中表现的民族语言性非常突出。文章从词语、句法、语音节奏和修辞等四个方面来论述黔北仡佬族傩戏剧本的语言风格,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黔北仡佬族傩戏;语言风格;形成原因
我国著名戏剧戏曲理论家黄竹三先生在《〈民族文学与戏剧文化研究〉序》中指出:事实上,中国各少数民族都有辉煌灿烂的文化。以文学而言,许多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英雄史诗和戏剧,少数民族戏剧丰富多彩、形态各异,尤其是各少数民族祭祀活动中演出的傩戏。贵州傩戏因其具有民族多、品种多、层次多、分布广、保存完整等特点,被学术界、艺术界誉为“中国戏剧文化的活化石”(庹修明《贵州傩文化》)。而黔北仡佬族傩戏是其代表之一,它同贵州其它民族傩戏一样,由能沟通人与天朝、地府的使者——掌坛法师主持傩坛仪式,向三界皇帝通报,各路神灵纷纷受命前来为主人“冲傩”或“还愿”。所谓“一傩冲百鬼,一愿了千神”,通过傩仪驱邪祈禳、消灾纳吉。在这样一个神、鬼、人交织的祭祀活动中,通过傩的宗教仪式和戏剧的表演,用傩戏这一有形的事物表达了共同的愿望、寄托了共同的虔诚、传达了共同的道德伦理准则、愉悦了人们的心灵。傩戏不仅娱神还娱人,在傩戏表演中往往有贴近生活、内容短小、生动诙谐、说唱歌舞结合的插戏,比如传说神怪故事、演义历史人物、书写人间俗事等。这使得戏剧的本质不断凸显,娱人的目的更加突出。因此,依托于宗教仪式的傩戏,不但高扬天国神灵,也肯定世俗肉体,体现人神平等,和谐相处;它让人们从恐惧、压抑、不安、痛苦中走出来,再度获得生存的条件和生活的信心,从而心灵自由、心情愉悦,给人们以崇高的审美享受。傩戏这一原始的戏剧,它表现出先民的粗犷、直朴,给人震撼心灵的原始崇高感;同时也表现出通过插科打诨宣泄对传统观念不满的喜剧美。这对立而又统一的审美感受,从戏剧剧本出发,是通过傩戏简洁、平实、明快、诙谐的语言风格表现出来的。
一、黔北仡佬族傩戏的语言风格
高尔基说:“戏剧是语言的艺术。”戏剧主要是通过人物语言,展现人物性格特征,展开故事情节。人物台词,是剧中人物的语言。其表现形式有:对话、独白、旁白、内白等。傩戏因其非常特别的表演者、对象、内容和目的,因而形成特殊的语体。这一特殊的语言表达功能体系,通过语音、词汇、语法、修辞方式等等语言因素,以及一些伴随语言的非语言因素表现出来,使傩戏呈现出口头语言的特征。下面从词语、句法、语音节奏和修辞方式等四个方面来具体分析黔北仡佬族傩戏剧本的语言风格。
(一)多运用乡音土语和固定俗语
通俗是戏剧特别是傩戏的首要特征和客观要求,因此傩戏多用口语词、方言词、俚俗词,使用乡音土语,语气朴实亲切,有巨大的表现力和浓厚的生活气息。俗语有惯用语、歇后语、谚语等,是人们在实践中的经验教训的提炼和总结,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它反映了人民生活经验和愿望,对后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和警戒作用。其形式活泼生动,常用来比喻一种事物或行为,具简炼、通俗、含义深刻或幽默风趣的特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
1.乡音土语
语言具有地方风味是民间戏剧普遍的特点。运用方言土语,使其表演更加通俗活跃、幽默、明快,收到特殊的戏剧效果。黔北仡佬族傩戏中多用口语词、方言词、俚俗词等乡音土语,如名词:“发挂”(面条)、“包包”(肿块)、“长年”(长工)、“扯豁闪”(闪电)、“开山”(斧头)、“荒瓜”(南瓜)、“二回”(以后) 等;动词:“默倒”(常作以为,还以为解)、“交接”(商量、约定)、“焦人”(羞死人)、“转去”(回去)等;形容词:巾巾吊吊、藤藤网网(均指破烂不堪)、“灰巴拢耸”(满身粘灰,很脏)、“趴活点”(舒适)等;副词:“老实”(确实是)、“断筋”(完全、硬是)等;代词:“啷个”(哪样,怎么);“哪一歇”(什么时候);“高上”(上面);“各人”(自己)等[1]。
乡音土语不仅听众听起来亲切、自然,而且也利于掌坛法师的表达发挥,因此,在不断的创造过程中,傩戏词汇语言不断丰富,增强了幽默、戏谑的戏剧效果。
2.固定俗语
俗语在汉语语汇里为群众所创造,并在群众口语中流传,具有口语性和通俗性的,是通俗并广泛流行的定型的语句,简练而形象化。作为口头语体的黔北仡佬族傩戏剧本中俗语非常多,如“汤粑打狗,有去无回”、“一口吞了城隍庙,乃是肚皮鬼”、“棺材肚里点盏灯,死鬼子心里明白”(《骑龙下海》);还有“你晓得个屁,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顾定安拜寿》)等,语言简练而形象,通俗易懂。精炼的俗语还对人物刻划及情节发展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如:“癞子在嫌癞子丑,癞子不在犹如打断了一只手。”(《骑龙下海》)该剧中,金婆因听信女儿的谗言把儿媳妇龙三女赶出家门,结果是“家里猪也无人喂,羊子无人放,碗也无人洗,地也无人扫”,就犹如打断了自己一只手。这从侧面反映出龙三女的勤劳、能干,是对幺女的污蔑、金婆的无端棒打等行为的否定。
除乡音土语和固定俗语外,黔北仡佬族傩戏词中还有些粗话或不雅之言,如“哥哥盖蓑衣,嫂嫂盖斗笠,只有我有元无法盖,盖他娘的一个吹火筒。”这是《骑龙下海》中有元与金婆的对话。有元从小家境贫困,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在他嘴里冒出一句对生活不满的粗话是合符人物个性的。又如,务川冲傩戏——《灵观正台》中土地神言:“东方那个大嫂嫂,哪会儿看见你夹一吥?”调侃与性事相关的话题。这与传统的文学样式所张扬的道德规范可能有些区别,但这正反映出傩戏的原始性——天真、质朴、粗犷。
(二)句法上,句子简短,多用询问句、祈使句、独词句、省略句等,语气词使用频繁。
仔细研读黔北仡佬族傩戏剧本,可以看出,黔北仡佬族傩戏用最简单的格式、最俭省的表达、最快捷的语速,最大限度地唤起听众的共同知识与想像。它句子简短,多用单句,即使用复句,也很少用关联词。人物台词多用询问句、祈使句、独词句、省略句等,较频繁地使用语气词。非常明显地体现口语语言的特征。
如,“我今启言说一声,奶奶在上听原因。”(《骑龙下海》)意思是:请允许我开口说一下,请婆婆听原因。它起一个开场白的作用,并不是每个人物都在表述什么原因。这样的祈使句在黔北仡佬族傩戏中很多,仅就务川县《骑龙下海》剧本中就有17处之多,都是唱词部分:有鬼仙师(圆梦先生)对过路人、金才的问题解答;有金才与把门人和圆梦先生的对话;有瞎子(算命先生)对柳公、柳婆启言谈柳毅的八字命运;有柳婆对柳毅的嘱咐;有柳毅与龙三女、海鬼夜叉的陈述;有龙三女对金婆、杨寡母、柳毅、龙三叔的哭诉,等等。
又如:
丑:哎,你是哪个啷个凶?
净:你猜来。
丑:(丑猜了一半天)我猜到了,你是天上的吗?
净:然也!
丑:天上的……哦,是打雷那个——雷公!
净:滚下去!
丑:(沉思)不是天上的……哦,是地下的!
净:唔!
——节选自《傩神等殿》
这一段有省略句,有的甚至是独语词,但并不妨碍我们对戏剧情节的了解,反而从简短的语言刻画出将军(净)的高高在上,土地(丑)的谦虚、恭敬、诚实,通过戏谑化的语言和动作也描写出土地神可爱的一面。通过简洁、平实、明快、诙谐的语言很好地展现了黔北仡佬族傩戏幽默、风趣、娱人的特点。由于口语交流的双方多为面对面,因此口头语体经常运用非语言因素,如表情、手势等态势语,而正是有了这些非语言因素的帮助,口头语言中句子常常省略某些成分而不致影响意思的表达。
再如,“哎哟!鸡都叫了三遍了。咦!(看厢房)哪些老爷们还在打哟!我塞,得了一觉瞌睡睡了!管它的,解了手又去睡,那草窝睡起还舒服,再去睡一觉。(走了两步)呃!不忙,刚才我耳朵多尖,听岳父说厨房给大哥准备得有宵夜的。嘿!他吃得,难道我就吃不得吗?”(《顾定安拜寿》)罗秀才和顾定安同时作为女婿给岳父拜寿,却受到两种款待,但顾定安并不计较、气恼。简短的语句、一连串的感叹词、跳跃性的动作描写,刻画出顾定安随遇而安、俏皮、机灵的性格特征。
语气词的运用还有如:“好苦呀,啷个开交哟!”《顾定安拜寿》。“嘿!帝王就是这么一套‘天命’封禅。”“但观朝廷旨意,要谨慎行事罗!”(《泰山封禅》)“嘿”在这里有哀婉叹息的意思,剧中人物王旦对宋真宗打了胜仗却还要赔偿以及泰山封禅的做法很气愤,但因帝命难违,也只能痛惜罢了。
(三)语音节奏变化丰富。
黔北仡佬族傩戏语音节奏上变化丰富,独白、旁白、内白用散文体,简洁、明快、随意、自然;剧中的戏文唱词部分大都为不押韵的诗体形式——无韵诗或自由诗。尽管行与行之间没有韵脚,但每行诗句都有固定的音节,例如《骑龙下海》即是七个轻重相间的音节。七言句是诗体中最成熟的语句,读起来抑扬顿挫,节律鲜明,能非常完美地表现人物的情感。七言诗原本起源于民间歌谣,黔北仡佬族傩戏在唱词部分选择七言这一形式来表达是最合适不过的。当然,唱词部分也夹杂了三言、五言或是更长的句子。比如:
柳毅(唱) 天不平、地不平,
可恨宗师大人心不平。
弟兄三人去赴考,
文官不取我一人。
龙虎榜上无名字,
辞别宗师转回程。
柳毅只是心不死,
一心只把书来读。
看来一缘二命三风水,
四积阴功五读书。
——节选自《骑龙下海》
这段是柳毅对宗师(考官)的唱词,写出文人急切考取功名的期盼之情,勤奋用功之心以及落榜后的无限遗憾之意。我们看出,在七言唱词中穿插三言、九言句,正是人物情感表达的需要。
(四)修辞方式上多用比喻、夸张、排比、对比、借代等。
希腊学者加朗纳斯曾说过:“美妙的措辞就是思想的光辉”。在戏剧创作中,正确地运用修辞手法,不仅使戏剧中人物的对话和唱词通俗、明白、准确,而且还能使文字鲜明、精炼、生动、优美。
比喻是最常见的修辞方法,在各种文体中都比较突出地运用。它能使所记叙的人与事更加生动形象,所阐述的道理更加浅显易懂,所说明的事物特征更加清晰,所抒发的情感更加具体动人。如,“坛子栽花冤屈死,活人抬在死人坑。口水淹人不用海,丈二长麻理不伸。”这是《骑龙下海》中龙三女的唱词,她有太大的冤屈,就如花栽在坛子里死掉一般,就好比直接把活人抬入死人坑。这都是因为小姑子的陷害,口水也淹死人啊;有冤无处伸,就象丈二长的麻,理也理不清。这写出龙三女有苦说不出,有冤无处伸的悲惨遭遇。又如“浑身打得墨染青”,(《骑龙下海》)写龙三女被棒打青得象墨染过一样。又如“宋王畏敌如虎,已是木朽虫生。”(《泰山封禅》)生动地描写出大宋皇帝宋真宗面对凶猛的契丹军队怯弱、畏惧的形象,大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已经是生虫的朽木,不堪一击。
除比喻外,还有夸张、排比、对比、借代、反复、互文等。如“铜鼓震天,铁鼓震地”(《毛鸡打铁》)互文手法,意思是铜鼓、铁鼓齐响震动天和地。如“我心听得心欢喜,心中欢喜二三分。”(《骑龙下海》)用反复的手法表达喜悦之情。
而更多的是各种修辞的综合运用,如:
柳公(唱)我儿路途凄凄惨,小心之上加小心。
逢着和尚叫长老,遇着导师叫先生。
遇着老的叫叔伯,遇着小的叫兄弟。
宿店要宿大瓦房,莫宿茅庵草舍家。
高门大户出君子,茅庵小屋出小人。
日出三丈你才走,日落黄昏你莫行。
三年两载辞官去,急早回程奉双亲。
父母好似风前烛,犹如鸡鸣草上寝。
若是朝中高中举,父母远接你回程。
——(《骑龙下海》)
柳公这段唱词运用多种修辞方法,非常高妙。有排比,柳公交代路上要格外小心:遇着不同的人如和尚、导师、老者、小的要注意如何称呼如何交往,住宿要多留心,行中程要妥善安排行、歇,并催促高中后要早早回家。这细致地写出父亲对而行千里求取功名的嘱咐,期盼、担忧、心痛、惜别之情。“父母好似风前烛,犹如鸡鸣草上寝。”运用了比喻的手法,深切地写出父母的担忧。此外,还有两处对比:日出行与日落歇;宿住君子的大瓦房与不宿住小人的茅庵草舍家。父亲经验丰富,对儿子一一交代。
二、黔北仡佬族傩戏语言风格的形成原因
黔北仡佬族傩戏的语体风格是口头语体,其主要特点是遣词造句较为随意,话题经常变换,语言生动活泼,风格平易自然。前面已经从四个方面举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那黔北仡佬族傩戏何以形成这种语言风格呢?下面从两个方面进行简要探讨。
(一)傩戏的主题
傩戏是在民族民间宗教傩仪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它经过了从傩仪型——傩舞型——傩夹戏——傩戏型的演变历程,经历了从娱神到娱人的递嬗过程,这方面很多学者都作了细致的论述①冉文玉等.贵州省文化厅艺术研究室编.傩·傩戏·傩文化[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9.。因此,傩戏与宗教有一致性,都是“把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幻化地反映为超人间、超自然的力量的一种社会意识。”[2]也就是傩戏与自然、社会关系紧密联系,是人们在生存中面对各种阻碍、和困难、心里上失去方向的一种寄托和超度。
冉文玉在《傩文化的生命泉源与未来走势——以贵州道真为考察中心》中指出傩文化的生命泉源主要来自五大方面:神秘的宗教特质;生命的全面关怀;随俗的宽和胸襟;艺术的灵性媒介;集团的职业助推。傩是一种实用性极强的宗教文化,但它把重心落实于现实的人生,致力于满足普通百姓祈福迎祥的现实需求,关注所有的生命,甚至是鬼魂、精灵。人们的婚姻、求财、求子、祛病、丧葬、居住、祈求平安、处理人际恩怨等社会关系无不进入到傩戏当中,因此在表演上处处洋溢着生活的气息。其主题非常丰富,或是驱邪祈禳,或是消灾纳吉,或是拜寿祷福,或是演义历史,或是和冤解结。在这些主题的表演中往往插科打诨,演唱山歌小调,甚至是表演与性事相关的内容。比如前面提到的务川冲傩戏——《灵观正台》中土地的调侃,再比如湄潭解乐《和冤解结》领牲部分穿插演绎杨八郎、秦童挑担、秦童戏妻的故事。秦童的故事主要来自《甘生赴考》,它在多个傩戏中都进行演绎。傩戏如此丰富多彩的主题,使得话题经常变换,随意性大。
傩戏的主题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傩戏之所以几千年来一直生生不息,就是因为它能满足乡俗人民驱邪祈禳、消灾纳吉、消遣娱乐的愿望,这是傩戏的社会性决定的。在演绎主题时随意变换话题(均与现实生活相关)决定了傩戏口头语言的风格特征。
(二)傩戏的表演形式
戏剧有四元素,包括了演员、舞台(表演场地)、观众和故事(情境)。戏剧事件发生在一定的时间与空间内。黔北傩戏是每到过年过节或是哪家红白喜事的时候,村寨男女老幼,不管是亲戚还是地邻都汇聚在主人家的院坝或是堂屋,参加到傩的活动中。并借此机会一遍又一遍敷衍历史故事,宣传人文掌故,这也是他们乡村生活的重大活动和乐趣。娱乐性、社会性和教育性都根植于此。戏剧事件是审美事件,参与者不仅关心故事世界的信息,也关心传达信息的形式。因此,戏剧的交流必须是两方面参与:观众与演员,对于傩戏就是法师与百姓观众。在傩戏与社会需求之间,掌坛法师与民间百姓之间建构起一种交流的关系。祭坛上的演出,使百姓观众内心得到慰藉与愉悦;反过来,观众席上的氛围也影响演员情绪,而演员的演出又再度影响观众。这是一种直接的感情交流,这种感情交流很快地融合为共同的生活感受,形成法师与百姓观众共建戏剧审美场。傩戏的宗教、社会性决定了这样一个审美场中,一切活动必须能同普通群众的愿望、审美心理高度结合;这一审美场的群体性的心理体验特征,使它比其他艺术更集中、更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心声、社会的风貌、民族的心理历程,在娱乐的背后隐藏着严肃而深刻的社会历史意蕴。
法师作为傩戏创造的主体,当着观众的面直接创作于舞台上,一切不被群众理解接受的内容和形式,将会遭到淘汰。从事傩艺的法师主要是分散在农村的匠人,石匠、木匠、杀猪匠,有的是野叟村夫,他们虽然少有文化,却是当地智者的象征。剧本的流传全凭口传心授,在代代相传过程中经艺人们不断修饰。傩戏因而形成了生动活泼的语言特点,平易自然的风格类型,口语体特征非常明显。
[1]贵州省艺术研究室.贵州傩戏剧本选[M].贵阳:贵州省艺术研究室,1988.
[2]吕大吉.关于宗教本质问题的思考[J].中国社会科学,1987,(5).
(责任编辑:王 林)
On the Language Style of Nuo Opera of Gelao Nationality in Qianbei(the Northern Part of Guizhou)
REN Zheng-xia
(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The Nuo opera in Qianbei,one of the Nuo operas in Guizhou,is featured by its predominance of national language.And this paper seeks to expound the language style of Nuo opera in Qianbei in terms of vocabulary,syntax,phonological rhythm and rhetoric,and then analyzes the reasons of the formation.
Nuo opera in Qianbei;language style;the reason of formation
I29
A
1009-3583(2010)-04-0052-04
2010-01-09
任正霞,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