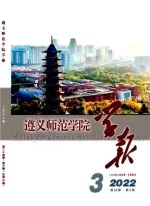风景、记忆与身份认同
——论钱邦芑隐居他山
2010-08-15周丹丹
周丹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084)
风景、记忆与身份认同
——论钱邦芑隐居他山
周丹丹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北京100084)
文章从“作为记忆的风景”与“作为文化表呈从而模塑个人身份认同感的风景”的角度开展文化风景研究。通过对明末流亡文人钱邦芑隐居贵州遵义市余庆县蒲村他山的个案考察,分析钱邦芑如何通过记忆的媒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风景,对风景行使命名、想像、挪用、再造、复制、书写和再现等权力,将江南家乡的园林风景移植到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从而构成他表达个人身份认同感的特殊途径和对抗清朝政权的独特方式。
风景;记忆;身份认同;钱邦芑
一、引言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于风景的界定不一。概而言之,风景可以“指涉 ‘地方’、‘景色’、‘背景’、‘土地’、‘农耕模式’、‘定居方式’、‘可视性的环境’、‘疆界’、‘自然’、‘空间’等意义”[1]。作为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风景研究日益成为跨学科研究的热门话题。英国学者本德(Barbara Bender)说:如果要在历史与政治、社会关系和文化感知的结合点上开展研究,那么,风景无疑也将成为我们研究的对象,因为它会打破各门学科之间的传统界限。[2]
就人类学界而言,早在上世纪末,风景研究就成为人类学家关注的对象。1995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由赫西(Eric Hirsch)和奥翰龙(Michael O'Hanlon)主编的《风景的人类学:地方与空间透视》(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一书。该书所收九位人类学家和一位艺术史家的论文从不同的视角,通过不同的个案研究,探讨了一个共同的话题,即风景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然环境,更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过程(a constructive process of culture)。但是,正如马考(JohnC.McCall)在评论该书时所说:风景这一术语近来经常被人类学家使用,但是它的意义和效用却几乎未被严格考察过。[3]因此,对于任何一个试图从人类学角度探讨风景的人而言,首先必须对风景这一术语的意义和效用进行考察和界定。
本文将从风景的诸多界定中选择“作为记忆的风景”(landscape as memory)与“作为文化表呈从而模塑个人身份认同感的风景”(landscape a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o shape individual identity)来开展研究,通过对明末流亡文人钱邦芑(1599-1673)隐居贵州余庆蒲村他山的个案考察,分析钱邦芑如何通过记忆的媒介连接过去和现在的风景,并将江南家乡的园林风景移植和复制到一个遥远的边陲之地,从而构成他表达个人身份认同感的特殊途径,成为他对抗清朝政权的独特方式。
本德(Barbara Bender)在《竞争的风景:运动、流亡和地方》(Contested Landscapes:Movement,Exile and Place)一书的序言中说:进行风景研究不仅仅只是一种学术的操练,它也关乎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历史的偶然性、论争、运动和变化。[2]在某种意义上讲,从风景、记忆与身份认同的角度对钱邦芑的解读,正是追寻和探求“运动和变化”(对于钱邦芑而言,运动和变化就是个人的流亡和王朝的更迭)中钱邦芑个人生活的复杂性(个人的身份认同危机、坚守与反抗)的努力。
二、无家可归:钱邦芑的身份危机
钱邦芑(1599—1673),字开少,丹徒(今江苏镇江)人。善诗文,精通书画,有“江左大儒”之称。据(清)康熙《余庆县志》记载:
“钱邦芑,字开少,丹徒人。由中翰历都宪。拒孙可望伪命,隐居蒲村。辟柳湖,与子衿唱和,从学者众。著《他山赋》,载《艺文志》。后削发为僧,改其居为“大错庵”,自号“大错和尚”。后归衡山终老。”[4](“人物”卷六)
民国《余庆县志》中又有:
“钱公邦芑,字开少,丹徒人。为诸生,屡困场屋。而诗文与张溥、徐孚远、陈子龙、艾南英、吴易齐名。由中翰,历都宪,播迁于黔。为孙可望囚系,迫以伪职,洁身不屈,秃发为僧,隐余庆之蒲村,与郑逢元为方外交。门下士执经请业,户履常满。清室开辟黔疆,芑乃出湖南,卜隐衡山,著述不倦……其所著有《他山·易诗》二十四卷,《读高士传》六卷,《古乐府》八卷,《十言堂诗、文集》各十六卷,《史切》二十卷,《诗话》二十卷,《焦书》二十四卷,《随笔》六十卷,《鸡足志》、《九嶷志》、《浯溪志》若干卷,各卷先后梓行于世。李守赙归其柩于衡山集闲书院中。”[5](“艺文第十五”)
钱邦芑身处明末农民起义和明清易代的乱世。1651年,因避张献忠部下孙可望,流亡途中避隐余庆蒲村。在他所写的《杨母白夫人寿叙》中载有:“……辛卯春,余因孙氏之乱,避地余庆”。[5](艺文第十五)当时,钱邦芑巡抚四川,永历帝朱由榔打算让他说服孙可望归顺南明,以增强南明的抗清实力。孙可望接到钱邦芑的劝解书,本打算“举全滇归朝廷”,但钱邦芑在向永历帝报告孙可望有归顺之意时,却又以“本朝无异姓封王者”加以驳斥,导致孙可望对他怀恨在心。但惧于钱邦芑当时的声望,孙可望知道纵其在外势将对自己不利,便想网罗钱邦芑到他手下做官,接二连三派人修书,逼迫钱邦芑。永历四年(公元1650年),孙可望假敕自称秦王,又一次次逼迫钱邦芑去他幕中。钱邦芑对其厌恶之心日增,决意弃官归隐,以避再度骚扰。[6]当时南明王朝已在风雨飘摇之中,钱邦芑虽为南明的右佥都御使(并以此身份巡抚四川),但本身已无法获得一个王朝对他的庇护。因此,面对孙可望的威逼,他所能选择的就是“走为上计”——逃,找个桃源胜地去隐姓埋名,自我保全。
当时,钱邦芑本打算从遵义(当时属四川),经余庆(当时属贵州平越府)、镇远,取道湖南回江苏老家。1651年春,钱邦芑进入余庆境内,因得知郑逢元在蒲村,便决定前往拜访。郑逢元,《余庆县志》记载:
“郑逢元,字天虞,平溪卫人,明末为制军。父卜葬余庆城南,奉母居蒲村守制。孙可望据黔中,强起之,逢元辞书有云:‘绝裾请缨,温太真之后悔何及;依刘为命,李令伯之陈情可怜’。自号‘天问和尚’,与钱开少为世外交。”[5](“乡贤隐逸第十三”)
因在当时局势之下归家不易,加上蒲村风景优美且不为外人所知,钱邦芑决定暂避蒲村,相机而动。哪知,一呆就是近七年。直到永历十一年(1657年)春,当得知永历帝在云南,他便决定离开蒲村前往云南,去追随永历帝。从而结束了他在余庆蒲村的归隐生活。
避隐蒲村期间,钱邦芑动荡的生活暂得安稳。在钱邦芑以第三人称所写、实为其自我写照的《蒲村老农》一文中,他说:“蒲村故黔地,俗俭陋无文,老农安之。”[5](“艺文第十五”)《蒲村归田诗》(其一)这样描述他的归隐心态:
“生平寡世情,赋性耽闲逸。尘网一羁牵,举步成碍窒。沉思本无味,忽忽如有失。一朝决去就,旷然深自得。理我荷叶衣,拂我笋皮笠。逍遥田亩间,昂首看云色。百物适自然,欣彼归飞疾。”[5](“艺文第十五”)
但是,归隐中的“旷然”与“自得”毋宁说只是“醒如醉”。期间,钱邦芑仍不得不继续与孙可望周旋,应付他屡屡的为官之请。而更深的痛苦在于:国家兴亡。正如清代贡生李光斗《咏他山》诗所写:想像当年湖上立,不言国事泪潸潸。[5](“艺文第十五”)在钱邦芑的内心深处,充满危机和威胁:亡国导致的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清代姚铃《蒲村》诗云:
“杖锡寄孤村,遗迹缅苍翠。人占乱离天,隐归名教地。入山恐不深,却聘醒如醉。耕凿聚生徒,兴亡结涕泪。时或抱琴弹,倦即枕书睡。柳湖迷烟花,息斋空霹雳。瞳瞳晓日升,簌簌霜风吹。岳麓倘归来,论诗我不愧。”[5](“艺文第十五”)
所谓“乱离天”,正是钱邦芑所处的动荡的无家可归的时代,也是他深深的危机之所在。
家,对于钱邦芑而言,具有双重的含义:江南故乡;南明王朝。身处西南边陲,他远离自己的江南故乡——江苏;明清易代,他已难以维系与南明王朝的身份归属和联系。在前者的意义上而言,他是一个落魄的游子;在后者的意义上而言,他是一个坚守的遗民。他正是这双重意义上的流亡者和无家可归者。
那么,钱邦芑如何为内心的危机寻找一个平衡的支点?他如何在蒲村获得“有家”(或“如家”)的自我慰藉?
在此,风景成为他选择的精微而绝妙的支点:他对蒲村的风景行使了命名和想象/建构的权力,经由风景而获得了“回家”的慰藉,缓解了身份认同的危机。
蒲村风景的建构过程和钱邦芑身份的建构过程是同一过程。由此,风景融入他个人的身份认同之中,成为其象征性表征(symbolic representation)。风景的建构者——钱邦芑将隐居和流亡之地的地方(place)和空间(space)个人化、自我化,通过对过去风景的记忆形成并强化了情感上的认同,使蒲村改造和复制的风景成为他进行自我定义的象征之物。在这种意义上,流亡和隐居之地的地方和空间成为钱邦芑个人的领地(疆域)(territory),成为他的家园(homeland)。
本德(Barbara Bender)说:要试图理解处于一个混乱的世界的人们是如何制造地方感和归属感、如何失去一个地方或与一个地方博弈,就应该让人们讲述充满竞争的风景、运动中的风景、移民和流亡的风景以及成为家园的风景。[2]对于钱邦芑而言,要理解他如何在蒲村制造“地方感和归属感”,就应该去看他的景观改造活动——对柳湖水景的再造和他山叠石的复制——和描写景观的诗文是如何讲述了那“成为家园的风景”。
三、记忆中的江南:柳湖的水景改造
《余庆县志·乡贤隐逸》中记载:“(钱邦芑)……拒孙可望伪命,隐居蒲村。辟柳湖……”。[5](“乡贤隐逸第十三”)所谓“辟柳湖”,即开辟田土为湖,围湖遍植柳树。此处的记载,显然是说钱邦芑对蒲村风景主动采取了改造的措施——“辟”:开垦与再造。
后人李文渊《咏他山柳湖》诗前小序也写到:
“县城之西,蒲村之阳,有山焉,不甚高,而怪石嵯峨:有水焉,不甚深,而溪涧萦回。乃有四川巡按使钱公邦芑字开少者,明季丹徒人也,避世隐居,由绥阳分水坝流寓于此,依山为宅,上则于山半镌‘他山’两大字。其余因形喝名,类皆毕肖。下则筑溪分湖,两岸植柳树百株。当绿荫浓翠时,与姬妓乘画舫,携琴书,放浪湖中。暇则教授生徒,决口不言国事。因名‘他山’、‘柳湖’。我邑前清江内外书院命名,盖本于此。待明社倾颓,削发为僧,更名大错和尚。[5](“艺文第十五”)
“筑溪分湖,两岸植柳树百株。”由此,亦可见钱邦芑对蒲村的风景改造活动——柳湖景观得以诞生。而此前,蒲村内并无“柳湖”之名,更无“虽由人作,宛如天开”(计成语)的柳湖之景。但在钱邦芑所写十二首五言古诗《蒲村归田诗》的小序中,对于此湖此景却有另一番描述:
壬辰春,率门弟子数人入黔之鳌溪,万山深处得平湖一曲,可二十余亩,渟水清泓中有柳数百株,旁多大竹,两山回映,风景幽胜,询之土人,地名蒲村,因剪除荆棘,伐木刈茅,构竹屋数椽于湖边居之,然后率僮仆开垦树艺,又招集土人苗民数家为邻,往来淳朴,耦居无猜,历两寒暑,桑麻渐熟,凡耕获种植,余不惮先劳。山农虽鄙,然脱去尘网,遨游世外,中甚乐也。[4](“艺文”卷八)
“万山深处得平湖一曲,可二十余亩,渟水清泓中有柳数百株。”在钱邦芑笔下,此湖此景实为固有之存在,他所做的不过是“剪除荆棘,伐木刈茅”。
不同人的书写,提供了“柳湖”风景诞生的不同解说文本。尽管有限的资料无法提供解决这一问题的清楚脉络,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钱邦芑对“柳湖”进行过景观改造——无论如何,“剪除荆棘,伐木刈茅”毕竟也是对此地景观的一种人为改造,只是力度有限而已。
尽管如此,这一小规模的景观改造仍构建了新的景观——“余庆八景”之一的“柳湖晓烟”:在他山之下,中有柳树数百株,大可合抱,晓露垂珠,烟岚缭绕,流莺耳见耳完,乳燕差池,俨然一幅图画焉。[5](“舆地第一”)这哪里是西南边陲山地一个偏僻小村庄的风景,其中分明有江南水乡风景的味道:秀气、柔美。
作为江左文人,钱邦芑对于湖与柳构成的水景无疑具有特殊的感情和独到的鉴赏眼光。经过他的审美趣味改造和提升的柳湖景观,成为他个人的风景:陌生的异乡风景变成熟悉的江南故乡记忆。
清人杨玉润《余庆县八景》(绝句各一则)之《柳湖晓烟》云:“古貌苍髯两岸垂,烟霞久待帝王师。莺歌燕语莫相问,怕使桃源世外知。”[5](“艺文第十五”)有趣的是,余庆的其它七景——翠屏晚照、两峰晴雨、古佛钟声、金龟锁水、玉笏朝天、牛塘积雪、慈云化雨——都是无人之景:纯粹的自然风光,并不与具体的个人相关联。却独“柳湖晓烟”一景十分特别,该诗中一“怕”字,向我们显示了一种悖论的风景(paradoxical landscape)——既敞开(open)又隐藏(hidden)的风景:风景本是敞开和召唤(invite)观看者的,“柳湖晓烟”却不敢完全敞开,因为它曾是一个流亡者的“秘密桃源”,这片风景被流亡者占有、控制和支配。在此,“风景不仅可以被看作名词,也可以被看作动词。”[7]——这片风景被钱邦芑挪用(appropriate),被重新赋予意义,因此象征性地成为挪用者身份的言说。
但是,仅改造柳湖一景并不够,水景之外,钱邦芑还要在蒲村照搬和复制(replicate)江南故乡的园林叠石景致——他山叠石。由此,构成完整的江南园林风景。
四、记忆中的江南:他山的叠石复制
(清)康熙《余庆县志》载:
他山,在县西一百六十里,地名蒲村,上多奇石,下有柳湖,钱公邦芑隐其下,镌刻“他山”两大字于石。[4](“舆地”卷一)
民国《余庆县志》载:
他山,距松烟铺三里,有地曰蒲村,在柳湖右岸,上多奇石,明巡抚钱邦芑避孙可望之乱,隐于其中,镌刻“他山”两大字于石,又刻“明少保钱开少放歌处”于其旁,其他象人、命佥名,均刻有字。[5](“舆地第一”)
他山在蒲村境内,其所得名,正是因钱邦芑隐居期间在其上叠石造园。在此,有一点需要特别说明:钱邦芑题“他山”二字之处,实为他叠石所造一组微缩园林景观中的一小块石壁。钱邦芑在《他山记》中写到:“村之上有柳湖,湖之阴为他山。”[5](“艺文第十五”)即他将那整座山称为他山而非那组叠石。县志的记载只强调了他山上“多奇石”和钱邦芑“镌刻‘他山’”等字的情况,忽略了钱邦芑如何按照他的想法叠石造景——钱邦芑行使对风景的命名权力。
这一忽略,极易导致后人对钱邦芑精心设计、巧妙布局、匠心独运的那组园林景观的忽略:以为那只不过是钱邦芑随意在一些模样有些奇怪的石头上提了一组字。相反,那完全是钱邦芑刻意而为、且精心构思的一处想像性(imaginary)的风景——江南园林。在此,江南家乡的记忆被江南风景的典型代表——园林——唤醒。复苏的记忆将钱邦芑过去的身份带回当下:熟悉的风景确证(confirm)了他的身份,恢复了他与“家”的联系——他乡即故乡。沙曼(Simon Schama)在《风景与记忆》一书中说:“对于民族认同感而言,如果没有一种独特风景传统的神秘性,它可能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其魅力。”[8]对于钱邦芑的双重身份认同而言,如果没有江南园林这种独特风景传统的神秘性,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试想:西南之地荒险、陌生的风景,何以慰藉一个流亡者?
明中后期,江南文风鼎盛,而几乎所有江南文人都有一个共同爱好:嗜园。
“明代中后期,江南士人竞修园林的情形时人多有记载。如何良俊称:‘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治一园。若士大夫之家,其力稍赢,犹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吴履震记松江一带:‘近世士大夫解组之后,精神大半费于宅第园林,穷工极丽,不遗余力。’诸如豫园、濯锦园、熙园等,皆‘掩映丹霄,而花石亭台,极一时绮丽之盛。’苏州地区园林尤多,凡较富裕的人家,‘多有亭馆花木之胜。’”[9]
作为江苏镇江人,流亡中的钱邦芑身上也携带着这一鲜明特征,并着手在流亡之地圆江南园林之梦。
《客欲移居蒲村问此中山水风俗长歌答之》中钱邦芑将蒲村的风景与宋代书画家米芾(1050-1107)的作品作了一番比较:米家书画差堪拟。[4](“艺文”卷八)米芾曾长期定居镇江,并在那里“创作了独特风格的米家山水”[10]。“米家山水”以水墨横点描绘江南氤氲、空朦的云山水树。而在钱邦芑看来,蒲村风景与江南山水也相差无几。
《余庆县志》中钱邦芑直接以“他山”为名之文有两篇,即《他山赋》和《他山记》。前者是对他山进行全景式的描写,后者则聚焦于叠石之处。在《他山赋》中,钱邦芑对他山上“多奇石”之“奇”有一番画家与造园家般的观察与描绘:
独是奇石磈磊,拔地插天:或赑屓而石吉石恒;或腭砧而曲鬈,或横仄而砹砹,或逆竖而倒悬,或龙盘而虎奋,或鹏举而凤轩,或蛟腾而鸿下,或狮怒而狂狻,或引而旗导,或羽展而翅翩,或云垂而烟断,或浪涌而涛旋。高者遏日,下者回峦,巨者藏谷,空者隐潭,皱者肤蹙,漏者窍含,瘦者骨削,薄者索殳彡,散者星落,簇者毛毵,仰者如啸,俯者如凝,立者如望,欹者如嘻,蹲者如怒,踞者如思,扬者如舞,抑者如企,端者如拱,斜者如窥,前者如待,后者如趋,联者如布,段者如亏,尖者如刺,利者如刲。既而,亦而礌峨。况龃龉而曲,又巧妙而因依。[5](“艺文第十五”)
且不论钱邦芑对这些奇石所作的生动形象的排比和比喻,单看如下几个字眼:皱者、漏者、瘦者——便可知他是绘画、赏石的行家里手。在《他山记》中又有:大约皆瘦、壮、皱、漏、耸、削、龈、嵌,不可名似。[5](“艺文第十五”)陈从周《梓室余墨·园林选石》中说:
“恽南田云:‘山从笔传,水向墨流。’此谓画山水之高超纯熟境界。又云:‘董家伯云,画石之法曰瘦、透、漏,看石亦然,即以玩石法画石乃得之。’余云园林选石亦然。”[10]
又,《痴妙与瘦妙》中有:
“明张岱《陶庵梦忆》评仪真汪园之峰石有‘余见其弃地下一白石,高一丈阔二丈而痴,痴妙。一黑石阔八尺高丈五而瘦,瘦妙。’痴妙,瘦妙,明代人品石之用辞也。清龚定庵(自珍)文中其形容人态有“清丑”之辞,亦同一表现手法。”[10]
钱邦芑显然对“明代人品石之用辞”非常熟悉,而他本身也精通书画。因此,这完全是一个内行人的品鉴和赏玩。
如果说蒲村天然地为钱邦芑的叠石造园准备了材料——奇石,那么,将蒲村想象和比拟为“米家山水”般的江南风景的钱邦芑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照造园的一般规则,进行布局、构景、叠山以及题字。
《他山记》载:
宇内山石之奇,无过川、黔、楚、粤,然幽遐荒险,车马不交之处,奇诡殆甚,而世或鲜知之。至川、黔、楚、粤之交,选第名山奇水,几以百计。而藜峨之鳌溪,幽丽为最。自鳌溪至湄水,约可百余里,幽岩深溪,堪怡玩者,何止数十,而蒲村为最也。村之上有柳湖,湖之阴为他山。山不半里,回曲斜抱,上多奇石,树多枫、樟、楠、梓。中一石最为奇突,高不及一丈,名曰“翠屏”,外削而内空,直立斜卷,余镌“他山”两大字于上……前后大石二十余处,离立作势,咸可坐踞。或蹲如猊,或奋如虎,如龙游凤翥,烟断云骞。大约皆瘦、壮、皱、漏、耸、削、龈、嵌,不可名似。中构一亭,六角茅宇,制甚朴拙,曰“拜石亭”。坐亭中,则诸石之奇,毕献于四周,而又回映杉、竹、花、树,朝昏烟霞,变现出没,给赏难遍……奇观哉!夫宇内名山巨川,载于经志者,宁可殚述。而是山之奇,迨未多逊也,乃千百年无知之者。余以逃名之故,远遁万山深处,始得遇此。然则世之奇伟名胜,隐匿幽遐而不复见知于世人者,又岂独此山哉
经过钱邦芑一番精巧构思和布局,他构建了一系列叠石景观:“翠屏”、“石帆峰”、“云房”、“九面峰”、“梅仓”、“梅囷”、“梅舟”、“小洞天”、“霹雳崖”、“藏书峡”、“回岚穴”。据笔者现场考察,除“梅舟”外,其它叠石与题刻均在。且还有一处文中并未提及:“烟断”。有该题刻的一组奇石与上述完整的叠石景观相隔较远(约50米)——正可谓“断”。但,“断”不过是似断实连:它在地理空间上与其它叠石相离,但在美学意味上,实与整个叠石布局融为一体:此“断”实为“合”。
钱邦芑造园非常讲究意趣:“古柏、老梅、黄杨、青杉,前后掩映”等——这是各种植物的相互搭配;“植梅其中”、“右壁一穴,园如磐口,梅干横生,从此透出”等——这是树景与石景的搭配;“斜侧怪异,随步换状”——这是移步换景;“坐亭中,则诸石之奇,毕献于四周”——这是借景;“名曰‘翠屏’”、“为‘石帆峰’”等——此为点景。
这片叠石风景中,最引人注目的,无疑是“藏书峡”——对于一个文人士大夫而言,书斋如同他们的生命。如果说,园林是文人士大夫的怡情养性之所,那么书斋就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处。“岩梢上二十步有峡,深九尺寸,高一丈五尺,名曰‘藏书峡’。”钱邦芑将“藏书峡”安排得十分隐蔽,就笔者现场考察来看,“藏书峡”实为整个叠石景观中最不易察觉的部分——足见钱邦芑造园之匠心独运。钱邦芑对“他山”之命名,也在此:
“中一石最为奇突,高不及一丈,名曰‘翠屏’,外削而内空,直立斜卷,余镌‘他山’两大字于上。”
“他山”取自《诗·小雅·鹤鸣》:“它山之石,可以为错”、“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诗中“它山”,后人也写作“他山”。)钱邦芑的这一“命名”,可谓别具深意。对于一个流亡中的隐居者来说,自我与它者(otherness)、此地与彼处、故乡与他乡等都会引起他灵魂深处的不安与痛苦。正如清人李光斗《咏他山》诗云:如何攻错借他山,欲识兴亡抱隐患。[5](“艺文第十五”)
在这组叠石上,有一处特别的题字:钱开少放歌处永历丁酉春题。永历丁酉年即1657年,为清顺治十四年。钱邦芑于这一年离开蒲村。永历是南明朱由榔的年号,钱邦芑的家国之思和国族认同从他刻下的这个纪年上得以表达。清知县黎大柄《游他山觅开少钱先生遗迹》一文前小序载:
山不甚高,数石丛立,各镌有字。先生放歌处,永历丁丑春题。他山、翠屏、洞天、云房、云归处、留云峡、梅仓、九面峰、米丈处、接不暇、藏书峡(岩)、回岚(风)穴、霹雳崖,志传古柏柳湖诸景,已杳无迹矣。所称永历年号,亦不知何指?[5](“艺文第十五”)
“所称永历年号,亦不知何指?”——这是另一种国族认同者的置疑。但对于钱邦芑而言,这个“不知何指”的年号太重要了,以至他需要用这组叠石风景为他铭刻和铭记。据县志,黎大柄于嘉庆九年至十年任余庆知县,这位只受过正统教育的文人已不知南明伪年号“永历”何指,怎不令人感慨!马考(John C.McCall)在评论《风景的人类学》一书时说:“……风景是社会感知的过程,由此建构起与社会过往意义丰富的关联。”[3]钱邦芑苦心经营他山叠石景观,正是要将自己与过去紧密联系起来,并将自己与那个正在陨落的王朝绑缚在一起:这是他个人身份之所系,也是他对于身份的坚守。那片风景负载了他的全部人生记忆:他的故乡家园记忆,他的国族记忆。
五、结语:他乡即故乡——钱邦芑的身份认同
通过一系列的景观改造和复制——水景、叠石、亭台等,钱邦芑终于将蒲村陌生的风景变成了可亲、可近、可居、可赏玩的熟悉风景——江南园林的基本要素都已具备——由此,拥有了“如家”的感受,暂缓了身份认同的危机、焦虑。
达比(Wendy Joy Darby)在《风景与身份》一书中说:“和其它物质结构一样,风景也是在一种意识形态的语境中被创造和破坏的。因此,如果要理解风景,就必须进行历史的还原:回到具体地点的意识形态特殊性。”[7]蒲村的风景是在无家可归者钱邦芑——遗民——特殊的意识形态语境中被创造的,理解蒲村风景的关键正在于:回到钱邦芑身份危机的特殊历史语境。由此,在加深对蒲村风景理解的同时,亦可体认风景对钱邦芑而言的特殊意义和作用。
从最基本的意义而言,风景是人们的居住之地,是所有活动在其上发生的地方与空间。而正是通过种种活动,人们建立起生活的意义以及与世界的关联。但是,风景不仅只是人们活动的背景——人们还制造风景,与此同时,被风景制造和规定。人是有根的,会在生命的某一阶段归属一种风景。但是,人也会四处奔走——运动、迁移、流亡、放逐等。对于奔走中的人而言,如何使不熟悉的风景变得有意义,从而制造一种地方感(sense of place)?如何对待已经远离的故乡,并与过去建立联系?如何确认自己漂泊中的身份?——作为文化表征的风景提供了一种可能而精妙的途径:建构风景,建构记忆,同时也建构身份。
钱邦芑对蒲村的风景行使命名、想像、挪用、再造、复制、书写和再现等种种权力,让蒲村“变成”江南——他乡“成为”故乡:蒲村成为风景建构者钱邦芑个人的疆域,确证他的个人身份。
[1]张箭飞.风景感知和视角——论沈从文的湘西风景[J].天津社会科学,2006,(5).
[2]Barbara Bender ed.Landscape:Politics and Perspectives,[C].Oxford:Berg Publishers,1993.3,2,1.
[3]John C.McCall,Review of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American Ethnologist.[J].1997,24(3):676,677.
[4](清)康熙.余庆县志[Z].(康熙五十七年刻本翻印本)
[5](民国)余庆县志·艺文第十五 [Z].(陈志)点校本(余庆县档案馆翻印,1985).208,210,184,207,233,242,217,184,243-244,8,254,8,205,213,206,205-206,242,216.
[6]钱再伦.钱邦芑避隐他山前后[J].遵义历史文化研究,2006,(3、4合刊).
[7]Wendy Joy Darby,Landscape and Identity:Geographies of Nation and Class in England.[M]Oxford:Berg Publishers,2001..2,106.
[8]Simon Schama,Landscape and Memory.[M]New York:Alfred A.Knopf,1995.215.
[9]陈江.退隐与抗愤——晚明江南士人的生存困境及其应对[J].史林.2007,(4).
[10]陈从周.梓室余墨[M].北京:三联书店,1999.157,356,289.
(责任编辑:王 林)
Landscape,Memory and Identity:A Research on the Exiled Qian Bang-qi
ZHOU Dan-dan
(Department of Sociology,Tsinghua University,Beijing100084,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landscape as memory"and"landscape as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to shape individual identity",the author chooses Qian Bangqi,an exiled intellectual in South China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who settled in Tashan,a village of Pucun County in Guizhou Province,as a case study of landscape research.Memory is connected with the landscape of Qian Bangqi's homeland and place of exile.Therefore,he made use of naming,imagination,appropriation,re-creation,replication,writing and representation to alter Pucun's landscape,turning a place of exile into a Southernstyle garden.Therefore,this became a special way to express his identity and lessened the degree of his identity crisis as well as to resist the Qing Dynasty.
Landscape;Memory;Identity;Qian Bangqi
I206.2
A
1009-3583(2010)-04-0043-06
2010-04-09
周丹丹,女,湖北宜昌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