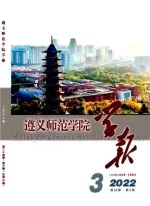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的问题
2010-08-15陈怀利
陈怀利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关于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的问题
陈怀利
(凯里学院人文学院,贵州凯里 556000)
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其实是其自觉选择的结果。古代文论强调文学理论只是整个文学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理论理性是贯穿在实践理性中的,所以反对纯思辨的抽象分析是古代文论的自觉行为。古代文论思想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在文学艺术观念上的具体反映,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背景,中国古代文论才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因而具有强调主体性、浑整性和会意性的特点。
中国古代文论;思辨理性;实践理性;清谈
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从中国文化思想批评史对待“清谈”(主要是为“辨析明理”进行的辩论)的主流观点上看,中国古代文论实际上是在自觉地排斥思辨的抽象分析。它认为“清谈”不务实,作为学术思想,它不能直接为文学实践服务,并因其抽象色彩而造成了与现实的脱节。为什么会反对其抽象色彩呢?因为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在文学艺术观念上的一个具体反映。我们知道,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得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这样的思维方式自然造成了如下的结果,即中国古代文论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亦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中国古代文论因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文论的强调主体性、浑整性和会意性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其自觉的选择
与西方文论强调从概念到范畴的逻辑演绎和学科体系的构建不同,中国古代文论有其自身的特点,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文论偏重于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具有整体性思维特点[1]。赵宪章先生认为中国古代文论在表现形态上较为显著的特点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1.审美的主体性。强调审美主体在艺术实践中的意义,侧重从主体角度去规定艺术的本质。2.思维的浑整性。即注重从整体上去把握和体悟审美对象,一般不作解剖式分析。3.表达方式的会意性。因强调审美的主体性,直觉、顿悟和对感性体验的描述就必然因个人因素而具有会意特点。正因为上述三个主要特点,古代文论在进行最具代表性的批评实践如论作品、作家风格时,常常用形象来完成其评述。杜甫《戏为六绝句》中评风格时用“或看翡翠兰沼上,未掣鲸鱼碧海中”,描述了词的艳丽和雄浑。最具代表性的当是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用诗的语言塑造形象从而从整体上评述风格,被郭绍虞先生谓之:“司空氏所作重在体貌诗之风格意境。”[2]杨慎的《词品》、姚鼐的《与鲁洁非书》等风格论述都概莫能外。这样的特点与西方文论相比,就显出了思辨理性的缺乏,所以学者们认为“中国美学则偏重经验形态,大多是随感式的、印象式的、即兴式的,带有直观性和经验性”[3]。其实,就中国古代文论而言,这一差别是其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古代文论对其承担任务的自觉认识。古代文论的理论批评总是贯穿于实际批评之中的,它的主要任务是如何指导创作实践、如何总结创作经验和如何纠正不良文风,所以它很少作抽象的纯理论的分析批评,而传统思想文化中“天人合一”的观念,又使主体性、浑整性和会意性构成了自身兼具创作性又能完成其批评目的的文论风格。
说古代文论缺乏思辨理性是其自觉选择的结果,是因为它的思辨理性的阙如,只是现代人的观点,于古人而言,他们实际上是在有意识地拒绝抽象(就一般而言)。不妨以魏晋“清谈”及其后人对之进行的批评为例。魏晋清谈又称“微言”、“谈玄”、“清议”、“清辩”等,它主要围绕当时文人雅士比较感兴趣的学术思想等问题进行辩论,希望达到“辨析明理”的目的。由于道家思想流行,对老庄之学感兴趣的人渐增,此外,同样被视为阐发玄学精微的“易”学,也受到人们的重视,于是探讨“老、庄、易”(并称“三玄”)就成了清谈的重要内容。自明代杨慎开始就已经有不少学者在辩证地肯定魏晋“清谈”的价值,但从现代意识出发来对此进行肯定的则是清代到现在,其中学者们大多从哲学理论、思想自由、审美意识与文艺批评等方面对“清谈”加以肯定,如马友兰、钱穆等等。当代的文学理论者当然也在强调它在开拓中国文论抽象思维方面的意义,比如刘国祥、何燕认为,玄学通过对一些命题的讨论,“大大提高了人们的抽象思维能力……这些思考与讨论进一步推动中国古代文艺理论走向成熟”[4]。
但是,除了上述肯定,及人们对魏晋文人雅士的风度,尤其是他们旷达放任、不拘礼法的自由个性表示欣赏之外,在中国文化思想批评史中——即使是近现代,对其进行批评一直是主流话语。如晋武帝时,傅玄在《举清远疏》中说:“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于上,清议行于下,近者魏武好法术而天下贵刑名。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其后纲维不摄,放诞盈朝,遂使天下无复清议。”[5]傅嘏认为“何平叔言远而情近,好辩而无诚,所谓利口覆邦国之人也”[6]。王羲之也以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7]。顾炎武认为清谈是“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的原因。梁启超认为“范宁谓王弼、何晏二人之罪深于桀、纣,卞壶斥王澄、谢鲲,谓悖礼伤教,中朝倾覆,实由于此,非过言也。平心而论,若著政治史,则王、何等伤风败俗之罪,固无可假借”,并指责当时士人“曾无雄奇进取之气,惟余靡靡颓惰之音,老、杨之毒焰使然也”[8]。蔡元培认为清谈家之思想,“至为浅薄无聊”[9]。虽然上述批评大多是从政治、教化的目的着手,但对于文艺理论思想来说,批评的角度也是一致的,即“清谈”不务实,作为学术思想,它不能直接为文学实践服务,并因其抽象色彩而造成了与现实的脱节。我们知道,古代文论强调文学理论只是整个文学实践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纯思辨的理论活动,它的理论理性是贯穿在实践理性中的,所以就一般意义而言,反对纯思辨的抽象分析是古代文论的自觉行为。
二、作为文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特点
从上面对“清谈”的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出,古代文论思想与古代哲学和道德思想在实用观念上是一致的,实际上,古代文论思想就是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在文学艺术观念上的一个具体反映。中国哲学的一个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天人合一”,即天与人、或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为的关系问题。作为认识论的基本范畴,“天”指认识对象、客体,“人”指认识主体。“天人合一”则是指认识主客体相互依存,相互包容的一体关系。中国哲学认为认识主体与客体通属宇宙大全,主体若从客体中分离出来,客体就不是完整的客体了;而从客体中分裂出来的主体,也不是完整的主体;进一步说,宇宙大全也就不是整一性的了。
认识的主客体是统一的,那么认识主体如何开展认识活动呢?中国哲学当然不能把认识客体置于主体的对立面去观察、分析,只能在与客体的交融共存中来体会它的存在,感受它的生命和领悟它的精神。于是产生了两种主客联系的方式。客观的认识态度是将个人经验觉悟合理外推,与外在事物融为一体。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流通贯彻,初无间隔。”[10]主观的认识态度则向心内求,将客观纳入主观内心。陆九渊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11]王守仁宣称:“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12]。主客体统一的观念当然产生了与西方不同的思维路径与方式。中国哲学思维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得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直觉思维是一种很独特的思维方式,它以个体经验与智慧直接切入事物本质。我们不能因为它具有形象和感知认识的特点,或因为它缺乏逻辑的表述,而简单地把它理解为粗浅。直觉思维因为强烈的主观色彩而带有模糊性,难以让人把握,但直觉思维的一些特征却是非常鲜明的,概括起来有如下几点:(1)直觉思维是非逻辑的思维;(2)直觉思维十分重视为认知者留下广大自由的主观空间,有极强的主观性;(3)直觉思维具有立体有机联系的特征。我们说中国哲学思维的非逻辑特征,不是说中国人的思维没有逻辑,而是说中国哲学偏好、追求非逻辑、非形式化带来的灵活、简捷、深刻。它压缩或抛弃了逻辑程序,开门见山地切入本质。
直觉体验的方法依赖于个人经验,与个体心智、心理情态相关,而旁人难以随同进入他人的主观思维过程。直觉体验的个体主观性是不确定的,认识本身也就有极大的随意性,灵活性,这正是直觉思维具有创造性能量的原因,是中国哲学思维的绝妙之处。正是基于这样的哲学认识背景,中国古代文论才不从二元对立的角度,去对客观对象展开认识,即不热心逻辑认识体系的建立,因而具有强调主体性、浑整性和会意性的特点。
[1]朱立元.走自己的路[J]文学评论,2000,(3).
[2]郭绍虞.诗品集解·续诗品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1.
[3]叶朗.中国美术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14.
[4]刘国祥,何燕.简论魏普玄学与文艺批评[J].广西大学学报,2007,(1).
[5]傅玄传[A].晋书[M].
[6]刘大杰.魏晋思想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167.
[7]击希仁,赵运仕,黄林涛.世说新语译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
[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9]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67.
[10]朱熹.答袁机仲别幅[A].朱文公文集(卷三十八)[M].四部丛刊初编集部,上海:商务印书馆.缩印明刊本.
[11]陆九渊.杂说[A].象山全集(卷 22)[M].
[12]王阳明.传习录(卷上)[M].
(责任编辑:王 林)
On the Lack of Dialectic Reason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CHEN Huai-Li
(School of Humanities,Kaili College,Kaili 556000,China)
The lack of dialectic reasoning of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is the result of its conscious choice.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stresses that literary theory is just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whole literary practice,with theoretical reasoning running through practical one;therefore,the abstract analysis against pure reasoning is the conscious behavior.Th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is just a specific reflection of classical culture upon the concept of literary art,because of which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 does not looks at the objects from the dual opposite way,viz.,it is not to establish the system of logical recognition,thus having the features of subjectivity,natural wholeness and tactness.
Chinese classical literary theory;dialectic reasoning;practical reasoning;pure conversation
I206.2
A
1009-3583(2010)-04-0026-03
2010-05-13
陈怀利,男,山东莘县人,凯里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元明清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