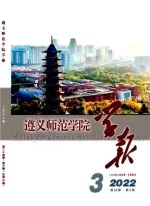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简·爱》中女性主义的探析
2010-08-15彭洪颖
彭洪颖
(遵义师范学院外语系,贵州遵义)
《简·爱》中女性主义的探析
彭洪颖
(遵义师范学院外语系,贵州遵义)
简·爱形象既没有符合激进女性主义者的期望,也并非如部分女性主义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主流文化的一种维护。实际上,徘徊于反叛与回归之间的简·爱看似矛盾,实为合理,正好展现了作者独特的女性视角和追求平衡的女性主义理想。
简·爱;女性主义;平衡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郎特的《简·爱》之所以成为有别于一般言情小说的伟大作品就在于它浸透了对妇女命运的思考,对妇女人格的重审。然而文本中透出的女性主义却惹来争议:简·爱的形象究竟是对传统的叛离还是对传统的回归?
一、历史背景与女性主义
“女性主义”一词最早出现于19世纪末的法国,20世纪初在欧美其它地区得以广泛流传。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历史大背景给它带上了鲜明的政治色彩和批判精神,因此“feminism”又被译作“女权主义”。一般而言,“女权主义”有着浓重的政治意味,“女性主义”则更多地体现出文化和学术性质[1]。然而不管怎样,女权运动的兴起,使得女性文学表现出如下特质:一是对传统女性形象及女性观念的颠覆;二是女性意识或女性视角的展现;三是女性独特情感的自然流露,它的兴起使得女性文学有了独立的文学地位和特殊的文化意义。
20世纪见证了妇女解放运动的两次高潮和世界妇女文学的普遍繁荣,女性主义文论由此进入发展的黄金时期,并于70年代趋于成熟。其内容既包括了揭露文学中男权中心文化的霸权主义,呼吁男女两性的平等与和谐,又包括了用女性视角和价值观念重新审视和揭示一切文学现象,探索与之相适应的女性美学体系以及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于是,种种女性文本会无一例外地进入女性主义者的研究视域,或引发他们的讨论或为其观点佐证。
二、矛盾的简·爱与追求平衡的女性主义
叛逆女简·爱因其强烈的争取个性解放、人格独立和平等的意识,备受女权主义者们的推崇,该作品也历来被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列为范本。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后,《简·爱》已被认可的反传统性却遭到了质疑。女性主义批评家们一方面对简·爱做出的从桑菲尔德府出走的惊人举措大加赞赏,另一方面却对作品安排的结局表示出了强烈的不满。因为他们认为简·爱最终还是回到了罗切斯特身边,这是简·爱对自我经过千辛万苦换得的独立女性身份的放弃,也是作者向男权社会的妥协,因此,这是小说的一大败笔。英美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肖瓦尔特提到《简·爱》时就曾批评道:“19世纪那些寻求独立的女主角,通常都被设计为最终仍回到了男人的大氅和安慰的避难所。”[2]。面对激进女性主义者们的尖锐,朴维却不无温和地称《简·爱》是一部充满矛盾的文本,是复杂的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既对现行的社会体制提出挑战,又呈现出听天由命的一面。[3]
她的矛盾论述对我们理解这部著名作品的深层含义大有裨益。实际上,作者本身就具有两面性:在备受压制的维多利亚时代,勃郎特渴望突破男权社会的樊篱,寻求真正的自我;但同时她也不期望另一个女权社会的出现,所以戒绝激进的女性主义,这就使作品显现出时而挑战,时而妥协的一面。作者希望以此展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即在女性自我需求和社会传统约束的矛盾中努力寻求一个平衡点,构建一种和谐。
长期以来,父权制文化就以天使或魔鬼来限定“女性”。唐娜温在她的论文《跨越网的界限:女性主义批评作为道德批评》中指出:西方文学实际上主要是“建立在一系列的妇女陈规形象之上。在西方传统中这些形象被归为两类,反射出西方文化思想中特有的善恶对立的二元思想。妇女陈规形象要么代表精神的善的,要么代表物欲的邪恶的”[4]。你若想成为“善的”,成为被社会所认同的“天使”,你就必须符合社会的标准,处处用传统的文化礼教约束自己,付出否定自我甚至泯灭自我的代价,否则你就会变成“魔鬼”。作品中时时克制自己的谭波尔小姐和逆来顺受、喜爱说教的海伦应该就是天使的代表;而“阁楼上的疯女人”博沙·梅森因其不听话似应被归为魔鬼一类。但是在对简·爱的塑造上,作者既不对顺从的天使完全肯定,亦不对叛逆的魔鬼完全否定,而是将这两种矛盾对立的性情统一到了同一角色上,成就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生灵、一个有思有想的女人,而不是一具玩偶,一种模式。基于追求平衡的女性主义思想,勃郎特在对待“女性”问题上的矛盾性则从多处在简·爱身上得以体现。
首先是女主人公的外貌
容貌无疑也是男权中心文化评价女性价值的标准,所以几乎绝大多数文学作品里的女主角都美得天上有、地下无,可偏偏勃郎特笔下的简·爱生得相貌平平,身材矮小,面色苍白,甚至五官还不那么端正——以至于罗切斯特戏谑她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简的丑绝不是偶然,是作者出于对传统文学作品中女性模式的不满而匠心独具的安排,是对父权制规定的女性标准的反叛。勃郎特曾经对她两个妹妹说过要写一个完全不同的女性形象,“她”将与作者一样没有美丽的外貌,却比那些美女有更加撼人心魄的人格魅力。通过简·爱和布兰奇·英格拉姆的对比,勃郎特想告诉世人女子的内在品质胜过外在美,且具有更强烈、更长久的吸引力。出生名门,美丽优雅的英格拉姆小姐最终被不起眼的简·爱打败更是寓意着作者对当时正统观念的颠覆。然而,作者的内心是复杂的:作为女人,她也渴求自己能有一副姣好的面孔;作为女人,她也希望在缺少美貌所许可的范围内尽可能使自己惹人怜爱。勃郎特曾借简·爱之口有过一段心酸的独白:“要是上帝赐予我一点美和一点财富,我就要让你感到难以离开我,就像我现在难以离开你一样。[5]”
其次,作品的矛盾性集中体现于对女主人公反抗精神的描写上
当父母双亡的幼年简·爱寄居于里德府时,按照世俗常理,她唯有俯首听命的份儿,应该表现出隐忍、克制的美德,但是骨子里具有反抗精神的简·爱在面对不公平时频频爆发了。然而,与里德太太之间的那次可怕争吵结束后,作为胜利者的简并没有得到报复的快感,相反却尝到了“醇酒”过后的苦涩。她觉得这种恨别人又被人恨的现状是可悲的,所以她甚至产生出请求舅妈宽恕的冲动。如果说简·爱的矛盾心理是因为此时的她尚小,不得不依赖舅妈造成的,那成年后的简在得知舅妈病危的消息后,立马前往探视,并一厢情愿地摒弃前嫌、真诚期盼与舅妈和好。
在劳沃德学校,简的反抗性格似乎被谭波尔小姐的“宁静气质”给镇住了,甚至出于一种莫名的崇敬和向往,简逐步向“天使”靠拢。如小说所述:“较为和谐的思想,较有节制的感情,已经在我心中扎了根。我忠于职守,克尽本分;我安然文静,相信自己已经心满意足。在别人眼里,通常甚至在我自己看来,我似乎都是一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人[5]”。只是后来谭波尔小姐的远走才带走了这一切,简·爱那颗“不安分”的心猛然复苏,又开始蠢蠢欲动。
为避免沦为罗切斯特的情妇,简毅然决然地离开了他——这将故事推向了高潮,也将简的反抗精神推向了顶峰。然而故事就此急转直下。与圣约翰相遇后的简较在桑菲尔德府的她,判若两人!也许前一阶段的分离太过痛苦,此时的简看起来是那么的脆弱,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段意外的亲密关系,对圣约翰表现出不可思议的依赖和敬畏。为获取圣约翰的肯定与赞美,简居然不惜拿出自我牺牲精神,极度克制自己的欲望,努力掩饰着真实的自我,尽量服从于他的每一道命令,直至发展到全然不顾自己的身体承受能力和精神需求,几乎答应做他的妻子、随他去印度传教。可是圣约翰的冷酷与专制使简最终认识到他不是一个完美的神,而是一个有缺点的人,因而唤起了她的平等意识,打破了对他的精神崇拜,鼓起了反抗的勇气。
备受争议的就是故事的结局:勇敢走出去的简·爱最后回到了罗切斯特的身边!在他们那个世外桃源般的庄园里,读者看到的似乎是一个循规蹈矩且怡然自得的家庭主妇,一个俨然符合社会习俗要求的“闺中天使”。然而,即便如是,此时的作者仍没忘记平等的要求:比如从二人经济地位来看,罗切斯特在火灾中失去了大部分财产,而简·爱却因继承,获取了一大笔意外之财;比如从二人外貌来看,简·爱固然相貌平平,而罗切斯特却成了残疾,行动都不便,甚至需要简·爱的扶持。
三、结语
毫无疑问,叛逆、反抗是简·爱精神中最闪光之处,可是我们总能在反抗的背后找出些许妥协的成分和回归的倾向。由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归结出简·爱形象究竟是对传统的叛离还是对传统的回归:正如上文已提到的那样,小说《简·爱》是复杂思想体系的一部分,既有挑战,又有顺天应命的一面。纯粹正统的简或纯粹叛逆的简都不是作者所支持的。因为这个社会毕竟是个矛盾集合体、是由男人和女人共同组成,我们不能在解构二元对立的同时形成新的二元对立,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矛盾的简、一个在独立自我和传统角色中不断挣扎,寻求平衡的简。这样一来,在妇女问题上,作者另劈蹊径,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理性而合理的探讨方法。
[1]杨莉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研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2.8.
[2]Showalter,Elaine.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 to Lessing [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7.13.
[3]Poovey,Mary.Uneven Developments:The Ideological Work of Gender in Mid-Victorian England[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8.126-163.
[4]Donovan,Josephine.Beyond the Net:Feminist Criticism as a Moral Criticism[A].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Theory[C].ed.Newton,K.Macmillan:Macmillan Education Ltd.,1988.265-268
[5]Bronte,Charlotte.Jane Eyre[Z].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325,105.
(责任编辑:魏登云)
The Exploration of Feminism in Jane Eyre
PENG Hong-ying
(Foreign Language Department,Zunyi Normal College,Zunyi 563002,China)
The image of Jane Eyre does not satisfy the expectations of the radical feminists,nor does it seem to comply with the main current culture.In fact,rationality lies exactly i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rebellions and compliances,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intention of re-evaluating traditional images through the heroine to achieve her own version of womanhood.
Jane Eyre;feminism;balance
I106.4
A
1009-3583(2010)-04-0040-03
2010-04-20
彭洪颖,女,贵州遵义人,遵义师范学院外语系助教,研究方向:英语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