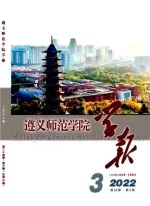论廖公弦诗歌“月”意象
2010-08-15麦成林
麦成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论廖公弦诗歌“月”意象
麦成林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
廖公弦诗歌中的“月”意象,是他追求、探索的意象美学象征,也是营造诗歌意境的主要手段之一。“月”意象,一方面展示了田园式的意境,另一方面又充斥着不协调的政治话语诉求。同时,廖公弦在创作的不同时期,诗歌“月”意象内涵也在无形中发生着变化。
《山中月》;月意象;田园牧歌;政治话语
在贵州的新诗诗歌史上,廖公弦是一个有力的存在。新时期以来,为方便当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全国30多所高校中文系与中国社科院文研所协作,曾于上世纪80年代初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丛书为国家重点研究项目,由茅盾、周扬、巴金、陈荒煤、冯牧等人为顾问。其中贵州仅有的一册只选了两位作家——蹇先艾和廖公弦,书名为《蹇先艾廖公弦研究合集》。足以见得,廖公弦当时在贵州确实是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虽然他的诗歌并不多,留给我们的仅有四本诗集:《山中月》、《美人醒来》、《山与我们合影》以及20世纪90年代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贵州文学丛书第二辑《廖公弦诗选》。但是其人在贵州的新诗史上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和光辉,尤其是他生活化的意象挖掘和田园牧歌式的意境营造,不失为一种纯朴生活的自由点缀和无言的审美享受。其中有关“月”意象和意境的营造在《山中月》一集中多次出现,这里“月”已经成了表达感情,增强诗感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机结合体。月亮也不单单是思乡怀远的象征,更是山里人对一种生活方式的期许和对自然、生命的一种审美关照与对视。
苏珊·朗格认为:“意象的真正的功用是:它可作为抽象之物,可作为象征,即思想的荷载物。”[1]当然在中国的古代诗词中,咏月的篇章多如牛毛。月亮这种本质的物质存在已经被赋予了丰富的美学内涵和文化象征意义。在诗人的笔下,它不再是一种客观关照物,单独的客观审美对象,更多的变成了承载和包含作者感受和经历的主观化的抒情客体。同一轮月,此一时,彼一时,此一人,彼一人,他们都在构造着不同的意境和审美感受,或思乡,或怀远,或慨叹,或伤情……而在廖诗中,月亮的静谧,月亮的调皮,月夜的静美,月色的朦胧,月亮和山里人的和谐关系,让我们领略了“月”意象的另一种美。诗人从小生活在黔北绥阳的大山中,他在《谈我写诗》中回忆道:“我来自农村。当我刚学会走路,便已经是在外祖母家里了。那里的肥田沃野、茂林修竹,平缓的山丘,弯弯的小河,以及那些老实的牛、欢快的羊,从小就给我一种特定的诗的启示。”廖公弦对月意象艺术美的追求,也带有一种独特的色彩,也是对月亮在新意境下承载意义的新的开拓。
在廖公弦薄薄的诗集《山中月》中,共收录了诗人68首诗歌。这些诗歌绝大多数写于1957至1964年间,只有开头和结尾几首写于文革结束之后。总的来看,写于50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这些诗歌主要特点表现在以下三方面:首先,从取材范围来看,均与家乡的生活和劳动场景有关,充满着泥土气息,诗歌呈现出了山寨之美、山民之纯,表现出浓厚田园牧歌的意蕴。其次,诗歌喜欢用大量的口语和通俗的语言入诗,既朴实自然,又不失活泼风趣,妙趣横生。再者,诗歌兼收并蓄,善于从传统诗词和民歌当中吸收养分,充实自己的诗歌内涵和增强艺术张力。诗集《山中月》中直接写到月亮的就有五首:《晚安》、《编箩》、《山中月》、《雨后月出》、《月下曲》,其中属《山中月》的影响最大,意境最美,该诗获1961年《羊城晚报》创作奖,曾受到著名作家陈残云的好评。这里“月”意象的营造很大程度上就得益于传统诗词中月亮所形成的原型意象的影响。本文就试从“月”意象的营造来反观廖公弦诗歌创作的某些独特表达方式和意蕴。
一、“月”意象的形态意象刻画
月亮作为现实之物,我们是能够看到月亮的实际轮廓的,当然常人眼中的形态感与诗人眼中的形态观念是不可等同的。最重要的是诗人笔下的月亮或者月意象已经承载了诗人的独特审美想象和情感负载。根据诗歌表达的需要,对月亮进行情感化的处理。
这里的“形态”并非日常逻辑观念中的月亮形态,或圆或缺,而是借助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将月亮赋予有形态的东西,或者说是直接观念形态和意念的产物。例如诗歌《编箩》中开篇就写到:“林里的夜风跑出来,/把槐树儿轻摇轻摇,抖落些银色的月光,/斑斑点点满地跳/……拈起地上的月片/……扛锄的人影窜过来,/满背尽是月光跳……”[2]全诗月光贯穿始终,并且将月光赋予了有形的东西,像树叶一样可以摇落,像地上残留的物体碎片,可以随手拈起,还像扛起的重物在肩上乱跳。这样生动的描写,使诗歌本来静态的文字表达,赋予了生物的动态感和生命力,进而使诗歌的意境活灵活现的展现在人们面前。“抖落些银色的月光,/斑斑点点满地跳”一句,是直接赋予了月亮“顽皮”的孩童形象,拟人化的效果跃然纸上,描写山中的夜月,在树林间仿佛过了滤似的,分外皎洁,投下了斑驳陆离的光影,境界显得更加宁静、和谐,和寂静的山村一起营造了一副田园式静寂乡村月夜劳动场景的意境图。月亮本是相对静止的,但用一“跳”字,便将它写得摇曳多姿起来:从夜风中探出头来的月亮,把月光洒在槐树上,这月光像给山村的夜蒙上了一层轻柔的白纱,晚风轻轻地撩拨着含羞带娇的白纱。树在月光的映照下摆弄着娇羞柔美的倩影,将“月”意象人格化了,富有了生命的质感。
二、“月”意象在静与动的互为辩证中的反衬比手法运用
诗人善于写山中皎月,当然诗人笔下的月亮不同于海上明月的空旷,也不同于大漠边塞夜月的孤独与寂寥。《晚安》一诗中:
好一个静谧的夜晚,/月亮跳进了秧田,/独自儿悄悄洗澡,/洗掉那些银色的鳞片//忽然间火星几点,/迸溅在广漠的夜间,/喓!是他呀,他衔着烟斗,/夜深了,未回还。//他在田野里走动,/眺望四周的群山,/群山变成了羊群,/驯服地躺在他身边。//他一时时弯下腰去,/和秧苗握手倾谈;/天上闪烁的星星,/齐向他眨着笑眼。//他那迈动的步伐,/走的多轻、多稳健,/因为这安谧的山乡,/连同梦中的社员,/全睡在他的心间。//洗澡的月亮爬上田坎,/微风吹拂着雾中的远山,/书记?,书记,/晚安!晚安……//[2]
诗中塑造了夜晚专心、认真、负责地查看秧苗的书记形象。为了烘托静谧的夜晚,没有直接地去写夜是如此的空旷和寂静,而是通过一系列的动词“跳”、“洗澡”、“洗掉”、“爬”、“吹拂”等来写月,静静的月亮,顿时“活”了,像一条活蹦乱跳的“银鱼”,进而以月亮的“动”衬托山乡的“静”,以月夜的“静”反观书记的专注和认真。这里的月成了勤勉书记形象的陪衬。
《山中月》一诗中,把“静”和“动”反用的笔法达到了极致。特别是他的名作《山中月》,更受读者群众们赞赏。诗是这样写的:
傍晚出来,/依依回头看,/明月与山民,/性格竟一般,/老在庄头竹林后,/默默长相看,/回首不知多少次,明月未回还。/出山转了弯,/上山复巅,/伴我下平川。//我走平坝,/月上中桥,/月涉浇水滩。/一而再,再而“山”/送我到明天。//山中月儿学山民,/感情也内涵,/倾给满腔热情,/留给你几多方便。/在它默默无言里,/你在不知不觉间。//[2]
“明月与山民,性格竟一般”一句,月亮成了山民的直接化身。[3]直接破题,点名主旨,直接了当地吐露出诗人的心迹。从立意和构思来看,诗人曾经在《新诗我见》一文中说:“诗人要争取读者,读者越多越好。故意把诗写得晦涩、难懂,让人费劲猜谜语,读者越来越少,此种情况,无异于诗人自杀”。并明确提出:“诗要让多数读者看得懂”。[4]他对自己的诗作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在创作中力图把中国祖传的诗歌、民歌和词曲熔为一炉,愿能识汉字的人,都能看懂自己的诗。众多人读懂诗歌,并不等于降低诗歌的水平,而恰恰相反。诗歌要走出诗人狭小的圈子,成为广大民众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精神产品,就必须反对难懂的诗风,反对晦涩,提倡尊重民族的欣赏习惯。因此,他强调诗人要把握住诗歌的内在规律,具有民族特色和个人风格。廖公弦的诗,易读易懂,同时也含蓄耐爵,让读者把握意象、意境的同时,引发联想、引人深思。
从诗歌的意境来分析,全诗以“我”的视角不断游弋变化为中心点,借月展情,不断地开拓新的意境和月亮的表现范围。“我”上山,下山,月亮也陪我上山,下山;我走平坝,过峡谷,过中桥,明月夜悄悄地“上中天”、“站崖边”、“涉浅水滩”。最后几句,与开头交相呼应,通过月之“象”,鲜明的表现出月之“神”。这何曾单单写月,分明是在写人,同时通过近似通感的表现手法将这种“象”和“神”直接地嫁接到山民身上来,将山民的那种勤劳、热诚、质朴、厚重的山里人品格和月的皎洁、纯瑕、静美对应了起来。这里月“活”了,不仅“活”的生机,而且极富山民的性格和大山的精魂。诗中赋予月完美的艺术形式,并活灵活现地刻画出了贵州的山、月与民的和谐统一的关系。
三、和谐“月”意境中的时代政治话语诉求
在《山中月》里面当然从诗歌中看到了不协调景象,那就是诗歌的功利性表现和强烈的政治话语诉求。因为前面已经提到,这些诗歌全部写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当时的政治环境和时代环境决定了诗歌必然要为其服务,实践出“颂歌”时代的强音。《山中月》中诸篇,好多处出现“公社的土地”、“公社的麦浪”、“公社的庄稼”、“公社的鸭”、“社员”、“书记”,这些词反反复复地在诗中出现,以诗人的才学和修养而论,不可能出现这样低级重复的错误。后来诗人自己也印证了这一点,1983年诗人的随笔《谈我写诗》中写道:“写诗于我,时日不算短了。每一回顾,总觉背冷。从十九岁到现在,期间除去不准写作的十一二年(文革期间,作者加),也有十四五个年头。十多年来的诗作,数量不算太少,但在严肃的历史面前,能经受考验,不会低下头去的作品,实在是寥寥无几。”仔细思之,方能理解诗人的苦衷和那个时代所有文学(包括诗歌)打上的“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时代烙印。
在那个时代,“大凡写山水风景诗,最惧被扣上‘无思想内容’的帽子,于是乎不得已,硬加上‘公社’此类的词儿,以示所谓‘时代精神’,免遭棍子。”[5]从这一点看出,因为时代政治环境的左右,诗歌的功利性话语就明显增强,这就造成了很多诗歌缺乏美学深度。虽然诗人一直在尝试和坚持着浅显易懂的诗歌创作道路,但是具体的创作实践深受时代环境影响,诸多诗歌为了表达时代的声音,诗人在结尾处就直接点题,把自己的思想直接说出来,缺乏含蓄和深度,使诗歌的诗味也逐渐减弱。
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明白,“十七年”的诗歌,在诗歌的理论和实践价值上主要是以政治价值取代审美价值,特别是对诗歌政治功利性话语诉求表现的尤为明显。诗的社会“功能”、诗歌作者的“立场”和思想感情的性质,是评断诗人及其作品的首要标准。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背景下,廖公弦的诸诗也表现出了相关的政治诉求。首先,诗歌正如贺敬之所说:“诗,必须属于人民,属于社会主义事业。按照诗的规律来写和按照人民利益来写相一致。诗人的‘自我’跟阶级、跟人民的‘大我’相结合。‘诗学’和‘政治学’的统一。诗人和战士的统一。”[6]在贺敬之看来,写诗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反对诗歌创作背离社会主义事业的方向。作为同时代的诗人廖公弦,他不可能不受这种思想影响,诗歌创作必然会不约而同的打上相同时代的政治烙印,践行这种诗歌创作的观念和主张。其次,作为贵州的诗人,廖公弦并不像其他高声呐喊的诗人,这种政治话语那么直白,直接歌颂祖国啊、母亲啊、社会主义呀等一系列民族国家的想象图式。而是将该时代的政治诉求转移到农村生活现实中去,将“公社”、“社员”、“书记”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物象写入诗歌,间接上是为歌颂社会主义、人民公社、中国共产党等功利性诉求服务的。所以说廖诗月意象的不协调景象是符合社会主流思潮,具有一定为政治服务的性质。廖诗的诗歌的政治功利性话语诉求,是符合主要价值取向需要的,而且,该诗也彰显了时代色彩,它向人们描绘了人们对特定时代的看法。这一点也充分说明,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掌握时代的脉搏,才能成为广大人民所欢迎的诗人。
总之,廖公弦诗歌政治功利性和十七年诗歌创作的审美要求标准是相符合的。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深入生活,紧紧把握时代的主旋律,这是诗歌健康发展的方向;一是坚持不懈地贯彻双百方针,促进民族化大众化和个人风格多样性的统一。只不过,廖诗在把握这样创作路线的同时,不断地探索自己独特的创作方法和理念。
四、“月”意象在文革前后诗歌中内含的转变
纵观廖公弦的整个创作,前面已经提到《山中月》里面的大部分诗歌都写于文革前期,当然这几首与“月”相关的诗歌也出自该时期。在新时期之后,廖公弦的诗歌里也有意象出现,但是已经不是早期的韵味和情景。这说明随着时代的变化和诗人心境的变化,诗人的创作审美关照也在悄悄地改变。“月”意象的审美趣味也在转换。例如《上海之夜》中的两节是最能体现这种转变的:“新月来到高楼边,/寂寞里透露出凄凉,/抬头看她一眼,/总觉又瘦又黄。/不懂事的霓虹灯/——那些灯的姑娘,/竟对月亮眨笑眼,/炫耀彩色的衣裳。//劝你月亮回山去,/不必随在我身旁。//”[7]
这短短的两小节,把完全不同的月亮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这里的月亮已经没有原来“山中月”的皎洁、明亮、温馨、静寂和闲适等情景,而变的“寂寞”、“凄凉”、“又瘦又黄”,完全没有原来诗歌中月亮温暖的诗意。同时,还拿城市的灯光和月亮之光进行了强烈的对比,从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到花枝招展的姑娘,全都在暗示着“月亮”的“土气”和不协调。所以诗人最后才发出了“劝你月亮回山去”的呼声。
从表面上看,诗人是拿两种灯光作比较,其实,两种灯光是“城市”和“农村”的两种关照的对应处理。城市的霓虹灯下,出现的是纸醉金迷、五颜六色和强烈的喧哗及浮躁,而月光关照下的乡村是一派静寂的田园,具有月光般的淳朴、厚实和恬静。从此可以看出,诗人通过月意象的营造,将城市和乡村的巨大差异性表现出来。同时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月亮简直就是诗人自己的化身,诗人“劝月亮回去”,实际上在劝自己回去,暗示自己,自己不属于上海这样的大都市,自己的出现与大都市的繁华是不协调的,只有回到自己的山乡,月亮才有那么美妙的意境。
简而言之,虽然作者此时已经定居贵阳,但对于上海来说,仍以乡下人的眼光关照自己和诗歌。以强烈的乡村本位和排斥都市物欲文明的思想进行诗歌创作。他不着重刻画乡村的落后与悲惨,而是通过月意象表现乡里人的淳朴和厚实。从本首诗看,诗人其实是拒绝都市文明的,尤其是发达的城市物质文明,充满了尘世的喧嚣,这是作者不乐意看到和融入的。同时,如果把这首诗纳入作者的城乡关照思想体系,或许从侧面也能印证诗人笔下月意象其实是山里人生活的自由点缀和浪漫想象的载体。
在廖公弦的创作视野中,月亮不再是一种无知觉的本然存在,而是做为一种有生命体,或是山民的象征而出现的,其笔下的月意象有诗情、近生命,无不渗透了诗人的情感和追求,澎湃着诗人田园牧歌式空灵与思考,点缀着大山中那些自由浮动的灵魂。诗歌的月色意境,不是凭空冥想出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诗人从小在黔北绥阳的大山中,诗人在《谈我写诗》中回忆道:“我来自农村。当我刚学会走路,便已经是在外祖母家里了。那里的肥田沃野、茂林修竹,平缓的山丘、弯弯的小河,以及那些老实的牛、欢快的羊,从小就给我一种特定的诗的启示。”这种对于人生的深刻记忆强烈地影响了诗人以后的诗歌创作,月意象当然也是对山里生活记忆的挖掘和升华。通过对月意象艺术美的追求,将月亮在新意境下承载意义的范围进行新的拓展。
综上所述,廖公弦诗歌在特殊的时代、特殊的时代环境中诠释了“月”意象别样的美学内涵和情感表达。这种诠释跟诗人们在不同的人生际遇中对自我的情感体验有关,而这种情感体验的内涵是对自身生活的期许和心灵的关照。
[1]廖玉萍.水意象:触动心灵的弦索——论徐志摩诗歌中的水意象[J].作家作品研究,2007,(05):94.
[2]廖公弦:山中月[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78.34-35,28-29,68-69.
[3]廖公弦.新诗我见[J].诗刊,1982,(01).
[4]张劲.简论廖公弦的抒情诗[J].贵州社会科学,1980,(03).
[5]梅翁.闲话“山中月”[J].花溪,1980,(02).
[6]贺敬之.贺敬之谈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89.
[7]廖公弦.廖公弦诗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50.
(责任编辑:魏登云)
On the Image of"Moon"of Poems by Liao Gong-xian
MAI Cheng-L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 550001,China)
The image of"moon"of the poems by Liao Gong-xian,a means of creating poetic imagination,is the esthetic symbol of image he pursues and studies.The image of"moon",on the one hand,can show us an idyllic imagery,and on the other hand,it is shot through with inharmonious political complaints of discourse.Meanwhile,the connotations of the image"moon"vary at different phases of creation of poems by Liao Gong-xian.
moon in the mountains;moon image;idyllic songs;political discourse
I207.22
A
1009-3583(2010)-04-0036-04
2010-04-12
贵州省教育厅人文科学基金项目“从新时期到新世纪:贵州新诗30年”(08JD015)和贵州省优秀科技教育人才省长资金项目“大西南文化与贵州20世纪新诗研究”(黔省专合字[2009]112号),项目主持人:颜同林教授。
麦成林,男,河南洛阳人,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