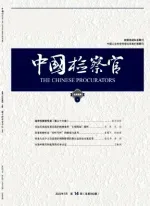有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的实践性检讨
2010-08-15文◎李勇*赵靖*
文◎李 勇*赵 靖*
有组织犯罪若干问题的实践性检讨
文◎李 勇*赵 靖*
一句话导读
本文以一起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件为切入点,从司法实践的角度界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同时探讨实践中对有组织犯罪实体法的诉求和程序法的期待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基本案情]被告人高某纠集有前科的社会青年,形成以高某为首,以尹某、汪某(另案处理)、张某(另案处理)为骨干成员的犯罪组织。尹某主要负责管理由丁某等六人组成的打手;张某带领一帮人插手政府拆迁;蔡某为高某开车,并与宋某、尹某三人充当高某的保镖。尹某带领丁某等打手集中住宿,配发砍刀、枪支、通讯工具,不定期发给报酬。对外以“高某公司”为名号(实际上既无实体,也无注册,仅称呼而已)。2007年初至2007年10月份以来,到娱乐场所“收保护费”、非法索要债务、拆手政府拆迁、强行向酒店销售假冒白酒。2007年11月7日,高某带领手下携带刀、枪准备与另一帮派进行殴斗,结果误将无辜百姓赵某父子打伤,因此而案发。2007年12月25日,公安机关将正在圣诞聚餐的高某等170余人抓获,后因证据不足,仅逮捕10人。
一、问题的提出
由于理论界对有组织犯罪概念、特征及其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实践性探索和规范性思考略显单薄,故此导致在打击有组织犯罪时遭遇重重困境。对上文所举案例,是否可以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争议很大:一种观点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必须有经济实力特征和非法控制特征,现有证据只有各被告人供述证明收保护费、插手拆迁、推销白酒,但被害人不愿作证,插手政府拆迁也没有获取政府方面证据;如何获取经济利益及获取多少利益均无法确定;非法控制也无法证实,因此不能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利益只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的目的,无需证明具体的经济实力,根据《刑法》394条的罪状描述,本案完全符合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特征。该案最终仅以聚众斗殴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进行起诉和判决。这一无奈的处理结果,引发我们对有组织犯罪的有关概念、实体法及程序法等方面的思考。
二、实践需要什么样的有组织犯罪概念
前述案例的争议,表现出学界和实务界对我国刑法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概念和特征认识上的分歧。法学理论终究是要服务于司法实践的,对有组织犯罪的界定应当结合本国的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对于我国刑法来说,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有组织犯罪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之间的关系。有人认为国际上通行的有组织犯罪相当于我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1]有人认为有组织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一种形式,除此之外,还包括集团犯罪和组织程度较低的团伙犯罪。[2]其实,只要厘清“黑社会犯罪”与“有组织犯罪”术语的来历,上述问题便可迎刃而解。黑社会“under-word society”起源于西方,最初原文为“svicicter society”,含义为“邪恶的帮会”,西方人简称为“黑色帮会”,我国把它译为“黑社会”。至于其法定名称,最初有人称为“enterprise crime”即企业型犯罪,但不久被否定,最终“organized crime”经联合国刑事司法处认可。由于“organized”是一个被动(过去时)结构,因此直译应为“已经组织化了的犯罪”,表明是一种有组织体制的犯罪。从有组织犯罪术语的来源、演化可以看出,有组织犯罪即黑社会犯罪,两者是等同的。刑法学是规范学,刑法学意义上的“有组织犯罪”概念必须是一个规范性的概念(这一点与犯罪学是不同的),结合我国的刑法规范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那么国际上通行的“有组织犯罪”与我国刑法中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应该是相对应的,可以在同等意义上使用。
对于司法实践来说,或许对有组织犯罪的定义并不是那么的重要,这一点正如日本学者长井圆所指出的“不过我们并不总是只需要有组织犯罪的简单定义。众多不同的定义取决于各国各地区研究有组织犯罪的目的和产生于受不同国家、地区的不同文化、政治、和社会经济条件影响的社会现象及其制度结构”。[3]对于司法实践来说,更为重要的是,学理上能提供有助于认定有组织犯罪的若干特征。对有组织犯罪定义或许是困难的,但是结合我国的实践和现实,并结合国际最低限度的标准,找出具有共性的特征,应该不是难事。既然有组织犯罪作为国际社会的通病,那么,就一定存在一些共同的“交集部分”。
首先,既然是有组织犯罪,那么作为一种组织化了的犯罪结构,组织结构特征就是必备的。同样,既然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就必须具有“社会”性的组织结构,就我国刑法规范及司法实践来说,至少是三人以上组成的,有明确的组织、领导者,成员相对固定和有一定分工。例如前述案例中以高某为首领,以尹某、汪某为骨干成员,打手、拆迁、推销白酒等分工相对明确。
其次,既然有组织犯罪集团与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同等意义,那么,黑社会与正常社会的区别就在于其反社会性。反社会性主要体现在非法控制上,具有长期生存的基础和防护体系,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领域内,形成非法控制。这里的非法控制,不可能向意大利黑手党一样,要求其控制一个政党或向政治领域渗透,因此,不一定需要政治上的“保护伞”,其所控制的既可以是一条街道、一个区甚至是一个城市;也可以是一个领域,如前述案例中的娱乐行业,也可以是多个行业或领域。
最后,通过实施暴力、威胁或其他非法手段,获取经济利益。一般认为暴力性是构成我国刑法黑社会(性质)组织不可缺少的要件,但近年来黑社会犯罪呈现软暴力化的趋势,比如在初期靠暴力起家,后来“漂白”成合法公司运作,此时司法机关再获取其起家时暴力方面的证据,难度很大。事实上,《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下文简称《公约》)也没有要求暴力性,而日本的暴力团经过修改“不限于暴力性犯罪组织,亦不需要行使暴力或者威胁手段。”另外,获取经济利益是有组织犯罪的基本追求(或者说是犯罪目的),也是《公约》最低限度的共识。这对我国情况而言,同样是适用的,但却并不需要像美国学者所界定的那样成立企业或公司。我们认为,黑社会(性质)组织对于经济利益的追求,在犯罪构成上,只需要作为犯罪目的进行理解,在证据上也只需要达到普通目的犯的证明标准,无需像证明客观要件那样必须证明经济利益的来龙去脉和经济实力的大小。
三、实践对有组织犯罪实体法的诉求
法律不仅需要被法学一再解释,“也必须被 ‘填补漏洞’,并且要配合情势的演变”。[4]前述案例最终无法以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起诉和判决,原因之一在于立法上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界定不明,歧义重生,导致司法实践中各执一词。从司法实践对实体立法的诉求来看,最要紧的莫过于对有组织犯罪的罪状进行明确化修改。[5]
(一)“黑社会性质组织”用语缺乏科学性
我国刑法规定的有关有组织犯罪主要是《刑法》第294条中的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如前所述,国际上通行的有组织犯罪与黑社会犯罪具有同等意义,我国刑法没有必要“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个新的名词。如果说当时的立法者是考虑到“在我国,明显的、典型的黑社会犯罪还没有出现”,[6]那么时至今日,从乔四案、张君案、刘涌案,到最近的重庆万贯财务公司陈坤志案……虽然比上意大利的黑手党,但是与我国港、澳、台的黑帮、美国的摩托车黑帮等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这种“良苦用心”似乎已经不合时宜了。实际上,我国大陆目前黑社会犯罪形势的严峻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7]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既不利于国内有组织犯罪的打击,也不利于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最典型的缺陷表现在以下三种情况:(1)参加境外的黑社会犯罪行为无法定罪,因为我国刑法规定的是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但由于行为人参加的是境外黑社会而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因此,按照罪刑法定的要求,不能以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定罪处罚;(2)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在境内从事黑社会犯罪活动的行为无法定罪,因为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境外的黑社会到境内发展成员的,构成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成员罪,对于其从事发展成员以外的犯罪活动,由于刑法缺乏规定而无法定罪;(3)包庇纵容境外的黑社会组织成员的行为无法定罪,因为我国刑法仅规定了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而对于行为人包庇、纵容黑社会(而非黑社会性质组织)的行为在刑法上也缺乏规定。[8]对此,有人主张增设新罪名。[9]其实产生上述立法漏洞的原因不在于刑法罪名覆盖面不够,而是在于使用了“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个不伦不类的术语,而无法与国际对接所导致的。只需将“黑社会性质组织”修改成“黑社会”,上述问题均可迎刃而解。
(二)立法对有组织犯罪构成要件描述缺乏明确性
我国《刑法》第294条以近乎文学化的语言对黑社会性质组织进行了界定,即“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这里的 “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均属非法律用语,歧义重生,含义模糊,在实践中如何用证据来证明这些带有强烈主观色彩和文学色彩的表述?这种不明确的话语,既可能扩大打击面,也可能缩小打击面,给司法实践造成适用上的困难。
在立法上对黑社会组织进行界定,或许短期内达成一致意见还相当困难,但是如前所述,有些特征是共通的。当我们无法界定一个事物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确实什么是该事物。因此,根据有组织犯罪(黑社会犯罪)共通的特征,立足于我国的打黑现实,并结合《公约》最低限度的要求,进行立法上的界定,应该是基本的努力方向和研究思路。我们冒昧地按照这种方向和思路,结合前文概括的有组织犯罪的三个特征,并结合有关立法解释和《公约》,提出如下立法建议供批判:由三人以上所组成的骨干成员稳定、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有组织地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并在一定的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控制势力的组织,是黑社会组织。
四、实践对有组织犯罪程序法的期待
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当地群众都称“高某公司”是黑社会,甚至坊间传言:谁家的小孩哭闹,大人就以“高某来了”来吓唬小孩不要哭闹。公安人员在实施抓捕行动时,一举抓获高某等正在圣诞节聚餐的170余人,但因取证不到位最终逮捕的只有10人。该案最终只能以普通犯罪起诉和判决,固然与实体立法不明确而导致的分歧有关,但同样也有程序立法滞后所导致取证不能的原因。有组织犯罪组织化、隐蔽化、智能化的特征,使得取证困难成为我国当前打击有组织犯罪的瓶颈问题。司法实践最大的期待之一就是对有组织犯罪在程序立法上规定特别的侦查措施和程序。
(一)成立专门机构
西方一些国家在议会下设打击有组织犯罪专门机构,负责直接指导、监督和协调全国的打击有组织犯罪工作。如意大利议会下设反黑手党委员会;美国除议会的相关委员会以外,在白宫还专设直属总统领导的有组织犯罪调查委员会。我国目前对黑社会犯罪的侦查仍然依赖于公安机关,尽管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了“打黑处”,但是毕竟只是公安机关内部设置,力量、技术以及摆脱地方行政干涉的能力都相当有限,更为重要的是在挖出“保护伞”上因无职务犯罪侦查权而只能请求检察机关协助。但毕竟检察机关和公安机关属于不同建制,领导指挥步调不一、沟通协调管道不畅,在所难免,这必然使打击黑社会犯罪的时机、力度大打折扣。尽管有时各地政法委出面进行协调,或者成立由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参加的专案组,毕竟只是临时措施,难以形成长效机制。
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对于高某等插手政府拆迁,相信必定有政府人员陷身其中,之所以取证困难,没能“拔出萝卜带出泥”,揪出“保护伞”,主要症结在于缺乏专门的机构设置。因此,为适应我国反击有组织犯罪的实践诉求,必须建立独立的反黑机构,可以考虑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下设全国反黑机构,各省、市级人大常委会下设分支机构,为防止来自地方“保护伞”的阻力,区、县一级不宜设立反黑机构。
(二)秘密侦查法制化
我国目前的秘密侦查在实践中遭遇两种尴尬局面:其一是“能作不能说”,秘密侦查的操作只有公安机关的内部规定,不能对外;其二是“作了也白作”,由于秘密侦查没有得到立法认可,因此秘密侦查获取的证据不能直接作为证据使用,而必须经过“转化”才能作为证据使用。[10]这样的现状,既妨碍秘密侦查作用的发挥,更容易侵犯人权。
为此,西方很多国家在立法上都确立了对有组织犯罪实行电子监控、卧底行动等秘密侦查措施。《公约》第20条也允许在适当的情况下使用其他特殊侦查手段,如电子或其他形式的监视和特工行动,以有效打击有组织犯罪。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公安机关抓获高某170余人,最终只逮捕10人,其余一一释放,原因就在于侦查不力,未能在抓捕前通过秘密侦查而摸清该组织的情况,并掌握相关证据。当然秘密侦查措施犹如双刃剑,有侵犯隐私和触犯人权之风险。所以,必须建立相应的正当化程序,包括审批程序、秘密侦查的范围和时间限定、秘密侦查后告知程序等,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审批程序。一般来说,秘密侦查需要由中立的第三方即法官批准以起到监督制约之功效,但就我国的实际情况而言,如逮捕措施一样,权宜之计应当还是由检察机关批准。
(三)完善证人保护制度
为分散和瓦解黑社会组织,西方国家的警察部门近年来非常注重对证人的保护工作。美国不惜花费高昂代价建立 “证人保护项目”(Witness Protection Program),由美国法警局审核是否参加证人保护项目,一旦被允许加入,证人及其家庭会被安置在国内危险比较少的地方,并提供新的身份和经济支持直到证人能找到可靠的工作,尽管花费高昂(2003年美国为执行该项目花费6000万美元),但是效果很好,在受到保护的证人出庭作证的案件中,定罪率高达89%。[11]
我国证人保护的立法,可谓一片空白。普通犯罪的证人作证尚且有难度,更何况是涉黑犯罪。民众对黑社会惟恐祸及己身而避之不及,哪里敢出面作证。本文开头引用的案例,我们在审查起诉过程中也曾试图说服证人作证,但最终均无功而返,我们切身感受到我国建立证人保护制度的紧迫性。在我国证人保护制度空白的情况,权宜之计是先建立反黑社会犯罪的特别证人保护制度,对于涉黑案件中的证人提供其免受威胁的必要保护。另外,也有必要建立类似污点证人制度,对于愿意配合司法机关作证的被告人,可以做相对不起诉或者在审判量刑时予以从轻处罚。
五、余论
我国涉黑犯罪形势越来越严重,司法实践中遭遇的困境越来越大,司法实践对有组织犯罪在实体和程序方面的立法,均有诸多紧急而迫切的期待。世界上多数国家为应对有组织犯罪均进行了单独立法,如美国《反有组织犯罪侵蚀合法组织法》(RICO法案)、日本的《反暴力团法》等。我国台湾地区的《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有组织犯罪法》也值得借鉴。为了有效应对有组织犯罪,满足反击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实践诉求,有组织犯罪立法建构和完善应当列入关注视野。我们认为,有关实体方面的立法,可以通过刑法修正案的方式对现有刑法进行完善;而程序方面,鉴于有组织犯罪侦查的特殊性,可以考虑单独制定特别法。
注释:
[1]何秉松:《犯罪团伙、犯罪集团、黑社会性质组织、黑社会组织、有组织犯罪集团辨析》,载《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2]陈兴良:《关于黑社会性质犯罪的理性思考》,载《法学》2002年第8期。
[3][日]长井园:《有组织犯罪:日本文化的产物》,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4期。
[4][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12页。
[5]当然,学界还比较一致地认为,目前我国有组织犯罪立法上还存在法定偏轻、缺乏财产刑、与洗钱等犯罪缺乏系统和完备性、缺乏减刑假释的特别规定等。鉴于讨论范围的限制,本文对这些问题不再论述。
[6]王汉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载赵秉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44页。
[7]田宏杰:《试论我国“反黑”刑事立法的完善》,载《法律科学》2001年第5期。
[8]事实上,境外的黑社会组织到我国境内除了发展成员以外,实施黑社会违法犯罪活动的情况已经出现。参见于立霄:《境外黑社会在京诈骗金额达数千万,手段花样翻新》,载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0/content_5186126.htm,2009年8月30日访问。
[9]张惠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立法完善浅析》,载《时代法学》2002年第2期。
[10]罗旭红、李文燕:《有组织犯罪与秘密侦查法制化》,载《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
[11]参见前美国司法部联邦检察官Amy Chang Lee于2009年7月15日在江苏省检察官培训学院所做的题为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in the Investigation and Prosecution of Qrganized Crime”的演讲。
*江苏省南京市建邺区人民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法学硕士,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210004]
**重庆市北碚区人民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主任,法学硕士,全国检察理论研究人才[400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