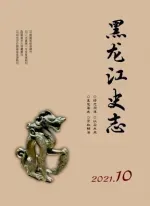王夫之论唐后期宗室典兵
2010-08-15刘兴云
刘兴云
(南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61)
王夫之《读通鉴论》第二十七卷《昭宗六》曰:“藩镇交横于外,则任亲军以制之,乃李茂贞以亲军跋扈尤甚于藩镇,昭宗凝目四注,无可任之人,乃出曹诚等于外,而令诸王统兵以宿卫,盖不得已之极思耳,然亦未尝非计也。”[1]王夫之此段话谈到了昭宗时期任用宗室诸王统兵,但正因为此,也导致了宗室的彻底覆灭。
宗室问题是封建社会中的一个重要问题,若宗室的权力无限扩大,会影响到其他社会群体的利益,也会危及到政权的稳定。但唐代尤其是唐代后期,对宗室采取过度限制的办法,却是矫枉过正,不利于发挥宗室群体的积极作用,甚至导致社会动荡。
关于唐代宗室问题的探讨,有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2]、李彦群的《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述论》[3],但他们较少涉及唐后期宗室问题,本文主要对唐代后期宗室及其典兵问题进行探讨,敬请方家指正。
一、唐代前期宗室典兵概述
唐高祖至睿宗时期,允许宗室典兵,但同时,也带来了宫廷政变;鉴于此,唐玄宗在位时期,限制宗室典兵,不许诸王出阁,虽有刺史、节度大使之号,但并无实权。
唐代初期,国家草创,诸王在政治生活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高祖建唐的过程中,其子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建立了功业,因而也握有强大的兵权。太宗、高宗在位时期,宗室诸王多任刺史、都督、都护,成为封疆大吏。鬱林王恪曾授安州都督、梁州都督。蜀悼王愔任过歧州刺史、黄州刺史。蒋王恽拜安州都督、迁箕州刺史。越王贞为豫州刺史、迁博州刺史。纪王慎迁襄州刺史、贝州刺史。曹王明也“累为都督、刺史”。[4](卷80《太宗诸子传》)太宗为加强宗室的权力与地位,曾于贞观十一年(637)颁令刺史世袭,因大臣反对,贞观十三年又加以废除。[5](卷47《封建杂录上》)但由于诸王握有重兵,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六月四日,发生了秦王李世民夺权的玄武门事变。
唐玄宗统治时期,诸王遥领,无实际权力。玄宗通过宫廷政变登上皇帝宝座后,吸取唐初以来皇位不稳的教训,对影响较大的诸王采取外刺手段,以防范诸王对皇位的觊觎。开元二年(714)六月,玄宗采纳姚崇的建议,相继罢免了诸王主典禁军的职务,外任刺史,并规定诸王外任刺史只领大纲,各州政务均由朝廷命官负责处理,自宋王以下每季只许两人入朝,不得同时留居京师。开元九年(721),为防止诸王在地方上形成私人势力,下令“诸王为都督、刺史者,悉召还京师,”[6](卷212开元九年十二月)给以极优厚的待遇,但不许他们担任知事官。对于诸皇子、皇孙实行长期幽闭,不许出阁,只是遥领,并无实权。
遥领并不始于玄宗,太宗时期就出现宗室遥领。贞观二年五月,“吴王恪除使持节、大都督益、绵、邛、眉、雅等八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濮王泰除史持节、大都督扬州、常、海、润、楚、舒、庐、濠、寿、歙、杭、宣、东睦、南和等十六州诸军事、扬州刺史。”[5](卷78《亲王遥领节度使》)玄宗为加强皇权,将唐初的遥领由个别情况变为普遍实行的定制。“开元四年正月二十九日,剡王嗣直除安北大都护,充安抚河东、关内、陇右诸蕃部落大使。陕王嗣升为安西都护,充河西道及四镇诸蕃部落大使、安北大都护,张知运为副都护。亲王遥领节度,自兹始也。其在军节度,即称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十五年五月,以庆王浑为凉州都督兼河西节度大使。忠王浚为单于大都护、朔方节度大使。棣王炎为太原以北诸军节度大使。鄂王瑶为幽州都督、河北道节度大使。营王湟为京兆牧、陇右节度大使。光王琚广州都督、五府节度大使。仪王瓍河南牧。颍王璬安东都护,平卢节度大使。永王璘荆州大都督。寿王瑁益州大都督、剑南节度大使。延王泗安西大都护、碛西节度大使。盛王沐扬州大都督。”[5](卷 78《亲王遥领节度使》)
唐玄宗开元、天宝之际,节度使领兵制度实行起来,中央也委派宗室诸王任节度大使,但玄宗皇帝规定的诸王遥领不出阁制度,又使宗室诸王对藩镇的控制流于形式,形同虚设,特别是唐后期藩镇强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二、安史之乱后宗室典兵情况
安史之乱后,诸王一度出阁;但唐后期大部分时间里,诸王遥领之制继续实行。唐后期由于军权分别掌握在宦官与节度使手中,宗室无兵权,这在制约宦官与藩镇方面作用不力,直接危及到唐王朝的生存。
安史之乱爆发后,玄宗出逃,在出逃途中,玄宗皇帝改变了诸王不出阁制度,任命皇子诸王担任军事统帅。至德元载(756)七月十五日发布的《幸普安郡制》,重申“命元子北略朔方,诸王分守重镇,合其兵势,以定中原。”[7](卷79《銮驾到蜀大赦制》)以太子李亨为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以永王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都使;以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路及淮南、河南等道节度都使;以丰王李瑛为武盛大都督,并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节度都使。但在诸王领兵平叛的过程中又发生了太子李亨与永王璘争权事件,最后永王璘兵败被杀。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冬十月辛酉,“诏天下兵马元帅雍王统河东、朔方及诸道行营、回纥等兵十余万讨史朝义,会军于陕州。加朔方行营节度使、大宁郡王仆固怀恩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戊晨,元帅雍王率诸军进发,留郭英乂、鱼朝恩镇陕州。壬申,王师次洛阳北郊。甲戌,战于横水,贼大败,俘斩六万计。史朝义奔冀州。乙亥,雍王奏收东京、河阳、汴、郑、滑、相、魏等州。乙酉,陕西节度使郭英乂权知东京留守,丁酉,伪恒州节度使张忠志以赵、定、深、恒、易五州归顺,以忠志检校礼部尚书、恒州刺史,充承德军节度使,赐姓名曰李宝臣。于是河北州郡悉平。贼范阳尹李怀仙斩史朝义首来献,请降。”[8](卷 11《代宗纪》)
唐代宗在位时,“悉王诸子,领诸镇军,威天下”。《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传》记载:“淄青牙将李怀玉逐其帅侯希逸,诏(李)邈为平卢、淄青节度大使,以怀玉知留后。大历初,代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大历十年,田承嗣不臣,而昭靖(李邈)夭,无疆土,帝乃悉王诸子,领诸镇军,威天下。於是以(李)述为睦王,领岭南节度,(李)逾郴王、渭北鄜坊节度,(李)迥韩王、汴宋节度,(李)造忻王、昭义节度,皆为大使……然不出阁。”[4](卷82《十一宗诸子传》)
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八月,以舒王谊为泾原节度大使。”贞元二年(786),虔王李谅“领蔡州节度大使,以吴少诚为留后;十年,徙节朔方灵盐,以李栾为留后;明年,又徙徐州,以程怀信、张愔为留后。不出阁。”文敬太子李謜,“历义武、昭义二军节度大使,以张茂昭、王虔休为留后,不出阁。”[4](卷82《十一宗诸子传》)“贞元四年七月,以虔王谅为申光随蔡节度、观察大使。”七年七月,以邕王璲为义武军节度、易定等州观察使。[5](卷78《亲王遥领节度使》)贞元九年(793),通王李谌“领宣武节度大使,以李万荣为留后,二年徙河东,以李说为留后,皆不出阁。”
顺宗子福王李绾,“历魏博节度大使。”宪宗子建王恪,“为恽州大都督、平卢军淄青等州节度大使,以(李)师道为留后,然不出阁。”[4](卷82《十一宗诸子传》)
可以说,唐后期,诸王虽有节度大使之号,但多不出阁,由于留后或节度副大使主管军政事务,宗室诸王没有多少实际权力。
唐昭宗时期,朝臣与宦官矛盾斗争激烈,双方争相与藩镇胶结,皇帝势孤,于是命诸王典兵,《新唐书》卷82《十一宗诸子传》:“通王滋……昭宗乾宁三年,领侍卫诸军。是时,诛王行瑜,而李茂贞怨,以兵入觐,诏滋与诸王分统安圣、奉宸、保宁、安化军卫京师。天子将狩太原,韩建道迎之,留次华州。建畏王等有兵,遣人上急变,告诸王欲杀建,胁帝幸河中。帝惊,召建谕之,称疾不肯入。敕滋与睦王、济王、韶王、彭王、韩王、沂王、陈王谒建自解,建留军中,奏言:‘中外异体,臣不可以私见。’又言:‘晋八王擅权,卒败天下。请归十六宅,悉罢所领兵。’帝不许。建以兵环行在,请诛大将李筠。帝惧,斩筠以谢。建尽逐卫兵,自是天子孤弱矣。”[4](卷82《十一宗诸子传》)昭宗皇帝可以说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曾利用藩镇的力量杀掉宦官杨复恭,任用宰相崔胤诛除宦官刘季述,但在诸灭宦官的过程中,藩镇更加跋扈。昭宗任命宗室诸王统领安圣、奉宸、保宁、安化等军保卫京师,这一举措引起藩帅李茂贞、韩建等人的恐慌,最终藩帅逼使昭宗杀掉诸王。昭宗皇帝和宰相崔胤虽做了一番努力,但李唐王朝已是江河日下,无论采取怎样的措施也无力控制骄横的藩镇了。即便如此,由藩镇将帅而来的五代帝王仍在继续着李唐皇帝的削藩梦想。
三、唐代后期宗室衰微的原因
唐代后期宗室衰微的原因主要有:
(一)玄宗限制宗室政策的影响。玄宗皇帝确立宗室诸王遥领政策,是在“中央政治革命”[9]盛行时期。因为唐前期,实行“关中本位政策”,军事上盛行府兵制,内重外轻,谁掌握了北门禁军,谁就控制了中央,谁就可以左右政局甚至皇帝的废立。故玄宗皇帝为巩固皇位,要加强对宗室诸王的约束,设立十王宅、百孙院,幽禁皇子诸王,不许出阁。而唐代后期,府兵制瓦解,军权下移到节度使、观察使手中,外重内轻,在这样的情况下,执行宗室诸王遥领政策,实际上是削弱了皇权,并没有达到控制藩镇的目的。
(二)宦官势力的强大。唐代后期,宦官势力日趋发展。肃宗即位得到宦官李辅国的拥立,返京后,李辅国得势;代宗统治时期,宦官程元振、鱼朝恩势倾朝野;德宗出幸奉天,怒朝官护驾不力,从此信任宦官,“德宗还京,颇忌宿将,凡握兵多者,悉罢之,禁旅文场、仙鸣分统焉。贞元十二年六月,特立护军中尉两员、中护军两员,以帅禁军,乃以文场为左神策护军中尉,仙鸣为右神策护军中尉,右神威军张尚进为右神策中护军,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策中护军,自文场等始也。时窦、霍之权,振于天下,藩镇节将,多出禁军,台省清要,时出其门。”[8](卷184《宦官列传》)宦官掌握中央禁军的领导权,从此,皇帝的废立掌握在宦官手中。唐昭宗时期,鉴于朝中宦官和地方藩镇势大,决定诸王典兵,枢密使蒋玄晖置宴杀害德王已下六王。《旧唐书》卷175史臣曰:“自天宝已降,内官握禁旅,中闱篡继,皆出其心。故手才揽于万机,目已睨于六宅,防闲禁锢,不近人情。”[8]
(三)藩镇力量的强大。《新唐书》卷50《兵志》:“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鐬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磎,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瓘、刘景宜请天子幸邠州,全瓘、景宜及子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扞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余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后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后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余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于是四军二万余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于大云桥。俄遂杀十一王。”[4]景福元年(892),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静难节度使王行瑜、镇国节度使韩建等人上表,以讨伐专擅朝政的大宦官杨复恭为名,请求以李茂贞为山南西道招讨使。景福二年(893),昭宗打算罢去李茂贞所任凤翔节度使之职,专任山南西道兼武定节度使,李茂贞拒绝任命。昭宗下令讨伐,以宗室覃王李嗣周为京西招讨使,由于宰相崔昭纬通敌,结果禁军战败,李茂贞进逼京师,左右朝政。被韩建劫持到华州的昭宗受到胁迫,遣散亲兵,诸王也被韩建杀害,天子孤弱。
《新唐书》卷82赞曰:“唐自中叶,宗室子孙多在京师,幼者或不出阁,虽以国王之,实与匹夫不异,故无赫赫过恶,亦不能为王室轩轾,运极不还,与唐俱殚。然则历数短长,自有底止。彼汉七国、晋八王,不得其效,愈速祸云。”[4]唐代后期无论是节度使掌握藩镇兵,宦官典掌禁军,还是宗室典兵,都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昭宗利用宗室典兵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制度设计的失败,应是唐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
[1]王夫之.读通鉴论[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介永强.唐代宗室管理制度论略[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科)2003(01).
[3]李彦群.唐代前期的宗室政策述论[J],理论界,2009(04).
[4]欧阳修,宋祁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
[5]王溥.唐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6]司马光.资治通鉴[M].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版.
[7]宋敏求.唐大诏令集[C],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8]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