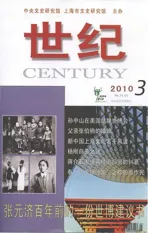杨 刚自杀之谜
2010-07-26钱江
钱 江
(作者为中国当代史专家,著有《乒乓外交》等多种著作)

杨刚是中国20世纪著名女记者,如果她在生命的最后十余年不是全身心地投入政治,或许会成为一个极出色的女诗人、散文家,因为诗的光彩、文学的色泽,早在她年轻的时候就显现出来,受到人们广泛关注。
但是杨刚没有这样。建国之后,她先后任职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和中宣部,于1955年初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成为《人民日报》编委中唯一的女性。更使人没有想到的是,1957年反右正处于高峰,副总编辑杨刚突然自杀。留下了一个长久不解的谜团。
我的父亲钱辛波是杨刚的老部下,他认为杨刚的遽然离去不可思议,因为他眼中的杨刚性格豪爽外露(但据说在生命的最后一年有明显的变化),能吸烟,好高谈。这样的人怎么会选择以自尽的方式告别人世呢?
父亲的挚友蒋元椿则是杨刚点名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是她倚重的国际部负责人之一、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在父亲和蒋元椿的晚年,他们许多次讨论杨刚的离去,蒋元椿还写下了一篇《忆杨刚同志》。他们一致认为,当年曾有一说,说杨刚因丢失了一个笔记本而导致精神苦恼而辞世,这是站不住脚的。
现在,随着更多史料的出现,或许可以帮助人们在探索问题时前进一步了。
杨刚长辞是有先兆的
事情发生在1957年10月7日,那天清晨,《人民日报》工作人员发现,杨刚衣着整齐,在自己住处的房间里静静地睡去,再也不会醒来了。
对于杨刚辞世是否有遗言,目前有两种说法。过去常见的说法是杨刚默默离去,什么也没有留下。现在,又有新说法。张宝林在今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各具生花笔一枝——高集与高汾》一书中说,杨刚辞世时留有遗书,最先来到现场者赶紧将遗书交给社长邓拓。邓拓又马上将遗书报送周恩来总理了。直至今日,未见对遗书文字的披露。如果有遗书,当是能够解释杨刚为何离去的重要文件。张宝林是一位严谨的学者,言必有据,他的论述值得重视。
闻得杨刚自杀,社长邓拓大惊,马上派人将她送到协和医院抢救,并派编委林淡秋、袁水拍到医院了解抢救情况,编辑叶遥也跟着去了。医检发现,杨刚吞服了大量安眠药,已经离世。
周恩来知晓杨刚去世感到震惊,邓拓等人也向他报告原委。看来他对所知情况感到不足。不久,周恩来到剧院看戏,看到了《人民日报》国际部西方部副主任高集。高集是杨刚早年在《大公报》的同事,曾得到杨刚许多帮助。演出开幕前,周恩来让秘书叫来高集,专门询问杨刚的离去是怎么回事?当时的高集显然说不出多少来。(张宝林《各具生花笔一支——高集与高汾》,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186-187页)
事后看来,杨刚选择离去是有先兆的。据蒋元椿所知,辞世前不久,或许就是之前二三天,杨刚找到同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的黄操良,谈了整整一个晚上。他们谈到正在国际部喧嚣展开的反右,这里将是报社打出成批右派的部门。就连黄操良本人也在半年后和杨刚一样突然自杀,而且在死去之后被宣布为右派。但在那个晚上,杨刚和黄操良谈了什么,永远不可能有人知道。
当时的文艺部年轻女编辑叶遥后来回忆说,1957年10月6日晚上,她在报社四层办公室里编辑一篇杨刚本人撰写的批判作家萧乾的文章。杨刚的文章写在白油光纸上,调子不高,还是有分析,讲道理的,好像规劝老朋友看问题不要太片面。稿子是编委林淡秋审阅后交给叶遥编发,因为杨刚的字有些写成草体,要叶遥核校小样。
叶遥快完成核稿了,有人敲门,进来的竟然就是杨刚。叶遥惊讶地问:“怎么这么晚你到办公室来了?”
杨刚说,她一个人慢慢走到王府井大街,看到文艺部——正是杨刚分管的部门办公室有灯光,就上楼来了。她问叶遥在做什么?
叶遥如实相告,正在核校她写的批判萧乾的书面发言。
杨刚有些烦躁地说:“没意思,没意思,不要发表了。”
在反右中说批判文章“没意思”,使叶遥感到吃惊,她说:“这是淡秋交的任务,我做不了主呀。”
杨刚说,她回家后打电话给林淡秋,这篇稿件不要发。
叶遥看她很坚决,答应把这个意见明天告诉林淡秋。她边说边劝杨刚赶快回家休息,并扶着杨刚回家。作为一个年轻女性,叶遥这时才注意到她这天穿的衣服很特别:上身穿一件中式对襟紫玫瑰红袄,下身穿一条折缝笔挺的黑呢裤子,一双白色袜子和黑色布底鞋,不像平时穿着那么随便。“我没有说什么,只扶她一道走。她有点责备我没带小三(指叶遥的孩子)到她家去玩。我没有辩解,让她发泄一下心里的郁闷,可能回去入睡快些。我陪她到家大门口,她双手抓住我的手不放,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我慢慢抽出手,祝她‘晚安’。她说:‘谢谢!’我们招手告别。”(叶遥《名记者杨刚之死》,《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12期)
没想到,杨刚就是穿着这身衣服离去的。而叶遥编辑的杨刚的最后一篇文字也就没有发表。
另据所知,杨刚几天前和一位亲戚一起吃了饭,席间关照他要好好生活。但她自己,却要与生活告别了。
在革命风涛中成长
杨刚(1905-1957)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她出生在湖北一个豪门望族,父亲曾是军阀时代的湖北省代省长。杨刚自幼学习优异,考入北平的燕京大学英文系。她在1930年加入共产党。不久在因病治疗期间退党,但一直坚持左翼文化活动,是北方“左联”的发起人之一,曾帮助斯诺编译《活的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杨刚于1938年重新入党,主编过《大公报》副刊《文艺》版。对杨刚的文学成就,研究者较多,这里不重叙。
在这一时期,她的婚姻破裂,与丈夫郑侃离异。后来郑在福建时死于侵华日军的轰炸。那以后,杨刚和女儿郑光迪一起生活。1944年至1948年,她担任《大公报》驻美国特派员,在美国从事新闻采访,并根据党的安排做国际统战工作。
1948年11月,杨刚奉命归国,经香港到西柏坡,在平津战役中参加接收天津,担任天津《大公报》副总编辑、党委书记。同年5月上海解放,杨刚南下,任上海《大公报》军代表。次年,杨刚调回北京,担任外交部政策研究室主任秘书,同年10月调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1953年,她任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处长;1955年春调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分管国际报道。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中共八大代表。
总体来说,她的工作经历大致上还是顺利的。但在1955年秋天,杨刚在北京机场路上遭遇车祸,头部受到重撞。受脑震荡影响她病休了半年。这以后她有头痛的病历,但可以肯定的是,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改版后扩大版面,杨刚是积极参加了,在这年大部分时间全天工作,那么应该说身体还可以支持。何况杨刚是一个性格坚强的人。同事普遍回忆,未见她在上班时因头痛而不能工作。
反右运动铺天盖地而来之时,杨刚是积极投入的。1957年5月6日,报社成立“整风领导小组”,成员共7人:邓拓、胡绩伟、杨刚、王揖、黄操良、陈浚、萧风。杨刚名列第三把手。进入6月,“整风”转为反右,原整风领导小组即转变为“反右领导小组”,还加上了新来的总编辑吴冷西。
离去前的杨刚看到了什么
1957年6月9日,标志着发动反右大反击的《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的第二天,杨刚以“金银花”为笔名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文章《请让我也说几句气愤的话吧》,这是她一生中发表的最后一篇作品,而且是配合当前“反右”的文字。字里行间,是她对那些“提意见者”的规劝:
“弟兄们,我想起那些年我们一起做的梦,不论人家怎样想,几万万人的梦想,会是很大的吧;那时候,美国人和地主官僚资本的鞭子抽得我们满地滚呵,我们的苦恼有天那么大,我的梦也有天那么大;天上飞着大红旗子,天帏和烟囱交颈拥抱,绕着我们的红旗呼呼地、呼呼地,喷出我们强烈的诗篇——钢铁的火焰和烟云;我们全站起来了,抬出了紫艳艳的晨曦,还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洪流把人们载送到永远,永远。虽然我们吵架,争工分,争猪食,反对官僚主义……可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弟兄们,我们一起做过梦,又一起把梦变成了生活。难道这一切都错了吗?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

“梦”,是全篇文字的立意。“难道我们做梦也做错了吗?”似乎可见杨刚批判之所指,是希望当年和她一起做梦而出偏者猛醒。杨刚分明有她自己的“梦”。1949年10月1日,她以新闻界代表身份出席开国大典,以抑制不住的兴奋写下了通讯《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文中说:“我们几千年来的希望,我们几千年来的要求,要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五者俱备的国家的要求——在过去常常使人称为是白天大梦,或者是唱高调,现在这个几千年的大梦一定会实现了。”
1986年4月,蒋元椿到美国密苏里大学讲学,他在杜鲁门总统图书馆查阅档案时意外发现了杨刚于1946年1月20日致杜鲁门的信,原件为英文。杨刚从燕京大学毕业,英文程度很好,信写得相当流畅,她以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名义,反对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军援,指出:“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态度正处在十字路口。”
杜鲁门阅读了杨刚的信,于当年1月25日致信商业部长华莱士,信中说:“我对中国政治知之甚少,我感兴趣的一件事情是看到一个对我们友好的拥有民主政府的强大的中国。”但是杜鲁门随后推行的扶蒋反共政策将中美关系推进了险境。
阅信人蒋元椿认为,杨刚信中表现出“忧国忧民、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奋斗的精神风貌”。
但是,反右风暴使杨刚看到了她不愿意看到的场景。当年和杨刚一起奔走采访的新闻记者们,特别是《大公报》的记者、编辑们,眼下纷纷陷入批判的包围中。老党员徐盈要戴上右派帽子,他的妻子、名记者彭子冈也跑不了落在帽下。就在9月里,杨刚亲身参加了《北京日报》社举行的批判会,还发言严厉批判曾经的《大公报》同事、同为中共地下党员的彭子冈。已一年多未看见杨刚的当年《大公报》同事吴永良(旋即被“划右”)发现,杨刚的头发花白了,按说刚刚50岁出头的杨刚本不该有那许多白发。他还觉得,杨刚批判彭子冈是怎样从资产阶级妇女堕落成资产阶级右派妇女的,调门不低。他不知道这是对着稿纸照本宣科呢,还是杨刚真的有如此之认识?
据现在所知,在风暴来临的日子里,杨刚和原《大公报》社长王芸生有一次谈话。后来杨刚曾和别人说起过,她和王芸生谈话了。谈了什么,未见披露。
这些天,杨刚参加文化界批判右派的活动有好几个。就在自杀的前一天,她参加了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大会。这次会议上,丁玲那些早已有过结论的“历史错误”又被拎出来清算。杨刚熟悉丁玲,她们都是早年就投身革命的女性。
更严峻的事态发生在身边
杨刚熟悉的、即将被打成右派的熟人、朋友何止于此。她在《人民日报》的同事,当年的《大公报》同事高集,曾向胡乔木提出一些意见,在运动中险些被扫入“右派”行列,但是高集的妻子,也是《大公报》记者的地下党员高汾没有幸免。叶遥后来回忆说:“许多人被打成‘右派分子’公之于众,其中有她(杨刚)多年共处的老同事和相知的朋友,难道对她没有触动?”
更为直接的,则是由杨刚点名,于1955年4月从新华社调来《人民日报》担任国际问题评论员的蒋元椿。恰恰在反右大反击前夕的1957年5月20日,蒋元椿响应负责国际部工作的报社副总编辑黄操良的号召,在办公室走廊墙报上贴出若干页小字报《论圣旨口》,对胡乔木对《人民日报》编辑事务管得过于琐碎,没有抓住大环节提了一些意见。这一下捅了马蜂窝,蒋元椿很快成为反右的靶子,渐渐落入右派泥淖而不拔。
眼看蒋元椿落入陷阱,杨刚在报社决策层面多方保护,希望使他免于被“划右”。也许杨刚的救助是有力的,在1957年10月前,蒋元椿的名字总在“疑右”和“右倾”的帽子之间徘徊。但到9月底,形势更加恶化,蒋元椿在劫难逃,杨刚再也救不了他了。果然,在杨刚辞世23天后,蒋元椿被划为右派。
后来蒋元椿回忆说,自从惹下文字大祸,时时有划右之虞,有时会在报社见到杨刚,但是杨只是朝他看看,什么话也不说。蒋元椿说:“我有一种预感,像她这样为争取中国的民主自由奋斗了几乎一辈子的革命知识分子,恐怕难以理解、也不能接受眼前这个严酷的现实。像她的名字一样,在敌人面前,她一生刚强。可是当自己的同志被当成敌人对待的时候,她越是刚强,痛苦也就越大,她承受得了吗?”
蒋元椿还只是一个人,问题是运动以来,各种斗争场面十分骇人,到9月中旬,编委会讨论,拟将11人划为右派,另有疑右10人、“未定”6人。更可怕的是,将被“划右”的远远不止于此数(最后达32人,另有一人因为是工人不该划右,就给他戴上了“坏分子”帽子)。而且,杨刚先后负责的两个部——国际部和文艺部成为运动的重点(后来地方记者部又“挖”出了更多的党员右派,成为报社中出右派最多的部门)。
和杨刚关系更为直接的是,1955年春,她向新华社点名要求调来的“骨干”蒋元椿、李慎之眼睁睁地看着成为“大右派”,同时从新华社调入《人民日报》的黄操良和部主任胡骑也是命运不济,后来都成了右派。杨刚和他们的工作往来密切。事实上,这把火烧将下去,距离杨刚本人是越来越近了。
在残酷的运动中,报社内部出现了自杀事件。8月14日上午,自“三反运动”后一直担任图书馆团支部委员的林安乾不堪批判,吞服毒药“六六六”自杀。但因药粉的强烈气味,林安乾服毒后即大部分吐出,被同事发现后马上送进医院洗胃抢救,林活了过来(在“文革”中,林不堪忍受折磨,在安徽农场投湖自尽。1979年,他当年错案宣布得到“改正”)。
更令人惊异的还在于,就在杨刚辞世的前一天,报社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一位部门副主任也因面临严酷的反右批判,于10月5日吞服安眠药自杀。当时因发现及时,这位抗战中参加革命的副主任被救了过来。但他和林安乾一样,在“文革”中不堪凌辱,最终还是服毒自尽了。他也在“文革”后被宣布“改正”。
报社内的反右正从党外延伸到党内,更惨烈的悲剧即将发生,在蒋元椿等相当一批党员干部将被戴上“帽子”的时候,杨刚选择了离去。
如果杨刚没有离去,随后的政治生活中会有什么等待她?
是什么使杨刚永远离去
杨刚辞世的第二天下午,社长邓拓在报社五楼大会议室召开全体人员大会,宣布杨刚去世。他含糊地猜测杨刚的死因,说大约在10月初,她偶然丢失了一个重要的笔记本,心情不好,前几年车祸造成的严重脑震荡使她很痛苦。
说到这里,邓拓就没有往下说。看来他自己也说不下去了。他说的是否实情?并没有得到证实。最后邓拓说,大家不要随便猜疑。他同时又宣布,不开追悼会了。
按说,自从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一文发表以后,在革命队伍里,凡是有人牺牲或死去,都是要开追悼会的,已经形成惯例。但杨刚的死却成为一个例外。
杨刚从此长眠在北京八宝山的山坡上,她的离去在当时没有引起多大的政治涟漪。但是,仔细思考那些时而被人提起的原因,比如“丢失笔记本”、“1955年遭遇车祸导致头痛”、“女儿远在苏联学习,她一个人生活缺乏家庭温暖”等等。按蒋元椿及许多熟悉杨刚的人的说法,只要熟悉杨刚,读过她较多作品,都感觉到,以她豪爽硬朗的男性化个性,前述原因都不足以让她选择离去。
几天前“丢失笔记本”缺乏实证。以杨刚当时情况,她不大会有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一般说来不会影响她的政治前景。何况以杨刚的豪放个性来说,丢失一个笔记本能有多大影响?对一个新闻记者或编辑来说,即使身居高位,丢一个笔记本不是一件不能承受的事情。
“车祸头痛说”缺乏医生的病历说明。此时距离车祸不过两年,杨刚的医疗条件相当好,不至于已经使她失去了继续治疗的信心。
198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杨刚文集》中,收入她生前故旧、亲人写的多篇回忆,几乎无一例外地回避了她为什么和怎样选择了离去。倒是胡乔木写于1983年6月的序中虽然也提及“车祸”和“笔记本说”,却有一句话指出,杨刚的死“无疑跟当时的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
历史学的作用不是复原历史,那是做不到的。研究历史的意义只是在于通过严格的考证和辨证一次次地接近原貌,虽然这是永远不会穷尽的过程。作为一代前辈,杨刚已经离我们远去,即便她的当年部下也在一一离去。但是,历史的教益只会因为更新材料的出现而变得更加真切,发人深思。这就是我们直到今天还在讨论杨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