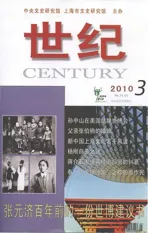新中国上海文坛若干风波
2010-07-26周天
周 天
(本文是作者为其岳母欧阳翠即将出版的《生命的灌溉》一书写的序言。本刊有删节)
岳母欧阳翠是一位老知识分子,今年93岁了。她的《生命的灌溉》一书,有许多对文学界的历史事件的回忆。其中有一些事件,我也有一些接触,可以另加补充,例如《钢人铁岛》事件即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现代文学编辑室的文艺理论读物编辑组组长,现将我所了解的有关事件回忆如下。
一、《钢人铁岛》事件
岳母欧阳翠书中叙说了钢人铁岛事件。其实,据我所知,她的叙说是极不完备的。这是她的写作特点,她决不讲那些自己所不了解、不熟悉的事物,决不强不知以为知。这是从小接触的中国传统文化教给她的一个习性: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所以她的回忆往往不免偏于琐碎和零散,但却又是惊人的真实。

《钢人铁岛》事件的过程,我倒知道一些。简略地说来,就是六十年代,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的一位常务副部长,曾经指示与支持上海戏剧学院部分师生到海岛解放军部队去深入生活,师生们去了一个月,归来以后,在兴奋之余,就写出了一个表现海岛解放军生活的多幕话剧,这位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就将此剧本推荐给《上海文学》编辑部。当时《上海文学》的主编是魏金枝、以群两人,岳母欧阳翠正在《上海文学》任编辑。编辑部接到这个任务以后,不敢怠慢,连夜审阅。不过,平心而论,平时生活在书斋中的、仅仅“深入”部队一个月的师生们,能写出什么像样的作品来呢?在这些经常审阅、发表全国范围的尖端作品的编辑们眼中,作品的概念化是可想而知的。由于是部长推荐来的,他们就提出了需要作较大修改的意见。这个意见当然也是两位主编反复商量、推敲后的决定;以我对魏金枝、以群两位判断文学作品的一贯标准的理解,说不定还是一个退稿的缓冲决定。那时候,正是在1958年各校学生到处批判老师之后,余威犹存,《上海文学》捋了虎须,他们马上就告到副部长处去了,支持“新生事物”的副部长勃然大怒,立即决定要对整个上海作家协会进行整风。
整风需要有具体的错误材料。副部长用的就是《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审稿意见。其中有两条最为突出。
一条是,《上海文学》的一位编辑,也就是我的岳母欧阳翠,在剧中一个人物的讲话之旁,划了一条线,而这段讲话乃是一句“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口号。如果稍稍冷静思考一下,就不难看出,其意是不赞成这种标语口号式的写法。但是,此时副部长由于支持“新生力量”而产生了误会,立即就认为:这是中了修正主义的毒害,不敢反对美帝国主义。
另一条是,审稿意见中有一段话,说是这个剧本没有能够写出典型人物,只是写了人物群像。照我今天作为一个老编辑的推测,这显然是一段经过仔细推敲的婉转措辞。其本意应是说,这个剧本写得十分概念化。但是因为这是副部长推荐来的作品,就换了一个自以为是婉转的说法。对于这段审稿意见,副部长上纲的份量尤其沉重而突兀,他认为,“写典型”的观点,突出个人,乃是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社会主义是崇尚集体英雄主义的,因此,社会主义的文学作品,应该写群像而不应该写典型,所以编辑部否定这个作品的出发点,乃是修正主义的。老实说,这条意见并不准确,解放前就以马克思主义者文学理论家知名于世的叶以群心中恐怕未必服气。只不过,“官大一级压死人”,副部长的革命资历与现任职务都高于以群,以群只能诚惶诚恐,承认错误,老实检讨。
两条意见,恰好都上纲到了修正主义的高度。顺便说一句,在那时候,修正主义这个名词还刚刚出笼,新鲜生涩,大家才学着、试着用,副部长或许也不过就是试用到《钢人铁岛》事件中了。
修正主义当然也是个可怕的名词,谁也不愿意戴上这顶帽子。但是,上海作协整风却铺天盖地而来,《上海文学》首当其冲。以群和《上海文学》的党员编辑们,不得不纷纷给自己扣上了修正主义帽子。反正这也不过就是一种过关手段。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生态。
不过,《上海文学》编辑部有两位非党编辑,却是较了真。一位是主编魏金枝,一位就是岳母欧阳翠,他们两人死也不肯承认自己有修正主义思想,岳母欧阳翠怎么也想不通,她只不过是不赞成剧中人物空喊口号,怎么就成了害怕美帝国主义的修正主义?《上海文学》的党员编辑们,反反复复做他们的工作,就是做不通。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一语旁边划了线的当事人,拒绝按领导要求检查,这可就是一件大事了!其后果是,魏金枝被撤去了主编;岳母欧阳翠是普通编辑,无职可撤,则被调离编辑岗位,到资料室工作,她随后打了报告,要求去了工厂劳动。其余按副部长规格检讨过的党员编辑们,一律仍回原职。今天看来,这当然是作协有关领导为了应付上级的一种高调处理。这类高调处理是有利于整个作协的顺利过关的。不过,这却又是岳母欧阳翠缺乏“政治头脑”的一个典型事件。检讨几句,给自己扣上一顶子,不就万事大吉了吗?她却宁可丢了自己所十分热爱的编辑饭碗,也不肯说几句违心之论,做若干自己所并不理解的检讨。其时,主编魏金枝也由于拒绝检讨而十分孤立,得有欧阳翠这位死硬的同道,聊慰寂寥;所以,魏金枝对岳母竖了大拇指,称她为硬骨头。
当时,我正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协会,乃是唇齿关系,有句古话说,“唇亡而齿寒;河水崩,其坏在山。”处于风口浪尖的是作协,我们出版社自然也不免胆战心惊;特别是理论这一头,许多文艺理论书籍中,往往涉及典型问题,“群像论”对于我们的冲击,可想而知。我们组里商量过好几次,总觉得“群像论”难以自圆其说,然而又来头太大,未知深浅。特别是我,刚从新闻单位转来出版社不久,对文学界还不大熟悉,心中更加无数。我问过编辑室主任刘金,刘金的态度很简单,他说,“某部长的水平当然很高,不过,这个理论别人没有讲过,就某部长讲了,没有文件为凭,我们暂时就不要管它吧!要不然,你去个别问问老蒯,他是作协党组成员,知道的事情比我们多。”我想拉刘金一起去问老蒯,刘金一口拒绝,说:“这是你们理论组一头处理稿件当中的事情,而且,两个人谈话,可以说得畅一些。我看稿太忙,你一个人去就可以了。”刘金的说法根本就是托词,他是室主任,理应管我们的事,不过,我知道,这也是反右以后的一种政治生态,凡是敏感的题目,往往避免三个人以上的谈话,以防今后可能发生的运动。这种政治生态,今天的读者已经比较隔膜了,所以需要略加说明。
老蒯是我们的社长蒯斯曛同志,他是左联的成员,老党员,革命战争中,又长期担任粟裕身边的秘书处主任,在文学经历与革命资历方面,都是不折不扣的老前辈;只不过因为解放以后粟裕比较背时,他也不大走运,只当了我们出版社的社长,不免有点大材小用,但在文学圈子里,则是相当受人们尊敬的;为人也沉稳厚道,颇有古风。
于是,我去个别找了老蒯。老蒯说:“‘群像论’我也只是听了某部长的报告,没有看到中央文件当中有这样的提法,出版社工作自然还是以中央文件为准;不过,某部长也是老同志了,也不至于凭空立论,也许是听到了上面的什么说法,做了点引申吧!不过,他也不是专门搞文学理论的,用词上也不一定经过仔细推敲。你们只要注意,出书当中不要去反对‘群像论’,不要撞在枪口上就是了,其他一切照常吧!另外,我同你的谈话,不必在编辑当中传了,你自己审稿时候掌握就是了。”两个“不过”,似是模棱两可,其实态度鲜明,与刘金口径一致,我一听就知道,他和刘金早就交换过意见了。老蒯的谈话,观点明确,但又婉转;不赞成“群像论”的态度,可以意会,而又如羚羊挂角、香象渡河,无迹可求,这当然也是当时政治生态的反映。
因着老蒯的沉稳,上海作协整风近一年中,有些文化单位不免有些跟风,上海文艺出版社这样的与上海作协唇齿相依的单位,却纹风不动,毫无反映。

这里,对于《上海文学》编辑部的编辑们在检讨问题上的不同态度,我想顺便说一点符合当时政治生态的持平的看法。我认为,以群与《上海文学》的党员编辑们的认真按副部长的要求检讨,和魏金枝、欧阳翠的顶牛,两方面应该说都是合乎情理的。党内有下级服从上级的明确规定,何况此时又是反右之后,而且,他们编辑部碰上的《钢人铁岛》事件,连累了整个作家协会,他们自己也觉得,具有迅速检讨、消弭事件的责任;魏金枝和欧阳翠,都是非党人士,无此约束,加之《钢人铁岛》那个本子也实在太概念化了,他们乃是不太熟悉当时政治生态的比较纯粹的文学编辑,又是在传统文化薰陶下成长的知识分子,又怎么可能按既定规格做检讨呢?
作协整风期间,《上海文学》发表了《钢人铁岛》,这其实是一个很粗糙的、大活报水平的剧本;在艺术水准上,与《上海文学》平素发表的作品远远难以比肩。白纸黑字,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查阅。
最后,整风结束,作为结束的标志的是,由上海戏剧家协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吹捧《钢人铁岛》。会上,《上海文学》主编以群,还做了几句检讨,说了自己没有认识到社会主义文学的集体英雄主义特点,所以也就认识不到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强调写群像而不应该强调写典型的特点,云云。这个座谈会,包括以群的检讨内容,以新闻的形式,发表在当时的文汇报上。
但是,最令人惊奇而且有趣的是,就是这条新闻,却引出了某种关于《钢人铁岛》事件的出人意外的崭新结局。
原来,中国作家协会和《文艺报》编辑部,是不赞成“群像论”的。以群的检讨,将副部长的“群像论”以文字形式公诸于报刊,这就使他们有了一个表达自己反对看法的机会。
于是,《文艺报》等等中央报刊,突然以较大篇幅,发表了批评“群像论”的文章,认为社会主义文学应该坚持写典型的观点,所谓写“群像”的观点,是有害于社会主义文学的错误观点。在我的记忆中,几篇文章的署名者当中,有张光年、侯金镜等,都是当时的文学理论权威;李希凡也在《解放军文艺》上写了一篇论述中国古典文学中一贯描写典型而不是写群像的长文,文中也批评了“群像论”,这显然也是一种侧面的呼应。
我们理论组的同事们,当时就推测,如果不经中宣部同意,似乎不可能有这批文章的集中发表。后来从北京作者处听来的传闻,也与我们的推测相近。不过,关于批评“群像论”的文章何以集中发表的背景,至今我也没有听到过任何正式传达。上述情况,也是仅止于猜测与传闻,特此说明。
于是,随后,这位副部长就在作协的大会上向《上海文学》的编辑们公开道了歉,岳母欧阳翠也从工厂回到了编辑部,作为《钢人铁岛》事件的最终句号。这或者也是某种“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特殊表现形态吧!
其实,这位副部长,乃是我所十分尊敬和崇敬的一位领导同志。他的一生,做过许多好事,《钢人铁岛》事件只是反映了他的一个次要的性格弱点的侧面。
二、《战斗的青春》事件
上世纪六十年代,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出版时由于曾受抵制而特别引人注目。当时,上海文艺出版社许久没有出版有影响的长篇小说,压力很大,《战斗的青春》由于责任编辑、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刘金的全力推荐,编辑们都抢着看了,并且举社欢腾,一致认为这本书可以打一个翻身仗。不料,书出了不久,作协党组一部分“左派”,突然提出此书美化了叛徒胡文玉,是宣扬叛徒哲学的作品。不但“邀请”出版社有关人员举行了两次名为讨论实为批判《战斗的青春》兼以批判刘金的座谈会,并且陆续公开发表了若干批判文章,来势凶猛。此事有些诡异:批判一个作品时,不涉作者,而是兼及责任编辑,颇不寻常。
《战斗的青春》的终审者,就是我们的老社长蒯斯曛。作为作协党组成员之一,蒯斯曛只能以沉默来抵制;刘金作为《战斗的青春》的责任编辑,多次发言与写文章,为《战斗的青春》作辩护。而出版社的所有文学编辑,则是完全一致地支持老蒯和刘金。我当然也是支持者之一。只是上海作协在上海文学界的实际地位,高于出版社,而作协党组成员、“左派”理论家姚文元也在会上发言认为,《战斗的青春》宣扬了叛徒哲学,增添了批判的声威。出版社于是明显地处于劣势。所幸的是,《战斗的青春》作者雪克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党委书记,河北省委宣传部不同意这个批判,于是由宣传部副部长远千里,在《天津文学》上发表了一篇热情洋溢地肯定《战斗的青春》的长文,算是对于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一点遥远的支持。
当时,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对此次批判没有表态。我曾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作过,于是,我找了宣传部的某个老同事,问问情况。
这位老同事告诉我说,事情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真正发动此次批判的始作俑者,并非姚文元,而是另一位作协党组成员,此人对于批判《战斗的青春》颇为积极,是实际上的发起者与组织者,姚文元倒是由他“请”出来的。凑巧的是,在此以前,刘金刚刚将此人的一个短篇小说集子退了稿,此人对于退稿之事,十分恼火。这位老同事说得比较婉转,只是说事有凑巧,未下任何结论。他也并没有告诉我此人的名字。其时,我对作协的情况了解甚少,也猜不出来此人是谁。老同事还告诉我,上海作协已经向市委宣传部提出了批判《战斗的青春》和该书责任编辑刘金的方案。不过,据他知道,文艺处对此并未表态。另外,这位老同事还向我忠告说,此事我心里有数就行了,当然也不妨作为传闻告诉老蒯。作协党组成员中,意见实际上也并不一致,文艺处对作协情况非常熟悉,既未表态,必有原因;事态发展目前难以预料,最终还要看部长的态度,最好能婉转地劝刘金冷静一些,静观事态发展。他说的“部长”就是前面说到的市委宣传部的常务副部长,当时正部长是由市委书记石西民兼职的,石西民平时并不过问宣传部的工作,所以副部长实际上是全权主持市委宣传部工作的。这位老同事说到“作协党组成员中意见实际上也并不一致”,我马上就想起了,党组成员以群、吴强、哈华等人,开会时都坐在比较偏远的角落里,始终不发一言,老蒯当然也是沉默的。
回来后,我就个别向老蒯汇报了。老蒯沉默了好半天,大概事情的某些背景,也使他有些震惊。他既是作协党组成员,显然对党组成员们的情况,比我清楚得多了。其后,他对我说:“你不必去劝刘金了,刘金的脾气,也不是你能劝得下来的,我会找机会叮嘱他一下的。”
此事又过了一两个月,这一两个月间,作协仍是紧锣密鼓地批判《战斗的青春》,兼及刘金。不过,一两个月以后,批判突然停止了。原来,就是这位副部长,在此期间,亲自看了《战斗的青春》,而后表态说:“《战斗的青春》我看过了,没有美化叛徒的问题;《战斗的青春》是反映冀中斗争的,冀中斗争是少奇同志亲自领导的,你们这样批判《战斗的青春》,合适吗?”(大意如此)这位副部长是政治家,而并非文艺家,所以,他仍旧是从政治角度对这次批判加以刹车的。此次讲话以后,批判乌云便烟消雾散。
刘金对这位副部长十分感激。直到刘金过世之前,在一次谈话中,他还对我说:“作协那些‘左派’们,那一阵子,真是想把《战斗的青春》和我全部一棍子打死,这些‘左派’,真是厉害得很哪!如果不是某部长亲自在百忙中抽空看了小说,出来制止,真不知道他们还会把我整成什么样子呢!”
不过,以我根据前述材料的推测,恐怕当时文艺处作为副部长的参谋机构,也起了重要作用,我记得,当时文艺处长是章力挥同志。

三、铁骨铮铮的陈其五部长
在“三面红旗”的鼓噪声中,这位副部长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听到了农民对于人民公社的食堂广泛不满的尖锐意见。回来以后,便下决心向党中央、毛主席上书,列举事实,要求取消食堂。农村食堂并不在宣传工作的范围之内,他是原可以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当时也有人提醒他,此举颇有风险,但是他还是坚决上书,为农民请命。据说,他当时还讲过,“如果我没有看见,当然可以不过问,我亲眼看到农民那么苦,再不讲话,于心何忍!”不过,此语得自传闻,未能确证,应该是大意近之而已。结果可想而知,他遭到了比《钢人铁岛》事件中一切人都远为严重的灭顶之灾:撤掉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职务,开除党籍,“戴罪”到某大学教书去了。直到十多年之后的新时期,他才得到改正,并且重又担任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宣传部的正部长。
如果说,魏金枝在《钢人铁岛》事件称我的岳母为硬骨头的话,那么,这位在《钢人铁岛》事件不免颇为莽撞、冲动的副部长,在向党中央上书为农民请命之事中,则是表现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两件事同样可以称为硬骨头,应该说,副部长的硬骨头程度,要高得多,称之为铁骨铮铮,大概也不算过分的。
世界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如果说,岳母欧阳翠的政治视野有不够开阔的缺点,在运动不断的政治生态下,甚至可以成为某种优点的话,那么,这位副部长的敢作敢为的性格,固然在掌握了某种较少受到制约的权力之后,可以给他的部下们带来沉重的委屈。而在另一种情况下,当他为民请命而敢作敢为时,缺点就化为巨大的优秀品质,让我们看到了一位铁骨铮铮的共产党人的英雄气概。并且,在上面更加不受制约的权力的威权之下,这位英雄遭受了几乎是灭顶之灾。这也是当时的政治生态,包括这位副部长的铁骨铮铮的性格,应该看成是一种更加不应忽视的政治生态。
尽管一个时期以来,传统文化受到了压抑和摧残,但是,孟子所强调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并没有消失,它仍旧活在许多领导干部和普通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特别是老一辈的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更是如此,一旦遇到适当的机会,就能够或高或低地萌芽、生发,甚至成长为参天大树!这位中共上海市委的常务副部长,以他的行动,也以他所遭受的灾难,向我们明确地证实了这一点。
这位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新时期又担任过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的共产党人,就是虽有某些弱点、缺点,但是仍然能使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从心底下备感崇敬的陈其五同志!
据老友荆位祜同志告诉我,陈其五部长的上书涉及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大跃进时农民生活的困苦情况,反映得十分尖锐。荆位祜新时期以来,长期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秘书长,了解的情况自然远过于我。我建议荆位祜能为文将这段历史写出来,再不写就没有人知道了。
我觉得,岳母欧阳翠在《钢人铁岛》事件中曾经受过的委屈,和陈其五部长曾经遇到过的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还是可以有类比之处的。岳母之所以遭受委屈,是因为其时陈部长手中掌握了某种较少受到制约的权力滥用所致;而陈部长为民请命以后所遇到的灾难,则同样是更高层的领袖人物手中掌握了更大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之故。所以,自十六大起,党中央十分强调权力制约,这就使人们明确感觉到,我们已经和必将出现一种良好的政治生态:当着权力制约逐步得到有力的落实之后,人们的灾难或委屈,就才会逐步减弱以致大为减少。这又岂止一位部长的命运或是一位普通知识分子的命运而已,这又岂止是宣传系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