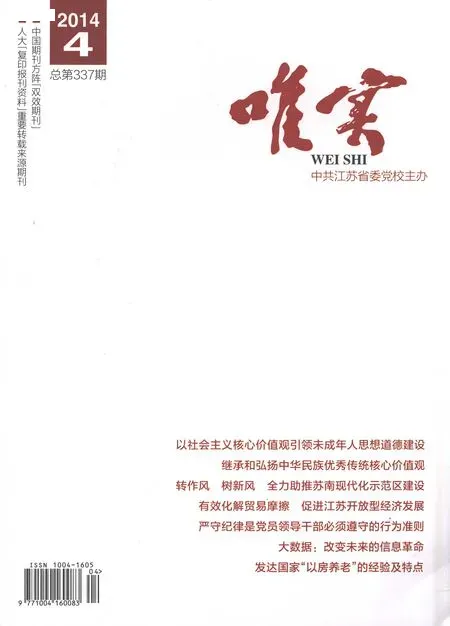老子反对“为学”么
2010-07-12朱明贤
朱明贤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法系,河北 廊坊 065000)
老子反对“为学”么
朱明贤
(北华航天工业学院 文法系,河北 廊坊 065000)
由“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不能得出老子反对“为学”。“为学”与“为道”同为人的能动性的基本体现方式,二者是统一的。“为学”,泛指人吸取知识、升华境界的认识活动,其价值目标是认识“道”以致“善为道”。“道”是可知的,人是能动的,人与道、天、地同为大,因此,人完全可以“为学”以知“道”。“绝学无忧”所绝之“学”有其特定内容,而不是“为学”活动本身,相反,“绝学”以“为无为,则无不治”正是“为学”所得出的结论。
为学;为道;绝学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1]29这句话是反对“为学”呢,还是肯定“为学”的价值呢?老学研究者或认为“为学”与“为道”是彼此相互排斥的,“为道”必须绝弃“为学”;或认为二者虽然不相互排斥,但“为学”绝不可能通向“为道”,同样也否定了“为学”与“为道”之间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笔者浅见:“为学”与“为道”同为人的能动性的基本体现方式,二者是统一的。“为学”,泛指人吸取知识、升华境界的认识活动,是认识“道”的必由之路。老子反对“有为”,主要是讲作为执政者“爱民治国”要“无为”,而不是在“为道”上的“无为”,相反,他一再强调要“善为道”。而要“为道”,首先就必须“为学”以知“道”;不知“道”,何来“为道”?“为学日益”,就是益于知“道”,而且“为学”能够益于知“道”。“道”是可知的,人是能动的,人与道、天、地同为大,因此,人自然可以学以知“道”。不错,老子明确讲“绝学无忧”,但是,所绝之“学”是有特定内容的学,而不是“为学”活动本身;绝弃圣智、仁义等之类的“学”,去学会和体验“见素抱朴,少私寡欲”、“为无为”,从而做到“善为道”,如此方能“无忧”。由此可见,“为学”对于“为道”是必要的,不可或缺。
一、“为学”之“益”
老子的“为道”含义是指主体逐渐减损自己“不道”的心欲和行为,使自己的行动与道为一。这里有个前提,就是“为道”者心中已经有了“道”。那么,心中之“道”何来,换言之,如何认识“道”?老子认为是通过“为学”得到的。“为学”的宗旨就是从所学的对象中发现“道”,发现天地自然的规律,发现社会治乱的规律,发现人生的法则。这也就是“为学”之“益”。
关于“为学”之“益”的含义,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认为“为学”会使“情欲文饰”的增多、膨胀。因此,“为学”“无益”,要通过“为道”而“损”这类的学。二是认为“为学”可以积累知识、增进技能,但这是与“为道”成反比例关系的,即这样的学越多,具体的知识、技能越多,越不利于“为道”之境界的提高,必须“损”此所“益”,才能臻于“无为”的境界。总之,都认为老子是反对“为学”的,“为学”不但无益于“为道”,甚至是与“为道”背道而驰、南辕北辙。研究老子的人当然有这样解读的权利,不过,老子明明讲过“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则无不为”。“为学”与“为道”是两种性质不同的主体活动,一个是讲学习有益于增进知识或提高学问,一个是说法道无为,减损“有为”,这显然是讲修道、行道,即道的实践问题。由此可见,老子是从正面肯定了“为学”这种认识活动的积极作用的。
“为学”之“益”在《老子》书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老子自己要学,并把毕生的研究总结成《道德经》,讨论“可道”之道,讨论“无为”之德。这就是学,就是立说或立言。不学、不反思,如何能够写出《道德经》?不要人学,又何必写出《道德经》?老子以其“道德”学说示教于世人,意在教人法道而功成、“无不为”,这难道不是老子思想之有益吗?“为学”“无益”在哪里?
老子无所不学,可谓是处处留心皆学问的善学者,这从他那丰富多彩的法道无为的论证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一是向自然界学习,即从对天地自然现象的观察中学习、体悟“大道”。第七章:“天长地久。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1]4这是关于天地不自生,故能长久的运作规律的认识,即天地自然无为。第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1]6这是由对具体事物有无统一的认识到关于道的一般性有无统一的抽象。第十六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1]9万物生生不息的根源在于“静”,这是万物的“根”和本性,即“命”,老子由此抽象出虚静的自然无为法则。第五十五章:“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虫不螫,猛兽不据,攫鸟不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气曰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1]33-34第七十六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1]45第七十八章:“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1]46这三处是讲对和谐、柔弱则生、坚强、枯槁则死的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由此抽象出柔弱胜刚强、以柔取强的处世法则。第八章:“水善利万物而不争。”[1]4第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1]40第七十三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1]43这几处是对处下、不争的自然现象及其规律的认识,并由此抽象出虚怀谦下、不争的治世和处世之道。可见,老子善于观察自然,善于从自然界中学习、发现“道”。
二是学习人生经验。这是老子极为重视的学习,如:“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1]5“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1]6人生如此贪得无厌、知进不知退是自取灭亡之道。做人修道,应当“为腹不为目”[1]6,应当知进又善于功遂身退。又如:“民之从事,常于几成而败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1]39一般人做事所以少有成功,在于不能善始善终,或有始无终,所以如果能够做到“慎终如始,则无败事”。老子还观察到:“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1]12相反,“自见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无功,自矜者不长。”[1]13-14这样一比较,自然就明确了虚己、谦下的人生之道。
三是学习社会实践经验。老子观察到,“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法令滋彰,盗贼多有。”[1]35作为执政者,如果把百姓视为防范和禁忌的群体,设置繁多的条条框框来限制百姓,势必会束缚百姓的身心,百姓这也不能干,那也不能想,怎能够自由生活、生产?怎能不“弥贫”?执政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制订了越来越严密苛刻的法令,而百姓不甘于喘不过气来的剥削和压迫,便铤而走险起来反抗,于是“盗贼”四起。总之,执政者越是大有为就越是造成大乱子,与此相反的“圣人之治”则是“为无为则无不治”。这是由社会政治来学习治世之道。
四是向古人、圣人学习。学习古之道,“以御今之有”[1]8。例如:“古之善为道者,微妙玄通,深不可测。”[1]8“古之所谓曲则全者,岂虚言哉!”[1]13“古之善为士者不武,善战者不怒,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1]41老子更重视学习圣人之道,《老子》一书中有30多处正面论述了圣人之道,以供效尤。
五是学习典籍。老子作为守藏吏,学习典籍是肯定的,他从典籍中吸取营养也是很明显的,如:“用兵有言:吾不敢为主,而为客;不敢进寸,而退尺。”[1]42
由上述可见,老子“为学”的范围和内容是相当广泛和丰富多彩的,而且他“为学”的目的就是为了总结并效法“道”。这正是“为学”之益,也是“为学”所能益。
二、道可学
老子“为学”的目标是认识道。为什么能够通过“为学”活动及其过程认识道呢?
一方面,道可知。《老子》五千言中的核心内容是论道、“法”道,我们以此为研究对象,可以认识老子的道。老子可知、可述道,我们可知老子道。道的可知性是“为学”可以认识道的首要前提。如果道是不可知的,当然也就谈不上怎样认识道了。道的可知性在于道的客观性和运动的规律性,道是客观存在的,“道之为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1]12道是一种物,当然,这种物不是具体的某一物体,其特殊性在于恍惚无定象,恍惚无定象却还是有象,这就是“道之为物”的“物”;它深远幽暗,其中有精气,精气的存在是真实不谬的,是实实在在的,这种“物”是“先天地生”的,对于人来说,它自然是客观存在。这个客观存在的道又是运动的,其运动是有规律的。“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1]21,“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1]25,这些都是道在运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规律。再者,道的存在和运动规律是自古至今恒久如一的,“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1]14,“自今及古,其名不去”[1]12。道的这些属性,为人们认识道提供了可能性。
另一方面,人能知。道所以可知,还在于人能知,人是能动的,具有认识客观及其规律的愿望和能力。老子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4“大”字,是说广大、伟大、包罗万象,甚至气吞山河。中国传统文化爱用“大”字来表示无法形容的力量、精神、修养、品德、意境等,如大天、大地、大海、大山、大帝、大圣人、大德、大意、大师,等等。孔子形容尧帝的伟大圣明,就用“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2]32《周易·乾卦》:“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2]141以大来形容乾的力量、德性无量。老子把这样的“大”字只冠给了道、天、地、人,足见老子是把人性张扬到了极致,尊人之至。人何以与道、天、地同大呢?因为人能“法”。“法”,就是学习和效法,认知而后遵守,以其为准则、法则。道、天、地的“法”都是纯自然的现象,只有人的“法”是因循天、地、道之规律、法则而矫正自己行为准则,使自己行动更加美好,使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能够兴旺长久的能动行为。《老子》不朽之作不就是老子“法道”、“法天”、“法地”“法”出来的么?人类文明的创造足以证明人的伟大!“法”是人能够且应该做到的,这是人能够与道、天、地同大的内在根据。“为学日益”,不论怎样解读这句话的内容,都不影响人能够“法”,能够学而有知,且越学越有知识。既然如此,同时道又有可知性,也就必然地包涵人能够认识道的逻辑。诚然,老子不是仅仅从逻辑上说明人能够认识道,他还论述了认识道的具体方法,这就是从认识角度讲,人之“法”的能动性表现为观察、反思、抽象、概括等,这些都是老子所运用的认识方法,当然也是“为学”的方法。这在前面论述的“为学”的内容方面可以看出来。
三、“绝”什么“学”
老子明确讲:“绝学无忧。”这四个字,似乎放在《老子》第十九章要好些。这一章的文字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老子要“绝”的“学”是什么呢?对此,有不同的解读,如:“政教礼乐之学”、卜筮之学及巫祝之学、儒学、一切学,等等。这里不想对这些观点一一点评,而只结合“为学”来分析“绝学”。如前所述,“为学”是泛指主体吸取知识、升华境界的活动,是有益于认识“道”的内容极为丰富的认识活动,这种活动,显然老子是不“绝”的。
“绝学”之“学”有其特定内容。“绝圣弃智”、“绝仁弃义”和“绝巧弃利”,这三“绝”的含义很明确:爱民治国,要让“民利百倍”、“民复孝慈”,实现天下无贼,就必须放弃圣智、仁义、巧利。圣智、仁义、巧利的主体是执政者,他们运用“有为”的圣智、仁义、巧取利于民,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于是造成“民弥贫”,不孝、不仁、不义、奸诈残忍、巧取豪夺、盗贼四起等丑恶社会现象不断发生。因此,“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文”是礼法,指上述三“绝”所绝的内容。执政者运用圣智、仁义、巧利的方法是不足以使天下“无不治”的,所以劝其另辟蹊径,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这样连读下来,“绝学”之“学”的内容就明确了,就是指圣智、仁义、巧利这些“不足”。也就是说,老子主张执政者放弃“有为”的政治,实行“无为而治”。上文已述及,这正是“为学”所得出的结论。可见,“绝学”与“为无为,则无不治”[1]2是等值的。
正因为“绝学”与“为无为,则无不治”是等值的,所以才能收到“无忧”的理想效果。忧天下“昏乱”不治,忧大事“败”而不能“成其大”,从而主张“为无为”以实现“无不治”、“无不为”是《老子》的思想主题。也就是说,老子所忧不是一般的个人忧患,而是忧国忧民之大“忧”。“绝学”所以“无忧”,就在于无为而治。“无为”,就执政者来说,重要的一条就是“以百姓心为心”[1]30,相信百姓善于自治、自为,并放手让百姓自治、自为,这样就可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1]35。果真能够实现民自化、自正、自富、自朴,当然天下百姓就不会有什么“忧”了,而百姓无忧不就实现了天下大治么?所谓天下治,根本说来就是天下百姓富乐安康了。因此,如果天下百姓真的“无忧”了,执政者或爱民治国的圣人还会有何“忧”呢?换言之,“无忧”,一是执政者“绝学”则天下治,民富乐安康,于是执政者“无忧”;二是执政者“无为”而民自富,于是民“无忧”。“圣人之治”旨在先使民事无忧、居无忧、食无忧、养无忧,而后自己“无忧”。
如果说“见素抱朴,少思寡欲,绝学无忧”是“善为道”的一种体现,那么“为学”以知“道”的实践价值也就不言自明了。
[1]国学整理社.诸子集成:第3卷[M].北京:中华书局,2006.
[2]陈戍国.四书五经:上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2.
责任编辑:戴群英
book=37,ebook=143
B223.1
A
1004-1605(2010)04-0037-03
2008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老子道德论与人生境界研究》(项目编号:HB08BZX006)阶段性成果。
朱明贤(1958-),男,河南濮阳人,北华航天工业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