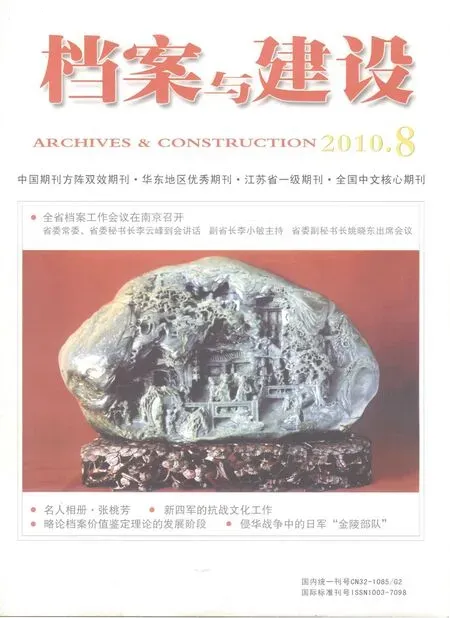日机轰炸六合竹镇
2010-06-12杨万选杨万里口述姜良芹整理
□杨万选、杨万里口述 姜良芹整理
杨万选,1922年生。杨万里,1928年生。住在南京市中央门外五塘新村。
六合襟江控淮,为五省通衢,是金陵的门户,江北之重镇,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后,日军继续追击向北撤退的中国军队,16日六合县城沦陷,一场大屠杀从石头城内蔓延到了这个郊县。此时地处六合城西北约30公里的竹镇似乎还享受着暂时的安宁,善良的人们未曾想到厄运即将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杨万选口述:
竹镇是六合县内最大的集镇,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明清以来是天长、来安、六合三县农副业产品的集散中心。抗日战争爆发前已有商号1000多家,并有私营发电厂一座,享有“小上海”的美誉。在镇上有一家“晋康祥京广杂百货店”,即我们的父亲杨竹君开的店。我和我弟弟万里当时分别是17岁、11岁(虚岁),在家里排行老二、老三,刚结婚不久的大哥杨万福在自家店里管帐目。我们一家本在六合城内居住,自日军侵入六合县城后一家就迁到此地,靠父亲经营百货店的收入生活,家境比较殷实。当时我们也算是小康生活了。然而命运就在1938年古历4月27日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天日本人的飞机对竹镇进行了疯狂的大轰炸。
1938年4月,驻六合的中国军队伏击了下乡“扫荡”的日军。恼羞成怒的日军迅速采取报复措施,先是血洗葛塘集,接着调动飞机对毫无空防能力的竹镇、马集、八百、瓜埠等乡镇实施连续的疯狂大轰炸。
古历4月27日上午9时许,正是竹镇商贩一天中营业的高峰期,集镇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一派繁荣景象。突然,九架日本飞机相继飞临竹镇上空。当人们开始惶恐不安时,一架架日机俯冲下来,先是一阵刺耳凄厉的呼啸声,机枪雨点般四处扫射,紧接着又是轰隆隆的炸弹爆炸的巨响声。刹那间,浓烟滚滚,火光四起,血肉横飞,瓦砾遍地,凄厉痛苦的求救声、恸哭声响彻云间。
日本飞机投下大约两三个炸弹以后,我们一家人和店里的伙计都开始躲,但究竟怎么样躲,自己糊里糊涂的,没得一个规划。这个时候主要是我家父亲组织,他是主人。我父亲跟我母亲站在一起,想维护我母亲,就躲在房子里头。
我家房子前面是店,后面是楼房。店里什么东西都卖,有南北货、五金、五洋,南北货就是秋油、酱、红枣、蜜枣、桂圆、麻绳、针头线脑、日用百货,五洋就是洋烟、洋火、洋油、洋胰子、洋蜡烛。货物有时候从六合城里批,有时到外地批货。家里有六条牲口,就是运货的。头天去六合城批货,第二天回来,回来后要歇两三天。店里有伙计十多个。前面是三间店面,墙是砖砌的,很厚,大门是铁的,石库门面,墙上有枪眼,是防土匪的,有四五条枪;后面是木结构的楼房,还有瓦房,有几进屋子范围。院子里头有做酱用的十几个酱缸,酱缸旁边的屋就是我父亲和母亲住的地方。
这时日本人飞机丢下的一颗炸弹正好从这个房檐口掉下来,掉到了酱缸里头。炸弹一爆炸,一股硫磺气味直冲人的鼻子,人的眼睛睁不开,也看不清楚。这个时候房子被炸塌了。我家父亲受到炸弹袭击,弹片正好从右肋进去了,人当时就倒下了。当时我父亲保护了我母亲,把我母亲遮住了。我父亲死得很惨,肠子都炸出来了。

我哥哥杨万福当时躲在屋里,和我父母亲隔着一个木结构的墙,上面是窗户。他也受到了炸弹袭击,身上伤处很多,没有大范围的,是小碎片子的,腿上有,肚子上也有,浑身是伤。这就是死了一个,伤了一个。我哥哥当时没有死,20多天后去世的。
还有一个小弟弟,大概只有三四岁,叫杨万钟,是我四弟,被我家一个表姐抱在身上,躲在一张桌子底下。表姐把他抱在身上,不知道他受伤了,实际上他身上已经受到弹片袭击了。后来我表姐抱着我弟弟往外跑时,走在路上我弟弟就不行了。
日本人飞机来的时候,我和二姐杨慧芳一头躲进厨房里头了。厨房中间是大锅,那种烧柴火的大锅。当时我思想动了一下,一抬头心里头就想:哎呀,这个地方,炸弹掉在远处震动了,这个房屋会不会倒?房屋一倒,我们怎么出来?心里就这一想,顷刻之间我掉头就跑出去了。我姐姐坐在小板凳上,我也没有来得及喊她,也容不得想。我跨到院子里,顾身不顾头躲在墙边。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来了,把墙炸倒了,但楼房没倒,木板和砖头压在我身上。我这个时候头脑清楚了,心里想:这个炸弹掉下来,我究竟处在什么地方?我死没死?我心里头有个怀疑:人死了还有魂魄,我现在怎么还清楚呢?心里想我大概没死。我上头是木板,自己活动不起来。那个时候心里有个求生的欲望,生出无穷的力量。那个时候我17岁,还是一个小孩子呢,我伸出一只手来,把木板和砖头一块块拿开。这个时候有人来了,是本店的伙计谢大个子,当时他有30多岁,是店里赶驴的,把我扶起来,带着我走了。我没觉得身上怎么样,没有受到弹片袭击,我还能走呢。只是我的耳朵受到了影响,导致我以后耳朵时好时坏,以致最终全聋了。
当时的情况是糊里糊涂,根本就没有想到我是从厨房里出来的,我还有一个姐姐在里头。这个时候我要是提出来,抢救还来得及,当时我想不起来了,至今想起来我就很内疚。后来房子烧起来了,我姐姐被烧死在里面,头都烧焦了。直到现在,我还时常梦到二姐坐在厨房板凳上的情景,似乎二姐的音容笑貌宛在。

这个时候日本人飞机又来了,我们就往向下空地跑,在路上躲在哪呢?路上有土造的墙,就躲在墙根下。我站不起来了,谢大个子就背着我往空地跑。跑到一个山坡上,山坡上都是坟茔,到了这个地方歇歇脚。这时我发现问题了,我受了内伤,想喝水。我依靠在谢大个子身上,想喝水,发烧,渴啊。这个时候旁边有很多人,都是躲炸弹的。旁边有位老太太说:“不能喝水,你喝水就没得命了。”离我几尺远的地方有个水沟,水沟是臭水、污水,还在流淌。我当时想只要有水喝死我也愿意。我想喝那污水,但动弹不了身子。谢大个子在地上拾了一个破瓦碴,尿了一泡尿给我喝,喝下去后,我眼前一黑就失去知觉,昏过去了。
自己不知道经过了多长时间才醒过来。到了晚上,家里人怎么碰到的,心里没得数,也想不起来这些事情。后来我们到了离竹镇二三里的熟人家里。这个时候我们家还剩下什么人呢?我家母亲、我大姐、我大哥、我三弟,还有两个妹妹,当时在六合我舅舅家,躲过了这一劫。我大哥杨万福后来的情况我前面讲过了。我三弟杨万里在这次轰炸中,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落下了残废,至今仍然是一个胳膊长、一个胳膊短。
我们全家是死的死,伤的伤,房子倒了、烧了,货物没了,以后我们该怎么办?日本人丢的燃烧弹把我家房子都烧了,没人救。店里的货物洋油、洋火、红糖、白糖等都没了。店里的保险箱外面是铁做的,中间是黄沙,要用特殊的钥匙才能打开,里面放着饼干听子盛钱,钱都被烤糊了、烤焦了,不能用了。伙计怎么样了也不晓得。当时可谓是家破人亡。特别是没得主人了,父亲一死就没主人了,家里没得人领导了。
当时在集镇上都是做生意的,店铺很多,我家店铺的前后左右都有别人家的店铺。商店用的货币还是法币,那个时候日本人和伪政府的钞票还没发行。当时我家的店铺在竹镇是大的,是批发兼零售,进货都是整船地进,周围集镇和乡下店铺都是到我家来批发。这场轰炸,我家是家毁人亡,房子、店铺烧了、倒了,货物没了。当时店里的货物值多少钱,我虽然没有管账,但是我看到我家有一间屋子里装了几折子黄豆,足有几万斤,这个黄豆不是做酱的,是哪来的呢?是乡下人来买东西和进货,先记账,等收成了,店里的伙计再赶着牲口,到乡下收黄豆、收粮食,然后我们再卖。我父亲生意做得很大,在竹镇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六合也是名声很大,很受人尊敬,人称杨竹或是杨四太爷。那时有土匪放话说,如果能绑到杨四太爷开价十万大洋,绑到我们兄弟五万大洋。当时大洋和法币是等价的。我家那时候有四个老妈子做事,我们穿的汗衫是“天鹅”牌的,袜子是“狗头”牌的,是当时最好的,是200支纱纺的,衣服的料子是麻纱的、哔叽的、绸缎的。
被炸后,我们什么也没有了,生活十分困难,家里这么多人生活没有来源,靠着城外几间房子的房租和亲戚的接济勉强度日。我母亲由于受到了惊吓,终日郁郁寡欢,几年后也去世了。
杨万里口述:
1938年我11岁,正在上小学,我家在六合县竹镇街上开了一家叫晋康祥的货栈,在这一带还很有名气。农历4月27日那天的早上,我正在学校上学,日本人的飞机来了,共九架,先是在空中盘旋侦察,然后就丢炸弹。听到日本飞机来了,大家就一起奔跑,我也躲起来了,但手臂被炸到了,断了。后来我还向六合方向跑了几里路。我读书的学校被烧得一塌糊涂,我家里也被炸了,烧得光光的。当时家里有十几口人,好几个被炸死,其中我父亲叫杨竹君,就当场被炸死。我大哥叫杨万福,也被炸伤,当时看起来伤得还没有我重,但受了内伤,5月20日就死了,那时他才结婚没多少天。
虽然事隔多年,年近90岁的杨万选老人对当时的情景仍然记忆犹新,他在讲述这段亲身经历时,那双经历了许多沧桑的手一直颤抖不止,浑浊的老泪纵横如雨。此情此景,令听者无不动容,唏嘘不已。近耄耋之龄的杨万里老人由于身体欠安,有些许的“糊涂”,但也对日军炸弹的轰炸给自己和家人的伤害难以忘怀,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杨万选老人在采访结束的时候讲:“多年来,从没有谁来问过这些事情,我们也没人谈。今天你们能来,我很高兴,我希望你们记录下我的经历。现在与我同等年龄的人越来越少了,以后再找这些老人没得了。”
是啊,随着时间流逝,经历过那场劫难的老人如燃尽的蜡烛,一个随着一个地离去了。血雨腥风的岁月已经逝去,今天处于和平时期的我们不应该忘记那段屈辱、惨痛的历史。美籍犹太裔作家伊利·威塞尔说:“忘记大屠杀就等于第二次大屠杀。”我们今天记住曾经的大屠杀不是为了仇恨,而是为了和平。在与杨万选老人的儿女交谈中,他们朴素的话语表达了中国人民热爱和平的精神,他们说:“我们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也不是为了让日本赔偿,只是我们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丑恶行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