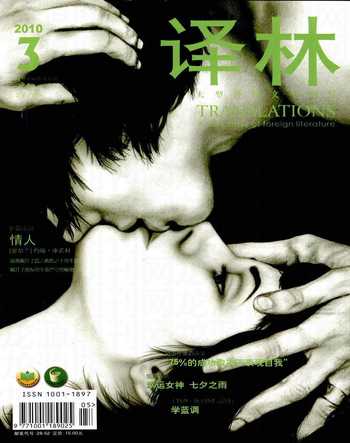人性的哀曲
2010-05-30许诗焱
英籍日裔作家石黑一雄的第三部小说《长日留痕》自问世以来就受到读者和评论界的强烈关注,荣登《出版家周刊》的“畅销排行榜”并于1989年获得在英语文学界享有盛誉的“布克奖”。这部作品被媒体誉为“一部精心杰作,它既对个人心理进行了令人折服的分析与深究,亦细致入微地描绘了败落的社会秩序”,作者“以消遣性的喜剧手法妙不可言地对人性、社会等级及文化进行了异常深刻和催人泪下的探究。”《长日留痕》的表层故事是一次旅行,这次旅行也是史蒂文斯进入自己过去生活深处的旅程,石黑一雄虽然只通过史蒂文斯一个人之口讲述了《长日留痕》的整个故事,但在小说的叙事情境中,经历者“我”与叙述者“我”似乎并不完全一致:这样就把读者放在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位置上,要求读者做出相当复杂的推断。石黑一雄把史蒂文斯的叙述分为八个不同的场景,除“序曲”和“韦茅斯”之外,其余场景均把史蒂文斯带入对于更早过去的回忆。读者跟随着史蒂文斯穿行于往事与现实之间,顺时的叙述交待事情的现状,表现他外在的活动,而逆时的回忆则展示其内心的变化波澜,形成小说的主干。如果读者将史蒂文斯在旅行途中看似散乱的记忆碎片拼贴起来,对主人公一生的命运轨迹作一番分析就不难发现,史蒂文斯的主要叙述都是在反思他与生命中最重要的三个人之间的关系——主人达林顿勋爵、父亲老史蒂文斯和恋人肯顿小姐。随着旅行的深入,史蒂文斯在其叙述中对过去事件进行的取舍、言语之间流露出来的话外之音以及叙述中出现的前后矛盾都使读者逐渐认识到,史蒂文斯在他自己的独白里告诉读者的一切恰恰是他最想隐瞒的,这种似是而非、表里不一的双重性令人不安,让读者感到一种复杂的张力和矛盾性。
小说主人公史蒂文斯的叙述首先聚焦在“尊严”这一主题上。从小说的第二章“索尔兹伯里”起,史蒂文斯就开始讨论有关“尊严”的问题。史蒂文斯曾对历史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比喻,那些能够理解和解决国家大事的大人物们就像车毂,而一般民众就像辐条环绕在他们的周围,撑托着车毂滚滚向前,创造前所未有的历史;而自己作为管家,能够非常荣幸地接近历史之轮的中心,史蒂文斯希望通过自己的敬业精神来成就一个小人物的伟业,而“隶属于某一显赫之门庭”是成就“伟业”的先决条件,他深信,对名门大家忠心耿耿的服务也就意味着让自己的工作成为天下大事的一部分。石黑一雄:《长日留痕》,冒国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以下关于小说的引文皆出自此书。因此,他对自己的职业倍感自豪,并且竭尽全力将自己的工作做到无可挑剔。尽管当时包括卡迪纳尔先生和贝恩先生在内的很多人都曾提醒他达灵顿勋爵所作所为的实质,但是“敬业精神”蒙蔽了他的双眼,让他看不清事实和真相。史蒂文斯曾说,“肯定地讲,一位‘杰出的男管家只能是这样的人:他能自豪地陈述自己多年的服务经历,而且宣称他曾施展其才华为一位伟大的绅士效过力——通过后者,他也曾为服务于全人类而施展过其才华。”当他自己回首职业生涯时,虽然他的确将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达灵顿勋爵,但他通过这位“伟大的绅士”贡献给全人类的却是巨大的灾难:达灵顿勋爵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实际上助长了一战后欧洲的法西斯势力,为纳粹上台提供了条件,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伟大管家的“敬业精神”为史蒂文斯构造了一座虚幻的、闪着辉晕的巅峰,变成了一种植入灵魂深处的“崇高理想”,“理想”激发狂热和盲从,最终导致悲剧性的终点。当旅行结束时,史蒂文斯坐在海边的长椅上,对着一个陌生人泪流满面:他最终明白了自己为证明个人生命价值所作的种种辩解都不过是不堪一击的自欺欺人,他毕生追求维护的职业风范不仅没有任何“尊严”可言,更导致了自己的一生都成了一个“愚蠢的错误”。
达林顿勋爵可不是个坏人。他完全不是个坏人。至少在他生命终止的时候,他能有权利说他自己是犯了错误。勋爵阁下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在生活中选择了一条特定的道路,只是这条道路被证实是误入了歧途,可他至少可以这样讲,他毕竟作出了选择。而对我自己来说,我甚至连那一点也不能承认。我信赖他。我信赖勋爵阁下的智慧。在我侍奉他的所有的那些岁月,我坚信我一直在做有价值的事。可我甚至不敢承认我自己曾犯了些错误。真的——人须自省——那样做又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石黑一雄通过史蒂文斯之口提出了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重大人生问题:我们与权力的真正关系是什么?我们是权力的拥有者还是权力的仆人?什么是伟大?什么是尊严?就像史蒂文斯最终所领悟到的“严酷的事实”:“很显然对你我这样的人而言,除了最终将我们的命运交给那些处于这个世界之中心地位、而且雇用我们为之服务的伟大绅士去掌管之外,便几乎别无选择了。”石黑一雄在这里出其不意地使用了“我们”一词。乍一看来,这个“我们”显得有些唐突——读者在史蒂文斯的人生故事中似乎应该只是一个局外人。然而对于绝大多数读者来说,这不正是“我们”的命运吗?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服务于更有益的事情,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有价值。尽管我们的动机是善意的,但结果却常常发现自己所做的事情违背了本意,正如石黑一雄在一次访谈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大多数人对周围的世界不具备任何广阔的洞察力。我们趋向于随大流,而无法跳出自己的小天地看事情,因此我们常受到自己无法理解的力量操控,命运往往就是这样。我们只做自己的那一点小事情,希望能够派上用场。所以我认为许多责任义务的主题都来源于此。在我看来这种本能是人类最令人瞩目的地方。让人难过的是人类有时认为他们生来如此,还自以为是。可事实上,他们通常并非真的献身于他们一直认可的事。”李春译:《石黑一雄访谈录》,《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4期,第136页。
尽管史蒂文斯所追求的以“尊严”为核心的崇高职业理想最终被彻底颠覆,但他几乎一生都沉湎于此而无法自拔,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他的“尊严”成了一副面具,让他总是言不由衷并最终导致他在亲情与爱情方面无法挽回的人生缺憾。史蒂文斯的父亲是一位资深管家,根据史蒂文斯的标准,父亲几乎就是“与其地位相称的尊严”的典范:他能够以极高的专业水准侍奉拉夫伯勒府的所有宾客,甚至包括那位因失职而导致史蒂文斯哥哥战死的将军。同时老史蒂文斯也将自己一生的梦想寄托在儿子的身上,时刻提醒儿子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控制局面,哀乐有度,悲喜有节,绝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失态。不仅如此,老史蒂文斯在其雇主约翰•西尔弗斯逝世之后仍然对管家一职恋恋不舍,以古稀高龄加入达灵顿府,甘于担当儿子的副手。在这种情况下,史蒂文斯与父亲的关系变得十分微妙。父亲和肯顿小姐加入达灵顿府之后不久,史蒂文斯就批评肯顿小姐不该直呼父亲的名字,而应该尊称为“老史蒂文斯先生”,但同时他又不肯因为父亲年老体衰而放松对其工作的要求。父亲病危之时恰逢达灵顿府召开重大的非官方国际会议,史蒂文斯选择了面带微笑继续工作,为一个抱怨脚不舒服的客人忙前忙后,而让父亲在楼上孤独地死去。父亲在他身上所培养出的伟大男管家的“杰出品质”令他舍弃了亲情,甚至还“油然产生出极大的成就感”,因为自己“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了那种‘杰出的品质。”故事叙述至此,“效忠精神”几乎将史蒂文斯提升到极其高尚的精神境界,以至于读者想用中国传统的“忠孝不能两全”来赞扬史蒂文森的“无私”。但随着故事的发展,读者又逐渐意识到其中的不妥之处,因为读者发现此“忠”非彼“忠”——史蒂文斯当年痛舍亲情所追求的“忠”最后全部奉献给了一个丑恶的事业,他所不断炫耀的那些他有幸亲自经历的重大幕后事件也最终都被证明是历史的污点。等到幡然醒悟,亲情早已随着父亲的去世而永远无法弥补。同样令人唏嘘的还有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无果的爱情。在小说的开头,史蒂文斯交代他此次旅行的目的是为了去见以前的同事肯顿小姐以求解决达灵顿府的人员配置问题。这里,石黑一雄巧妙地运用了经典叙事学中经常提到的“不充分报道”的叙事技巧,有意让史蒂文斯隐瞒自己这次旅行的真正动机。史蒂文斯的叙述中断断续续透露出的种种细节足以证明,尽管他确实有合理的职业理由拜访肯顿小姐,但这种职业目的似乎不过是其个人目的的一个托辞,此次拜访的背后还有一些更为重要的个人理由——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之间曾经有过超乎工作关系的“私人关系”,他内心深处其实一直在期待着通过这次重逢与肯顿小姐再续前缘。两人在达灵顿府共事期间,史蒂文斯一直用“真正的男管家”所必须遵守的“克制”精神约束着自己,他认为“此类婚姻事件若发生在地位较高的雇员之中,对工作就会产生极具破坏性的后果。”面对着肯顿小姐对他流露出的真挚爱意,他刻意压抑着个人情感,张口闭口总是谈论工作上的安排,假装意识不到两人之间日益深厚的感情,最终导致他们与爱情失之交臂。当史蒂文斯与肯顿小姐在人生的黄昏时分再次相见时,他终于得知当年肯顿小姐决定嫁给贝恩先生仅仅是让史蒂文斯烦恼的“另一种伎俩”,他伤心不已,“说实话——我为何不应该承认呢?——在那一刻,我的心行将破碎”,但他又一次习惯性地将自己的真实情感掩藏起来而仅仅作出一个几乎是程式化的回答,“你是非常正确的,贝恩夫人。正如你所说,要使时钟倒转确实太晚了……你和贝恩先生以后的那些岁月会是特别的幸福。你真的不应该让任何更为愚蠢的想法使自己与你所应得的幸福隔离开来。”史蒂文斯的真实情感与实际言语之间的又一次脱节彻底割断了两人之间残存的一丝缘分。小说中这段因为交流的失败而错失的爱情成为史蒂文斯人生悲剧中最为纠结的部分。遥相暌隔的往事虽然已经无法挽回,但它所留下的伤痛何时才能淡忘?史蒂文斯日后的人生故事中必然会有更多追忆与反思时的黯然神伤。
故事的结尾看似平淡,却是整部小说的高潮所在。在对自己的人生幡然醒悟之后,史蒂文斯却决定用自己一贯的职业态度严肃认真地对待调侃打趣的技巧,以迎合美国新主人的作风。这一结局不免令人失望,但仔细想想,这又是唯一可能的结局。如同小说的题目(玊he Remains of the Day)的字面意思,“白天剩余的时光”,对于史蒂文斯来说,他已进入生命的黄昏期,“白天剩余的时光”已经所剩无几,已经没有可能改变坚持了一生的生活信条和准则,他唯一能做的只能是为原来的信条和准则寻找理由,通过自我欺骗的方式继续“体面”地生活下去。石黑一雄曾如此表述他的文学观念:“我是一位希望写作国际化小说的作家。什么是国际化小说?简而言之,我相信国际化小说是这样一种作品:它包含了对于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都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活景象。”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现代世界中,如何才能突破地域的疆界,写出一本对于生活在任何一个文化背景之下的人们都能够产生意义的小说?在这个多元文化碰撞、交流的现代世界之中,什么东西才足以穿透疆界,激起人们的普遍共鸣?《长日留痕》似乎给出了答案:该小说通过一个看似波澜不惊的故事成功地再现了个体在繁杂纷扰的现实世界中的困惑与无奈,它所包含的悲剧意蕴像一首挽歌,唱出了人性的哀曲,无疑能在“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心中引起共鸣。
(许诗焱:文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邮编:2100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