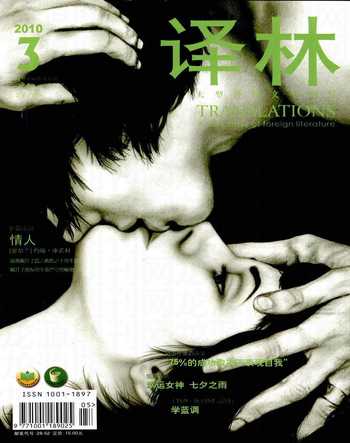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
2010-05-30潘望
潘 望
阅读伊夫林•沃,难免会想到和他同时代的另外两位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和格雷厄姆•格林。这三位都著作等身。奥威尔投身西班牙内战,后来写了《向加泰罗尼亚致敬》;格林更不得了,几乎五大洲全留下他神秘莫测的身影,他为英国军事情报六处工作的经历至今仍留有许多谜团。格林的故事大都和他的冒险有关,尤其是《哈瓦那特派员》;伊夫林•沃则是真刀真枪地参加了二战,1940年入伍后,毫无指挥才能的他不仅
没有光鲜的战绩,甚至遭到手下兵士的怨恨。1943年12月,沃跳伞负伤,于是离开军队休息,并开始写作《旧地重游》。小说伊始便是英国军官查尔斯•赖德的独白:“在这里,我和军队之间的爱已经完全消逝了。”想来也不啻为沃自己的心声。然而战争只是小说的远景,最终他奏的是一曲对于青春、激情和已然崩塌的旧世界的挽歌。这是沃最柔软的小说,没有以往的嬉笑怒骂,代之以温情与怅惘,仿佛无力的喉咙唱着旧日的谣曲,而歌者在狂欢后的夜色里渐渐隐去。站在40岁的当口上,离战争并不遥远的沃,突然在废墟里建造起这座美轮美奂的布莱兹赫德庄园,并将它笼罩在不灭的光晕之中。但它一击即碎,因为它是用回忆做成的,因为它是已经失去的。
这个故事有许多贯穿始终的线索,比如宗教,以及人们来来往往的布莱兹赫德庄园。此外还存在另一个焦点,黑洞般吸引着喜怒哀乐,它就是酒。查尔斯第一次在牛津校园遇见塞巴斯蒂安•马奇梅因时,塞巴斯蒂安喝醉了。第二天,他送来满满一屋子鲜花赔罪。后来他们在布莱兹赫德过夏天,将地窖里的藏酒喝了个够,半醉半醒间评价葡萄酒“像一只天鹅”,或者“像最后一头独角兽”。有时,喝完之后他们坐在图书室里,“图书室在宅院的侧面,俯瞰着湖水,窗户都敞开着,星光照进来,温馨的空气飘进来,满窗都是幽蓝的和银色的山间月夜景色,可以听见喷泉滴水的声音”。终于,塞巴斯蒂安从嗜酒变成酗酒,他必须醉才能把自己藏起来。家人想尽办法让他戒酒,而查尔斯隐约明白他内心的焦灼,偷偷给他钱买酒喝,于是被逐出了布莱兹赫德。这委实是一本关于醉生梦死的小说,有时特别美,比如沐浴着初夏的阳光,年轻人们坐在榆树的阴影里喝酒谈话;有时引人叹息,当塞巴斯蒂安喝进医院,仍旧偷偷叫看护买酒,藏在床铺下面。伊夫林•沃本人就嗜酒如命,读书时的择友标准是“有不为酒精俘虏的能力”。谈到写作《旧地重游》的背景,他说:“那是一个暂时匮乏和灾难迫在眉睫的时代,因此这部书里就充满了对酒食的贪馋和华丽辞藻的爱好。”于是,塞巴斯蒂安和查尔斯的青春如烈酒一般倾泻而下,既短暂又芬芳。两个相亲相爱的年轻人,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庄园,没有过去,没有将来,这样的夏天最好永远不要过去。
然而,狂欢总有醒来的早晨。那些给予我们力量的最终可能成为束缚,反过来,那些一直束缚我们的可能正是某种力量。在变动不居之中,能够倚赖的真实或者信仰又是什么?沃在1930年9月(26岁)皈依天主教,这是他人生和写作的分水岭,也成为伦敦当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报纸上蜚短流长,于是他写了《皈依罗马:为何发生在我身上》。他说,这无关于仪式,也无关于对他人意志的顺从,而是在基督教和混乱之间的抉择。1959年《旧地重游》再版,沃在序言里提到,小说的主题是“天恩眷顾各种不同而又密切联系着的人物”。 别忘了他给小说起的副标题是:
查尔斯•赖德上尉神圣和渎神的回忆(Brideshead Revisited:The Sacred and Profane Memories of Captain Charles Ryder)。信仰问题从头至尾都笼罩着塞巴斯蒂安•马奇梅因和他的家人,按照小妹妹科迪莉娅的话来说,那是“一根看不见的命运之线”。在故事的结尾,这个贵族之家的每一颗不平静的灵魂,都皈依神圣,蒙受天恩。但这恰恰是小说的失衡之处,伊夫林•沃感人肺腑地记录了信仰在人们身上引发的疑问,却没有同样充分地写出他们笃信的原因与历程。比如说,查尔斯与塞巴斯蒂安的友爱、查尔斯与朱莉娅的情爱如此完满,他们为何必须放弃凡人的同样真实的爱,去寻找“上帝的慈悲”?也许是,伊夫林•沃过于精彩地展现了人情,以致掩盖了神恩。或者说,这根本就是一本酒神之书吧。
故事将要终结时,朱莉娅难敌罪孽深重的焦虑,感情爆发。而马奇梅因老侯爵的临终独白,是一个浪荡子对神无力的抵抗与最终的降服。这些激烈的场景,伊夫林•沃是下了许多工夫的,可它们的力量比不上另一些小小的碎片,比如塞巴斯蒂安抱着大大的玩具熊坐在繁花似锦的栗子树下;比如在暴风雨的甲板上,查尔斯与朱莉娅东倒西歪地走着,因为颠簸不停地冲撞在一起,她的头发吹到了他的眼睛里。这部主观上以“天恩眷顾”为主题的小说,客观上获胜的却是异教徒的欢乐悲伤。同时也必须承认,小妹妹科迪莉娅的信仰令人信服,那确是发自身心的信和爱,温暖如春天一样。
小说里最可爱的人物无疑是塞巴斯蒂安,既干净又透明。一开始,他抱着大大的玩具熊在牛津校园里游荡,给它取名阿洛伊修斯并视为挚友,直到查尔斯出现。他就那么心不在焉地走来走去、喝酒沉睡,却使人充满爱怜。至于他和查尔斯的同性恋情,沃写得非常隐晦,不留心几乎看不出痕迹。倒是2008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将他们的感情大书特书。在小说里较为明显的有
两处,其一是他们在布莱兹赫德消夏,塞巴斯蒂安的妹妹来找他们玩:“天哪!”塞巴斯蒂安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去拿毯子。“像是我妹妹科迪莉娅的声音。你快把身子盖上。”接着大喊:“走开,科迪莉娅,我们还没穿衣服啊。”第二处是他们去威尼斯游玩,遇见塞
巴斯蒂安父亲的情妇卡拉,她安详平淡地说:“这种友谊是一种爱,在孩子们还不懂得它的意义的时候,他们身上就产生了这种感情。在英国,这种爱在你快长大成人时出现;我觉得我是喜欢这种爱的。对另一个男孩子怀有这种爱要比对一个女孩子怀有这种爱好一些。”后来三十岁的查尔斯爱上塞巴斯蒂安的妹妹朱莉娅,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面时,
查尔斯觉得朱莉娅实在太像她的哥哥了,那么他对女孩的爱里是否包含着对男孩的追忆?从沃引而不发的字句寻找确凿证据并不容易,但也不失为一个有趣的拼图游戏。这就好像表面故事之下藏着另一个故事,当你画出迷宫地图,便发现真相是立体的,角度的转变带来解释的变化,好在它们都是关于爱的故事。
塞巴斯蒂安实在太耀眼了,他身上招人喜爱的东西怎么都不会失掉,酗酒也好、流浪也好、变成醉醺醺疯癫癫的修道院守门人也好。光芒何来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这样的人,哪怕只在书页上。
《旧地重游》出版时,评论界称赞它“具有那种只有在一个处于创作巅峰期的作家身上才能找到的深度与分量”。诚哉斯言,当代小说里极少读到如此纯正的田园牧歌。对于伊夫林•沃来说,这也是回顾前半生的倾力之作,生死爱欲,形而上下,尽在其中。另一方面,跟他的好朋友,同样信仰天主教的格林相比,他更加控制与内敛,用董桥的话来说,他是“最忍得住情的作家”。那些简单平淡的句子却魅力不凡,比如:
“我们应该天天晚上都喝醉吗?”一天早晨塞巴斯蒂安这样问。
“不错,我想是这样。”
(潘望:南京大学文学院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邮编:2100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