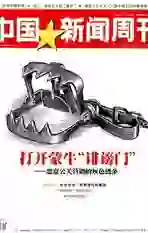李强:探索适合中国特色的民间自治
2010-05-14舒琳
舒 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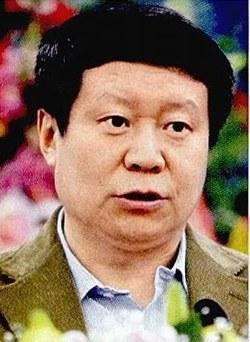
从9月29日的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到刚闭幕不久的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都强调一个重要思路,就是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并强调解决之道在于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等。
在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胡锦涛着重强调要加强社会管理基层基础建设,“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能力”,加强社会组织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
近日,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专访时,从社会结构变迁的角度深入分析中国的社会矛盾现状以及应对之道,并提出探索建立自治社会的重要性和现实困难。
“大跨度流动越来越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你怎么看待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社会结构变迁?今天又有哪些新特点?
李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首先,政治分层转变为经济分层;其次,改革从社会的边缘阶层农民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段时期,城乡差距明显开始缩小。
但是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社会主体阶层大量涌入市场,拥有权力的人更容易聚集财富,腐败等问题严重。城乡差距再次被拉大,农民群体再次被边缘。旨在实现社会公平的改革,结果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现象。
最近一个阶段出现了新的趋势,我将之定义为“阶级结构定型化”,即社会流动从剧变时期进入稳定时期,阶层之间的上升和下降从无序状态进入有序状态,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渐趋稳定。社会下层群体、边缘群体获利明显下降,向上流动比率减少。从趋势上看,大跨度流动越来越困难。
中国新闻周刊:改革推进到今天,在引起社会结构剧烈变迁的同时,也出现了无法回避的社会矛盾和冲突,经济快速发展并没有给老百姓带来相应的幸福感,如何解读?
李强:改革到今天,社会矛盾和冲突似乎更多了。具体表现为,拆迁之类问题大量出现;劳资矛盾激化;新的城市社会运动,诸如业主和物业、房产商之间的矛盾等大量涌现。
这是一个大问题。按照“发展是硬道理”的逻辑,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应该更缓解,人民的满意度会更高。但是事实却相反。
有观点认为,由于阶层因收入分配问题影响导致贫富差距加大,从而导致了利益冲突尖锐。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也没有面临我们这么多的问题。
其中很核心的问题就是阶层分化严重,同时各阶层的利益诉求与现实之间差距拉大。我认为,戴维斯“J曲线”或许更适合解释中国当下的情况。他认为,经济急剧增长时,老百姓的期望值被刺激得更高,比经济发展更快。并用大量数据表明,同时期的社会矛盾也会大量增加。
我注意到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老百姓的期望值和实际发展之间的差距增大,这一提法很精彩。未来一段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欲望没有止境,仅仅靠经济发展不能解决问题,还要重视发展中的公平正义。
重视社会力量
中国新闻周刊:胡锦涛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解决之道,就是提高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能力。而法学泰斗江平在最近凤凰周刊“现在与未来—中国时局展望”高峰论坛上也提出要给予企业、个人、团体等自治的权利,你怎么看待中国自治社会的建立?
李强:这一点很重要,也是我要提出的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社会力量的重视。我们要重视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力量的发展,因为民间资本增强了,NGO、慈善事业等的发展也要跟上,如果它们发展起来就会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问题。
首先,在城市社会转型中,与老百姓联系最为密切的组织资源是街道和社区居委会。它们在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照顾老弱病残,建立城市社区医疗保障体系,协助城市失业下岗人员再就业,解决家庭困难、纠纷与矛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缓冲带功能。
还有就是类似妇联、工会、希望工程之类的组织,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NGO,但是也在相关领域缓解着社会矛盾,今后还会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中国社会的传统模式确实有一个大问题,就是整个社会是总体型社会,由政府一手操办。改革开放之后有进步,就是市场自由了,但是老百姓自身的组织依然比较被动。因此,大家都认为随着市场经济发展,民间自治组织虽已有很大发展,但是远远不足。
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过去一直都比较小心谨慎,担心放开自治组织的力量之后会不好控制和管理。但是,现在意识到了自治组织的重要性,政府也开始了探索。
不可忽视的一点是,公民社会是西方提出的概念,这和西方社会的历史基础有关系,而中国的传统和它们很不同,因此推行起来很艰难。经过前一时期的研究我认为,我们的大多自治形式上是民间的,但实际上仍旧是官方的,这需要一个平衡。因此,我认为,从长远看,应该是探索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国情的民间自治。
总之,从长远来看,要实现自治社会的建立,中国需要一个较长时期的培育过程,其中包括国民素质的提高等等很多内容,不可操之过急,否则容易产生更多的不稳定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