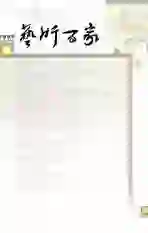丁玲赵树理戏剧创作之比较
2010-05-10王力
王 力
摘要:通过对赵树理与丁玲戏剧创作的比较研究,发现强调“唱”和“演”的戏曲思维使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具有特殊的形式美,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民间文艺气息;而重视人物“说”和“行动”的现代叙事思维使丁玲的话剧创作具有更多的理性色彩,也因此与其小说创作追求宏大叙事达成内在的一致。这种差异正好暗示了解放区文学以至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不同资源之间特殊的对话关系。
关键词:丁玲;赵树理;戏剧创作;艺术特征;比较
中图分类号:J8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091-04
在解放区作家群中,赵树理与丁玲因为小说创作先后成为文艺界的“明星”,读者和研究者对他们小说的关注几十年来始终不衰,却往往被忽略了他们的戏剧创作这一特殊领域。社会阅读选择是文学评论引导的结果,文学研究的视野却不应该被社会阅读的“惯性”所遮蔽,无论是就作家评判的全面性要求而言,还是从现代文学叙事传统研究的整体性来看,既然戏剧创作是他们文学活动的一种重要方式,那就必须认真考察和思考这一特殊的创作领域及其作品形态。何况对于赵树理来说,戏曲创作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
赵树理与丁玲的戏剧创作之所以有着重要的比较研究价值,在于他们的戏剧观差异正好暗示了解放区文学以至新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的不同资源,他们对于戏曲与话剧艺术内涵的理解与实践差异,恰又反映了民间文艺传统与新文学传统存在着的深层对话关系。简言之,通过对他们戏剧创作的比较研究,可以发现强调“唱”和“演”的戏曲思维使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具有特殊的形式美,也使他的小说创作具有浓郁的民间文艺气息;而重视人物“说”和“行动”的现代叙事思维使丁玲的话剧创作更具有理性色彩,并与她在小说创作中追求宏大叙事的特点达成内在的一致。
丁玲和赵树理对于戏剧的理解差异甚大,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各自的戏剧创作。
赵树理所理解和创作的戏剧类型,主要指长期流行在山西长治晋城地区、以上党梆子为代表的上党地区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各类戏曲。从1939年至去世,赵树理创作、改编了大小计13个剧本,并且留下了25篇关于戏曲的文艺评论,这在现代作家中,是非常少见的。他对于戏曲的音乐、唱腔、表演程式都有着深刻的理解,所以他评价和创作戏曲非常重视“唱”和“演”。丁玲则是以比较稳定的“现代小说”思维进入话剧创作,虽然和赵树理一样追求“政治上起作用,老百姓喜欢看”,但她的目光聚焦在以人物的行动和心理展示性格冲突与变化上,在戏剧创作中强调人物的“说”和“做”,而且常常不自觉以剧本阅读的方式反思自己和评价他人的戏剧创作。这种差异分别反映了民间艺术和西方近代文学观念的复杂影响,也折射出现代中国文学的不同叙事传统。
赵树理把在农村地区流行的戏曲分为两种,即多演历史故事的“大戏”和主要表现家庭生活内容的“小戏”,而且特别强调“小戏”的艺术价值。他总结了“小戏”的两个特点:其一,故事单纯,往往带点浪漫成分,不过这种浪漫不是惊心动魄,而是异想天开,使人觉得娓娓动听;其二,唱腔虽然简单,却引人入迷,“听进去好像在一个平静的湖面上泛舟,一定也用不着吃力,心情自然随着剧情而荡漾起来。”他认为这种“小戏”的艺术价值在于,能够给劳动者以休息,使他们得到和风细雨式的愉悦和教益,而不是让人大大振奋一下,所以他非常强调地方戏曲对于农民的娱乐功能,一再回忆起农民热爱戏曲的生活细节,即使贫穷,“有机会也还要偷个空子跑到庙院里去看一看夜戏”。
基于这些认识,赵树理的戏剧创作充分发挥了“唱”的特色,特别重视汲取戏曲的地方特色,使“唱”和“演”充分结合,比较完美地实现了戏曲的艺术表达功能,而又贴合农民观众的接受习惯。《十里店》和《焦裕禄》是赵树理独立创作的上党梆子剧本,非常系统地反映了他对于戏曲艺术程式的“本色当行”。在表达音乐与唱腔的衔接时,他延用了传统地方戏曲表达中的“切”、“还腔”、“过”等用语,而且娴熟运用“大开门”、“阴阳板”、“转流水”、“剁板”等乐调变化;在剧情安排方面,他有意识地保留了戏曲脚本的言语声口,比如“斟酒一巡”、“落”、“介”、“屏入”“倒下”等动作术语,以强化戏曲的“本色”风貌。对于一些比较短小的曲词,他也着意点出“唱”的重要性。“小唱剧”《巩固和平》开头就交代:“不布景,不限调,各种地方戏均可唱。”在这一作品中,他主要使用了快板和丝弦两种乐器,也是出于可以到处传唱的目的。较长些的《开渠》,则是以“七字调”为主,参以“打酸枣调”、“钉缸调”,共十一场,每场一韵,既有独唱也有合唱形式。这和当时解放区的戏剧普及背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村村有秧歌、人人唱新戏的浓郁氛围使合唱成为当时农村戏剧活动的重要特征。为了适应不同地方戏曲的交流和搬演,赵树理在剧本设计方面作了比较周到的安排。《开渠》是为上党地区创作的,其中第九场末的“穿场”,作者特意注明:“要是在其他剧种演,穿场可移在下场。”这表明赵树理创作吸取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演”,一切以演出效果为重。
地方戏曲中很多表达幽默的程式在赵树理笔下呈现出新的特点,而又非常妥帖地和剧情演出结合在一起,具有强烈的农村生活气息。《十里店》最后一场,李玉屏故意刁难王东方的母亲,一农妇气不过,拿锅底煤烟抹向她的脸,李玉屏“急闭目躲避,但未躲及,被抹了个黑鼻子”。这是化用了传统戏曲中丑角画白鼻梁的方式,虽然以黑易白,但对于农民观众来说,演出效果是一样的,而且富有现实生活趣味。当刘宏建终于明白自己上当时,有这样一句独自:“我真是个——唉!二百五呀!”这也是戏曲中反面人物自曝其短时常用的声腔,赵树理显然是考虑到表演效果才如此设计的,有的研究者也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
丁玲的童年记忆中也有戏曲的影子,一个善于插科打诨做清客的堂表嫂,为她塑造了李白这一脱俗的英雄诗人形象,但她所接受的新文学熏陶以及惯用的思维方式,是“现实主义”。她第一次看的话剧是20世纪20年代洪深导演的《少奶奶的扇子》,虽然没有完全看懂,“但这种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是合乎我的理想的”。正因为她对音乐、唱腔和表演程式的隔膜,她的文学视野是充分“现代化”了的:“我只是喜欢‘看人,看演员创造的人。”至于《重逢》与《河内一郎》,“这两个剧本的写作都不是我本人在生活中有什么灵感,也不是经过仔细酝酿、构思,精雕细刻出来的作品;而只是适应宣传工作的需要,完成戏剧组分配给我的一项写作任务。”若干年后重校时,她觉得《河内一郎》“第一幕还勉强有点文学意味,第二、第三两幕实在缺乏生活,比较公式化而且乏味。”其实,后来的《窑工》仍未避免这些毛病。
总起来看,丁玲对戏剧的认识集中在人物的“说”和“行动”,她无论是创作话剧还是评论戏剧或者剧作家,都立足于“文学”的基本立场,但很少注意话剧这一艺术体式的特殊要求;她所使用的术语、所关注的重点,都带有明显的“小说”特
征,或谈人物塑造,或论作家修养,或谈情节线索,对于话剧创作所要特别重视的冲突、场景、表演等,多从小说叙事的角度笼统而论。她对表演基本上没有多少经验,即使谈及也是从剧本阅读的角度。她曾经坦率地提到《河内一郎》是“编”出来的,事实上,连这部话剧中反映日本家居生活的舞台布局也是泽村利胜帮着画的,她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和生活经验。丁玲也意识到自己对话剧并不内行,虽然初到解放区便骤享大名,人们对她的作品普遍报以较高评价,她也希望人们能够指出缺点,“不要象一些关于《重逢》的来信或谈话,总是说好,使我反而感到寂寞。”
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期间是丁玲从事戏剧创作的开端,“除了写通讯报导以外,主要是各种形式的宣传演出,并且常常以话剧为主。”《重逢》就是为了配合这一形势而完成的:“剧本表现了一个幼稚姑娘如何通过一次流血的‘重逢才明白了抗日斗争的艰巨性与复杂性,具有新鲜的教育意义。”。这部作品继承了“五四”以来独幕剧注重布局的优长,剧情设计冲突迭起而又合乎抗战中人的情理模式,所以上演后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此剧完成后,不仅在延安、西安地区上演,还被推荐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推广到了国统区。后来此剧还被翻译成英文,在印度发表和公演,好评较多。但有的研究者清醒指出,此剧“虚设的戏剧性与战争实际的距离,浪漫情调与劳苦大众的距离都是明显的”。这应该归因于丁玲对自己所写的题材缺乏生活体验,与赵树理相比,她在反映现实生活的真实度和艺术感染力上相形逊色。
由于长期的文学活动和解放区写作经验,丁玲具有根据理念而不是生活积累创作的能力,虽然较高的文学才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生活经验方面的不足,但无法从根本上克服公式化和概念化的毛病,这在台词和人物行动的设计上表现得比较突出。《河内一郎》第一幕的故事发生在家庭之内,主要冲突也存在于男女情感与外部社会压迫之间,这是丁玲在小说叙事方面的强项,所以比较成功。到了第二、第三幕,无论是日军对中国农妇的兽行,还是河内一郎被俘后的行为,都变得概念化了,这个人物的忏悔充满了流行的标语口号,诸如“我有罪”、“我非常后悔”、“打倒军阀、财阀,消灭战争的祸根”等。与这一形象苍白、性格萎缩的主人公相比,本来是作为冲突副线的反面人物山本显得真实鲜活。《窑工》一剧,是全面内战爆发前夕丁玲“出于一种责任感”依靠“采访材料”完成的,目的为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巩固胜利、巩固新区”,就像建国初她为配合抗美援朝的宣传主题而赶写电影剧本《战斗的人们》一样。《窑工》中的张永泉是集万恶于一身的反面形象:汉奸、狠毒的矿主、欺男霸女放高利贷者,当日本人投降、八路军进城后,他的狗腿子李生财都明白“八路军来了咱们全活不成”的道理,作者却不让张永泉逃走,反而安排了八路军和民主政府轻易被他蒙蔽的情节,任其一度逍遥法外,这虽然突出了张永泉狡猾和愚蠢并存的性格特征,却不太合乎生活常理。对此,丁玲后来也承认《窑工》“粗糙、人物概念化等毛病是很明显的”。
丁玲和赵树理在戏剧观念和创作上的差异,缘于深刻的叙事观念分歧,这可以在比较分析他们的小说创作时获得更全面的认识。也就是说,赵树理的小说受到了戏曲叙事思维的深刻影响,而丁玲的话剧受到了现代小说叙事观念的复杂影响。
传统戏曲的叙事思维和其他中国古典艺术的思维方式是相通的,是一种“散点透视”的审美思维,即视角常随人物的穿场和在每出表演中的主次地位而变。这一方面发挥了全知叙述者无所不晓的功能,故事性和传奇性并存;另一方面,情节的不同阶段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叙事单元,戏曲的“出”、“折”和古典小说的“章回”之间有着内在的相似性。赵树理的小说叙事常取散点透视的方式,情节因人物变化而演进,视点也常因人物的转换而变化,这样在每一个具体场景中,情节与人物关系是单纯的,叙事视角也呈限制状态,而不同场景与情节的衔承则全由一个外在的叙述者控制,又在整体上打破了这种相对独立的限制叙事,使之呈现出情节进展与人物性格变化的统一性。比如《万象楼》,分别将布景设在万象楼上、李积善家门外、街上高地,三处布景构成了剧情的三个叙事单元,最终汇聚成两大阵营的冲突。《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也都遵循这种叙事结构,前者若干小标题的设置构成了不同的情节单元,各有主要行动者和行动空间;后者则以一个全知叙述者观察李有才生活的特殊窑洞,以老杨同志的眼睛看出老槐树下农民的生活境况,然后由全知叙述者将视点移到阎恒元的家中,不久由以李有才为观察者发现量地的秘密。叙述者的不断转换就形成了整体叙事的散点透视效果。研究者常将赵树理的小说称为评书体叙事,其实“评书”和“戏曲”同样遵循这种散点透视的叙事思维。
建国后,赵树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比较艰难的阶段,虽然《三里湾》因为描写社会主义农村建设获得较多的好评,读者也可以从中发现这种散点透视审美思维的存在,而这恰恰与越来越要求典型集中的主流话语相矛盾,赵树理不得不转而从事戏曲创作。这是他可以保有自己的审美观念和政治理想的最后领地。许多与赵树理关系密切的人都记得他在写作时有哼唱戏曲或者敲打鼓点的习惯,对此,人们应该充分感受到戏曲对于赵树理文学生命的非凡价值。事实上,戏曲对于赵树理来说,拥有比小说更长久、更深刻的意义,他的小说创作活动始于三十年代,终于五十年代末,前后经历了不到三十年的时间,而戏曲演唱、创作和评论则贯穿了他的从童年到临终的生命历程。
丁玲的话剧也追求传奇性,在叙事结构上则多取用现代小说的“内在焦点”,叙述视角稳定。《重逢》中贯穿全剧的人物是白兰,种种冲突也都围绕她发生,故事被限制在密室中,一切皆由她目睹亲历,其他人物都是作为与她相关的环境要素出现的,因此观众是从白兰的视角观察与判断情节进程和人物关系乃至冲突的。《河内一郎》第一幕中比较成功的动作设计也是如此:贞子进屋后,“望着壁上的相片”,“有顷,复抚手上的戒指”,这是舞台设计,也是小说以动作刻画人物心理的常用技法,有利于读者进入女主人公的心理世界,感受那种喜悦难撩的情绪氛围。接下来,就是明显的单一焦点透视技法了:“廊上传来皮鞋的声音。两人一惊。”“贞子慌忙跑到门边,又羞又怯地退回室中。”“菊子冲去开门,贞子迅速跪下。”如同小说一样,这里存在着一个冷静旁观的叙述者,这些语言也像小说一样节奏明快。
丁玲戏剧创作中对于人物的设计,像小说一样,注重在同一行动元中刻画性格各异的角色,使之形成互补格局,互相映衬,以强化总体冲突。这在她的作品中,常有人物彼此陈述、回忆对方身世和命运的情节,《窑工》中的工人们虽然跟张永泉相比属于同一行动元,但角色性格差别很大,有的拼死要去告发,有的胆小怕事,有的顾虑自己的微薄家业,只有赵满,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张裕民、程仁那样,义无返顾地走到斗争最前沿。这两部作品在叙事主题、人物关系与故事结构方
面都存在着很强的“互文性”。
赵树理特别重视“小戏”的艺术价值,他的小说创作也更多注目于农民村社、家庭生活,彼此形成了有趣的呼应,在他的戏曲和小说中,农民对于不公平的反抗和对合理生活的渴望是基本主题,所以他的小说与戏曲创作“互文性”地呈现了一幅“农民中国”的图景。他的审美思维和民间文艺传统密不可分,以农民的接受为写作基点。丁玲的话剧创作具有一种宏大叙事倾向,是为“革命”和“人民”而写的,比如《重逢》将一对恋人的故事置于民族大义的背景下,既显示了革命加恋爱小说叙事模式的某种影响,又体现了浓郁的抗战文化氛围对其文学活动的内在规约。也就是说,丁玲对于时代政治理念的领悟和响应更为迅速与合拍。
作家交往与相互评论是理解其文学观念的重要资料。丁玲与赵树理都是解放区的文学明星,赵树理曾经去拜访过丁玲,令人奇怪的是赵树理对丁玲的文学活动没有留下什么评价,丁玲却在日记和书信中对赵树理多次作出过耐人寻味的分析和评价。
1948年6月,丁玲写信给陈明,建议他把创作的大鼓词《平妖记》和《夜战大风庄》送给赵树理看看,“他这人给我的印象是有见解的(当然也有狭窄之处),他较长于民间形式,或者对你会有些启示。”同月,在山东临朐,她听说人们对《地覆天翻记》评价很高,“有人说比赵树理强,但也有人说不如赵树理”,她打算去要一本看看。后来见到了这本书和作者王希坚,认为“书写得很好,是属于《吕梁英雄传》一类的章回小说,这类书都是说故事的,通俗。有人说比赵树理好,未免有些夸张了。”1955年3月,丁玲在江苏太湖疗养院创作《在严寒的日子里》期间,书信中提到了《青年近卫军》和《三里湾》,她说自己喜欢中国味的作品,“可是赵树理的《三里湾》我还没有看下去。……”后来对《青年近卫军》作了细致的分析,却不再提及《三里湾》。作为新中国文学界的领导者之一,丁玲在演讲中还多次提到了赵树理在文艺大众化方面的成绩,但主要体现为一种政治姿态,而不是理性的文学评论。
这些资料有的涉及曲艺创作,有的谈论小说,实际上反映了两个作家的叙事思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应该从民间文艺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深层对话关系去思考。赵树理文学活动的出发点是“为农民”,他在建国后屡次强调民间文艺传统与新文学传统的平行关系,甚至以民间文艺为中国文学的“主流”,虽然他因为小说叙事大众化的成功而被纳入现代文学史的主流评价视野,但他生命的后十年只能以戏曲活动为中心,戏曲思维为他的成功提供了审美基因,也是他抚慰自我灵魂的最后一道屏障,当初是对农民的真诚理解造就了他在解放区文坛的崛起,最终则是对农民文化立场的坚守导致了他的被冷落。丁玲则是以成功的现代小说家身份兼事戏剧创作,她的文学活动始终处于新文学与政治权力相博弈的潮流之中,新文学发生之初就以“现代国家”的振兴为基本价值指向,无论戏剧还是小说创作都预设了“中国”这一象征丰富的背景;丁玲的写作对象是“人民”,她超越了赵树理的“农民”视野,所以她并不成功的戏剧创作能够在更大范围内获致认同。这两个作家戏剧活动与命运的浮沉,从一个侧面说明新文学叙事传统影响普泛,形成了对民间文艺传统的俯视态势,这反映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不同传统之间的特殊对话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