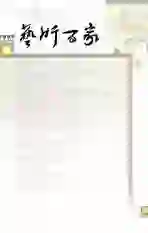以文学的方式见证历史
2010-05-10贾丁丁
贾丁丁
摘要:奈保尔是当代无可争辩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不仅题材丰富,而且寓意深刻。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剖析了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现实问题,探讨了殖民统治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波尔(Ball)认为,奈保尔“并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第三世界的记录者和代言人。”在奈保尔的代表作《河湾》这部小说中,他运用了许多象征殖民的意象和符号,以此阐释殖民的过程,以及殖民对非洲大陆造成的后继影响。殖民过程由虚假政策手段开始,渐渐过渡到明目张胆的武装镇压,最后又导致了殖民地国家对宗主国的附属状态。表面看来,小说中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已经完全摆脱了殖民时代的屈辱历史,赢得了走向现代化的契机;但实际上,“大人物”不过是殖民者的另一种体现,其推行的非洲政策并未使这个国家从原始状态中解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奈保尔既是称得上是一名无根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多元文化学者。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视角让人们得以从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殖民给非洲大陆带来的种种影响。
关键词:影视艺术;艺术批评;奈保尔;《河湾》;殖民象征
中图分类号:I0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153-05
维·苏·奈保尔是一位生于特立尼达的印度裔英国作家。由于他特殊的文化身份与人生经历,形成了其与众不同的文学路径。自1957年发表第一部作品《神秘的按摩师》以来,奈保尔一直对跨文化的创作题材倾注着自己的心血与力量。1979年他的代表作《河湾》引起了世界文坛的普遍关注。2001年,奈保尔荣膺诺贝尔文学奖桂冠。至今为止奈保尔创作的文学作品多达33部,是一名多产作家,同时也是一位颇受争议的作家。瑞典文学院称赞其作品“将极具洞察力的叙述与不为世俗左右的探索融为一体,具有驱策我们从扭曲的历史中探寻真实的动力”。注释在《河湾》中,奈保尔将小说设定在一个虚构的非洲国家里,这个国家刚刚摆脱殖民统治,获得独立。故事的叙述者萨林姆是一位印度裔穆斯林,他来到非洲内陆的偏远小镇经营一家商店。萨林姆在经历一系列波折之后,最终离开了小镇,不知去向。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运用了诸多象征手法,向我们阐述了殖民主义统治对非洲大陆的深远影响。斯图卢克(Struek)曾表示:“象征是一种可以产生强烈共鸣的文学意象,它与象征所包含的寓意有着某种特殊的关联。”在这部小说中,奈保尔大量运用了象征与隐喻的表现方法,描述了他心目中非洲大地的文化生态和历史变迁,使我们能够在字里行间领略到奈保尔对非洲现实的真切感悟,所以,奈保尔作品中的一系列象征性符号并不仅仅是文学技巧的简单运用,它是奈保尔精神世界的一种自然再现,也是对于处在殖民主义统治下的非洲人民的现实状态的真实展现。在《河湾》与殖民有关的象征的分为是表示“诡饰”、代表“暴力”和指向“附属”的符号。而这三者恰恰是对殖民非洲的真实写照。
一、诡饰性符号
在《河湾》中,奈保尔提供了两条与诡饰相关的格言。第一条刻在小镇码头门外的纪念碑上。原文为拉丁文“Miscer-ique probat populos et foedera jungi”,意为“各族融合,团结合一,深合他意”。萨林姆在破败荒芜的码头边发现了这句格言,而周围的环境似乎暗示,整个小镇最终会遭遇不幸,化为废墟。当萨林姆前去拜访小镇的神父惠斯曼时,这位对非洲信仰怀有崇敬之情的神父告诉了萨林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原来,这行拉丁文的意思是罗马诸神反对非洲大陆各种族间的融合,但小镇的人们却把它改为了和原来截然相反的语言,也就是说,变成了罗马诸神同意民族混杂。这种诡饰的做法让萨林姆大为惊愕。没过多久,纪念碑就被人毁坏,周围也变成了破败的废墟。更改格言的做法无疑是对罗马诸神旨意的背离。在蒂姆(Thieme)看来,“这种做法只能导致小镇走向毁灭,而萨林姆的这种想法后来也得到了证实。因为,纪念碑是在殖民时代刚刚结束时建立起来的,其本身作为殖民时期的功绩之一,是一种年代错误的产物,最终迅速土崩瓦解了。”
第二个格言也同古罗马密切相连。在这个虚构的非洲国家,总统新建了一所学校,该校的校训是“Semper aliquid no-vi”,意为“总有新东西。”然而在这个荒芜的非洲国家里,基本毫无“新东西”存在。除此之外,校训的诡饰性还体现在书中另一位人物费尔迪南的遭遇中。他开始是满怀期待地步入学校深造,最终却沦落为一个虚无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费尔迪南刻意地模仿达官贵人的举止扮相,期望有一天能够出人头地,最后却成为了这个充斥虚饰与谎言的非洲国家的随葬品。
由此可见,殖民带来的种种诡计现实体现在“有意识地曲解格言引用。”。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纪念碑本是具有神圣含义的象征,却并未建立在庄严肃穆之地;相反,纪念碑前的开阔地带是喧嚣的集市,丝毫没有敬畏可言。正如福克斯(Folks)所言:“奈保尔意识到,人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充满了逃离主义、自我幻灭和虚伪做作。”
与此类似,在《河湾》中,面具同样也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整部小说中,有三处体现了面具的诡计性意象,有两处是真人如同面具般的面孔,另一处是惠斯曼神父收藏的面具。在西方文学中面具作为诡计性的象征可以追溯至济慈的诗歌中,这位英国浪漫主义时代的诗人曾经“用面具来解释人性的特点。在他创作的许多作品中,他回归到了古希腊或是日本的面具模式,用它们揭示生活中虚假的基本作用。”在奈保尔的《河湾》中,萨林姆初次与费尔迪南相见时,他便察觉出这个男孩独特的面部特征与非洲的传统面具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费尔迪南的真实意图似乎总是掩藏在其酷似面具的脸庞下。他很少向萨林姆表露心声,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丰富的内心世界。费尔迪南的疯狂、绝望并没有写在他的脸上,尽管这些特征实际占据了他性格中的很大一部分。费尔迪南诡计多端的一面在他偷窃惠斯曼神父账簿时暴露得淋漓尽致,让人突然觉得这个角色变得既陌生,又恐怖。在小说结尾处,费尔迪南成为了新领地的一位官员,解救了被困入狱的萨林姆。但那一刻,萨林姆仍然清楚地意识到,费尔迪南那张酷似面具的脸庞似乎从来没有改变过。
耶苇特在《河湾》中是个浅薄轻浮、对生活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西方女性,但她的这些性格的特点并没有直接呈现在她的脸上,而是掩藏在她面具般的脸孔下。当萨林姆邀请耶苇特外出时,她面具一般的脸孔忽然变得布满笑意,与她平时的表情截然不同。她成为萨林姆的情人,并不是因为爱情,而是因为她厌倦了在非洲内陆国家单调而乏味的生活。最后,萨林姆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耶苇特虚伪而又诡计的一面,无情地撕破她的伪善假面,离开了这个女人。耶苇特精心设计的面具并没有拯救她的命运,只是使她的内心多了一层伪装而已。
也许,面具的真实意义是作为神父惠斯曼的收藏品才得以展现。神父惠斯曼的收藏从传统的非洲雕刻制品,到充满
神性的非洲面具,应有尽有。但令人震惊的是,惠斯曼神父去世之后,那些珍贵的面具收藏便失去了往日的神性,变得破碎不堪。作为对非洲信仰怀有崇敬之情的神职人员,惠斯曼神父一直坚定地维护非洲的宗教,他之所以收集面具,正是为了使非洲的种族信仰得以代代相传。但他不仅在混乱之中残忍地遭到杀害,而且苦心收集的面具也不复存在。如果面具是非洲文化的象征符号,那么神父之死,也使得这些受他保护的文化灰飞烟灭。由此可见,在奈保尔的作品中,其所代表的宗教信仰也是一种虚假的、脱离现实的幻想。它们经不住岁月的涤荡,历史的冲刷。在《河湾》中,面具所包含的意象无论是在殖民时期,抑或在殖民结束时期,都是伪饰和诡计的象征。
对非洲圣母像的崇拜是小说里又一处象征诡计的意象。这个虚构非洲国家的总统希望通过崇拜圣母像的目的,来达到宣传非洲妇女解放的宏大主题。然而,这种崇拜的诡计性正是体现在其与这位“大人物”的紧密联系上。实际上,圣母像的原型就是“大人物”的母亲。当地的居民越来越感到所谓的解放非洲妇女仅仅是空话,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而真正的平等自由也遥遥无期。圣母像的建立只是为了强化“大人物”对这个非洲国家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他不仅在首都建立了庙宇,还在全国各地都兴起了崇拜圣母的热潮。圣母像从首都到其他地区的逐渐扩散,似乎也印证了总统对国家渐渐强化的控制。总统让人们互相以“男公民”、“女公民”称呼对方,却没有做出丝毫有助于改变非洲国家现状的举措。蔓生的崇拜让人们对现实生活产生了幻灭感,从而加重了对“大人物”的虚假印象。
在整篇小说中,“大人物”设想构建的新领地也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总统希望通过建立新领地的方式,让这个刚刚摆脱殖民统治的国家逐步走向现代化。然而,几乎所有新领地的新事物都与总统虚假的特征密不可分。正如卡伦(Cullen)所指出的那样,“‘大人物建立并且管理这个后殖民时期的国家,特别是他苦心在丛林中建立了现代化城市,还希望把丛林中生长的孩子变成学者。这一切都是这个独立后的非洲国家虚假现状的缩影。”“大人物”建立了研究中心和大学城,但并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意图究竟是什么。费尔迪南来到新学校接受教育,渴望学习理工课程,却发现人人都笼罩在“大人物”的阴影之中。他根本没有获得新知,反而对自己的前途产生了一丝隐忧。虚饰的新领地带来的仅仅是空虚和厌倦,并没有为国家的发展起到任何实质性作用。随着新领地的逐步扩张,其内部的种种弊端也暴露出来。书中,奈保尔明显透露出了新领地的最终命运。第一个雨季刚刚过去,那里的许多路边植物都开始腐烂枯萎,似乎也预示着新领地最终会走向腐败,走到尽头。显然,在这片虚假的领地中,人们就像坐在失去指南针的帆船上,生命摇摇欲坠,理想遥遥无期。“大人物”承诺的种种愿望也如同泡沫一般最终破碎。
二、暴力性符号
在《河湾》这部小说里,奈保尔把虚构非洲国家蔓生的暴力描写得淋漓尽致。这不仅表现在小说在故事情节方面设置了大量的杀戮、涂屠的场面,而且在小说中,非洲的热带国家繁多的动植物群落也充满了暴力的象征。而不管是这个国家的本土居民,还是外来的异乡客人,都处于凶残动植物的重重包围之中。
丛林是小说里时常出现的自然景观,代表着潜在的危险,无边的黑暗和最终的绝望,也是滋生暴力之地。萨林姆越是驶向丛林深处,越是感到丛林黑暗的一面在向他袭来。萨林姆以及其他来到非洲内陆的他乡异客是无根的漂泊者,又是无关的局外人。期望在这个国家得到安全的保障其实只是这些人的幻想罢了。事实上,丛林作为黑暗与危险的象征在历代众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体现。根据费博的观点,“木头是自然界的基础,是最基本也是最低等的事物。”费博还表示,“在但丁的《神曲》中,那些自杀身亡的人在地域里遭受了严酷的惩罚,变成了树木。”
在《河湾》中,非洲热带的原始树丛蜿蜒曲折,继而让人无所适从。罗伯(Rob)认为,“丛林是奈保尔形容蛮荒的词汇,这个词与植物毫无关联。”在非洲树丛里,时常有凶猛残忍的热带动物出没,而他们的存在也对人民构成了威胁。萨林姆在树林中觉得自己迷失了方向,失去了自我。他不断地寻找自己的身份,却成为了暴力的无辜受害者,找不到出路何在。当萨林姆夜晚回家时,他感到了月光之下丛林带来的恐怖压力。费博总结道,“月光在文学中与‘多变性,不稳定性和脆弱性有着密切的联系。”。椰在这种不安感的笼罩之下,萨林姆的生活经历了许多波折和变化,而丛林的意象一直都是危险的化身。可以说无论是在殖民时代,还是在独立时期,抑或叛乱时刻,这种危险都从未改变过。
水葫芦是《河湾》中最具特色的暴力象征。之所以这样认为,并不是因为水葫芦的暴力性最强,而是因为这种植物是非洲大陆的特有物种。奈保尔每次都把它与暴力的特征紧密相连。雨季时节,萨林姆在河堤漫步,初识水葫芦,“水葫芦坚韧的枝蔓和叶子纠结在一起,形成厚厚的植被,黏附在河岸上,堵塞了河道。”河道的阻塞,意味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会给人们带来灾难,不同的只是水葫芦的暴力性是“隐型”的,非武力性的,它是以一种渐变的方式实施力量,比一般的那种依靠武器的物质力量实施的暴力更难以抵御。事实上,水葫芦不仅在物质上对当地居民构成威胁,在精神层面,它同样是暴力的体现。这种暴力形式体现它在与小说中的总统,即“大人物”的联系上。水葫芦是新事物,“太人物”的观念则代表的是新思想,表面看来,“大人物”把新思想灌输给了这些非洲民众,但这些观念实际上却充满了危险性与不确定性。水葫芦不仅让萨林姆感到陷入危机,更使整个国家都陷入不安之中,“水葫芦常常让人想起灌木丛林,它永无休止地阻挠着建设文明社会的企图。”
更为明显的是,小说中的其他场景也暗示了水葫芦的暴力特性。当惠斯曼神父惨遭杀害时,“他们把遗体放人一只独木舟,独木舟沿着大河一直漂流,最后被水葫芦缠住,靠在了河岸上。”萨林姆注意到“河上的水葫芦还在,不停地飘游:在叛乱时期,他们诉说着鲜血。”这样把一种非洲的植物与血腥的暴力事件直接联系起来的写法,已经喻示着奈保尔要在它们之间建立一种象征性的内在联系。在小说结尾,萨林姆逃离了这个虚构的非洲国家,而水葫芦也在急流之处到达了它们旅程的终点。对主人公而言,脱离水葫芦的羁绊就意味着逃离这种象征性的暴力威胁。
三、附属性符号
在《河湾》中,表示附属关系的象征性具体体现为人与人的附属关系和人与社会的依存关系。萨林姆和费尔迪南以及萨林姆和墨迪都是典型的主仆式关系。正如奈廷格尔(Night-ingale)所言,“每一种附属关系都是一种束缚的形式。”与之类似,附属关系的象征意象在《河湾》这部后殖民小说中暗示了主人公与其他人物面临的重重困境。小说里的费尔迪南是魔法师扎贝斯之子。他是个穆斯林,来到非洲的内陆小镇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和栖身之地。当萨林姆初次见到费尔迪南
时,就对他的外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男孩身材魁梧,肤色黝黑,面部轮廓也很鲜明。开始,萨林姆认为这是个精力充沛的男孩。不久他便发现,费尔迪南表面看来是个诚恳的孩子,但实际他轻蔑和掩饰的一面有时候会显现出来。似乎二者间的主仆关系并非出自费尔迪南的本身意愿,而是大部分来自其母扎贝斯的愿望。特别是这个男孩常常给人一种佩戴假面的印象,这使得萨林姆与费尔迪南的主仆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种阴影成为了日后两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
萨林姆既是费尔迪南的物质支撑,又是他的精神寄托。依靠萨林姆的资助和供养,费尔迪南才得以进入新领地的文理学院。但没过多久,费尔迪南就偷走了惠斯曼神府的账簿,这让萨林姆感到既震惊,又愤怒。后来,费尔迪南又贸然提出,希望去美国留学,并希望萨林姆可以承担他留学的一切费用。这种想法无疑遭到了萨林姆的坚决反对。他既没有这种义务,也没有足够的财力。费尔迪南正一步步地撕下他的伪装,一步步地破坏本来就脆弱的主仆关系。在小说最后部分,萨林姆不幸入狱,身为当地官员的费尔迪南把他释放,暗示了二人之间的主仆关系其实还是依然存在的。虽然二人的关系在最后得以挽回,但萨林姆已经要离开这个充满混乱和绝望的地方,而费尔迪南也失去了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正如蒂姆(Thieme)所言,“他之前希望成为非洲的百万富翁,但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虚无主义者,觉得每个人‘都要下地狱。”
在《河湾》中,萨林姆与墨迪的关系当属主仆关系的最明显体现。墨迪是个有着一半非洲血统的男孩,曾经在萨林姆位于非洲东海岸的家里成长生活。二者之间的这种主仆关系其实很早以前就确立了,在他们到达非洲内陆国家时更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但是,墨迪并非奴隶身份,两人之间的关系总体上是比较融洽的。早在东海岸共处时期,墨迪就已经享受了一些自由和宽限。来到内陆小镇之后,墨迪在萨林姆开的商店里帮工,以此维持生计。与费尔迪南不同的是,墨迪并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不想成为出人头地的非洲新贵。然而最后时刻,当萨林姆“离开这个世界,并在早前就表示了他的悲观,不安,被动和无根的感觉”时,他独自逃往,把墨迪一个人丢在了内陆小镇,什么也没给他留下,两人的主仆关系也随之瓦解了。
萨林姆与费尔迪南以及墨迪的这种关系是主仆关系的体现,而他们的关系与殖民时期宗主国与被殖民国家的关系存在着很大相似之处。在殖民过程中,随着宗主国影响的日益渗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也越来越对宗主国产生附属的心态。小说中的“大人物”控制非洲国家的一切,他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非洲,建立大学和研究机构。因此,无论是在新领地居住的人民,还是其他城镇的居民,都在他的统治中生存,对他有着强烈的附属感。
雷蒙德是“大人物”从欧洲聘请的历史学专家,专门收集总统的有关信息。雷蒙德小心翼翼地为总统办事,却又担心有一天自己会被辞退,因此表现得忧心忡忡。与雷蒙德有相似心态的还有马赫士与舒芭。马赫士与舒芭是一对来自非洲东海岸的夫妻,两人经营着一家汉堡王。虽然店铺的生意很好,但他们还是会时常关注“大人物”的一举一动,觉得自己的生活完全由他掌控。其他在这个虚构的非洲国度生活的人们同样时刻关注着“大人物”。“大人物”通过向人们许诺美好未来,打造全新非洲的方式,骗取了民众的信任,而这些承诺最后全都化为了泡影。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大人物”的统治欲望和影响也愈加明显。有的西方学者甚至指出了这个“大人物”的原型,“例如,蒙博托,即小说中的‘大人物,以及他的狂热自我崇拜,这种崇拜可以看作是走向‘真实的非洲国有化构想的支柱。然而,这种做法却遭到“大人物”虚假名誉的损毁,并因其无所不在的照片和小说里的政策而得到削弱。”值得一提的是,总统的画像悬挂在这个虚构国家的每个角落,这种铺天盖地式的宣传让非洲民众感到,他们的命运是与总统息息相关。但是,这种附属关系却因总统即将展开的残酷屠杀而变得粉碎。小说中的“大人物”与非洲的人民之间的关系恰当地表明了统治者与被压迫者的联系。殖民过程中,在总统一系列虚假的承诺和欺骗花招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严酷的暴力镇压和征服,这些手段既而导致了被统治人民对“大人物”的附属状态。
在小说里,因达尔是出生于非洲东海岸的学者,他同主人公萨林姆一样,祖籍都是印度。因达尔对自己以前在非洲东海的日子非常厌倦,因此在伦敦生活了长达八年之久。国家独立后,“大人物”请他来到新领地教书,因达尔便与萨林姆再次相见。虽然来到了非洲内陆,但因达尔对伦敦的精神寄托却仍然存在,尽管他在英国的经历充满着痛苦和紧张。在英国大学毕业后,因达尔渴望在伦敦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是,由于他祖籍印度,又在非洲生活,身份复杂,因此在找工作时处处碰壁。因达尔告诉萨林姆,人必须学会“践踏过去”,才能生存下来。尽管他对自己在伦敦的遭遇感到愤愤不平,但他一举一动都流露出了模仿英国人的神态。其实从内心深处,因达尔还是渴望被英国所接纳,成为曾经的宗主国的一名成员。
因达尔这种对英国的精神附属状态在他漫步于伦敦街道时体现得尤为明显。他凝视着街上由海豚和骆驼组成的灯杆装饰,不但觉得这种设计别出心裁,而且觉得他沿途走过的风景是如此的美妙,令人陶醉其中。西方学者麦克劳德(McLeod)认为,“灯杆上的海豚和骆驼装饰体现了伦敦作为殖民的中心地位,这种殖民既是陆地的征服,又是海洋的统领。”因达尔对伦敦的精神附属也体现了他作为曾经宗主国的臣民所表现出的附属状态。
与因达尔对伦敦的精神附属有所不同,萨林姆对河湾小镇的物质附属经历了三个阶段。起初,他对这个内陆小镇并无好感。这里混乱不堪,同时又是蛮荒之地。叛乱时期,无休止的战斗几乎让他的性命都得不到保障。萨林姆作为一个初来乍到的异乡人,不免有漂泊和无根的感觉。而当萨林姆得知自己在东海岸的家乡已经遭到破坏,家人都四散逃离时,他对小镇的感情开始与日俱增。与其他家庭成员相比,萨林姆的境况虽然平平,但至少小镇为他提供了一个栖身之地,而他在小镇经营的商店也是他的生活来源。虽然镇上的生活有些单调乏味,不如新领地的娱乐活动那样丰富多彩,但萨林姆却没有在新领地找到任何归属感。新领地那种矫饰、虚假的感觉让人觉得厌烦,反而是小镇的生活显得更真实些。
但是,萨林姆对小镇的物质附属却随着“大人物”的政策而最终瓦解了。萨林姆渐渐意识到自己虽然可以解决温饱等基本的生计问题,但是他那种无根感和失落感,那种找不到适合自己位置的感觉常常萦绕心头。有时夜深人静,他感到整个世界都对他充满敌意,感到生活没有归属。他们复杂的文化身份像不可逾越的鸿沟,这种隔膜让他们在遥远的他乡没有生存的希望。最后,萨林姆感到他“是个远离自己生活团体的人,在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下拼命挣扎。”因此,主人公萨林姆对河湾小镇的附属关系经历了从陌生,熟悉,再到瓦解的三个阶段。小说中,萨林姆的附属状态可以说是很多人生存状态的缩影。
四、结论
奈保尔是当代无可争辩的文学巨匠。他的作品不仅题材丰富,而且寓意深刻。作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剖析了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现实问题,探讨了殖民统治产生的影响。西方学者波尔(Ball)认为,奈保尔“并不仅仅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位第三世界的记录者和代言人。”在奈保尔的代表作《河湾》这部小说中,他运用了许多象征殖民的意象和符号,以此阐释殖民的过程,以及殖民对非洲大陆造成的后继影响。殖民过程由虚假政策手段开始,渐渐过渡到明目张胆的武装镇压,最后又导致了殖民地国家对宗主国的附属状态。表面看来,小说中获得独立的非洲国家已经完全摆脱了殖民时代的屈辱历史,赢得了走向现代化的契机;但实际上,“大人物”不过是殖民者的另一种体现,其推行的非洲政策并未使这个国家从原始状态中解脱出来。值得注意的是,奈保尔既是称得上是一名无根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多元文化学者。他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敏锐的视角让人们得以从独特的角度,重新审视殖民给非洲大陆带来的种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