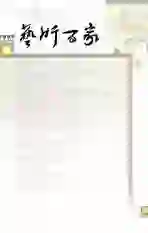从动画《孩子来了》看新“中国式”语境
2010-05-10薛峰
薛 峰
摘要:当今的中国动画面临着构建产业链的巨大压力;除了对于产业模式的探索,真正能使中国动画产生从“量”到“质”的变化的核心内因的是创作观念的革新和发展;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动画创作无论从思想立意、题材选择到“民族性”的具体化呈现都始终难以摆脱上世纪五十年代由“中国学派”构筑于传统绘画基础上的语境——在世界文化快速融合的背景下,通过各种形式的创作实践从而探索一种既有中国人文内核又能充分展现当代中国社会的新的表达语境,这对于中国动画艺术形态是否能更为开放是非常必要的。通过结合学院派作品《孩子来了》的实践和分析,我们进行了一次对新“中国式”语境的探寻。
关键词:语境;语言因素;非语言因素;当代;动画;影视艺术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104(2009)07-0149-04
动画是一种特殊的电影,是在生活基础上提炼出高度假定性的艺术语言,因此不同民族的动画艺术作品都体现出具备各自特点的“语境”。
所谓“语境”,既是指“语言环境”,其中包括了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对于一篇文章来说,上下文、时间、空间、情景、对象、话语前提等与语词使用有关的都是语境因素;而对于动画创作来说,语境并不只是针对某一部作品而言,而是指由群体创作实践所形成的一种体系化的,包括了创作的视角以及具体形态风格表现的创作思路,并具体影响了动画作品中的情境以及各种视听元素,总的来说,是语言因素和非语言因素综合作用形成了语境。
在世界范围内的动画艺术创作中,地域性的风格特征人文情怀愈渐显著——美国动画片夸张奇幻,欧洲动画个性自然、日韩动画成熟独特,各大动画阵营与流派在动画技术取得长足进展的强有力支持下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尽情展现着各自的艺术魅力。
如何构建出一条以艺术创作为基础的支柱型的产业链,这使得当今的中国动画面临着巨大压力;除了产业模式的探索和构建,真正能使中国动画产生从“量”到“质”的变化的核心内因的是创作观念的革新和发展。而产业初创的同时,我国动画高等教育的大力发展使动画创作具备了摆脱商业模式限制并大量进行实验创新的可能性,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高校的师生创作出大量艺术学院动画艺术短片,其质量和水准已日益达到了一线标准——《孩子来了》是一部以学院为依托的动画艺术短片创作实践,除了制作流程的规范化之外,在最初的构思阶段并未过多的考虑到商业性(成本与回收)的细节,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以“艺术”的名义向“商业”对立——目前尚处初建的中国动画产业模式急需大量的艺术创作实践的储备,否则对日本模式或欧美经验进行浅表的照搬套用只能是隔靴搔痒式的“洋务运动”,而《孩子来了》的创作并非只是对一部作品的探索,更是一种对以往的“突破”——这种突破重点在于寻找一种新的视角,一种全新的表达态度。
1面临动画“中国式”的困扰
随着时代的反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曾经以“东方学派”辉煌著称的中国动画在长期的文化干涸期中被积挤压在尴尬的缝隙里,而夹缝中的生存状态在艺术创作观念上束缚和阻碍了中国动画的创新,同时动画制作技术的相对滞后也使中国动画至今仍旧在被动与跟随之中匆忙前行。
《孩子来了》尝试表现出一种相对独特的民族趣味——既能准确的体现出中国的特点又让观众耳目一新,然而如何真正摆脱似乎被定义好的“中国动画”的概念范畴是一个考验。
1.1“强制定位”产生的恶性循环
世界认知中国动画,从传统风格的美术片《大闹天宫》正式开始,这标志着由此“中国学派”诞生。时过境迁,如今面对着上世纪末我国动画发展减缓造成的局面,我们主动地把重新寻回光荣的希望大大的寄托在了“走民族道路”的努力上,从而逐渐形成了一定意义上的“强迫症”。
结果是由两个方面造成的:一个是我国的动画创作者希望走出国门的迫切性、一个是国际上对中国的片面认知。
自八十年代开始中国出现了一批充分展现传统题材和元素的电影作品,如《霸王别姬》、《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等等的在世界影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更加充实了动画创作的信心,这主要反映在大量传统题材的选拍和传统美术风格方面的尝试。其中最具备代表性的电影作品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宝莲灯》,该片是我国将动画电影创作与国际接轨的首次尝试,而其他的影视动画、各类短片或相关创作也都纷纷希望能像电影取得的成功一样走“国际包围国内”的路线,希望以画面的“中国式”弥补甚至是规避编剧及导演叙事方面的不足,结果逐渐暴露出风格单一、内容空洞、观众定位模糊的总体缺陷。
同时,以上情况又直接加剧了国际评价对中国动画作品的狭隘理解,以进入国际交流最多的动画短片创作来说,历年来得以获得入围正式参赛的几乎都困死在“水墨动画”的小小圈子里,如三维动画渲染水墨效果的《夏》或以三维完全模拟皮影戏效果的《桃花源记》等展示。虽然偶有获国际奖项,但可以说并未对我国的动画带来真正的突破。
于是,一方面很多创作者为迎合“国际认可”逐渐钻入一种“民族样式”的死胡同;另一方面这又加剧了国际上对“中国学派”的狭隘片面认识,双方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这使得一些尝试创造新规则的作品面世承受了更大的考验。
1.2现代生活与传统表现的错位
水墨动画曾经是中国动画艺术界的不传之密,主要特点是突破了以往动画“单线平涂”的形式,运用渲染发挥墨色浓淡和虚实的效果来描绘对象——这是动画史上一次由技法性创新所带来的艺术革命。
然而任何一种艺术的表现形式和技法的确认都不能脱离内容而存在,时代的飞速发展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的融合,当代中国社会中人们的生活从价值观念到生活节奏都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画强调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这种表现技法在一些神话或古典题材的动画表现上是恰如其氛的,但对于现代元素的题材则无法完全从容掌控。
正如“新诗派”的先行者黄遵宪为倡导白话文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的口号一样,为了摆脱传统题材带来的限制,《孩子来了》将创作起点定在了关于“生育”的题材上——城市的人口控制现在已经成为规律性的行为,但是在中国的新农村,生个儿子延续香火的观念还是根深蒂固。对于新农村年轻的新婚夫妇来说,他们接受过现代社会的教育,过着富足安定的生活,但是长期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对于这一问题未免也有些难以抉择,这最终成为了他们焦虑的选择题。在这样的情境之下就会发生很多有趣的故事。
生个孩子,是动画片的题目,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家庭的题目,也许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群会有不同的困扰和选择,但一定是可以互相理解、感同身受、和平等的,这为作品在形式表达和主题方面都能找到全新的切入点赢得了有利的条件。
2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的促进了动画创作新语境的形成
范迪安先生曾提到,无论何种艺术形式所反映和表现的
都是现代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心理特征,作品最终丰富了人们的审美经验,并开拓了艺术的视觉表现——当代是什么?就是今天。而今天中国社会的特点是什么?就是非常快速的变化。
将动画与以变化为特征的当代主题结合在一起,寻找到一种新的动画创作形式,力求能捕捉到其中某一特殊状态并表现变化中特有不同文化的碰撞、新旧观念的碰撞、各类视听元素的碰撞等等——这种表达形式事实上就是一种新的“语境”。
其中各种时代性的题材及相关视听元素即是这一语境中的“语言因素”;而作品创作的立场、态度及相关的思想情感则是该语境中的“非语言因素”。而快速的社会发展及产生的多样性的结果则促进了这两大因素的形成。
2.1社会结构的时代性变化构成了新语境的语言因素;
《孩子来了》所反映的是时代性的人和事,具有着我国现今特定的发展阶段所特有的典型性。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当代的中国正面临着全新的社会变迁与人口迁移格局——为了创造与都市社会结构变迁及都市化进程相适应的、与现代市场经济关系相适应的“都市性结构农业经济的模式”,我国的传统都市化的模式与农业发展理论正面临全新挑战,其中最为显著的特点是:“乡村人”正在向“都市人”转化——这正构成了“新语境”的语言因素。
2.1.1动画语境的视听形象的“当代主义”
由于经济上的相对滞后,在西北地区旧的文化习俗传统仍然得到相对完整的传承,作为黄河文化的发源地,以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电影多将目光投向了“黄土地”的闭塞与陈旧从而对民族性进行不同视角的拷问和反思——《孩子来了》的故事就定位在今天中国的西北高原,画面空间主要由包括角色、道具、场景及音乐等在内的一系列西北风情的视听造型构建而成。
首先在视觉形象方面,角色造型风格方面吸收了中国主流当代派油画风格,从形式上突破了以往中国以传统古典的元素的标准总体定位将写实与动画的变形夸张相结合,从而设计出带有“城乡结合”的特点,又具备动画特有趣味的视觉形象。(如图:1)
1、在传统造型符号的基础上新元素的细节化表现。
片中角色造型总体上只保留了能体现西北人物耿直、憨厚以及与生育暗示相关的“符号式”体形态比例,其余则被赋予了更多“当代”的特性。以承担主角的夫妇为例,男主角梳着小分头,穿着还留着折痕的新衬衣,打着领带,具有乡土气的现代感是中国新农村农民造型的典型提炼;而女主角身体肥硕,烫着时髦的“大波浪”,丰润的脸庞,饱满的红唇,符合中国面相的“相夫益子相”,和丈夫的形象相得益彰,造型风格统一,都属于宽厚、圆润的造型体系。
也许一开始,很多人觉得造型风格挺“怪”或“土”,但回首以往那些已被我们接承认的“造型模式”:挎刀的“新佑卫门”、背书包的“没头脑和不高兴”、穿水手服的“大力水手”……无一不是从真实生活中提炼和捕捉出来的——正如著名导演贾樟柯所说的,除了被理想化处理的形式以外,电影也可以表现出一种真实的生活秩序;事实上,正是这种对于细节的捕捉最能让人感受到真实生活的气息,这样动画里的角色才能成为血肉丰满的当代生活化形象。
此外,相关的道具如片中的拖拉机则是采取了“新瓶装旧酒”的手法,将一辆非常现代的拖拉机变为新婚夫妻进城逛街的“坐驾”,而四周窗户上贴满了鲜红喜庆的传统剪纸更用现代混搭的手段喜剧化的呈现了传统文化变革中的现代社会缩影。
2、不同动画形式表达特征的融合。
所谓不同形式表达特征的融合,主要是指在电脑三维动画中表现出更多的手工绘画的艺术特点。
《孩子来了》主要由三维技术制作完成的,在对各种造型的质感和色彩处理方面,作品努力创造出一种糅合了真实质感以及油画笔触的厚重效果,这与中国北部高原特有的风土人情有很好的协调性;并在整体的画面色调控制上采取了分层渲染后期合成的技术,以便在整体的画面控制方面强调3D真实效果上的绘画主观性,同时,本作品在粗壮厚实的模型骨骼设置中加入了一些强调柔软、弹性的控制件,追求一种只有中国北方泥塑所特有的“灵动的笨拙”,这是一次新旧技术表现的融合。
如在造型的材质处理时,刻意的在模拟真实光影关系的基础上加强了色彩的冷暖关系和手绘笔触的效果;而在设计制作大面积的黄土高原场景时在“全局光”的效果模拟的前提下更强调了色彩的指向性作用,颠覆和突破以往人们对黄土高原“干旱、贫瘠、古老”的程式化理解,而是着重展现出一片充满生机的绿色梯田,辽阔起伏的平原,巍峨壮美的山脉,这些自然环境都给故事的发展营造出了自然和谐的、轻松的、时代气息的气氛和情景。
其次,在音效和音乐的处理上,片中的音乐风格以陕北民歌的基础上结合了大量的时尚元素,主要以诸如竹笛、三弦等民族乐器塑造不同角色的形象,而各段落的情节则以不同类型的短促音型构成,特别是贯穿首尾的主体曲则汇集了诸如民谣、唢呐、电子MIDI效果,给观众从以听觉造型的手段上营造出了一个节奏明快的故事空间。
2.1.2角色表演趣味的夸张与生活化
动画是运动的艺术,所有的造型设计都以运动形式的结果得以进行展现。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指角色的表演风格——生活化与夸张的充分结合。
事实上,表演的夸张是有多种形式的,而夸张的程度与动画造型的风格基本相互呼应;而在《孩子来了》中,表演的夸张的程度则大大超出了造型方面的夸张程度——主题的写实性和造型质感、光影的写实与角色的“超常发挥”形成了一种特有的“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效果。
这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
首先在情绪表达方面,将两个农民夫妇的情绪完全外在化——这里完全摆脱了“中国式”文化中特有含蓄风格的限制,而是吸收了更多的“PIXAR”(美国著名三维动画公司)动画作品的表达方式,片中的对白较少,主要以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完成情节的衔接和发展,诸如喜、怒、哀、乐、无奈等情绪的符号化表达基本借鉴了美国动画的经验:强调常规的叙事表达的准确性并在以极至夸张表现的手段突出重点情节。
其次,充分发挥了动画艺术的高假定性,在表演内容设计上突破了角色的年龄及能力上界限,如仅有四岁大小的“小胖子”基本完成了八岁孩子才能做到的劈闪腾挪;而新娘则在一声怒吼中单臂抓住弱小的树干将拖拉机甩回了安全地带等。
再次,强调了一些常规动画中不常出现的生活化细节,诸如胖新娘带有“性暗示”作用的努嘴、扭动躯体;小男孩儿和姐姐的大鼻涕泡,不经意的挠痒等等都使角色的表演充满了一种该片特有的动画情趣和勃勃生机。
2.2多元文化观念的共存成为新语境的非语言因素
世界正在变成“地球村”,文化的融合正在各种交通、咨询技术的飞速发展下逐渐加强。一方面,原来的区域性的文化特征呈现出逐渐消退的现象;而另一方面不同文化的碰撞则带来了更多元化的评价标准和审视视角。这些都满足了动画创作新的“中国式”语境中非语言因素的条件。
2.2.1不同观念的碰撞是新题材发掘的良好契机
简单的讲,学会发掘良好的题材就是学会捕捉有典型意义的矛盾,而矛盾来自于不同观念的碰撞。
首先,是横向的碰撞。事实上动画短片中的“时代性”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来自不同文化观念的碰撞。无论我国实行了多年的人口政策也好,还是“越生越穷”与“子孙满堂”这一中国现代社会的矛盾命题也罢,都只是问题的表象,关键是由中国由农业大国向现代化国家转型而产生的横向文化冲击,现代物质生活的基础促成了西方价值观影响力的扩大,而普通农民在“多子多福”的家族幸福观到务实的个人商业生活价值观之间则表现出了特有的“时代性”的困扰。
其次,是纵向产生的观念碰撞,重要是指新旧观念,世界范围的文化融合同样加速了同一区域的文化演化和变异,这最终也反映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总的来说,《孩子来了》中展现的关于传统家庭传承观念的题材是具备了以上所述的双重性的。作品之所以立足这一题材主要是一种“以小见大”的动机,将目光聚焦在能完全掌控的微小事件上并能实现更深远的创作意义——这正是由社会快速发展带来的良好契机。
2.2.2文化融合为动画短片创作提供了更多角度的创作基调。
观念的碰撞属于文化融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使我们得以在针对同一题材的不同评价标准之间快速转换并不断获得新的认识和立场。动画短片的创作有着异常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横看成岭侧成峰”,动画的创作可以从不同的技术呈现,如手绘的、CG的、材料的;不同的表达方式,如强调情节性或实验性;不同的传播方式如传统媒体或新媒体、播放还是互动等等。
在《孩子来了》创作中,我们确立了基调:积极的生活态度、平和的叙事情绪、单纯地讲述、表现,不批判,不妄下结论。我们对这个现象的关注并没有任何的主观倾向,我们只是纯粹地想在这个现状之下讲述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当代的中国动画是一种脱离于外化的传统样式的、具备中国当代社会特有的文化精神内涵及世界属性的艺术形态,是一种新的动画语言组成方式,而看似复杂而难以捉摸的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正成全了动画创作新语境建立的可能性。
3探索全新的动画艺术语境是真正意义上的继承和发展
总体上来说,寻找和建立一种全新的“中国式”语境包括了由动画创作观念开始到技术实施以及最终结果呈现各个环节,是一种建立在传统观念基础上的继承和发展而非颠覆重建。
首先,如果脱离了传承那么成功的“原创”便无从谈起。在我们将更多目光投向身边的人和事、表现“今天”的喜怒哀乐、柴米油盐之余必须使作品始终保持着中国特有的精神文化内核: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各种新的观念和题材表达中立足于我们自身的评价标准或赞同、或批判、或怀疑或无奈或讽刺,从而使自身作品产生独有的典型性。
正如《孩子来了》中的主体表现无论评判态度如何,却始终是真正中国人才会有的故事,在动画表达中从外在形态、行为习惯切入重点表现出了中国人从容豁达的生活态度以及对生命繁衍生生不息充满希望的中国人的精神特征。
另一方面,将中国动画的创作放人新的语境之中,使作品无论元素还是审美趣味都具备了现代社会的共同性以及中国当代所特有的个性,从而使中国动画的作品艺术具备了更广泛意义上向世界开放的形态。
因此,寻找到一种新的并能背现代社会普遍接受的“中国式”语境对于中国动画重新确立国际话语权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事实上,置身于今天的文化环境,作品就必然反映出特定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创作者对于“当代”存在不同方式的理解——学院动画短片《孩子来了》正是一次以探索为目的创作实践,而倘若更多的人和思想加入到这种实践和论证中来,那就是真正中国动画之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