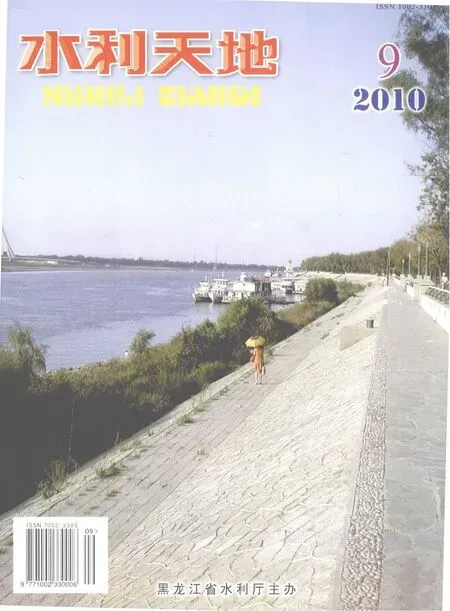泥石流频发的背后
2010-04-14陆相辉魏莉莉冯建维
□ 陆相辉 魏莉莉 冯建维
泥石流频发的背后
□ 陆相辉 魏莉莉 冯建维
随着2010年泥石流在多地发生,和国土资源部关于2010年上半年地质灾害10倍于去年同期信息的发布,尤其是甘肃舟曲泥石流致1 000多人死亡的惨状,泥石流成为我国2010年最主要的灾害。于是,关于泥石流成因的文章大量出现,极端气候说、地震余害说、植被破坏说等不一而足。
从巴基斯坦的洪灾到俄罗斯热浪,极端气候确实在2010年频发。对于地震余害说,2008年5·12地震的震中汶川,距离甘肃舟曲200多公里,当时舟曲也是地震的重灾区,因此其地质结构受震后相对松散,遇洪水易发生泥石流是必然的。随后的2010年8月13日,汶川也因降雨发生了多处泥石流。这进一步支持了地震余害说。但地震余害说不能解释全国从南到北更多地方没有发生地震的地区也发生了泥石流。于是植被破坏说开始登场,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当属著名林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沈国舫。
在林学和水土保持方面造诣颇深的沈国舫先生,多年来一直强调洪水和水土保持的关系,尤其是森林能涵养水源,水多能吸水、水少能吐水,还能消减雨水的冲刷力。
根据我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对黑龙江省伊春市的调查和当地的观测,在原始红松林地区降一场50毫米的暴雨,茂密的红松林树冠就可蓄住一半(约25毫米)的水量,原始森林中地表松软的腐殖层,还可蓄住落地雨水的一半(约12毫米) 的水量。因此,降在原始红松林中的暴雨,当天流出森林的,只有约四分之一的雨量。剩余的雨水形成所谓“控山水”,这些缓慢流出森林的控山水,是保证下游河流不断流的水源。
因此,良好的植被不仅可以减少暴雨成灾,还可以保证下游河流不断流。至于良好的植被可以减轻水力对地表的冲刷,进而减少泥石流的产生,则是不言而喻的。这些,就是1998年长江、松花江和嫩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后,中央政府在沈国舫等人的呼吁下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直接原因。
近年来风靡全国的橡胶坝,是为了解决上游森林破坏后,下游河流变成季节河的难题。在解放前号称陇上江南的甘肃舟曲,曾孕育过举世闻名的原始森林。而长期关注森林与泥石流关系的黑龙江省的老一辈们,早已把松花江哈尔滨段的长期枯水归咎于1964年修通加格达奇的铁路后对大兴安岭的开发,和1948年对小兴安岭的开发,这些开发的初期其实就是对森林的只砍不种。
那么为什么要只砍不种?中国水土保持、中国林业究竟有着什么的致命伤?是什么原因不断地诱发旱季河流断流、雨季洪水泛滥后的泥石流频发?
1950年代至1980年代对大小兴安岭林木的采伐,可能是当代人最野蛮的采伐。由于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我国还不懂得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和可持续发展。到了八十年代末,当时任省委书记孙维本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发出了大小兴安岭已基本无林可采时,政府才开始研究林业的资源危机、经济危困。而在这之前的几十年里,发达国家由于大部分林权早已明晰地归个人,因此,他们在伐树时要连根拔起,以免不易腐烂的树根影响迹地更新即重新种树,拔起后还要补种。
事实上,中国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学习前苏联的皆伐,和对天然林的全面禁伐都是在走极端。过熟林采伐是所有成熟国家的普遍做法,否则等到树木枯朽了对人类又有何用?只是要研究、找到人类合理利用资源的平衡点,以利于保护环境并永续利用资源。
然而,直到今天,中国的伐树有把树根清除掉以利于迹地更新的吗?不把树根清除掉新的树木能正常生长吗?然而,天然林全面禁伐,客观上使林农民、森工企业及其职工只能看着过熟林枯朽,靠林为生的人只能变通采伐天然林的各种手段。
为什么国有森工企业和农民都不愿意造林?我们经过多年的调查了解后得知:其原因一是林权,二是限量审批。
中国的产权改革制度设计者,出于相信有任期的政府,不相信“有恒产者有恒心”的自然人——即政府会保护资源、自然人会破坏资源的传统思维,和需要部分改革产权来解放生产力,如农业的联产承包制的思考。而设计出的产权改革,都不顾“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常识,只肯给被改革者部分产权或称半吊子产权,使中国的林权制度改革只给自然人以部分的经营权、收益权、处置权,距离完全的产权还缺少抵押权和买卖权,更缺少自主采伐过熟林的权利。而且,设置林地的承包年限为70年,也与完整的所有权相悖。
更重要的是,被媒体热议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与其说是从2003年才开始的“迟到的改革”(比农地改革晚20年),不如说它是“被逼出来的改革”。因为在此前20年,发生了一些强势集团利用产权模糊、司法不公等公然抢夺、逼迫农民出让林地,在农民多年种树心血付诸东流案件频发的背后,不仅是林权矛盾此起彼伏,更有林农和林业职工对“谁造谁有”政策的怀疑。在这里,模糊的产权是各种林权纠纷的根源。
因此,二十几年的林权矛盾多发后才搞林权制度改革,绝对属亡羊补牢,更何况这种补牢还远没到位。
另外,为什么林业承包没能与土地承包同步进行呢?相关的文献显示:当时顾虑的主要原因,是怕农民乱砍乱伐。所以农村承包制的同时就没有进行林权制度的改革。但二十多年后我们看清了究竟是谁在破坏林地?大小兴安岭距离木材销售区上千公里,没有林业部门核发的采伐证、准运证,谁能越过重重检查在木材销售区卖掉林木呢?不相信自然人“有恒产会保护资源”的背后,是什么原因在作祟?
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化,我们逐步认识到:不把林权交给自然人,中国就是365年天天都是植树节,也解决不了年年造林不见林的问题。
中国这种半计划、半市场的模糊产权改革,造成人们普遍没有长远打算,只有短期行为。而这种短期行为对资源的竭泽而渔,对环境的破坏比比皆是。
但就是这种模糊的林权改革,也仅仅在集体林地内进行。国有林权改革仍旧是雾里看花,阻力巨大。在此我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问:雷声大、雨点小的伊春国有林权改革为什么停滞不前?泥石流多发后上千条的鲜活生命换不来深层次的思考和警醒吗?
关于限量审批,我国制定的《森林法》规定了森林采伐限额制度,试图通过控制森林采伐总量来遏制森林滥伐现象。但这种“试图”,不仅没有遏制森林滥伐,有资料显示:有的县(市)和森工企业局超限额采伐高达150%。据调查,某些林区报表上的林地面积,最高的已有三分之一甚至更高的已变成耕地。因此,中国的林业普查有必要引入与林业没有关联的独立第三方重新核实。全国遥感照片中增加的耕地面积,有多少是林业开荒?另外,还有必要核实林业山上开荒对山下水土流失的危害,这已经十分严重了。
更为可怕的是:森林采伐限额制度反而遏制了那些守法自然人的造林热情。过熟林能不能办下来采伐手续?怎样才能办理采伐证?种种激烈的投诉正在打击自然人的造林热情!
即便如此,我们仍旧对沈国舫先生的下列观点高度认同:“水土流失最严重的表现形式就是泥石流,高强度的水流连泥带石,冲击力非常大,破坏性强。但如果那个地方植被比较好,树根扎下去了,就能固定住,水不容易下来,下来也不容易带走土,能起到一定的防护作用。因而滑坡、泥石流的形成是有一定条件的,是可以预防的。”
因此,我们希望更多的林业人士,其科研活动不应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还应向社会科学拓展,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的预防、减少直至消除泥石流。
2005年9月,由中科院、中国工程院与水利部共同组织的“中国黑土区水土流失与生态安全综合科学考察组”,经过在内蒙和黑龙江的几天调研考察后,在哈尔滨市召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笔者曾就农地、林地产权与水土保持之间的关系,做了专题发言。发言中痛批了中国农民种地不养地的根源是没有产权。照此推理,我们仍旧可以负责任地说:林农和森工企业砍林不造林的根源也是没有林权。因此我们在会上强调:从事涉农、涉林和涉水科学研究的专家们,一定要走出“为了完成项目而科研,为了争取资金而科研,为了研究生毕业论文而科研和为了晋职称而科研”的怪圈,用自己苦练出来的“功夫”,扎扎实实地为中国的涉农、涉林和涉水事业做出贡献。以水土保持科研为例,50多年的水土保持科研,我们已经有了相对成熟的治坡、治沟和防治水蚀、风蚀及冻融侵蚀的技术。但这些技术,又有多少走下了学者的书架,成为活生生的现实?
综上所述,中国从制度上控制泥石流灾害,要从改革林权和限量审批始。至于十分了解林业的沈国舫先生所言:“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造成的伤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愈合的。”其实也与几千年战乱不断带来的产权不断转移,使“有恒产者没恒心”有关。
未来的涉林改革,决不能再给自然人以模糊产权或是不完全产权,决不能再给政府和行业管理部门预留寻租的空间。目前,中国的各项产权改革,到了一定要一步到位。
(作者单位:黑龙江省绥滨农场水务局 156203;黑龙江省农垦水利工程建设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50040;黑龙江省水利宣传中心 15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