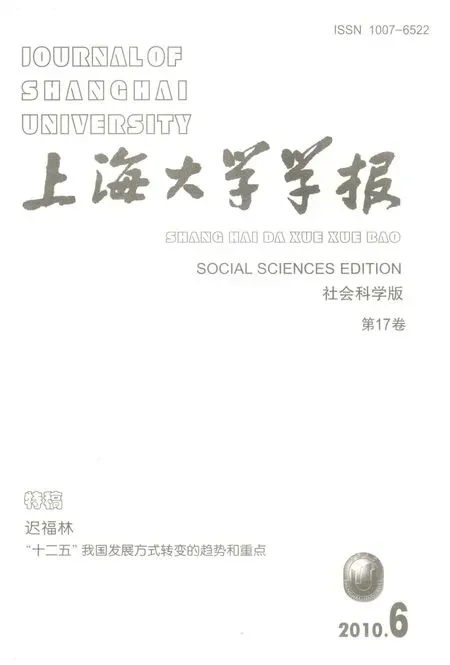图像性的减弱: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2010-04-13刘奕
刘 奕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图像性的减弱:汉代咏史诗的一种解读
刘 奕
(上海大学 文学院,上海 200444)
咏史诗从班固到建安诗人,表现出一种图像性减弱和个体情志增强的趋势。班固的咏史诗的特性从正面看是具有较强的图像性。从历史记载来看,缇萦故事很可能是班固经常见到的画像故事,他的诗歌当与之有较强对应关系。到了阮瑀与王粲的咏史诗中,情节的概述似乎不那么被看重,图像性减弱的同时,诗人的情志被凸显。这种倾向在曹植《三良》诗中有最充分的表现,显示出建安时期,咏史诗向抒情诗靠拢的倾向。
咏史诗;图像性;个体情志
诗至建安,壮采奇情勃然而发,这是后人的普遍看法;咏史诗也自不例外,学者对此撰述已夥。笔者不揣浅陋,愿尝试从图像性这一角度,对班固与建安咏史诗的差异略作分析,以见其流变之迹。一得之愚,望方家见教。
一
班固的《咏史诗》是古今首标“咏史”之作,钟嵘《诗品序》称“班固《咏史》,质木无文”,遂为后世定评。所谓“无文”,大概是就其文采、文辞而言,但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作为五言诗,班诗在技巧上已经比较成熟。清人何焯论张协《咏史诗》云:“咏史者不过美其事而咏叹之,隐括本传,不加藻饰,此正体也。太冲多抒胸臆,乃又其变。”[1]893据何焯的概括,这种咏史正体的特征是:(1)“美其事”,发于颂赞;(2)“隐括本传”,概述史事;(3)“不加藻饰”,即无过多发挥。如此则班固《咏史》正是当之无愧的“正体咏史”之祖。从奠定后世咏史诗体制的角度而论,也不能不承认班固诗歌的成熟吧。
只是后人论咏史诗,往往强调班固与左思之异在于抒情性之有无,其持论是以左思为正而从反面审视班固。如果正面考察班固《咏史》,那么其特征是什么?从班诗到左诗,又是如何流变的?
细读班固《咏史》,可觉其叙事与绘画有一种较为明显的对应关系,因而呈现出较强的图像性,仿佛是借诗歌的形式来描述画图的故事。先来看班诗:
三王德弥薄,惟后用肉刑。太苍令有罪,就递长安城。自恨身无子,困急独茕茕。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圣汉孝文帝,恻然感至情。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2]170
首二句写历史背景,①按,首二句实寓赞于述,盖三代以后始有肉刑,则汉文帝废除之,即是德跻三代,这也是班固技巧成熟的例证吧。末二句感叹,中间则是对故事的叙述。而叙事又明显刻画了两个场景,其一是淳于意就逮时的恨骂与缇萦的立志救父,其二则是缇萦伏阙上书的场面。如果对照史书,可看出这里的隐括与历史记载各有侧重。缇萦的故事在当时一定是一件让人啧啧称叹的传奇,太史公在《孝文本纪》和《扁鹊仓公列传》两处都详细记载了此事,后来刘向又将缇萦故事收入所编《列女传》中。②按,缇萦故事在今本《古列女传》卷六《辩通传》内。据《四库提要》,刘向《列女传》流传中有后人增添窜乱的成分,只有传后有颂的篇什才是刘向原文,故四库馆臣将这部分原文编成《古列女传》。可知缇萦故事大致可定为刘向原作。稍不同者,《孝文本纪》中既收缇萦所上之书,又载文帝废肉刑诏,《仓公传》中则无诏书而已;刘向所述则一依《孝文本纪》。今节录《史记·孝文本纪》中文字以资比较:
齐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徙系长安。太仓公无男,有女五人。太仓公将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有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乃下诏[3]427
上书与诏书文长不录。可以看出,诗中淳于意被逮时的场景来自《史记》的记载,而班固着力刻画的另一场景,即“上书诣阙下,思古歌鸡鸣。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在《史记》中则仅“上书”二字而已。司马迁看重的是上书与诏书之文,这既是史家实录之本职,也由此表现其褒奖颂美的道德评判。班固诗歌则既是叙事,又像在用诗歌文字描述两个场景、两幅图画,不妨称之为“绘史”。
诗与史的不同,固可以用文体有异解释,但班固何尝不能隐括缇萦上书语入诗呢?试加入“言身愿入官,赎父罪与刑”两句于“思古歌鸡鸣”之后,未尝不可,但班固没有,益可见班诗并非对《史记》、《列女传》文字的直接隐括。由二者的不同,不妨大胆设想,班固写诗时也许还有其他依据,即当时流行的列女图的屏风画或壁画吧。若将缇萦故事绘图,那么可以入画的该是那些场景呢?显然只有淳于意被捕时回身骂女、缇萦与父同行和缇萦伏阙陈情三个场景比较适合表现,而尤以一、三场景最能概括表现故事的内容,并表现其中的戏剧性与紧张感。至于上书与诏书内容是无法在画图中表现的。看来,班固诗与设想中存在的绘画的对应关系要远比史书记载更为密切。
那么以缇萦故事为内容的绘画是否真实存在过呢?答案也许是肯定的。根据传世典籍的记载可知,西汉宫廷即多壁画与屏风画,其宫中有由专人执掌的画室。清代学者周寿昌进一步指出,除了专门画室之外,“汉宫殿皆有图画也”。[4]1298①见王先谦撰《汉书补注》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磾传》中“光闻之,止画室中不入”句后注,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 1298页。按,霍光所止之画室,如淳以为是“近臣所止计画之室”,颜师古同意另一种说法,即“彫画之室”。奕按,《汉书·霍光传》中有武帝“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之事,可知省内自有专职画师。司马彪《续汉书·百官志》中有“画室署长”一职,为宦者之官,管理画室自亦当管理画者,此职虽见于后汉,当有所因。似当以师古是而如淳非。而周寿昌则进一步据《汉书·杨敞传》中杨敞观西阁壁画的记载,指画室即殿前西阁。又引蔡质《汉官典职》、卢硕《画谏》为证,指出汉代各宫殿皆有壁画。杨敞为西汉人,蔡质东汉人,卢硕唐人,所见、所闻、所传闻皆备,周说当不误。所画内容,主要是“古帝王”、“古烈士”之类,且富于故事性。如汉武帝去世前曾“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 (霍)光”,[4]1297这是以昭帝相嘱托之意。而班固的伯祖班伯曾亲见汉成帝的屏风上画着纣王与妲己长夜醉饮的场景,成帝且以之问班伯,此画劝诫的意义何在。[4]1735由此可知,这个屏风不是成帝命人绘制,而是前代遗留之物,所以成帝不太清楚其中的深意。正可见绘古帝王事以为劝诫是汉室一贯的传统。又成帝妃子班婕妤也自称她所看到的古图画上“圣贤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也是其证明。[4]1668
除此以外,列女故事同样也是汉人常用的绘画题材。刘向因为成帝宠幸赵飞燕诸人,“以为王教由内急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 ,以戒天子 ”。[4]948据刘向《别录 》所载 ,书成之后,列女故事又被“画之于屏风四堵”,[5]337放置宫廷之中。这是史料首载的《列女图》系统绘制之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同时成帝的妃子班婕妤,在其《自悼赋》中也有“陈女图以镜监”之语。[5]186班婕妤赋中自述观看《列女图》是在恩宠未衰之时,也即赵飞燕等专宠之前,那么她所看的《列女图》当成于刘向编定《列女传》之前,可能反映了这一绘画题材在汉代自有其渊源,并不待刘向而后起。②同样说明列女图画源远流长的证据是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王氏在这座岿然独存的西汉早期宫殿中,看到了绘有“烈士贞女”图像的壁画。见《文选》卷十一。[6]171到了东汉,列女画像同样被广泛描绘,光武帝即曾以新制列女图屏风围于御座之后,结果在接见朝臣时忍不住频频回顾而遭到宰相宋弘的批评。[7]904在宫廷以外,列女故事也越来越多地被人们以各种图像方式加以表现应用。顺帝的梁皇后入宫前即“常以列女图画置于左右以自监戒 ”。[7]438
遗憾的是,今天这些绘满帝王、列女的壁画、屏风画和卷帛画都已不复存在。但现存汉代画像石 (砖)、铜镜等竹箧文物上仍能看到不少列女故事画。不过,其中是否有“缇萦救父”的画像,因为缺少榜题作为直接证据,尚不敢确切肯定。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员杨爱国先生曾将山东嘉祥武氏祠的一幅画像石命名为“缇萦救父和七女为父报仇的故事”,而此前学者一般以之为“水陆攻战图”。该图分上下两层,占据绝大部分空间的下层即一般以为“水陆攻战”的内容;上层为车马行列,图的“右边一妇女席地而坐,周围有执兵器的男子和另一辆无盖的马车”,马车上则有一男子回身向女子伸手。[8]下层的攻战图经苏兆庆、刘云涛、王思礼、杨爱国、邢义田等多位先生考证,可基本确定为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故事。[9]那么,与之存在紧密关系的上层图像也应该是一个与孝女有关的故事。看看那四围手执兵器的男子,那独坐的女子,那无车盖的车上回身伸手的男子,遍检《列女传》,具有类似场景的故事只有“缇萦救父”了,因此杨爱国先生的命名颇为合理。反过来,这一画像也证明前文的设想,即淳于意就逮时的场景适合入画。
只是即使上面的推测成立,仍然不得不承认,缇萦故事在今存汉画中比较罕见。试究其原因,今存汉代画像石 (砖)一般是普通贵族、官员祠堂、墓室的遗物,在有限的空间上,要表现从神仙、幽冥世界到尘世生活的方方面面,任何一部分内容都只能根据需要加以精选。汉代尤其是东汉社会,妇女对丈夫的贞和对夫家的义被看作一般女子最重要的道德规范,与之相关的列女故事则是妇女的行动指南,它们自然成为画像石(砖)最热衷表现的题材。著名的武梁祠画像石上的列女故事集中在《列女传》“贞顺”、“节义”两类,可为例证。对此巫鸿先生在其大著《武梁祠》中有充分说明。[10]187-196,271-286而缇萦的故事在《列女传》中被置于“辩通”类,且她所体现的对父亲的孝顺显然不是夫家对女子的首要要求,因而不容易在画像石 (砖)上被绘制,这是可以理解的。相对的,宫廷中有足够的空间与大量的装饰需要,可以将《列女图》比较系统的加以绘制,以“缇萦救父”的知名度而论,其被绘制是可以想见的。若承认武氏祠画像的确是“缇萦救父图”,那么宫廷中存在这个画像的推想就更加可以接受。
幸运的是除了杨爱国先生检出的这一材料外,另有一时代稍晚的证据。曹植曾于魏文帝黄初中作新乐府《精微篇》,其中也提到缇萦的故事,称“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图》”。[11]332可知曹植是亲眼见到过缇萦故事的图画的,这是宫廷绘画以缇萦救父为题材的直接证据。我们依据上述材料推论班固时代已存在这一内容的图画,当离实事不远。
而班固与这些宫廷《列女图》又是否存在密切关系呢?似可确认其有。直接记载见诸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其书卷三“叙古之秘画珍图”中记载《汉明帝画宫图》一种,且自注曰:“五十卷。第一起庖犧五十杂画赞。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诏博洽之士班固、贾逵辈取诸经史事,命尚方画工图画,谓之画赞。至陈思王为之赞传。”[12]77-78按,汉明帝“雅好画图,别立画官”之说不见于正式记载,但从有关文献所透露的蛛丝马迹看,这可能是时人所习知之事。命人在南宫云台之上图画中兴二十八将的正是明帝。[7]789又今存曹植《画赞序》,唯记明帝与马皇后观画事。[11]67凡此皆可见明帝确实喜好画图,张彦远所述当有一定根据。张氏又称班固、贾逵直接参预了宫廷画图内容的选定工作。其图既自伏羲起始,又依据经史,正是前汉古绘帝王、古烈士的传统;又光武帝有列女图屏风,则明帝图中当亦有列女图。班固长于史,列女故事的选定必经其之手。又考《后汉书》,班固于明帝永平中先除兰台令史,后迁为郎,典校秘书[7]1334而贾逵亦于永平十七年 (74)“拜为郎,与班固并校秘书”。[7]1235班、贾两人确曾共事于明帝,时间当即永平十七、十八年。则两人确有共同为明帝选画的可能。
稍有疑问的是,据《后汉书·明帝纪》,明帝于永平三年 (60)“起北宫及诸官府”,至永平七年 (64)北宫成。[7]107,111①又班固《东都赋》也称明帝“增周旧,修洛邑……于是皇城之内,宫室光明,阙庭神丽。奢不可踰,俭不能侈”,可想见其时宫殿修建规模。《文选》卷一。[6]32此外张衡《东京赋》对明帝修建宫殿的情况作了更详尽的描绘,并可参看。若宫图是为新宫所绘,当稍后于永平七年,而不当等到十七年后。如果是张彦远记载有误,则贾逵无缘参预选画之事,但班固其时正在京师,且“自为郎后,遂见亲近。时京师修起宫室,浚缮城隍”,[7]1335他受命选画的可能性非常大。再衡诸史实,永平十七年,“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殿前,神雀五色翔集京师。西南夷哀牢、儋耳、僬侥、槃木、白狼、动黏诸种,前后慕义贡献;西域诸国遣子入侍。夏五月戊子,公卿百官以帝威德怀远,祥物显应,乃并集朝堂,奉觞上寿”。[7]121这种情况下大兴绘事以为庆贺也不无可能。那么,张彦远称贾逵与班固共同选画之说,似亦有成立的可能。
据上述史实来看,张彦远的记载并无大悖谬之处,不妨据信。受到喜好图画的汉明帝赏识,并且可能受命为其选定图画内容的班固,对这些图画的熟悉程度可想而知。现存汉画像石 (砖)上所绘历史人物画像,大致有故事性与非故事性两种类型。“古帝王是以单个肖像来表现,而这一大群男女英雄(按,指列女、孝子、义士等)则被描绘为人物故事画的中心。”[10]186盖后者的事迹主要体现在一件或几件著名的事件上,具有很强的传奇性。如果只能用一幅图画来表现,那么绘画者必然选取事件最高潮、最紧张的瞬间。[10]271-332宫廷中的《列女图》应该与此类似。张彦远说班、贾等人“取诸经史事”,即他们有所选择,不会将整部《列女传》一百多人都变成图像。即便如此,从《列女传》七类中各选三五人加以绘像也有二三十人之多,若都像顾恺之绘《洛神赋图卷》那样,显然也是不可能的。因此,宫廷《列女图》的存在形式当与今存汉画像一致。从北魏司马金龙墓中出土的人物故事漆屏正是这样的形式,可为佐证。[13]那么,前面推测的缇萦故事可能选取逮父与伏阙两个场景,应该不是臆想。
可作为辅证的仍是曹植《精微篇》,该诗记叙了 4个孝女故事,即苏来卿、秦女休、缇萦、女娟。其中写缇萦的部分为:“太仓令有罪,远征当就拘。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缇萦痛父言,荷担西上书。盘桓北阙下,泣泪何涟如。乞得并姊弟,没身赎父躯。汉文感其义,肉刑法用除。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图》。”[11]332“乞得”以下是对缇萦上书与汉文帝诏书内容的概括,而前面的描写则显然是班固声音的回响。既然曹植特别提到了《列女传图》,那么他所描写的就逮与伏阙场景与图画的对应关系当在情理之中。这可以视为曹植对班固的继承。当然,曹植更有超越班固的成绩,这是笔者即将论述的问题。
也许我们可以想象班固作《咏史诗》时心中的蓝本除了《史记》、《列女传》外,还当有深印脑海中的“缇萦救父图”,也许正是后者使得他的诗歌呈现出一种较强的图像性格。有意思的是,逯钦立先生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书中辑出的班固它诗残句,有“宝剑值千金,指之干树枝”之语,[2]170所描绘的场景与今存山东嘉祥宋山画像石和四川雅安高颐汉阙上的“季札挂剑图”正好相对应。这种对应真是耐人寻味。
二
班固之后,专门咏史遂无作者,直到建安时期,才又出现阮瑀、王粲和曹植的咏史之作。①按,曹操有《善哉行》“古公亶父”、《短歌行》“周西伯昌”等以咏史,其诗既为四言乐府,每解各咏一人,实近“赞”体,非班固专门“咏史”之体。而前述曹植《精微篇》则似是班固、曹操的合体,既“隐括本传,不加藻饰”,又合四事于一诗以达己意,可谓体制之新创。然终是乐府诗歌,不当与非乐府的专门咏史诗混为一谈,故不在此文列论。阮、王各有《咏史》二首,都以三良与荆轲为题材,曹植也有《三良》诗一首,当是同时唱和之作,时间大概是在建安十六年(211)左右。②按,赵幼文先生《曹植集校注》定此诗作于建安二十年稍后,误。盖赵氏忽略了阮瑀也有同题诗作,而阮氏卒于建安十七年,故不得迟于此年。且建安十六年,曹植从曹操西征马超,至关中,此诗乃此时有感而发乎?说详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曹植从曹操西征在建安十六年》。[24]43-44比较前后之作,可灼知咏史诗演变之迹,即图像性的减弱与个体情志的凸显。
因为荆轲故事是汉人最热衷的绘画题材之一,不妨先来看阮瑀与王粲的两首诗作:
燕丹养男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阮瑀)
荆轲为燕使,送者盈水滨。缟素易水上,涕泣不可挥。(王粲)[14]88,159
图像性的减弱在这两首诗中体现得较为明显,同时其中所表现出的诗与画艺术特性的差异也值得注意。王粲诗似乎并不完整,但对照阮瑀诗可知今存应是其主体部分。两诗都生动摹写了“易水送别”这一场景,素车白马、击筑高歌,也颇具画面感。这两首诗是否也与当时画像有某种对应关系呢?在文字记载中,荆轲故事最紧张激烈的无过于“送别”与“刺秦”两处,能入画的似也以此两处为最。只是今存汉代画像石 (砖)无一例外都是描绘“刺秦”场面的,“送别”的画像迄未见到。对此大概可以作如下解释。其一,人们选择荆轲故事入画,多半是看重其“忠义”,显然就画面而言,“刺秦”远比“送别”更能直接地表现这点。其二,在阅读感受上,“送别”的悲慨与“刺秦”的激烈,其对人的感染力是接近的;但是一旦表现为绘画,则后者能表现出强烈的画面效果而前者恐怕难度较大,这点毋庸置疑。因此,如果将荆轲故事绘制成图卷,“送别”和“刺秦”必是两个焦点,但若只有单幅的画面空间,则人们必取“刺秦”。阮瑀与王粲的诗详细刻画送别的场景,仍然具有一定的画图感,但是与现存汉代画像比较之后,不能不承认这种图像性因素是大大减弱了。既然今天还能看到许多荆轲刺秦的汉画,那么阮、王当时一定更为习见。他们选择以荆轲为题材作诗时,其实无妨如班固那样在诗中表现两个高潮场景,对刺秦的场面也作一详细描述,使得荆轲故事更加完整。现在诗歌对后一场景的忽略,不能不视为阮瑀、王粲的有意取舍,他们对诗歌与图像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同时对完整复述故事的兴趣在降低。
对于故事诗与故事画艺术特性的异同,钱锺书先生在其《读〈拉奥孔〉》一文中已经有所涉及,本文则专就咏史诗略作申发。故事画所表现的都是包孕最丰富的“片刻”,[15]35-37如荆轲正在行刺、秦王正在躲避的那一刻。而咏史诗虽然可超出“片刻”的限制,但其概括本事的特性决定了它同样需要选择史事中包孕性最强的一个或几个节点加以放大以串联故事。而故事本身包含事与情两方面,二者在故事中的流动既可能重合在同一节点中,也可能有各自的节点。①节点的不同我们不妨通过最有名的《长恨歌》与《长恨歌传》的比较来加以说明。《长恨歌》写杨玉环之死用了六句,而写蜀地相思则用了八句。反过来,陈鸿用了长得多的篇幅详细写了马嵬之变,而对玄宗在蜀只用了“既而玄宗狩成都”一句。二者的区别固然有文体不同以及作者艺术手段高下差异的原因,却也正好说明,“马嵬之变”是一个情事重合的节点,“夜雨闻铃”则是一个单纯的情的节点。纯粹属情的节点容易被散文叙事者忽视。对节点的不同选择、处理,可以看出作者创作倾向。班固的诗歌选择了两个节点,即“逮父”与“伏阙”,应该说它们都属于事与情相重合的节点,诗歌中它们也轻重相埒。所不同者,前者基本转述史事,后者则忽略上书的内容而强化上书行为本身。通过“忧心摧折裂,晨风扬激声”这样的描述,既能突显伏阙行为的神态、动作、环境等因素,又稍刻画了人物心理与精神。能否直接描绘人物情绪固然是诗与画的重要区别之一,所以班固之诗也不可能完全等同于画。但是,班固的主要意图看来不在传情言志,而在于通过节点概述故事,因而他对节点的选择主要还是从情节完整的角度考虑,必会与绘图产生对应关系。
阮瑀与王粲的诗歌则不同,他们似乎并不试图将完整的情节在诗中复现,而只选取了“易水送别”这一个节点加以放大。很显然“送别”与“刺秦”两个节点对故事呈现的作用是各有偏重的。后者主要是个情节性节点,强化它则故事性情节性增强;“送别”则基本上是个属情的节点,其作用在刻画人物的品格,加大故事的情感感染力。选择前者而完全放弃后者,充分表明诗人的目的在于颂扬荆轲等人的忠义之节、慷慨之气,而不是完整复述故事,咏史诗图像性的减弱,这是重要因素之一。亚里士多德曾说 (悲剧、史诗)诗人“和画家与其他造型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16]90在他看来与绘画的复现性质近似,叙事诗歌的性质则是“对于一个完整而具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因此“最重要的是情节”。[16]31,35这提示我们,叙事诗中其情节性节点与绘画的对应关系最为紧密。由此也可以说班固咏史诗的图像性还表现在他选择了两个情事重合的节点,对故事进行了基本完整的再现。
在咏荆轲的诗中,诗人选择了表现人物情志,从而减弱了诗歌的图像性,只是其变化是通过节点选择来实现的,比较隐蔽。而令外三首咏三良之作则以显明得多的方式实现了这种变化。先来看阮瑀和王粲的两首:
误哉秦穆公,身殁从三良。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低头闚圹户,仰视日月光。谁谓此可处,恩义不可忘。路人为流涕,黄鸟鸣高桑。(阮瑀)
自古无殉死,达人所共知。秦穆杀三良,惜哉空尔为。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妻子当门泣,兄弟哭路垂。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黄鸟作悲诗,至今声不亏。(王粲)[14]88,159
首先,阮瑀与王粲的诗仍然具有相当的图像性。他们选择了“三良殉葬”一事中情与事重合的节点加以突出渲染。这个节点就是三良临穴就死这一幕。阮瑀的“低头闚圹户,仰视日月光”,俯仰之间刻画三良最后时刻复杂的心态,已属难得之笔。王粲诗则更加点染,先写妻子兄弟的哀恸,然后写三良“临穴呼苍天,涕下如绠縻”的情景,表现其对生的眷恋。对生的留恋愈甚,则其毅然抉死的忠义之心就愈可贵。何焯曾称扬王粲此诗“最为沉郁顿挫”,[1]892其根源正在于王粲对此节点善为铺写,使得其事其情都充满张力。显然,如果入画,阮、王的选择会是最好的画面,这正是其图像性的体现。但是,也正是从这一节点的选择中,可以看到诗人的个体情志在咏史诗中的意义已超越于其图像性。盖这个节点取自《诗·秦风·黄鸟》,其诗有云“临其穴,惴惴其栗”,郑玄解释说,这是秦人登临墓圹为三良惴栗哀悼之语。[17]373阮瑀与王粲却采用另一种解释,将其视作对三良临圹时的描写,这样本来与三良无关的事情却变成三良自己的行为与情感,变成其殉葬事件中最高潮的节点。诗人的高明手段正在于此。因为有了这样的巧妙转换,使得这两首咏史诗跳出《黄鸟》诗和《左传》记载的限制。按《左传》与《毛诗序》的记载都是谴责秦穆公以活人,甚至以国内最贤者从殉,对三良的反应并无只字涉及。阮、王之诗固然承继这个谴责,在诗歌一开头就表达了这层意思。但是后面的描写却不再是对史实的隐括,而是诗人设身处地想象三良的心理与行动。殉葬这一事件由史书中客观的记述变成了诗歌里三良主动的选择。阮瑀的“忠臣不违命,随躯就死亡”,王粲的“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殁要之死,焉得不相随”,都强调说三良的行为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是他们恪守臣子的忠义之节的行动。虽然有所不舍,但是“恩义不可忘”、“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这样才能“生为百夫雄,死为壮士规”。这时,诗歌的主旨已由《黄鸟》对秦穆公残暴的控诉转变成对三良忠义的歌颂。这种在记载中本来不存在的“忠义”被创造出来并贯注给了歌咏对象,使得这两首咏史诗较之咏荆轲的两首,诗人的个体意志表现得更加明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阮瑀和王粲在诗中都强调三良的忠义实际是一种报恩的行为,这就是典型的东汉人思想。今天学者早已熟知,忠于恩主是东汉人的思想和行为准则,这个恩主既可以是皇帝,也可以是举主、老师等。因为世家大族在东汉的强盛和察举制度等因素,东汉的高级官僚对庞大的门生故吏群体有很强的控制力;反过来,这些门生故吏对门主也有极大的忠诚,甚至有知有门主而不知有天子之事。作为联系纽带,“恩义”思想影响整个社会。这就是复仇故事和刺客画像流行于东汉的重要原因。可见阮瑀与王粲诗中的思想是典型的汉人思想,诗歌表达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看法,这样的咏史诗表面上看起来接近班固,但其内在精神却更接近“多抒胸臆”的左思《咏史》了。这一现象,在曹植的《三良》诗中表现得更加显著。
曹植诗云: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秦穆先下世,三臣皆自残。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长夜何冥冥?一往不复还。黄鸟为悲鸣,哀哉伤肺肝![11]135
起首两句,何焯称“功名一联是说自家话”,[1]892开宗明义,即“人生不可觊觎非分,功名自有天定,惟当以忠义自励”。[18]253与阮瑀、王粲不同,曹诗立意中已看不到对秦穆公的直接谴责,三良被迫的殉葬已经变成遵守同生共死约定的“自残”。这种不同首先当源于《毛诗》与三家诗解释上的差异。应劭曾经记载:“秦穆公与群臣饮酒酣,公曰‘生共此乐,死共此哀’。于是奄息、仲行、鍼虎许诺。及公薨,皆从死。”[3]195大概这是三家诗中《鲁诗》的说法。[19]453“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一句正与这一记载相吻合。从曹植诗文用《诗》的情况看,曹植所习应是《韩诗》,同时他也应该熟知《毛诗》与《鲁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太祖从妹夫?强侯宋奇被诛,从坐免官。后以能明古学,复征拜议郎。”[20]3是曹操习古文经。《隋书·经籍志》载魏太子文学刘桢撰《毛诗义问》十卷,知刘桢习《毛诗》。丕、植兄弟都崇拜父亲而亲近刘桢,必当稍知毛诗。而当时学风尚简易,复重融通。汉末大儒郑玄宗《毛诗》,而述《毛诗传笺》,兼采三家之说,足征一时风气。是邺下文士多兼习诸家诗。如崔琰,初“读《论语 》、《韩诗 》”,后又“就郑玄受学”。[20]367阮瑀“少受学于蔡邕”,[20]600蔡邕宗《鲁诗》,[21]212,247-249则阮瑀初学《鲁诗》。王粲曾祖龚、祖畅都位至三公,其家所传自当是今文经。而前引阮、王咏三良诗都用《毛诗》义,知二人兼习今、古。又,应劭传《鲁诗》,其侄应玚、应璩也当习《鲁诗》。而徐幹也是《鲁诗》一派。[21]212,250-253可知邺下诸人于鲁、韩、毛三《诗》各有所长,史载曹丕“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20]57是汇通诸家大旨的做法,子桓如此,子建当也不例外。
阮瑀、王粲弃鲁取毛,表现了他们作为文学侍从对君主的复杂心态,而博知众家《诗》的曹植独心有戚戚于自愿殉葬的记载,当然也是别有心曲。首先可能是如王先谦推测的那样,《韩诗》与《鲁诗》在《黄鸟》的解释上相同。[19]453但在取舍之际,他更看重的恐怕还是其中君臣相得、死生与共的忠忱。没有了对秦穆公的谴责,“忠义”几乎占据了诗歌的全部空间,诗人的个体意志也更显突出。曹植的这种忠义固然称赞“等荣乐”的一面,但他显然更欣赏和强调“同忧患”的一面。这种“同忧患”的思想与“忠义我所安”相结合,显然暗示曹植的儒家思想较之阮瑀、王粲显得更加正统、更为保守。这种正统与保守不妨视作对汉末以来浇薄士风的反动,也是铸成曹植一生悲剧的重要根源。关于曹植的仁厚天性和正统儒家思想,清代学者宋翔凤有过非常精彩的阐发,他说:“子建三良诗云,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此谓人生不可觊觎非分,功名自有天定,惟当以忠义自励。至其他作,大约感朝露之易晞,伤荣耀之难久,无系恋富贵之意,有齐一大化之情。至于发忿所作,直追湘累,赋物之词,亦深托兴。魏武于建安十五年令,以桓文自比,中言子植兄弟,则以植意与己同也。其后势不容己,而植必尚执前意,故其宠寝衰。”[18]253①另可参见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曹丕曹植之争条"。[22]4-6以及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第二章《曹植论析》。[25]29-84正由于这种忠贞情怀,让曹植宁愿相信三良是自愿殉葬,而再三致意于这一典故。《咏三良》写成 15年后,他又一次在《文帝诔序》中表示自己“追慕三良,甘心同穴”,[11]341足以与前诗相印证。钟惺曾云:“子建柔情丽质,不减文帝;而肝肠气骨,时有磊块处,似为过之。”[24]429正是这肝肠气骨,让曹植的咏史诗彻底跳出了班固的格套,借古事以抒写一己之情怀,为后来如左思者开辟了新的道路。②按,左思的表现手法应该也受到郦炎《见志诗》的影响,笔者此处只是就咏史诗梳理其流变,指出从班固经建安发展到左思的必然,故不及郦炎。
在诗歌艺术上需要说明的是,曹植诗中仅仅用两句描写三良的临墓悲叹,较之阮、王,诗中的细腻描摹,曹植的减省固然是图像性因素更加减弱的表现,但同样具有情绪强化的功能。阮瑀、王粲、曹植都是把故事中最富激情的戏剧性动作凝固在诗歌中,这一富于情感的动作在空间中静止,却在时间中绵延,形成一种情感的张力。这与建安抒情诗歌中诗人对自我形象的强化方式是一致的。如王粲《七哀诗》的倒数三四句“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如他在荆州的另一首同题之作中的“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又如陈琳《游览诗》二首其一的结句“惆怅忘旋反,歔欷涕霑襟”,都是在前后浓烈的情感表达中用一个夸张的姿态,塑造一个凝固的戏剧化的“自我形象”。咏史诗与抒情诗在创作手法上的一致,进一步瓦解了咏史诗与故事画的对应关系,而是前者向抒情诗靠拢。这是建安诗人的一种新创,大概也是觉醒的个体表现在诗歌中的例证吧。
三
总结前文,也许可以得出以下四个结论:
第一,班固的咏史诗具有较强的图像性,这种图像性的形成与他在隐括史事时所选取的情节性节点有关。而咏史诗在建安时期的发展,则表现出图像性减弱和诗人个体情志凸显的倾向,这与建安时期个体觉醒的时代大潮是相一致的。
第二,咏史诗变化的具体方式又大概有以下两种现象:其一是不再追求故事的完整性,而只突出史事中最富包孕性的某一个节点。其二是节点选择由班固的重事变化为阮瑀、王粲的重情,至曹植则对叙事性的隐括史事失去兴趣,而只表现为议论抒情性的提出史事,因此不再能看到明显的史事节点。
第三,反映出来的诗人的立场也由班固相对客观复述的立场转为主观抒写,因此诗歌摹仿性、图像性逐渐消失,诗人更多是要借被歌咏的史事和人物来抒发自己的情感、意志,表现出较强的个体意识。
第四,推测这种变化发展的原因大概也有两点,一是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造成他们在各类诗歌中都极力表现自我。二是中国诗歌强烈的抒情传统也会有所推动吧。正是这样的双重影响,使中国咏史诗的叙事性很快就被大大削减了,左思的出现也就成为必然之事。
[1]何焯.义门读书记 [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4]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5]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6]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7]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8]中国美术全集·绘画编[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
[9]邢义田.台湾学者中国史研究论丛·美术与考古·格套、榜题、文献与画像解释——一个失传的“七女为父报仇”汉画故事为例[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175-215.
[10]巫鸿.武梁祠——中国古代画像艺术的思想性[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11]赵幼文.曹植集校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2]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3.
[13]大同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20-33.
[14]俞绍初.建安七子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5]钱锺书.七缀集 [M].北京:三联书店,2002.
[16]亚里士多德.诗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7]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8]宋翔凤.过庭录 [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9]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1]唐晏.两汉三国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3]钟惺,谭元春.古诗归 (续修四库全书第1589册据明闵振业刻本影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24]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2003.
[25]景蜀慧.魏晋诗人与政治[M].北京:中华书局,2003.
Abstract:From the time of Ban Gu to the era of Jian An(196—220),the poem about history shows a tendency to image weakening.Accompany with this weakening,the personal emotion gradually strengthens.Ban Gu’s poems about history,judging from a positive viewpoint,feature a strong image.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Ti Ying’s story is very likely to be one of the picture storiesBan Gu often sees.With it,hispoems have a strong correspondence.But,later,in the poems about history of Ruan Yu andWang Can,the narration of the plot seems not to be attached importance to.While the image weakens,the poet’s emotion is highlighted.This tendency ismost obviously displayed in Cao zhi’s"Three Goods",which proves that the poem about history is going towards the lyric.
Key words:poems about history;image;personal emotion
(责任编辑:梁临川)
Image Weaken ing: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Poem about History in the Han Dynasty
LIU Yi
(School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Shanghai200444,China)
I206.2
A
1007-6522(2010)06-0093-11
2010-05-10
刘 奕(1978- ),男,四川乐山人。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讲师。研究方向:明清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