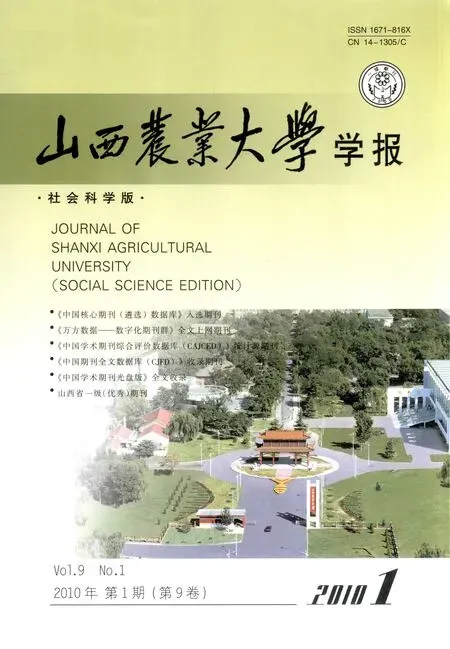《呼啸山庄》悲剧艺术探析
2010-04-12杨东升杜军
杨东升,杜军
(1.忻州师范学院外语系,山西忻州034000;2.山西农业大学文理学院,山西太谷030801)
爱情与复仇是西方文学中的一个永恒主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神话。希腊三大剧作家之一的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美狄亚》就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中伊阿宋夺取金羊毛的传说。在这出悲剧里,美狄亚为了惩罚丈夫伊阿宋的忘恩行为亲手杀害了自己的两个孩子,其残酷而骇人听闻的复仇行为源于爱,又最终毁灭了爱,给人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恐怖感。无独有偶,英国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艾米莉·勃朗特 (1818~1848)的《呼啸山庄》恰若老酒新酿,讲述了一个惊心动魄、凄厉残忍的爱情与复仇故事,被称为“19世纪最奇特的小说”。英国著名作家毛姆曾评论道:《呼啸山庄》 (以下简称《呼》)具有一种很少有小说家能够给你的东西,这就是力量。我不知道还有哪一部小说其中爱情的痛苦、迷恋、残酷、执著,曾经如此令人吃惊地描述出来。然而如果穿过爱情故事的岩层继续深入,我们不难发现该作品的非凡之处并不仅仅在于以“吃惊”的方式讲述一个惨淡的爱情故事,更在于其悲剧精神的不寻常表现。作品冷峻的叙事风格之下时刻有一股狂风暴雨般的力量在酝酿着爆发,而主人公震撼心灵的浪漫主义嘶喊则如荒原呼啸主旋律中几处高亢激扬的音符,凸显出人性与生俱来的超越精神,它时刻冲击着、试图穿透着那张由所有不和谐音符搭建的人性与文明对峙的张力大网,而作者所着意刻画的人性扭曲则恰到好处地承载起人类生存原本具有的悲剧内涵和崇高意义。
一、穿透坚实叙事的浪漫主义嘶喊
《呼》的整个故事是由一个名叫洛克乌德的闯入者为我们叙述的,他叙述的故事中又套出了呼啸山庄和画眉田庄的女管家艾伦叙述的故事。而艾伦的叙述中又套着其他人的叙述,以补充艾伦不曾目击的细节,使故事全过程更加完备。这种多重叙事风格历来为评论家所赞赏,其艺术效果主要在于营造小说的真实性和强烈的现实感。然而透过小说的严肃叙事去体会其人物语言和环境描写却可以发现,《呼》是一部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小说,小说中男女主人公濒临死亡时高亢激昂的浪漫主义嘶喊似乎在极力穿透着文本叙事结构如墙壁般的坚实,它恰如黑暗中的几枝火把,划破死亡的黑暗阴影,烛照着凄惨人生终极处生命意识的奋起前行。
在浪漫主义时期由于宗教传统和文化的影响,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展现了更为豁达的转变,体现了由“乐生恶死”向“乐死恶生”的死亡哲学的转变。“死亡是多么美妙的事啊!死亡与他的兄弟——沉睡!”作为拜伦《麦布女王》的开篇句,也成为了概括这一时期死亡的主题。死亡摆脱了中世纪那狰狞恐怖的阴影,幻变成了一个美的象征,带有致命吸引力。[1]在《呼》中人类的爱恨情仇以直面死亡的方式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面对死亡,凯瑟琳没有丝毫的恐惧,她对希斯克利夫说:“但愿我能一直揪住你……直到我们两个都死了为止!……我只愿我们俩永不分离……”[2]同样,希斯克利夫发自肺腑的话也无疑是一段彻头彻尾的关于生与死的悲剧独白:“……苦难、耻辱、死亡以及上帝或撒但所能给予的一切打击,都不能把我们俩拆开,而你!……我还要活下去吗?这叫什么生活呢?当你……啊,上帝!当你的灵魂已进了坟墓……你还愿意活着吗?”[2]凯瑟琳临死时,“她躺在那儿,脸上露出甜蜜的微笑;而且她最后的思念迷迷惘惘回到了童年的快乐日子里。她的生命结束在一个温柔的梦里”。[2]而希斯克利夫在完全实现了自己的复仇后,感到无比的空虚,他在哈里顿身上看到自己年轻时的影子,在小凯瑟琳身上看到自己恋人的影子。他终于决定放弃了,不仅放弃复仇,而且放弃生命。他临死前四天四夜不吃不睡,“我只有一个愿望,我的整个身心都渴望着实现它。我已经渴望了这么久,这样毫不动摇,以至于我确信它定能达到——而且很快就要达到——因为它已经耗尽了我的一生,我已经在期望它的实现中被吞没了”。[2]
小说的浪漫主义色彩还表现在作者在环境刻画以及意象、情节构造方面采用了典型的哥特手法。梦幻中血淋淋的幻象,挖掘坟墓,与尸同眠的渴望,这一切无不令人触目惊心。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局外人洛克伍德的一个噩梦,让人感到恐怖气息,“我咕哝着,用拳打穿了窗玻璃,伸出一只胳膊去抓那捣乱的树枝,谁知我的手抓住的不是树枝,而是一只冰凉的小手的手指!梦魇的强烈恐惧压倒了我,我想抽回手臂,那只小手却紧紧抓住我不放……我隐隐约约看到有一张孩子的脸在向窗子里张望,……把她的手腕拉到破玻璃处,来回擦着,直到淌下的鲜血沾湿了床单。那声音依然哀求着‘让我进去’……”[2]除此之外,凯瑟琳精神崩溃之前的幻觉描写,希斯克利夫死后,人们看到的两个人的灵魂在荒原上漫游的描写,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
多重叙事视角下真实而凄惨的人生境遇与主人公生命意识强烈爆发时的浪漫主义嘶喊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哥特式的恐怖渲染中,打破了读者所惯常感知的世界,扩展了读者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再思考,赋予《呼》以浓厚的悲剧色彩。
二、人性与生存的悖论
人性中的超越精神与生存的客观现实性这一永远的悖论是悲剧题材的永恒话题。《呼》并不以主人公的悲欢离合体现其悲剧意义,如果说艾米莉在该小说中意欲表现一股伟大力量的话,这种力量并不在于传达希斯克利夫与凯瑟琳的爱情故事,而在于透过这种力量体现一种人性与生俱来的超越精神,而这种精神籍着文本严密的叙事结构呈现为悲剧精神。
西方悲剧惯以高尚不凡的人物为主人公,别林斯基强调:“只有拥有高尚天性的人才能够是悲剧的英雄或者牺牲物。”[3]车尔尼雪夫斯基主张:“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者是伟大人物的灭亡。”[4]《呼》的主人公希斯克利夫是呼啸山庄原来的主人老欧肖先生从利物浦的大街上捡来的一个乞儿,谈不上具有高尚的天性,更不具备伟大人物的资格,其最终灭亡也不能凸显生命的意义。然而《呼》并不着意于表现“主人公的伟大与崇高”,而在于表现“人物伟大的痛苦”,希斯克利夫令人发指的复仇行为的终止及其人性回归才是整部小说悲剧意义所在。小说以希斯克利夫的“爱-恨-复仇-人性的复苏”作为贯穿文章始终的线索,而无论在这条情节发展线的哪一个阶段,希斯克利夫都在经历着“伟大的痛苦”,其伟大之处在于他的顽强与不屈的超越精神,其痛苦之处正在于他的生存境况,无论贫穷之时,还是富有之时,他始终不能摆脱痛苦的煎熬。从小说的整体结构来看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行为集中体现在女主人公去世之后,而他与凯瑟琳的爱情也在小说的后一部分代之以小凯瑟琳和哈里顿的爱情。一些评论家认为小说的后半部分是画蛇添足的行为,破坏了小说的整体艺术,然而,从故事的发展可以看出小说的重心并没有随之落在对下一代人爱情的描写上,作者所突出刻画的仍是希斯克利夫扭曲变形的灵魂与张牙舞爪的复仇行为以至最后的人性复苏。从悲剧剧情发展的观点来看,“由悲剧冲突导致的悲剧结局,不应当是矛盾的调和,不应当是平静美满大团圆,而只能是苦难与毁灭”。[5]希斯克利夫在小说前半部分追求平等与追求爱情的动机与努力没有实现的情况下,在小说后半部分以复仇的行为方式持续出现并且注定要落空的事实恰当地说明:动机与结果的悖反现象是悲剧主体的一个重要特征。小说所要凸显的“人物伟大的痛苦”只有在复仇无法进行下去的时候,在希斯克利夫人性回归之时才终于得以实现。在《呼》第33章中希斯克利夫对耐莉说:
“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结局,是不是?”“对于我所做的那些残暴行为,这不是一个滑稽的结局吗?我用撬杆和锄头来毁灭这两所房子,并且把我自己训练得能像赫库里斯一样的工作,等到一切都准备好,并且是在我权力之中了,我却发现掀起任何一所房子的一片瓦的意志都已经消失了!我旧日的敌人并不曾打败我;现在正是我向他们的代表人报仇的时候:我可以这样做;没有人能阻拦我。可是有什么用呢?我不想打人;我连抬手都嫌麻烦!好像是我苦了一辈子只是要显一下宽宏大量似的。不是这么回事:我已经失掉了欣赏他们毁灭的能力,而我太懒得去做无谓的破坏了。”[2]
毫无疑问,“希斯克利夫的复仇起源于人格平等和个性尊严的被扼杀与践踏,而他最终放弃复仇回归人性是因为他在小哈里顿那里看到了即使处于精神虐待中仍然顽执地对人格平等和个性尊严的渴望——他曾经所被侵夺的东西”。[6]因此,尽管希斯克利夫表现出恶魔般的性格特征,如果从象征意义上来解读其灵魂,却不难发现人性中追求灵魂解脱的自由意志与现实环境的冲突是造成人生痛苦的根源,跨越死亡门槛之前的任何努力与挣扎都将陷入虚无的意义。
三、扭曲的崇高
西方悲剧继承荷马史诗的英雄主义和悲壮风格,酒神祭祀的“悲剧性的合唱”赋予悲剧庄严而悲怆的精神内涵。车尔尼雪夫斯基称悲剧为“崇高的艺术”,认为“悲剧是崇高的最高、最深刻的一种”。[7]《呼》震撼心灵之处在于该作品营造了一个善恶交加、爱之深与恨之切的气氛。小说中构成冲突的要素纠缠于一起谱写着爱与恨、人性与魔性、人性与文明的斗争,而希斯克利夫寻求复仇,运用残忍、卑鄙的手段扭曲他人人性,甚至企及无辜,来达到复仇的目的的丑恶行为,那种爱不能爱、恨到极致的渲染使这个本该平凡的故事具有了无限的悲剧色彩,而《呼》的悲剧色彩集中体现于其独特的“崇高”内涵。
西方文艺批评中素以崇高 (sublime)和优美(grace)来区分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西方的一些美学家不承认恐惧和痛苦在崇高体验中的作用,认为崇高感是伟大引起的,无疑sublime一词的内涵是雄伟、宏大之意,如果只从这一意义来说,《呼》并不算得上是崇高艺术的典范,即使是男子气概十足的希斯克利夫也只是展现了个性粗犷的一面。然而黑格尔认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崇高则是理念大于或压倒形式,因此“崇高一般是一种表达无限的企图,而在现象领域里又找不到恰好能表达无限的对象”。[8]美与崇高同样都以理念为内容,以感性的表现为形式,然而,这两种表现并不相同,在美里内在因素即理念渗透在外在的感性的现实里,成为外在现实的内在生命,使内外两方面相互渗透,成为和谐的统一体;对于崇高,则由于用来表现理念的可观照的外在事物自身的有限性使其无法容纳内在意义,内在意义并不能在外在事物里显现出来而溢出事物之外。可见正是由于无限意义无法显现在有限的形式即叙事结构中而必然产生变形,《呼》的怪异风格与扭曲刻画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在《呼》中“崇高”是通过扭曲变形实现的,人性的扭曲在希斯克利夫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他不择手段的复仇方式超越了伦理、道德的约束,他甚至将自己的儿子作为泄愤的工具,希斯克利夫有一句话最能说明其扭曲的性格:“我没有怜悯!我没有怜悯!虫子越是扭动,我越想挤出它的内脏!”[2]天才的女作家在小说的第一章就以一段环境描写预示了小说人物性格的扭曲:
呼啸山庄是希斯克利夫先生住宅的名称。“呼啸”一词,在当地来说有着特殊的含义,它形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里,这座山庄所经受的风呼雨啸。当然,住在这儿,一年到头,清新纯净的气流该是一年四季都绝不会少吧?只需看一看宅子尽头的那几棵生长不良、过度倾斜的枞树,还有那一排瘦削的、全把枝条伸向一个方向,就像在向太阳乞求布施的荆棘,你就能捉摸出从旁刮过的北风该有多大的威力了。[2]
《呼》的“崇高”产生于爱情与仇恨冲突的巨大张力,体现于对残酷现实题材的浪漫主义表现之中,而文本所营造的哥特式恐惧、以及读者阅读该文本时无可名状的审美体验正是导致作品崇高艺术效果的根源,也是该作品的美学意义所在。《呼》的剧情发展也同样体现了如汹涌波涛的文本意义必将融入平静而无限的大海才能得以显现。正如叔本华所言:“写出一种巨大不幸是悲剧里唯一基本的东西,……那些最高尚的 (人物)或是在漫长的斗争和痛苦之后,最后永远放弃了他们前此热烈追求的目的,永远放弃了人生一切的享乐;或是自愿的,乐于为之而放弃这一切。”[9]艾米莉所极力营造的复仇悬念,即“作品本文中引起复仇主体同仇主间尖锐对立、冲突解决到正义实现的根本性动机”[10]随着鲜活、张扬的男主人公的离世终于瓦解,随着“善”与“恶”之间无情斗争的结束,读者强烈的好奇心和惩恶向善的阅读期待在希斯克利夫的人性回归中永远化为了对人性悲剧与现实世界生存法则的深刻思考。
《呼》以其冷俊的多重叙事风格构建了一个爱与恨、迫害与反抗、原始与文明互相对峙的文本世界,这些对峙的力量如同一股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彼此侵袭着、吞噬着对方,卷起千层巨浪,终于溢出文本的边缘而汇聚成一股仿佛寂静的溪流。小说结尾是这样的:“在晴朗宜人的天空下,我 (小说的叙述者洛克伍德)流徊在这三块墓碑周围。望着飞蛾在石楠和风铃草中间振舞,听着那和风轻轻拂过草丛,我心里想,谁会想到,在这片安宁的土地下,长眠于此的人却并不安宁呢?”[2]哥特式恐怖血腥的场景描写与暴风骤雨般的恩怨故事最终落笔于小说结尾这一蕴涵象征意义的场景描写:人类生生不息的溪流将还会一如既往的激荡前行。
[1]刘琼.论浪漫主义时期死亡观对西方诗歌的影响 [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S1):232.
[2]艾米莉·勃朗特著,宋兆霖译.呼啸山庄 [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160,164-165,170,326,323,156,31-32,4,345.
[3]别林斯基著,满涛译.别林斯基选集 [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76.
[4]车尔尼雪夫斯基著,辛未艾译.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 [M].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分社,1965:88.
[5]苏晖,邱紫华.但丁的美学和诗学思想 [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30(2):6.
[6]杨经建.复仇:西方文学的一种叙事模式与文化表述 [J].外国文学研究,2004(2):119.
[7]车尔尼雪夫斯基.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 [A].西方美学史资料汇编 (下)[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116.
[8]黑格尔.美学 (第二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79.
[9]叔本华著,石冲白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 (第三篇)[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1.
[10]王立.文化·审美·题材主题——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综论 [J].毕节师专学报,1995(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