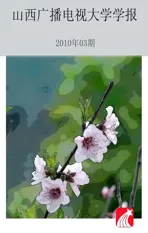原来自传还有另一种写法
——简评《我的上世纪》
2010-04-12张宏图
□张宏图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宁 272037)
一
自传是以记述自己的生平事迹为主的传记。自传中要有事实,要反映出人物的成长变化经历,要有一定的时间感。但是在《我的上世纪》这本书中,你看不到作者的思想性格和外貌特征,更看不出作者完整的成长变化经历。有的只是作者对社会变迁、城市变迁、生活变迁的记忆,对上世纪北京平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四季更替到风土人情,从城市变迁到个人经历的记忆,而且这些记忆又都是没有任何评价的素描。
这好像不是自传,只是一种文化记忆,但笔者认为它是。这主要有两点:一是“从心理学角度看,自传应该是一种基于叙事活动的自传体记忆。自传体记忆是对个人信息或个人所经历的生活事件的回忆,它包含感知体验、情节记忆、语义记忆、自我表征等成分的复杂过程,是自我记忆系统的核心部分。从内容上,自传体记忆主要包括自我描述信息和个人经验两部分,个人经验又分为生活历史、概括性事件和具体事件等不同的层次” ,而且自传体记忆不仅是对过去自我经验的加工和提取,还反映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二是自传是记忆与文化和叙事之间动态发展的结果,它建构在微观(如家庭)和宏观(如文化)背景中。一方面,微观和宏观的文化背景通过生活方式、家族仪式、文化实践、文化符号 (如民俗、民歌、宗教、语言和文化象征物)等影响自我。另一方面,自传通过对这些生活方式、家族仪式、文化实践、文化符号的保持来起到传承文化的作用。因此,在文化、记忆、叙事相互作用的过程中,自传也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叙事活动的文化记忆。既然我们的记忆反映社会文化背景,而自传又是一种文化记忆,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我的上世纪》是自传,虽然作者没有以自我信息和个人成长经历为主。
笔者还认为它不仅是,而且还是比较好的自传。首先,作品具有传记非常可贵的品质真实客观。既没有为自己隐恶,也没有为自己贴金;既没有对尊者讳,也没有对贱者轻。对经历的人和事只是作为一种记忆,进行平实客观的记录。例如父道其五中的“吓一跳”,“‘吓一跳’是一个姓夏的女招待,她有一姐妹,名叫‘吓二跳’,‘吓一跳’曾和呆呆、金大舅有过一段交往,闹得风风雨雨,全家不得安宁。……”,呆呆是作者的父亲。再如变迁其十一中的“日本女子学校”,“禄米仓的仓院,日本占领时期改成了日本女子学校,专收在华日籍女学生。……娘在那里教国文,当时学生对老师是极其尊敬的,学生见了我娘都要行九十度的鞠躬礼,喊‘先生好’”。母亲在侵略者的学校里教书和日本人的尊师传统都如实地记录下了。其次,它是一部平民作品,是我们一直以来在呼唤的“小人物”传记。因为作者虽然是有所成就的建筑师,与广大弱势群体比,不能说是“小人物”,但在数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大军中,还不能称作是“大人物”,只不过是我们常说的“工薪阶层”而已,而且作品中的人物也都是一些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例如商贩其十中的“老西儿”,“老西儿是一个卖糖果的,小店就开在我家不远处,孤身一人,好养黄雀,人很和善。我经常去他家买糖,他很喜欢我,经常多给我一些糖。老西儿在我上大学前就半身不遂,不久就去世了,我非常想念他”。还有如“孙大叔”、“羊肉铺掌柜的”、“卖油郎”、“小一子”、“大老黑”等等。作品中所记录的事件也都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家长里短小事,既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悲喜剧。例如学伴其八中的小瞎子,“小瞎子他妈有点‘二百五’,每次拖交房租时,都要说些‘好话’,如:‘大爷您再给缓两天吧!您瞧您长得多好啊,跟芍药似地’”。再如建国其十二中的“怯装自行车”,“五十年代自行车是‘三大件’之一,有谁买了一辆自行车后都要装饰一番。先用旗杆布裹好架子管,安上线织的花把套,要有穗子,座套也如此。车轴套上彩色的擦轴圈,装饰完了再看这辆车——那叫怯”。这是老百姓在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平平淡淡却生活气息浓郁。
二
作为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不同的作品,它的不同首先就在于叙述结构的不同。作者没以自己的生平事迹为主,而是以故乡的印记为主,写了老北京的方方面面,是一部老北京人的民间生活史。由于事无巨细,也就不能采用一条主线贯穿始终的写法,只能分门别类。作品的章目就很清楚地体现了这一点,一生其一、玩儿其二、大院其三、……流影其二十、故事其二十一、见证其二十二。而这一分类写法其实是作者历史记忆散片的整合,是一种单元化的整合,如年华其十六中包括:毕业分配、二次分配、三大、捉蛇、看蛇惊魂、猫坟、抓麻雀、批斗会、党校办班、烧砖、绑钢筋、去延安中学取经、十字坡中学、最后的太监、强身健身法。作为建筑师的关庚先生,笔者权且认为他不具专业作家驾驭作品的能力,无法史诗般地记录下自己的一生。但也正是这种没有传记理论束缚,不按常规出牌的单元化写法,形成条条大路通罗马的格局,同时也让人想到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的“冰糖葫芦结构”,这让笔者突然意识到自传或者传记也是可以这样写的。其实作者是在用修史的手法来进行自传的创作。他把传记关注的重点从传主本人转移到了传主的生活现场,借鉴了中国传统史书的体式,以类似“表”、“列传”的形式将许多原本无法纳入传记叙述框架的第一手材料进行梳理,共时性地呈现出来。这部作品的出现,为自传或传记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思维程式、结构形态和存在方式,让我们意识到原来文本结构的设置其实可以更灵活。
其次它的绘图与文字并举、以图带文的叙述方式也有别于传统的自传或传记,这也是该书最重要的特点。我们已经进入了“读图时代”,《我的上世纪》的出版恰恰迎合了时代。传记“手绘”的独特之处在于探索一种传记叙述的新方式,用丰富生动的图画资料充实、重构对传记的叙述与想象。而“读图时代”所代表的只是一个以图为主、为读图而读图的阅读方式和阅读时尚。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与“读图时代”同时把“图”作为拓展思路的突破口,正是自传、传记文学抓住时代脉搏、不断创新突破的最佳表现。
人生记忆中有许多人、事、物是终生难忘的,当时的情景、动作用语言文字是无法表达清楚的,只有图画才能够给人以直观的印象。然而,自传、传记却一直难以把这些丰富复杂的内容收纳其中。一般来讲,传记关注的是人生轨迹、事件真相的揭示和精神品格的建立。这种做法无疑是能够把握和体现传主的“大叙事”,但是把复杂而丰富的历史社会生活信息省略或“屏蔽”掉了,无数真实丰富的社会生态信息无法进入自传、传记的“大叙事”之中,这样就会使自传、传记显得干枯、僵硬,缺乏鲜活具体的历史细节与现场感。《我的上世纪》就是试图以最直接的方式返回历史的发生现场,还原社会文化生态环境。这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小说需要一百个读者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传记却不需要一百读者就有一百个柳如是。图画的直观有力地扼制了读者的再创造,更贴切具体地锁定了历史的“这一个”。
图文并貌的手绘本,该书是笔者见到的第一部,很多东西是作者凭记忆画出来的。作者把许多事物、场景的最原始的式样,把书里所写的各人物及其所行之事以素描的形式显现在我们的面前。这当然是足以增高读者的兴趣的。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插图使我们得见各时代的真实的社会的生活的情态。其实,图传、画传已经屡见不鲜,可是那些图传或画传并不能做到“左图右史”,照片固然清晰真实,但往往是在多部图传里重复使用毫无新意,很多场景的再现往往也是照片无法实现的。所以这本书被编辑称为“清明上河图”是有道理的。
这部手绘本总共有六百多幅图画,这些绘画蕴涵着丰富的信息必须借助于文字,绘画的内涵才能被充分地阐释出来。文字阐发绘画的意义,绘画解释文字的信息,由此图与文融会成为互动互释的互文性文本,融会成具有生命情趣和人文意味的意义相关体。这种互文性的文本,就是以图文互动作为自传叙述方式的新自传。
应当注意的是,《我的上世纪》这种自传叙述方式的转变是作者的创作观念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结果。图文互动的自传叙述放下了对“宏大叙事”的追求,不以构建人物精神品格为主要目的,也不用历时性叙述方式,而是“以图带文,由图出史,图史互动”,巧妙地以图画作为传记的线索,用具像丰富的历史记忆散片逐渐累积,塑造出了一个真实生动,较有现场感的怀旧文本。我们虽然为其叫好,但其效仿难度很大。首先传主自己能不能画?能写能画又看怎么画,素描?工笔?浮世绘?绣像……,这讲究又很多。一本好的“手绘本自传”或“手绘本传记”绝不是过去时代的“小人书”,需要认真探讨之处很多,拙文意在抛砖引玉,以期引起理论家、评论家们对“手绘本传记”的更多关注。
参考文献:
[1]张镇,张建新.自我文化与记忆:自传体记忆的跨文化研究[J].心理科学进展,2008,(2).
[2]李扬.遭遇“读图时代”——也谈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转变[J].北方论丛,200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