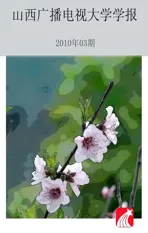论王保忠小说的创作特色
2010-04-12谢虹光霍惠玲
□谢虹光,霍惠玲
( 1.广播电影电视管理干部学院,山西 太原 030013;2.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山西 太原 030027)
小说是最能精确、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的艺术样式,也是最易于直刺人情世故至深处的文学利器。王保忠的小说继承现实主义传统,毫不妥协地进行文化剖析,实现了当代小说揭示乡镇无奈生活的社会功能,留给后人以精彩的风俗画卷和丰富的人文意蕴,因而其文化弘扬与批判的意义非常重大。本文就其上述特色,以他新近发表的小说集《张树的最后生活》作为当代晋北雁同地区文学圈小说创作的范本,尝试性地加以分析与描述。
一、创作内容的分类
王保忠迄今为止的一系列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创作的主要内容大致有三个方面:其一是着力揭示乡村中干群之间复杂的利害关系,旨在批判一些基层干部畸形变态的恶劣作风。以中篇《愤怒的电影》、《谁跟我开了个玩笑》以及短篇《张树的最后生活》为其代表作。其二是揭示城乡之间生活层次与利益分配诸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旨在说明当代农民进城务工甚或作为北漂生活期间心灵深处所受到的污辱与损害。以中篇《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和短篇《城市里的老玉米》为其代表作。其三是展示丰富的农村生活场景与风俗画卷,旨在表现农业文明与乡村传统的深厚与灿烂、民心民德的纯朴与善良。以短篇《1973年的乡村婚礼》为其代表作。非常明显,富于作者独特创作个性的精品集中在第一类内涵的小说作品中,即:属于矛盾揭示与社会批判的小说力作。小说家以此类小说作为筑构系列当代生活场景的核心框架,集中笔力全方位地俯瞰当代社会人生的特殊环境与复杂剖面,从而真正彰显其小说艺术见微知著、意蕴深弘的魅力。
二、作品的人物塑造
王保忠小说创作的重要特色,在于客观冷静、不动声色的叙事手法和白描写照,以及本色质朴而又生动各色的人物对话,从而加强了小说系列人物形象塑造的层次感与立体型。短篇小说力作《张树的最后生活》集中体现了上述特色。小说精确地描写了两代羊倌的生活悲剧:张树与他的父亲的悲剧;前者明写详述,后者暗合略带。张树小时候,娘因为老羊倌家穷,撇下张树父子俩跟人跑了。张树在白天放羊、晚上挨打的童年过去之后仍然过着两代光棍羊倌的贫困而孤独的日子。小说中对于张树接下来的岁月链接更具普遍的艺术概括性及其形象张力。由于偶然撞见了村主任与马二媳妇的苟且之事并由自己无意间张扬了开来,年龄才45岁的张树被炒掉了放养的差事、并被排挤出自己的家乡、进而被专门“照顾”进了镇上的养老院。由于迫害的进一步和生活的百无聊赖,张树将养老院中唯一的女性“老太婆”奉为亲娘,可惜“老太婆”被气走了;张树喜欢善于吹牛的“石板头”给寂寞生活所填充的些许色素,可惜石板头也病死了;张树在百般无奈之下逐渐暗恋上了诱使他不断花钱买烟酒瓜果的游商小贩秀姑,因为这是唯一可以让他轻松聊天并感受家庭温暖幻觉的女人。可秀姑也因为新开张了一爿小店而远离了养老院门口的售货点。当经过辛苦追随终于见到秀姑并被其严词拒绝后,恓惶寂寞的张树只有按照秀姑的最后指点找到“小香港院”的女人来聊取安慰;但是命运的捉弄仍然不放过这个可怜到极点的小人物,他先是“无功而返”,继而被公安局的检查人员和记者逮了个正着。两天后被领回养老院的张树在深刻地检讨了自己无聊的一生后,在无奈地大口大口地吸烟中顿生幸福幻觉:“他的眼前忽又浮现出卖东西女人的头像”,“他在烟雾里看到了快乐的石板头,他的脸上竟浮起了一丝灿烂的笑,就像从云缝里挤出来的阳光”。倒霉的张树就在吝啬的现实生活挤出来的阳光到来之前,无奈地自杀身亡了。
王保忠一系列小说创作中的人物形象塑造是发展的、相互联系的。其笔下的人物形象在渐次丰满之余,总是表现出一种抗争情怀和无奈心绪。如果说多余人张树对于无聊生活和变态的基层干部尚还缺乏清醒、自觉地抗争意识,从而造成了这一小人物于无奈中的死亡悲剧,那么中篇小说《愤怒的电影》则正好相反,它反映了一个清醒而自觉地反抗基层干部畸形变态的恶劣作风,在官官相卫的体制氛围下终至无奈地以死抗争的当代悲剧。异样地无奈、反抗和以死抗争的张生形象,让我们感到了社会基层、民生底层发出的地震前极为压抑愤恨极为喑哑恐怖的轰鸣。因而这个现代张生的悲剧命运更容易让我们清醒和警觉,更容易使我们认知当前县乡村三级干部管理体制中的弊端与干部素质的卑劣猥琐。可以想象得到,在上述人文环境下的农村改革所遭遇的阻击必定是空前严酷的。同时在王保忠一类小说家的笔下,上述这样的人物形象系列之塑造远没有结束,并且必将于日后的小说创作中持续延宕下去,小说人物形象也将会日益复杂而更加具有社会批判的意义。
三、小说的形象意蕴
王保忠小说人物形象系列的塑造有着深刻内涵与现实诉求。透过他的小说我们可以发现,当前农村中非人性化管理弊端的核心问题是缺乏公平公正的文化氛围,缺失基本的信息透明度以及对于民众知情权的起码尊重。在现代农村文化建设中不仅要强化对于各级干部的监督制约机制,而且必须给予广大农民以政治民主与民生平等的启蒙教育。否则,现代农村的文化教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就无从谈起。农村物质生活的富裕是乡野现代文化教育的前提条件之一。但是富裕绝不等同于现代文化教育本身,人的思想觉悟也绝不能以物质文明的程度来论高下。文化教育如若背离了基本的人伦道德的优秀传统框架,那就只是意味着知识的庞杂而了无根基及其道德水准的沦丧。这是当代社会潜在的最大危机,而且这样一种危机并不仅仅表现于农村。小说《愤怒的电影》中那位名义上是下乡为农民群众送文化送电影的县城文化局干部,实际上是以自己腐化堕落的都市风习严重地污染了农村风气;而那位为求得乡村生产发展却宁愿放弃党的基本原则,协同文化局“许同志”一起迫害张生并致其死亡的村长,无疑是现代农村中伪道德原则与官场潜规则熏陶下的玲珑叭儿狗,地方保护主义原则和封建官场恶习的忠实维护者。他们与现存的都市罪恶、伪精神文化、腐朽变态的帝国文化与封建思想遗留共同剥夺了当代张生们和张树们对于善良民风和对精神文明与社会理想不懈追求的权利。
在王保忠创造的系列小说人物中,居于张生与张树两个人物形象之间的,还有中篇《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里热衷附势于上流社会,最终沦为杀人犯的大光。其实张生、张树与大光极为相似,他们在临死前都会心存一个至善至纯的愿望:即去天安门看一眼吧!再“伸出手臂做一种拥抱的姿势,口里喃喃道,我爱你,北京!”然后却在“狼也似的吼”声中,“像一只大鸟被子弹击中了翅膀”一样,无奈地走向残酷而无奈的死亡。
由此我们看到了由政界渗透到商界、企业界、新闻出版界日益严重的经济利益的倾轧和对于现代生活的毒化以及必然引发的社会矛盾的激化。在作者王保忠笔下,虽然张生和张树们于无奈中孤独地死去了,但他们或厚重憨直或执着聪慧的灵魂并未获得丝毫安宁,他们都无比遗憾地告别了无法协调的充满现代气息、日益扭曲而又日益复杂化的乡村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丰年》中的梁万仓、《遍地西瓜》中的庆有和木匠、《城市里的老玉米》中的老玉米和小梅、《柳叶飞刀》中的来宝、《说个媳妇给根娃》中的山子等小人物,甚至包括中篇小说《谁跟我开了个玩笑》里的镇党委书记李维等一批小官们,至今仍然活在心灵的无奈与处境的尴尬之中而无力自拔;他们将延续着张生和张树们可怜可悲的灵魂遗梦。如果国人的灵魂从此变得识时务而苟且偷生,农村改革的健康发展必定顺势消亡;而如果他们从此继续厚重、憨直而逐渐充满理性思辨精神,张树和张生们的死亡所催生的就将会是理想的社会与人性的充分觉醒。而这正是作者王保忠通过小说意蕴展现给我们的精彩艺术画面和未来城乡和谐发展的精彩画卷。为此我们宁愿赌咒:无奈、悲伤而残酷的死亡只属于“张树的最后生活”;然后让我们一起为美好、精彩的未来理想生活而继续奋争并大声礼赞!
参考文献:
[1] 吕微芬﹒21世纪中国文学研究[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1.
[2] 王保忠﹒张树的最后生活[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