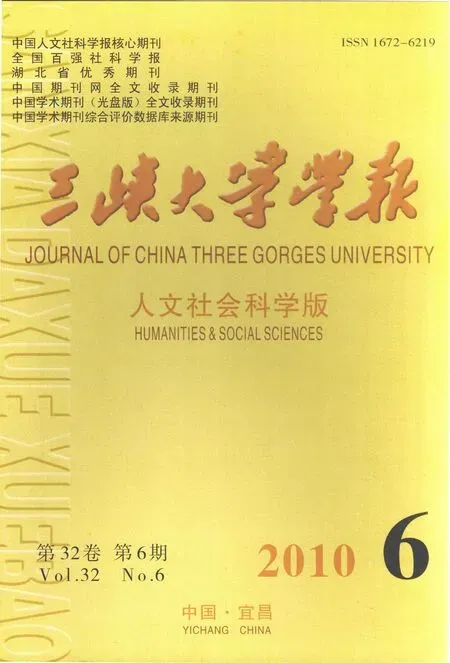警察行使职权时执法过当问题研究
——以“当场击毙”法律规定为视点
2010-04-12董伟,陈军
董 伟,陈 军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警察行使职权时执法过当问题研究
——以“当场击毙”法律规定为视点
董 伟,陈 军
(三峡大学政法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通过对“当场击毙”问题的国内立法、国际人权法相关法的比较分析,提出了“当场击毙”侵害公民基本人权的观点,建议我国立法从本体和关联中进一步加强对公民基本人权(尤其是危害行为实施人的相关人权)的尊重,使法律效能与社会效应达到最大程度上的优化。
国内立法; 国际人权立法; 当场击毙; 人权保障; 执法过当
为了保卫国家和人民的财产与生命安全,为了遏止抢劫、绑架等恶性暴力犯罪,前几年各地公安机关纷纷出台了警察在执行公务中对于严重暴力的犯罪分子比如抢劫银行、运钞车等可以采取“当场击毙”的政策,规定对正在抢劫银行或运钞车等的罪犯,可以“当场击毙”。在银行门口挂出了大幅横幅,在运钞车上赫然醒目地印上这四个大字“当场击毙”。这一强制行为对犯罪份子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从而“当场击毙”也一度成为了一个令人肃然起敬、望而生畏的词汇。在犯罪分子为之一片哀号的同时,也引起了我们对这一措施和政策的一种逆向思考。
从现今的社会治安条件和该政策、措施的主观基点出发,“当场击毙”的实施应当更大程度上地加大力度,涉及犯罪形态及犯罪主体范围也应进一步有所突破,只有这样才能满足最初“立法者”之宏愿——以暴制暴、天下无事!以“当场击毙”为口号来威慑犯罪分子,威慑犯罪行为,的确是“没办法中的最好办法”,也的确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但与此同时,该措施也将公民的基本权利毫不犹豫地践踏在脚下。“当场击毙”的合法性和可行性如何?这值得我们深思!
一、国内正当防卫有关法律规定及分析
我国关于“当场击毙”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规定之中,包括对火器和武力的具体规定。
第一,《人民警察执行职务正当防卫规定》第1条规定:“执行拘留押解人犯遇有暴力抗拒,行凶等非常情况,人民警察必须采取正当防卫,使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丧失侵害能力或者中止侵害行为。”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可以按照1980年7月5日国务院批准的《人民警察使用武器和警械的规定》,使用警械直至开枪射击。”第5条规定:“人民警察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第二,《人民警察法》第5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执行职务,受法律保护。”
第三,《关于人民警察执行职务中实行正当防卫的具体规定》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关于对不法侵害采取正当防卫行为的规定,适用于全体公民。鉴于人民警察是武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在打击和制止犯罪、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保卫国家政权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负有特定责任,现对人民警察执行任务中实行正当防卫问题,做如下具体规定:一、遇有下列情形之一,人民警察必须采取正当防卫行为,使正在进行不法侵害行为的人丧失侵害能力或者中止侵害行为:(一)暴力劫持或控制飞机、船舰、火车、电车、汽车等交通工具,危害公共安全时;(二)驾驶交通工具蓄意危害公共安全时;(三)正在实施纵火、爆炸、凶杀、抢劫以及其他严重危害公共安全、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行为时;(四)人民警察保卫的特定对象、目标受到暴力侵袭或者有受到暴力侵袭的紧迫危险时;(五)执行收容、拘留、逮捕、审讯、押解人犯和追捕逃犯,遇有以暴力抗拒、抢夺武器、行凶等非常情况时;(六)聚众劫狱或看守所、拘役所、拘留所、监狱和劳改、劳教场所的被监管人员暴动、行凶、抢夺武器时;(七)人民警察遭到暴力侵袭,或佩带的枪枝、警械被抢夺时。”
第四,《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2条规定:“人民警察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可以采取强制手段;根据需要,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警械;使用警械不能制止,或者不使用武器制止,可能发生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使用武器。”第3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警械,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警棍、催泪弹、高压水枪、特种防暴枪、手铐、脚镣、警绳等警用器械;所称武器,是指人民警察按照规定装备的枪支、弹药等致命性警用武器。”第5条规定:“人民警察依法使用警械和武器的行为,受法律保护。”第9条规定:“人民警察判明有下列暴力犯罪行为的紧急情形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用武器:(一)放火、决水、爆炸等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二)劫持航空器、船舰、火车、机动车或者驾驶车、船等机动交通工具,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三)抢夺、抢劫枪支弹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的;(四)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实施犯罪或者以使用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相威胁实施犯罪的;(五)破坏军事、通讯、交通、能源、防险等重要设施,足以对公共安全造成严重、紧迫危险的; (六)实施凶杀、劫持人质等暴力行为,危及公民生命安全的;(七)国家规定的警卫、守卫、警戒的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袭击、破坏或者有受到暴力袭击、破坏的紧迫危险的;(八)结伙抢劫或者持械抢劫公私财物的;(九)聚众械斗、暴乱等严重破坏社会治安秩序,用其他方法不能制止的;(十)以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十一)在押人犯、罪犯聚众骚乱、暴乱、行凶或者脱逃的;(十二)劫夺在押人犯、罪犯的;(十三)实施放火、决水、爆炸、凶杀、抢劫或者其他严重暴力犯罪行为后拒捕、逃跑的;(十四)犯罪分子携带枪支、爆炸、剧毒等危险物品拒捕、逃跑的;(十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使用武器的其他情形。人民警察依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第五,《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条例》第六条第四款规定:“人民警察执行职务遇有拒捕、暴乱、袭击、抢夺枪支或者其他以暴力破坏社会治安不听制止的紧急情况,在必须使用武器的时候,可以使用武器。”
由此可看出,“当场击毙”的行为主体主要是执法人员(主要是人民警察),而并非是全体公民。也有学者指出,“当场击毙”实际上就是公民的无过当防卫,是一种正当防卫权的行使。对于这一点,笔者并不认同。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7条规定:“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采取的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于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一种普遍意义上的正当防卫行为。无过当防卫权是法律赋予个人的权利,强调个人的自救性,是合法利益与不法利益间的冲突中的特殊权利。而在刑法规定中并没有明确规定警察“现场击毙”的行为属于正当防卫。在正当防卫中,冲突双方的力量是基本均等的,或者是实施正当防卫者占下风。而在职务行为(现场击毙)中,执行职务行为的一方显然占有优势。公安机关是国家暴力机关,其权力来源于国家权力。警察的行为是职权行为。因此从刑法理论上而言,警察的职务行为不应属无过当防卫行为。其次,警察的职务防卫行为是不同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卫”的,它行使的是一种职务防卫权力。而正当防卫是公民的基本权利。“防卫权并非天赋的权利,而是来自于国家法律的授权,其次,防卫权是保证权利人利益的一种法律手段,因而,它是自主性的而非强制性的权利,这种自主性意味着权利主体既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使这项权利,也可以放弃这项权利”。即是说在出现正当防卫所规定的具体实际情况时,普通公民可以选择进行正当防卫,也可以选择放弃。对警察而言,在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必须行使职务防卫权,这是履行职责的表现,否则,就是违法。
二、国际人权立法相关规定及分析
早在1966年12月16日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就有对公民生命权保护进行国际法上的规定。其第6条第1款规定:“人人有固有的生命权。这个权利应受法律保护,不得任意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这可说是国际上最早对执法人员执行公务过程中所有可能造成“当场击毙”的法律约束了。虽然未经具体详尽的分类论述、规定,但从原则上给予“当场击毙”结果的产生以法律上的基本限制,因为“不得随意”这一用语在执法上可认为是强调合法性和必要性,禁止执法人员法外执法(无法律依据)、违法执法(违法法律)和合法但属于“滥用权力”的执法。同时,《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6条第1款的规定也为其后联合国以此为基础作出一系列的关于限制执法人员公务过程中暴力作为危害公民生命权的法律规定提供了立法上的依据。
《执法人员行为守则》第3条规定:“执法人员只有在绝对必要时才能使用武力,而且不得超出执行职务所必需的范围。”本条强调,执法人员应在特殊情况下才使用武力;虽然本条暗示,在防止犯罪或在执法或协助合法逮捕罪犯或嫌疑犯的情况下,可准许执法人员按照情理使用必要的武力,但所用武力不得超出这个限度。各国法律通常按照相称原则限制执法人员使用武力,即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与执行法律的要求是否相称(适当)。应当了解,在解释该条文时,应当尊重各国的这种相称原则。但是,该条文决不应解释为准许使用同所要达到的合法目标并不相称的武力。使用武器应认为是极端措施,应竭力设法特别不对儿童使用武器。一般说来除非嫌疑犯进行武装抗拒或威胁到他人生命,而其他较不激烈措施无法加以制止或逮捕时,不得使用武器。每次使用武器后,必须立刻向主管当局提出报告。
《有效防止和调查法外、任意和即决处决的原则》则对执法人员执法行为进行了进一步的限制。其第3条规定:“各国政府应禁止高级官员或公共当局授权或教唆其他人进行这种法外、任意和即将处决的命令。所有人员都有权利和义务违抗这种命令。对执法人员的培训应强调上述规定。”第9条规定:“应对一切可疑的法外、任意和即将处决案件、包括亲属控告或其他可靠报道提出在上述情况下发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进行彻底、迅速和公正的调查。各国政府应有调查办事处和有关程序来进行此类调查。调查目的应是确定死亡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对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任何可能造成死亡的模式或做法……”可见,虽然执法人员要严格依据法律执法,但为了防止执法人员借执法为借口,肆意践踏公民的生命权,联合国人权法律以防止法外、任意和即将处决为由,做出上述相关法律规定,用于保护公民的生命权不受非法、违法和滥法的执法行为的侵害。给政府、官员及公共当局以约束,不使其以“法外、任意和即将处决”(即不经审判予以处决)为奖励条件,来鼓励甚至教唆他人打击犯罪、保卫正义,尤以执法人员为胜。反之,赋予“所有人员都有权利和义务违抗这种命令”明确的抗争权,甚至引申为每一个人的义务,这在公法中是几乎不可而见的。同时,从制度上制定一系列程序,来严格约束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不经授权无以为执法根据。对于发生执法过程中死亡的事与人,不可简单处之;而是进行调查,确属无法避免造成死亡之行为,也应给与公开明确之说明,不可随意以合法谨慎执法为由,给行为定性作结。对于有可疑之行为,则必须“进行彻底、迅速和公正的调查”,“确定死亡的原因、方式和时间、对死亡负有责任的人以及任何可能造成死亡的模式或做法”,决不可在可以经审判时而不经审判,任意或故意处置其生命权,并决不可以官方命令作为一切不合适、不相称执法的原由。
三、关于警察职权设定的思考
同国际上通行的人权保护机制相比,我国国内立法对人权保护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我们的社会正处于复杂的转型期,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不规范的交往很容易诱发一些极端的个人行为。在这种不确定的威胁下,执法人员执法更应当追求人性化执法,加大对人民群众的人权保护力度,也不能忽视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保护,只有这样才能缓解现实社会中的矛盾,对人民负责。在此,笔者建议,应从如下方面加强对我国执法环境的规范:
第一,专门立法予以规定废除“当场击毙”的提法。按照我国的《立法法》,凡涉及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或处罚,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来规定。据此,像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权这类事关重大的问题,当然只能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来决定,即使中央政法部门和地方权力机关也无权擅自作出规定,更不用说地方政府或者某一部门了。
第二,设立等级标准,规范我国执法人员执法行为。标准问题是防范“当场击毙”情形产生的根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10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第9条都只针对相应情形规定了“可以使用武器”,但使用的“度”则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而所谓“标准”不可能针对已发生和可能发生的所有“突发事件”一一制定,但基本的标准并非法律不可规范。比如对突发事件或危险行为是否可以设定级别,在不同级别间划定击毙、击伤、谈判和控制的基本标准。同时,针对当事人及其亲属对警方处置方式可能提出异议,应当规定相应的听证程序,最终还应当可以进入司法程序,让警方的处置方式接受司法审查。在处理突发事件上,必须有法可依,对“击毙”这种剥夺生命权的绝对性手段,更不能脱离法律的精神和应有的基本标准。
第三,加强发展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执法工具及火器,并最大限度装备执法人员,以便可以在不同情况下有区别地使用武力和火器。好的执法工具既能最大限度威慑、限制犯罪嫌疑人的预备行为,也能在具体执法过程中最大限度保护犯罪嫌疑人不必遭受不必要的损伤,更能有效地保护执法人员自身的安全。大力开发使用非致命性执法工具,既符合当今国际潮流,又可大力改善西方对我国人权状况抨击的现状,还能真正体现我国“执政为民”的思想,可说是利远大于弊。
第四,规范执法系统中的监督机制、调查机制和处理机制。犯罪分子也是人,是人就有逃生的欲望。我们不能因为他是坏人就一毙了之。即使犯了死罪,他还要经过公开、公正的审判,严格按照诉讼程序行事,更何况许多被当场击毙的犯罪分子并未犯下死罪。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犯罪嫌疑人抢劫运钞车而未遂,也未造成严重后果和严重社会影响,那么罪尚不致死,而现在,仅因为他要逃跑,就“当场击毙”,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生命是宝贵的,只有在犯罪分子威胁到其他人的生命权包括执法干警的生命权,而且这种威胁迫在眉睫,又没有其他办法制止的情况下,才可考虑万不得已的开枪下策,而且也应仅使其丧失继续犯罪的能力为限,不可随意击毙之。除此之外,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可以剥夺违法犯罪嫌疑人的生命权的理由。对于违法执法、不规范执法或法外执法的情况,则需要执法系统中的内部监管系统发挥作用。应该借鉴香港警察监管系统——内部调查课,在我国各级执法机关中设立相关内部调查机构,专门监管执法人员执法不当的情况,以警惩执法人员中的害群之马,净化执法队伍,进一步树立执法人员的应有形象。同时,也应加大力度惩治违法乱纪执法之人员,“知法犯法,罪加一等”,使每一位执法人员时刻谨记自己身上的责任,依法执法,公正执法,恰当执法。
第五,要理性对待“群众拍手叫好”。长期以来,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了“以人民的名义”、“群众拥护和支持”来证明任何一项政策的合法性,但英国学者阿克顿的一段话也许会给我们以启发:“少数的压迫是邪恶的,但多数的压迫更邪恶。因为民众中蕴藏的力量若被唤醒,少数人将无法抵挡他们。面对全体人们的绝对意志,他们无可诉求,无可援助,无可躲避。”牛津大学犯罪学研究中心主任罗吉尔胡德院士在讨论死刑问题的研讨会上,针对有人提出民众支持死刑所以不能废除死刑的观点,他反驳道:“民众都希望减税甚至不交税,为什么政府还要求他们纳税呢?可见,政府不光是要听民众的,还负有引导民众朝着理性方向思考的职责。”
四、结语
在我国,之所以人们对“击毙”有着不同的评价,根本上还是发自于对生命的尊重。正义感使人们确信,那些正在实施剥夺他人生命的人是必须被阻止的,即使为此要消灭那个实施者的生命;反过来,一个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人,如果他的行为尚未或者已经不构成对他人生命的伤害,那么此时剥夺其生命显然就成为不必要,至于其罪该死,那应当由法庭说了算。这样的事一旦越过了正义的界限,反而会使正义蒙羞。我国法律未将“当场击毙”规定于具体法典中,并努力回避这个字眼,规避这个结局,其足以说明在立法思想上,我国还是十分注意各种情况下,特殊人员的基本人权保护的。只有获得法律的支撑,执法才能真正找到正确的“时机”,表现出应有的“果断”,人民群众的心目中也才能有一把相对明晰的尺度,进而作出符合理性的评价。
[1] 刘 权.政府立法的科学化探讨[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2] 崔 凯.刑事司法中的公共利益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2).
[3] 李国际,陈 军.法治环境中的契约自由[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2).
[4] 冯仁强,张 曦,李益明.司法规律与检察权配置的协调性研究[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09(1).
[责任编辑:马建平]
D 815.7
A
1672-6219(2010)06-0066-04
2010-10-20
董 伟(1965-),男,湖北京山人,三峡大学政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民商法学的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