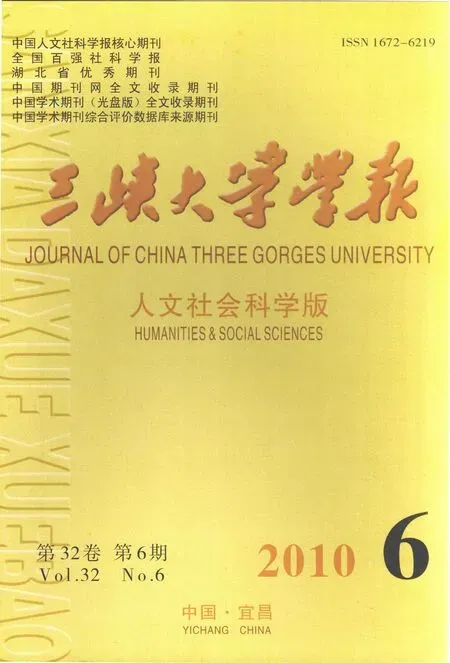论《红楼梦》的意境美
2010-04-12胡家全
杨 勇,胡家全
(1.三峡大学期刊社,湖北宜昌 443002;2.荆楚理工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论《红楼梦》的意境美
杨 勇1,胡家全2
(1.三峡大学期刊社,湖北宜昌 443002;2.荆楚理工学院,湖北荆门 448000)
“意境”是中国诗学的核心范畴,它同样适用于《红楼梦》。曹雪芹以其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在《红楼梦》中营造了一种博大、深沉而多层次的意境。《红楼梦》主要通过整体艺术构思、人物诗作、自然环境等来创造意境。
红楼梦; 意境; 意境创造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和文艺理论的一个重要范畴。刘禹锡对意境有一个最基本的规定——“境生于象外”,也就是说,意境首先是一种情景交融的“象”,但它又具有超越性,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趋向无限的“象”。司空图进一步指出“思与境偕”,标举意境的“象外之象”、“味外之旨”。明代王夫之则从情景关系进一步规定意境的内涵,提出“有形发无形,无形君有形”的深刻思想。叶朗主编的《现代美学体系》提出:意境是“‘意象’中最富有形而上意味的一种类型”,并进而指出“意境”的意蕴是一种“带有哲理性的人生感、历史感、宇宙感”[1]。文艺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层的人生哲理或精神内涵就是意境,它的意义就像黑格尔《美学》所说的:“意蕴总是比直接显现的形象更为深远的一种”。意境理论产生于作为抒情文学的古典诗歌,并普遍运用于中国绘画、戏曲、园林等传统艺术,但在中国古代小说等叙事文学的创作与批评中比较少见。曹雪芹以其丰富的文学艺术素养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深刻思考,以如椽之笔,在《红楼梦》中营造了一种博大而深沉的意境。《红楼梦》所开拓的多层次的意境使读者的审美体验超越了具体的形象和情节而达到对人生的深刻体悟。
一
《红楼梦》意境营造的方式有多种,首先是整体艺术构思、艺术风格的意境美。
清末小说评论家眷秋曾分析了《水浒》和《石头记》所创造的不同境界,他认为“小说之趣味与词颇近”,并把《水浒》、《石头记》比作辛弃疾、周邦彦的词,指出“《石头记》之境界惝怳,措语幽咽,颇类清真”,“《水浒》之雄畅沉厚,直逼稼轩”,最后他得出结论:“故小说必自辟特别境界,始足以动人”[2]。把一部鸿篇巨制与一首词进行类比,正是从整体艺术构思的角度来谈《红楼梦》的意境之美。今人对此多所关注,如认为《红楼梦》具有《离骚》式的抒情结构,曹雪芹是“将一首诗抒情结构衍变为一篇巨幅而详尽的叙述”[3];更有人借大观园来形容《红楼梦》的整体结构,认为“这包罗万象的园子已不仅是一幅故事情节的布景,而竟成为全部小说境界的本体”[4]。
曹雪芹由锦衣玉食坠入绳床瓦灶,个人遭遇的不幸促使他对生活有了更深切的感悟。“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可以说,正是这种对人生况味的咀嚼以及他自身的文化反思使《红楼梦》能达到一种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意境。
他将自身对世态人生的深切品味与审美情趣灌注在整体艺术构思上,在进行创作时“不仅仅注重人生的社会意义、是非善恶的评判,而是更加倾心于人生生命况味的执著品尝”,使《红楼梦》迥异于一般的世情小说,“在更宽广、更深邃的意义上,表现了人性和人的心灵”[5]。从而增强了其价值的普泛性,使历代读者痴迷不已。同时,小说通过对民族心理特征与历史文化意识的总体反思,在“好便是了,了便是好”的虚无主义尘雾笼罩下,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传统价值观和人生道路的厌弃鄙薄,对个性自由的热烈追求,对被摧残的美好心灵人生的深深同情与哀伤,对过往皆云烟、唯情可追忆的感叹。这样的整体化意境创造,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长篇小说在整体性意境创造方面要比篇幅短小或以抒情、写意为主的艺术品种困难得多,《红楼梦》可以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一个例外。这与曹雪芹精深的艺术修养和作品的整体艺术风格是密切相关的。
毋庸置疑,《红楼梦》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杰作,但全书又笼罩着一种神化的、虚幻的意境,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实。无才补天之石幻化为宝玉,赤瑕宫神瑛侍者凡心偶炽下凡造历幻缘变成贾宝玉,绛珠仙草为报其灌溉之情亦下凡为人还泪即为林黛玉,太虚幻境一群仙女遂陪同她下凡结案,一僧一道时时出入于现实、梦境与太虚幻境之中,如此等等。所有这些描写都使全书在整体艺术风格上构成一种空灵、超脱、幽远的境界,这和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也是一致的。作者惨淡经营的这一非现实的意境蕴含着他对人生的深切感受和体悟——其中虽有人生如梦、世事虚幻、“沉酣一梦终须醒,冤孽偿清好散场”等消极思想;但是,更主要的是,它包含着作者的伟大发现:平凡的人物来历不凡,实是其性格、精神、命运之不平凡;女子来自情天,又回到情天,为现实社会所不容;现实社会是“有法之天下”,而非“有情之天下”(汤显祖语)。可以说,《红楼梦》高度的思想性和不朽的艺术魅力正是与这一非现实的意境紧密相联的,割舍掉这一部分,《红楼梦》将不复为《红楼梦》矣。
不少研究者在论及《红楼梦》意境时往往局限于某一情节或章节,而忽视了对其意境整体性的研究。其实,“《红楼梦》的意境,既有浓缩的整体感,又具有象物质结构一样的可分性。全书构成一意境。很多章节也自成意境。各章节中,或情节,或场面,或细节,也各自构成独立的意境。同时每一个局部的意境,都与整体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包含在整体意境之中。”[6]忽视小说意境的层次性和整体性,无异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二
《红楼梦》营造意境的另外一个重要方式是作品中人物的诗歌创作。甲戌本《石头记》第一回在贾雨村中秋诗旁有一段脂批:“这是第一首诗,……余谓雪芹撰此书,中亦有传诗之意”。将自己的得意诗作借助小说这种形式写入书中以便流传,这是明清时期小说家常用的方法。曹雪芹是否有传诗之意姑且不论,但《红楼梦》中的诗词数量之多及其重要地位是众所周知的。曹雪芹具备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他能诗善画,才气纵横,在小说中有意识地融铸诗画等艺术的意境品格当在情理之中。
历史地看,由于传统的偏见,中国小说理论不甚发达。即使在小说获得空前发展并占据文坛主导地位的明清时期,小说仍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消闲品,小说评点家仍然较少关注意境理论对小说创作的影响。但是,古典诗歌抒情性向小说的不断渗透却是不争的事实。小说的诗化倾向不仅表现为直接运用大量诗词“成为小说的一种表现手段”,并构成“中国古代小说艺术的民族形式的基本特征之一”[7],而且表现为小说的某些章节或段落化入了诗词的意境。《红楼梦》的评点者脂砚斋就曾多处点明小说富于意境美的章节,并云“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第25回庚辰脂批)。
《红楼梦》通过人物的诗作来营造意境,最典型的莫如黛玉葬花吟。过去红学家大都把《葬花词》看成是林黛玉自作的诗谶,其实整首《葬花词》不仅是林黛玉“质本洁来还洁去”的人格精神的集中体现,而且含蕴着对人生的哲理思考:其中既有“柳丝榆荚自芳菲,不管桃飘与李飞”所寄寓的对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愤懑以及“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所发出的对无情现实的控诉,也有主人公从自然界的“春残花渐落”、“明媚鲜妍能几时”所感悟到的人生亦有“红颜老死时”、青春易逝、人生短促的遗憾;而“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既是对现实人生的否定,更是对纯净自由的理想人生境界之向往,同时读者从这种强烈的渴望中深深感受到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在沉重的封建压迫下探索人生道路时的迷惘和艰难。因此,笔者认为,这首《葬花词》与其说是林黛玉身世遭遇的写照及其性格特征的凸显,毋宁说它经营了一种凄清哀艳的人生境界。正因为如此,后世读者在对葬花这一情节引起共鸣的同时就会超越具体的意象(零落的桃花)和具体人物形象(黛玉)的不幸遭际而达到对社会、对人生、对生命的深切感受和启悟。
它如咏菊诗、海棠诗等等,无一不是通过情景交融的意象既表现了诗作者(宝、黛、钗、湘等人)的性格、气质和精神,同时又含蕴着他们各自独特的人生感慨,其意蕴虽各不相同,但其意境之美同样引人入胜。即使是俚俗如《好了歌》,如果和《好了歌注》合起来看,也自有其意境在。
《红楼梦》是一部诗化了的小说杰作。它那行云流水般的叙述中处处沁透着诗情的芬芳,其中的大量诗词曲赋犹如镶嵌在碧海青天里的星星,闪耀着奇异的光芒。甚至可以说,《红楼梦》就是一首婉约的诗,生命和美是它吟诵的主题,而意境则是它的灵魂。不难想象,如果没有意境,《红楼梦》将会成为一场毫无意义的红粉丽人秀。
尽管如此,《红楼梦》通过人物诗作来创造意境仍有别于古典诗词的意境。中国古典小说的本质是叙事与再现性艺术,其意境创造不能脱离塑造人物形象这一根本特征;其意蕴也更为深邃,往往寄寓着深沉的人生感和历史感。《红楼梦》的意境创造是对诗词意境创造的巨大发展,它将叙事与抒情、再现与表现、写实与写意、人物塑造与意境创造完美地统一起来,并以这种独特的美学风貌屹立于世界小说之林。
三
对自然景物和环境的描写也成为《红楼梦》创造意境的重要手段。
意境最初产生于中国古代诗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往往在登临之际,诗人通过对自然山水的审美观照达到“身与物化”、“天人合一”的状态,并进而超越具体的物象,“与天地精神往来”,体悟到人生的某种真意。因此中国古代那些登临诗和山水田园诗每每最富意境。前人说得好:“诗以山川为境,山川亦以诗为境。”[8]王昌龄最初就是在谈到山水诗的创作时提出“意境”这一美学范畴的。在《红楼梦》中,自然景物或用以渲染环境气氛,或作为人物性格的陪衬,或以为人格精神的象征,而寄寓深沉的历史感或人生感受于其中,这样,读者在审美欣赏和审美再创造活动中就会通过情景交融的意象进入一种富有哲理意蕴的意境[9]。《红楼梦》在这方面别具匠心,对潇湘馆里那些修竹的着力刻画即是一例。
在曹雪芹笔下,“竹”不是作为一般的意象出现,而是有深意存焉。“岁寒三友”向来是中国画的主题,经过长期的文化心理积淀,“竹”在中国人(特别是文人)眼里已成为一种人格美的象征。小说中的竹,从总体上而言,是林黛玉风流雅致、孤芳自赏、愤世嫉俗、宁折不弯等人格精神的表征;同时,作者又不惜笔墨,先后六次从不同视角以不同方式对“竹”这一意象进行有层次的深化,从而使之具有更丰富深厚的意蕴。第十七回“大观园试才题对额”首次从贾政等人的视角写潇湘馆“一带粉垣,里面数楹修舍,有千百竿翠竹遮映”;第二十三回则直截写出林黛玉对翠竹的喜爱:“那几竿竹子隐着一道曲栏,比别处更觉幽静。”寥寥数笔摹写了潇湘馆清幽的环境并点名主人公的精神气质与竹有共通之处。第二十六回写宝玉看见潇湘馆“凤尾森森,龙吟细细”,这是情人眼中之竹,为竹绘形绘声。同时,浓密茂盛的竹叶如舒展之凤尾恰是林黛玉优美体态的象征,而微风拂动竹叶发出的飒飒声响应和着“每日家情思睡昏昏”的叹息,正是初恋之中的黛玉在礼教重压下发出的幽怨的心声。第三十五回则写竹影:“满地下竹影参差”,“窗外竹影映入纱来,满屋内阴阴翠润,几簟生凉”。斑驳的竹影使潇湘馆更显得沉寂、静谧、清冷和凄凉,恰如其分地映衬了林黛玉苦闷、怨愁的思绪和凄凉的心境。第四十四回则通过刘姥姥的眼睛写出:“两边翠竹夹路,土地下苍苔布满,中间羊肠一条石子漫的路”,这正是林黛玉狭窄艰险的人生之路的象征。林黛玉生活在那个“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环境里,不仅不能自由地发展个性,而且要时刻提防地下的“苍苔”,其人生可谓艰难矣。第四十五回又写阴沉墨黑的黄昏,秋风、秋雨以及雨滴竹梢的秋声使潇湘馆沉浸在凄风苦雨之中。这风雨交作之势正是封建势力对林黛玉迫害加剧的象征。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竹”这一特定意象不仅是对林黛玉体态、人格、处境及其心情意绪的形象展示,而且深含着主人公独特的人生感受。因此,从更深的层次上讲,我们感受到的是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风流而凄迷的人生境界。
小说人物对自然景物的欣赏亦能创造出意境。如《红楼梦》第五十八回贾宝玉对杏花的观赏。作品写贾宝玉病中去瞧林黛玉,看见堤上“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由此生发出许多感慨。小说细腻入微地刻画了宝玉的心理活动——宝玉起初想到自然景物的变化:“能病了几天,竟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倒‘绿叶成荫子满枝’了!”随之而生的是抱愧和留恋之情;继而宝玉又由自然的变化联想到人事之变迁,即邢岫烟已择夫婿一事,其心情是对又将失去一个好女儿的惋惜和同情;接着宝玉又由近及远,由现在想到未来:“再过几日,这杏树子落枝空,再几年,岫烟未免乌发如银,红颜似槁了。”未来是落寞凄凉的,令人感伤,不堪想象;宝玉进而由杏树枝上的啼鸟联想到人生虽然变化不定,前途未卜,但尚有一丝慰藉,那就是情的补偿作用。对女儿们的一片真情和对林黛玉的纯洁爱情使贾宝玉落寞的人生带上一丝亮色,失去了情,其人生便会显得毫无意义。“情”正是贾宝玉观察现实、评价人生的尺度和出发点[10]。“情”作为其生命哲学的核心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贾宝玉从自然现象感悟到的人生真谛,至少在此时,宝玉从雀儿对杏花的依恋、同情体会到“情”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结合下文所描写的“杏子阴假凤泣虚凰”情节我们更能体会到这一深意。总之,曹雪芹通过杏花这一意象营造出一种包含作者自己(也是贾宝玉)独特的人生感受的意境。与杜牧寻春因“狂风落尽深红色”而生惆怅不同,贾宝玉是在叶稠阴翠之时就想到了将来的凋残,一是因衰生叹,一是由盛见衰;一是托物言志,一是由物及人,思考生命的去向和含义,显然小说的意境更深一层。
[1] 叶 朗.现代美学体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139.
[2] 眷 秋.小说杂评[M]//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259.
[3] K.Wong.红楼梦的叙述艺术[M].黎登鑫,译.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7:3.
[4] 浦安迪.红楼梦与“奇书”文体[C]//93中国古代小说国际研讨会论文集.北京:开明出版社,1996:354.
[5] 宁宗一.红楼梦·前言[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5.
[6] 姜耕玉.红楼梦艺境探奇[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6.
[7] 林 辰.古代小说与诗词[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3.
[8] 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评诗[M]//胡经之.中国古典美学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8:248.
[9] 车淑萍.论王蒙的《红楼梦》研究对文学批评的启示[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1).
[10]杨 勇.论《红楼梦》里的龄官及其爱情悲剧[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
[责任编辑:赵秀丽]
I 206.2
A
1672-6219(2010)06-0032-04
2010-07-16
杨 勇(1968-),男,湖北当阳人,三峡大学期刊社副编审,文学硕士,主要从事编辑理论和明清小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