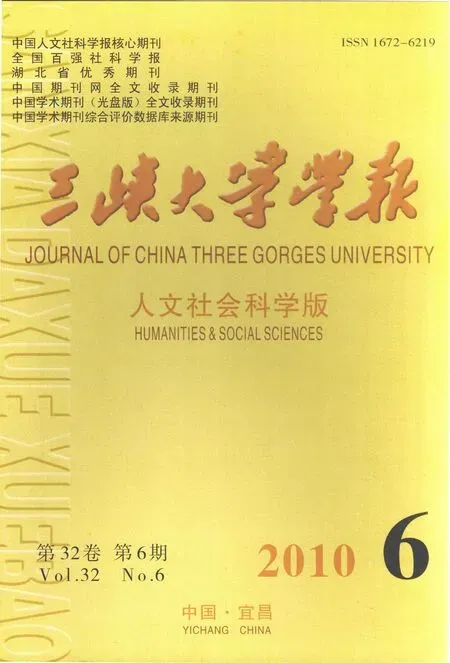南冠之思与南冠之诗
——以陈亡入隋文人群体及创作为中心
2010-04-12李建国
李建国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南冠之思与南冠之诗
——以陈亡入隋文人群体及创作为中心
李建国
(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以陈亡入隋文人及其创作为中心,探讨了所谓“南冠之思”是作为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悲剧性生命体验,包括对南方故土的乡关之思,对国家倾覆的惨痛记忆,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失落感和旧臣情怀,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感。这种体验的语言呈现构成“南冠之诗”,从而反过来昭示、确认并强化了他们的存在悲剧。从文学史来考察,南冠之诗还明显突破了南朝文人原来的审美情趣,导致诗歌的新变。
南冠之思; 南冠之诗; 南陈; 隋代; 文学史
一
南冠本是春秋时期北方人对南方楚人所戴之冠的称谓。《国语·周语》云:“陈灵公与孔宁、仪行父南冠以如夏氏。”韦昭注云:“南冠,楚冠也。”[1]67从此条文献可见,北方贵族也有戴南冠者,当是南北文化交流的结果。南冠成为中国文化体系中一个特定的符号,典出《左传·成公九年》:
晋侯观于军府,见钟仪,问之曰:“南冠而絷者谁也?”有司对曰:“郑人所献楚囚也。”……问其族,对曰:“泠人也。”公曰:“能乐乎?”对曰:“先父之职官也,敢有二事。”使与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对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问之,对曰:“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不知其它。”公语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称先职,不背本也;乐操土风,不忘旧也;称太子抑无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旧,信也;无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虽大必济。”[2]309
缘此,南冠凝固为一个有着特殊文化意味的语词,指被俘囚或因其它变故而羁留异国他乡者①。由于南北文化的差异与阶段性的政治隔离,南冠一词在很大程度上专指那些被羁留和掳掠至北方的南方人。南冠作为符号,不仅强调虏囚或羁旅的身份,而且积淀了“不背本”、“不忘旧”等文化精神之坚执。双重的煎熬给他们带来无尽的哀思与深沉的苦痛,成为他们生命存在与体验的文化心理原型,不妨称之为“南冠之思”。
所谓“南冠之思”是指入北的南方人士在遭遇变故后,对自身存在状态的一种悲剧性生命体验。具体说来,对南方故土的乡关之思,对国家倾覆的惨痛记忆,对自身社会身份的失落感和旧臣情怀,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感,构成了南冠之思的几个主要层面。这种体验的语言呈现构成“南冠之诗”,从而反过来昭示、确认并强化了他们的存在悲剧。
南冠之诗在南北分裂和政权易代之际,往往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征之集部,“南冠”一语在中国文学中的意象化,始于南北朝时期。其时,南北各方长期处于军事、政治、文化对抗之中,内部的权力倾轧和争斗也异常激烈,上层人士的非正常流动比较频繁。从总体状况来看,由于北方在军事力量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由北入南者数量相对少,且以政治人物为主。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北魏末年北海王元灏南投,后来又在梁武帝的扶持下回洛阳试图称帝。而南朝士大夫被掳掠、羁留,或无奈北奔者则相当多,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的南冠群体。
他们在北方异邦充分体验到南冠之痛,其文学创作亦由此蒙上浓厚的悲剧色彩,属于典型的南冠之诗。比如庾信,他在诗文中不止一次强调自己的南冠身份。其《率尔成咏》诗云:“昔日谢安石,求为淮海人。彷佛新亭岸,犹言洛水滨。南冠今别楚,荆玉遂游秦。倘使如杨仆,宁为关外人。”[3]339在与北周诸王交往的《又谢赵王赉息丝布启》亦云:“南冠获宥,既预礼延;稚子胜衣,还蒙拜谒。”[3]570而他的《哀江南赋》则可称得上是南冠之诗的巅峰之作。赋中有云:“钟仪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孙行人,留守西河之馆。”[3]99序言所谓“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3]95,即当以南冠之痛为注脚。倪璠为庾信集作注,其题辞云:“予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若夫《枯树》衔悲,殷仲文婆娑于庭树;《邛竹》寓愤,桓宣武赠礼于楚丘。《小园》岂是乐志之篇,《伤心》非为弱子所赋。《咏怀》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连珠》之四十四章,汉将自循其发。……凡百君子,莫不哀其遇而悯其志焉。”[3]4-5凡其悲怨述怀之作,无不可视为南冠之思的艺术表达,所以后人认为:“钟仪之悲,开府为至矣。”[4]本文重点观照的是南陈灭亡后,由陈入隋的这批文人的境遇与创作,因为他们是整体沦为南冠,故最具代表性。
二
随着南陈灭亡,江左士族和官僚贵族大多迁入关中。隋承周制,选举上打破旧门阀士族的政治特权,注重功勋和实际行政能力,江左士族原来以门荫入仕的道路行不通,而他们又缺乏实际政治才干,无法迅速进入新政权体制。隋文帝素不喜南朝文化,依靠文化修养而得到现实政治利益的可能性也不大。所以刚入隋时,有些江左旧贵族陷入了非常困顿的境地,连生活都难以维系。虞世基入隋后“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傭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悽切”[5]1572。虽然被授予了官职,却家贫如此,南陈降人的处境可见一斑。出身皇族的陈子良一家更为凄苦,他回忆甫入关时,“……家君有钟仪之操,怀敬仲之心,遂屏跡杜门,茹忧成疾。忽悲风树,痛深陟岵。其時,余年十九,尔(陈子良弟陈子干)始八岁,伶仃辛苦,实廹饥寒。青门乏种瓜之田,白社无容身之地。一溢之米巳索,一瓢之饮屡空。日夕相悲,分填沟壑”[6]4457。虽不无夸张,但也确实反映南陈旧贵们入隋后一度非常狼狈的窘境。
入关之时,南朝旧人对新政权的排斥和精神上的痛苦非常强烈。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南陈君臣尽数被俘,很多家属女眷都成了隋军的战利品,所遭受的政治耻辱令他们痛心。开皇九年,隋军凯旋班师。“献俘于太庙,陈叔宝及诸王侯将相并乘舆服御、天文图籍等以次行列,仍以铁骑围之”,完全将他们作为战利品展示。后来“帝坐广阳门观,引陈叔宝于前,及太子诸王二十八人,司空司马消难以下至尚书郎凡二百余人。帝使纳言宣诏劳之,次使内史令宣诏,责以君臣不能相辅,乃至灭亡。叔宝及其群臣并愧懼伏地,屏息不能对。既而宥之”[7]5516,可谓恩威并施。而北周武帝灭北齐后,接见齐后主高纬,“降阶,以宾礼见之”[7]5372。两者之待遇不可同日而语。陈叔宝后宫诸姬还有他们的许多女性亲属,则或入文帝后宫,或赐与功臣为妾。人事如此,情何以堪。
其次江左士人对南方政权的认同感和向心性要执着得多。自五胡乱华以来,南方就以华夏文化正朔自居。面对北人,充满了文化优越感,常呼之为夷狄。这种文化心态不仅形成文化认同感,还直接强化了政治向心性。出身南朝世家的周罗睺,是江左难得的文武双全之才。史载:“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时罗睺守上江)。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睺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乃降。髙祖慰谕之,许以富贵。罗睺垂泣而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贺若弼谓之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渉,果如所量。’罗睺答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知可也。’”[5]1524周罗睺在降隋后,始终保持一贯的节操和尊严。直到大业初,陈叔宝去世,许善心与周罗睺、虞世基、袁充、蔡征等同往送葬,许善心不避忌讳,在所写的祭文中仍称陈叔宝为陛下[5]1428。正因为这样,江左士人入关后,虽然被迫接受了国破家亡的事实,但降虏之耻深深地刺激他们敏感而脆弱的心灵;虽然客观上承认关陇集团的军事胜利和政治统治,但长期以正朔自居的文化尊严在此情境下更加深了他们的精神痛苦。
南朝的历史文化培育了江左士人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如此巨大的精神创痛激发了他们一度柔弱纤靡的情绪体验。在吞声含辱的生存境遇中,诗歌成为他们的唯一的宣泄途径。
三
从现存的作品来看,对故乡的思恋是“南冠之诗”的普遍心声。陈子良《于塞北春日思归》云:
我家吴会青山远,他乡关塞白云深。为许羁愁长下泪,那堪春色更伤心。惊鸟屡飞恒失侣,落花一去不归林。如何此日嗟迟暮,悲来还作白头吟。②
关西风光与江南风情迥然不同,这种巨大的差异对被迫离开故土的江南士人们来说,无疑是更大的刺激。这“羁愁”使得他们在很长时间内一直将自己视作“客”,并以此定位自身与新帝新朝的关系。这种定位当然更多地含有情感方面的因素,“客”中的心态也更多地凸现为悲痛的情怀。像刘梦予《送别秦王学士江益》所云:“百年风月意,一旦死生分。客心还送客,悲我复悲君。”同为异乡客的江南士人们除了缅怀故乡和旧国,还能有何作为。而故乡渺渺,遥不可期,人在新朝,身不由己,所谓“乡关不可望,客泪徒沾衣”(周若水《江学士协》)。江左士人对故乡的思念不仅缘于节物风光的不同,还包含了一种文化的疏离。江总与薛道衡、元行恭等人唱和的《秋日由昆明池》就含蓄地表达了这种惆怅:
灵沼萧条望,游人意绪多。终南云影落,渭北雨声过。蝉噪金堤柳,鹭饮石鳞波。珠来照似月,织处写成河。此时临水叹,非复采莲歌。
“采莲歌”是江南水乡的典型风情之一,在干旱的西北之地绝难得闻。虽然关中大地的壮阔气象对江总不乏新奇的审美意味③,但还是那软侬娇媚的采莲曲更让人流连难忘。
离乡同时意味着去国,以及一种政治身份的失落。虞世基《述怀》云:“去国嗟人事,返袂岂须论。岭外无春草,何处觅王孙。”④这里“何处觅王孙”不仅指自己去国离乡,更深层的含义还在于,王孙一旦去国离乡就会彻底丧失他们原有的政治身份和优越感。所以,尽管虞世基后来在炀帝朝荣登高位,写了很多与炀帝唱和的宫廷诗。但他在入关之时是无比沉痛的,一路写来,泣不成声:
敛策暂回首,掩涕望江滨。无复东南气,空随西北云。(《初渡江》)
陇云低不散,黄河咽复流。关山多道里,相接几重愁。(《入关》)
由南陈贵戚转眼间变成南冠俘囚,如此巨大的身份落差自然引发无限的悲愤,吕让的《和入京》表达得最为直白:
俘囚经万里,憔悴度三春。发改河阳鬓,衣余京洛尘。钟仪悲去楚,随会泣留秦。既谢平吴利,终成失路人。
这样的境遇当然更增强了他们对故国的追伤,即使在政治高压之下,旧臣情怀还是难以完全断绝。旧臣情怀表达得最为激烈的当属江总之《哭鲁广达》:“黄泉虽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义死,不作负恩生。”号为“狎客”的江总也终于在鲁广达的悲愤辞世中,唤醒了沉睡已久的政治伦理感,发出如此激昂之声。这种身份失落感和旧臣情怀,源于前文所说的耻辱感和文化自尊,并且保持得相当顽强。
造成此种身份失落的原因只有一个:亡国。入隋后的江左士人对这场巨大的变故并没有从政治和历史的角度来理性思考,他们的体验是相当感性的,那就是“忽闻朝市变,斯乐眇难追”。他们的惨痛记忆在于转瞬换了人间,以及由此给他们带来的创痛。周若水这首《答江学士协》正是在今昔对比之中,流露出亡国之痛的个人体验。诗曰:
弱龄爱丘壑,与子亟忘归。开襟对泉石,携手玩芳菲。忽闻朝市变,斯乐眇难追。意气酒中改,容颜镜里衰。祁寒伤暮节,落景促余晖。野旷蓬常转,林遥鸟倦飞。故友轻金玉,万里嗣音徽。乡关不可望,客泪徒沾衣。
而这种惨痛体验进一步转化为他们对人生和命运的幻灭感与悲剧感。王胄的《酬陆常侍》、《言反江阳寓目灞涘赠易州陆司马》、《别周记室》和虞世基的《秋日赠王中舍》等诗都集中表现了以上多种情绪。这里引第一首:
相知四十年,别离万余里。君留五湖曲,予去三河涘。寒松君后凋,溺灰余仅死。何言西北云,复觌东南美。深交不忘故,飞觞敦宴喜。赠藻发中情,奇音迈流征。追惟中岁日,于斯同憇止。思之宛如昨,倐焉逾二纪。畴昔多朋好,一旦埋蒿里。无人莫已知,有恸伤知已。抱臂还相泣,岿然吾与子。沾襟行自念,哀哉亦已矣。吾归在漆园,著书试词理。劳息乃殊致,存亡宁异轨。大路不能遵,咄哉情何鄙。
诗中既有对故乡的思念,又有今昔对比的惨痛;既有物是人非的感慨,更有人生倏忽的悲凉。清辞丽句在此已经失去原有的美学意义,“思之宛如昨,倐焉逾二纪。畴昔多朋好,一旦埋蒿里”,“抱臂还相泣,岿然吾与子”这样自然和直白的表达才是性情的真实流露,所谓“直述真情,虽率亦复悲”[8]。对人生和命运的悲剧体验,渗透到他们的意识深处,即使以往容易流于游戏或宫廷格调的咏物诗也被改造,虞世基《零落桐》云:“零落三秋干,摧残百尺柯。空余半心在,生意渐无多。”虽不知作于何时,有何寓意,但我们宁可相信它是在入隋之初的悲郁心境中所为⑤,这“生意渐无多”的梧桐不就是那“怏怏不平”的落魄诗人吗?
南陈入隋之人中身份最为特殊者非后主陈叔宝莫属,他也是一位天才的诗人。但较之后世南唐李后主入宋后的沉痛,此人虽为南冠之首领,却似乎全无悲痛。相反,他还写了这样一首《侍宴应诏诗》:“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太平无以报,愿上东封书。”此诗乃其随隋文帝东巡,登芒山而赋,歌功颂德,建议封禅。所亡之国是他的国,身份落差最大者也是他,按说人生之无常感最强者以及悲剧体验之最沉痛者也应该是他,陈叔宝却能写出这样的诗来,难怪文帝曾称其“全无心肝”[7]5519。其实仔细想想,他这样做也不无道理,亡国之臣还有利用价值,亡国之君有几个能落得善终,陈叔宝入隋后终日买醉,图的就是苟全性命。他的所作所为从另一个侧面加深了我们对入隋后南陈士人境遇的理解和同情。说来奇怪,陈叔宝这几句诗倒获得过不少佳评,谢榛《四溟诗话》卷二云:“陈后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气象宏阔,辞语精确,为子美五言句法之祖。”[9]1159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三也说“在沈宋集中,当为绝唱”[10]1000。因人废言固然不可,但这样的作品还是让人觉得不堪。一联,非亲历丧乱不能道。而《于长安归还扬州九月九日行薇山亭赋韵》:“心逐南云逝,形随北雁来。故乡篱下菊,今日几花开。”构思依然精巧,上承薛道衡《人日思归》,下启王维《杂诗》“君自故乡来”。语言淡雅,“哀伤至情,语短而意无极”[8]。此诗韵味深远,意境浑成,已不殊于盛唐时期的五绝名家。而像作于南归途中的《并州羊肠坂》:
三春别帝乡,五月度羊肠。本畏车轮折,翻嗟马骨伤。惊风起朔雁,落照尽胡桑。关山定何许,徒御惨悲凉。
情绪更为激荡,连一贯清雅的语言风格也发生了些许改变。从江总的诗风变化,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一个作家的风格的改变,更多地受到由于人生命运的转变而导致的生命体验之内涵的影响。而当我们考察虞世基等诗人的创作时,不难发现,随着他们在隋代政坛重新确立自己的地位和身份,南冠之思逐渐消解了,诗歌创作也开始故态重萌。
注 释:
四
这些南冠诗人现存的作品不多,且以入隋后之作为主,因此对大多数作家来说,无法考察其前后文风之变化⑥。但有充分的迹象显示,他们入隋后的风格发生较明显的转变。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家是江总,尽管他后来回到江南,但其创作仍可视为南冠之诗的延续。江总在陈时就已经文名大著,徐陵、张正见之后当以此公为文坛巨擘。入隋时江总已年近七旬,所以开皇十三年放归江都,次年即卒。关于江总入隋前的文风,《陈书》本传云:“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故为后主所爱幸。多有侧篇,好事者相传讽玩,于今不绝。”[11]347从其现存作品来看,确实有一些宫体艳诗,比如《秋日新宠美人应令诗》、《新入姬人应令诗》等。但更多的是诸如赋得、咏物、唱和、应酬诗等样式的纯宫廷诗。语言风格倒也并不怎么浮艳,以清丽闲雅为尚,也就是所谓的“清气”。亡国之后,江总诗歌为之一变,一往长悲,首首都是真情实感的流露,意绪极为悲凉,沉痛蕴籍,与此前诗风大异,前引《哭鲁广达》即是明证。他的《南还寻草市宅》:
红颜辞巩洛,白首入轘辕。乘春行故里,徐步采芳荪。径毁悲求仲,林残忆巨源。见桐犹识井,看柳尚知门。花落空难遍,莺啼静易喧。无人访语默,何处叙寒温。百年共如此,伤心谁复论。
乃其南归后所作,物是人非,情景悲切。“见桐”
① 参见《辞源》“南冠”条,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421页。随着文化语境的演变,“南冠”有时候也仅指称阶下之囚,比如初唐骆宾王《在狱咏蝉》“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之句。
② 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华书局1983年出版,本文所引诗歌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该书。
③ 王船山《古诗评选》卷六称:“终南”一联,“大极远而细入微,声偶得此,雄视千秋”。
④ 此诗乃骆玉明、陈尚君据唐僧皎然《诗式》卷四补入,见《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补遗》,《文学遗产》1987年第2期。
⑤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五云此诗后二句“语太甚,不能信之”,正点出其有所寄寓。倒是他自己疑心太甚,不相信世基一度处于如此悲凉幻灭的心境之中。
⑥ 这里所说的前后变化是指在陈时和入隋后的不同,就虞世基、王胄等人而言,存在着南冠之诗与后期炀帝朝文风的明显差异。
[1] 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 春秋三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庾 信.庾子山集注[M].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北京:中华书局,1980.
[4] 王士禛选.闻人倓笺.古诗笺·凡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5] 魏 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6] 陈子良.平城县正陈子干诔[M]//李 昉,等.文苑英华.北京:中华书局,1966.
[7]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8] 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六[M].乾隆十三年刻本.
[9] 谢 榛.四溟诗话[M]//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0]王世贞.艺苑卮言[M]//丁福宝.历代诗话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责任编辑:杨 勇]
I 206.2
A
1672-6219(2010)06-0028-04
2010-08-26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隋代文学研究”(07JHQ0031)。
李建国(1973-),男,土家族,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汉唐文学及文学批评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