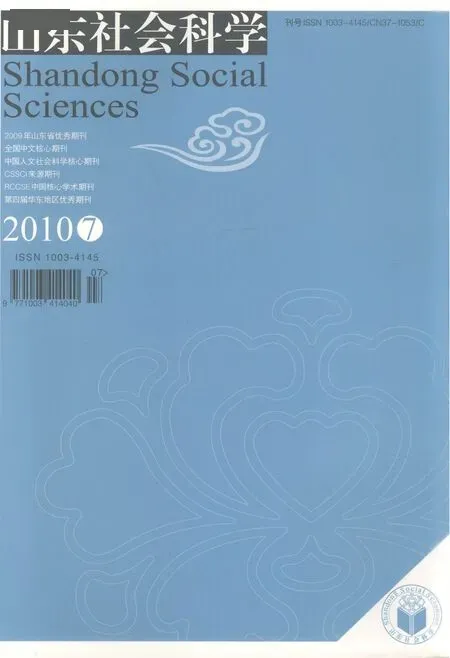文学典型论争的美学思考3
2010-04-12胡灿
胡 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文学典型论争的美学思考3
胡 灿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成都 610064)
在“典型”这一美学概念传入中国后,1935—1936年发生了以胡风和周扬为主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论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刚刚引入我国、而国内典型理论还基本上处于一片空白的草创阶段,这对我们加深对典型本质的理解和对典型艺术特征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来的典型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国文学史上典型理论的建设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文学;典型论争;美学
我国现代文学界先后展开了诸多的文艺论争。先是关于“民族主义文学”的论争,这是左联和国民党几个文化领袖为争取文艺领导权的一次斗争。然后发生了左联与“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京派”与“海派”的论争,左联内部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左联与“战国策”派的论争,等等。典型的论争是一次相对比较特殊的论争,因为,与其它论争相比,它是一次基本上无党派性的、纯文学的论争。
关于文学典型的论争主要是1935-1936年发生在胡风与周扬之间,他们的论争也吸引了其他人,如:茅盾、冯雪峰、艾芜等等,这些人纷纷撰文参与论争,发表自己的见解。胡风与周扬之间关于典型的论争到1936年就基本上结束了,但是,由他们的论争引发的、关于典型的更大范围内的争论一直延续到40年代,甚至到建国后还有反响。本文仅就胡风与周扬的论争进行美学上的思考,阐明这场论争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一、“典型论争”的缘起与过程
1、“典型论争”缘起。据笔者目前已发现的资料所载,在我国最早引入“典型”这个美学概念的应是鲁迅,1921年4月,他在《译了〈工人绥惠略夫〉之后》一文中就使用了“典型”和“典型人物”的概念。1924年,创造社的成仿吾在《创造》(季刊)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呐喊〉的评论》一文,文中使用了“典型的性格”(typicalcharacter)的概念。1932-1934年,瞿秋白在《现实》、《读书杂志》和《译文》等刊物上相继用俄文编译和发表了恩格斯的几篇文艺通讯,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1934年12月,胡风在《译文》第1卷第4期发表了根据日文翻译的恩格斯的《致敏·考茨基》一信的全文。1935年11月,《文艺群众》第2期上发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文艺问题的五封著名书信的译文。这些信中很多地方就谈及“典型”,涉及“典型”的有关理论。这就为典型的论争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2、“典型论争”的大致经过。1935年5月,胡风为了答文学社问写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此文在同年12月的《文学百题》上发表,文中谈到了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但对典型的特殊性的界定不是很准确。1936年1月1日,周扬在《文学》第6卷第1号上发表了《现实主义试论》一文,文中附带提及了典型,并在第5节中指出了胡风的谬误,试图帮他修正典型的特殊性这个概念。针对周扬的批评,胡风在同年的《文学》第6卷第2号上发表《现实主义的一“修正”》一文进行反驳,坚持自己的立场,并认为周扬对典型把握得不够,陷入在混乱里面了,是对恩格斯的话误解的结果。1936年4月1日,周扬又在《文学》第6卷第4号上发表《典型与个性》一文,认为陷入混乱的是胡风自己,最后跳出论争的圈子,把话题引入到现实生活中去,给胡风加上了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接着,胡风在同年的《文学》上赶紧发表了《典型论的混乱》为自己辩护。这是他们论争的整个经过。
二、“典型论争”的内容
1935年胡风发表了《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文中谈到了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问题。胡风对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作了界定,认为:所谓普遍的,是对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群里的各个个体而说的;所谓特殊的,是对于别的社会群或别的社会群里各个个体而说的。并举例说,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的少数落后地方和农村无产者说,阿Q这个人物的性格是普遍的;对于商人群地主群工人群或各个商人各个地主各个工人以及现在的不同的社会关系里的农民而说,那他的性格是特殊的了。①③④⑥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第342-345页、第343-345页、第346页。胡风在关于典型的特殊性的界定中,存在很明显的理论漏洞。所以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一文中附带提及了典型,指出了胡风的谬误,帮他修正了典型的特殊性这个概念。他认为这解释是应该加以修正的。阿Q的性格就辛亥前后以及现在落后的农民而言是普遍的,但是他的特殊性却并不在于他所代表的农民以外的人群而言,而是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阿Q的性格单单是不同于商人或地主,他就不会以如此活跃生动的姿态而深印在人们的脑海里的。因为即使是在一个最拙劣的艺术家的笔下,农民也总不至于被描写成和商人或地主相同的。②⑦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1页、第163页。
本来周扬为胡风修正这个错误应该是很有积极意义的。因为他注意到了典型形象的个性特征,这有可能使我们把关注的重心放到丰富多彩的各个个体身上,放到典型的审美艺术特征上来。但胡风对周扬给自己的修正并不接受,相反,他写了《现实主义的一“修正”》一文,极力为自己辩护,并对周扬的“修正”反“修正”,用胡风的话来说是对周扬的“‘修正’的‘修正’”。胡风首先摆出上面周扬“修正”的那段话,接着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说阿Q这性格对于某一类农民是普遍的,周扬先生却说阿Q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是特殊的存在。两个意见完全相反。”指责周扬是“对于典型的普遍性的一侧面的否定”,是“前后矛盾”和“混乱”。③
我们再来看胡风批评周扬的三条理由是:第一,既然阿Q“就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他也是一个特殊的存在”,那么,这个人物的性格里面就不会含有普遍性,因而也就决不能是一个“典型”(type)了。第二,周扬却同时用了“他所代表的农民”这样的说法。这个代表要么是自封的,要么是人物所代表的一类人所常有的所能有的,依然不是他的“独特的”东西。第三,既然是共同的或共有的,就不能是独特的,在这一点上,周扬是前后矛盾的。④
事实上,普遍性与特殊性,作为典型的两个方面,是缺一不可的。笔者以为,“阿Q这性格对于某一类农民是普遍的”(胡风语)与“阿Q在他所代表的农民中是特殊的存在”(周扬语),这两种说法都对,他们说的都只是典型的一个方面而已。所以,并不像胡风所说的那样,“两个意见完全相反”。胡风的一些辩论初看起来觉得很精彩,但他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他否认了“共同的或共有的”与“独特的”东西也可以统一在同一“典型”里,从而走向了谬误。
胡风强调典型的普遍性。胡风文论受传统整体思维的影响,具体体现为创作论上的“天人合一”,作家论上的“内圣外王”和文艺本体论与功用论上的“体用合一”。⑤权绘锦:《胡风与〈文心雕龙〉》,《求索》2008年第3期。他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里,以阿Q为例进行说明,这并非没有他的道理。因为典型的认识价值主要在于它的普遍性,在于它里面深厚的社会人生与时代历史内容,这无疑是很有眼光、很有见地的。他还主张不要拿一般的身体上的特征当作本质的特征来描写,在当时也有它的现实意义。但胡风认为周扬对典型特殊性的强调,是对“典型的普遍性的一侧面的否定”,“结局也就是对于‘典型’的否定”,⑥却有点危言耸听。周扬对此也是否认的,他在《典型与个性》一文里辩护:“我不是形式逻辑主义者,共同的和独特的两个概念我不觉得是不能同时并存的。”⑦
周扬在文中列举的“经历”、“生活样式”、“心理的容貌”、“习惯”、“姿势”和“语调”等,是否都只能属于人物独特的个性,确实可以商榷。但胡风却走了极端,用“常有的能有的”等诡词,把这些都统统归属到只能是“共有”的名下,否定它们是“独特的”东西,这无疑是欠妥当的。如果胡风是沿着这条路子——把周扬列举的这些去进行逐一地分析,到底哪些是共有的,而哪些是独特的——去走,他就有可能走出偏执的迷误。然而可惜的是,他并不是沿着这样的路子去走的。
其实,胡风也并非完全忽视典型的特殊性。但是,胡风在文中是把重点放在了典型的普遍性上,并且,由于他对典型的特殊性把握得不够准确,事实上却导致了对典型特殊性的彻底否定。他认为“独特的个性”“独有的性格”与“典型”不相容,是“典型”就不能有“独特的个性”“独有的性格”。
包含有“共性”的“个性”是胡风所坚持的“个性”,他说周扬“所要求(至少是无意识地)的是没有群体的特征的‘独有的性格’或‘特殊的存在’”。这是他与周扬观点不同之所在。对此,周扬说:“我并不抹煞胡风先生也承认典型是应当有个性的,但他的‘个性’却有另外不同的解释。‘作为典型的作品里的个性是代表许多个体的个性。是包含了某一社会群的普遍性的个性。’这实际上是否认了文学中具体的、个人的东西,把个人的多样性一笔勾销了。”①②⑦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第163-164页、第161页。这是周扬对胡风非常公允的评论。
总之,一方面,胡风承认典型应当有个性,另一方面,由于强调个性必须包含普遍性,实际上却否定了个性。他走进了这样的一个死胡同。胡风这样做的结果,极有可能掉进他所担心的“类型化”的陷阱。胡风说周扬“陷进了无法收拾的混乱里面”。可事实恰恰相反,不是周扬,而正是胡风自己陷入了“无法收拾的混乱里面”。
三、典型论争所引出的艺术课题
这次典型论争实际上涉及两个艺术上的问题,一个是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们是否统一的问题,一个是典型的艺术创造——即怎样创造艺术典型的问题。事实上,这两个问题不能截然分开,谈第一个问题不能避开第二个问题,谈第二个问题必然会涉及第一个问题。从他们的论争可以看出,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他们争论的中心,而对于与这个中心问题有关的艺术典型的创造问题,他们也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特别是胡风,对这个问题阐述得较为全面,较为深入。
关于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们是否统一的问题,胡风也坚持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统一的,但由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的机械理解,当然,其中也有高尔基典型化理论误导的因素,使得他过分强调典型的普遍性,而在无意识中否定了典型的特殊性。周扬针对胡风的缺失,提醒对典型的特殊性的注意。他认为个人的多样性并不和社会的共同性相排斥,社会的共同性正通过各个个体而显现出来。一个典型应当同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从来文学上的典型人物都是“描写得很生动,各具特色,各具不同的个性征候的人”。②
在论争当中,两人都谈及典型的创造过程。胡风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一文中就谈到:作者为了写出一个特征的人物,得先从那人物所属的社会的群体里面取出各样的人物的个别的特点——本质的阶层的特征,再具体化在一个人物里面,这就成为一个典型了。③④⑤⑥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96-97页、第160页、第363页、第98页。周扬在《现实主义试论》的第5节里也描述了典型的创造过程:典型的创造是由某一社会群里面抽出的最性格的特征,习惯,趣味,欲望,行动,语言等,将这些抽出来的体现在一个人物身上,使这个人物并不丧失独有的性格。所以典型具有某一特定的时代,某一特定的社会群所共有的特性,同时又具有异于他所代表的社会群的个别的风貌。④他们俩对典型的创造过程的描述其实都是来自高尔基的观点。高尔基认为:艺术非有普遍化的能力不可。文字的创造艺术,性格及“典型”的创造艺术,想象,推察,“考案”是必要的。描写一个所熟知的小店主,官吏,或个人,作家可以造出多多少少是成功的一个人的照相,但那不过是丧失了社会的教育的意义的照相而已。但如果作家各个地从二十个五十个一百个小店主,官吏,工人抽出最性格的群体的特征,习惯,趣味,信仰等等,如果能够把这些事物抽出而且结合在一个小店主,官吏,工人里面,作家就能够用这手法创造出“典型”——那就是艺术。⑤
将这三个人关于典型的艺术创造的概括比较一下,我们会发现:胡风的关于典型的创造理论与高尔基的极为相似,而周扬的则有些不同,他强调了典型的特殊性一面。周扬并没有去死搬教条,他对高尔基在不同场合下所讲的话作了综合的理解。
胡风和周扬都提到了想象在典型创造中的作用。胡风认为:“艺术家在创造‘典型’的工作里面,既需要想象和直观来熔铸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一切印象,还需要认识人生分析人生的能力,使他从人生里面取来的是本质的真实的东西。”⑥而周扬说:“典型不是模特儿的摹绘,不是空想的影子,而是作者用丰富的想象力把实际上已经存在或正在萌芽的某一社会群共同的性格,综合,夸大,给予最具体真实的表现的东西。”⑦他们都还注意到了艺术典型的创造与生活实践的关系和作家艺术家在典型的创造过程中所需的分析概括能力。但胡风对典型创造过程中普遍性的概括问题认识得更充分,他一方面承认周扬也多次提到“概括化”,另一方面也指出光有“概括”还不行,必须是“艺术的概括”,这一点很独到,很有美学的意义。他说:“我们用的‘艺术的概括’那艺术的三字并不是随便加上的。”他还提到艺术概括与科学概括的不同,认为:“艺术和科学同样是为了认识客观的真理,但艺术和科学不同,科学是用一般的理论的规定去再现感性的个体,文艺是通过具象的个体(thisone)去表现普遍性(=现实的本质的内容=合理的思想内容)的。”“没有个人的物事就不是艺术,没有了社会的物事就不是‘典型’,不能达到艺术的使命。这就是典型个性化理论的主点”。①④胡风:《胡风评论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363页、第365页。可惜胡风没有朝着这个思路深掘下去。既然“只有群体的特征不能成为艺术”,那么要成为艺术的典型,就必须得有丰富多彩的个性了。陈望衡在《论艺术典型的美学实质》中说:“美既是艺术典型的基点,在考察艺术典型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内部结构时,就要强调、突出个性特征,这有助于扩大、加深对生活本质、规律的概括,因为个性总是大于一般,形象总是大于思想。另外,它也能增强艺术形象的美感魅力,因为美总是具体的、个别的。”②陈望衡:《论艺术典型的美学实质》,《求索》1984年第3期。
四、“典型论争”的结束及其述评
这场论争的结束是富有戏剧性的。在《典型与个性》一文的结尾,周扬突然转换了方向,谈到文学与现实的关系,要求“要使文学成为民族解放的武器之一”。他说“国防文学由于民族危机和民众反帝运动而被推到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文学者应当描写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件和任务,努力于创造民族英雄和卖国者的正负的典型”。他指责胡风“对于文学的这个最神圣的任务竟没有一字提及”。并针对胡风在《现实主义的一“修正”》一文中对当时流行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学现象提出的批评,指责胡风把典型的创造意义和当时的文学战斗任务分离开来,轻视抗战文学中的小形式的文学,质疑:“胡风先生的理论将把读者,作家引导到甚么地方去呢?”③周扬:《周扬文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68-169页。这就有了给胡风扣“帽子”加罪名之嫌。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现实情况下,要求文学为现实服务,其抗战热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周扬给胡风乱扣“帽子”,是不利于学术之健康发展的。因为胡风对当时流行的不利于文学发展的“标语口号”式的文学提出批评,其出发点是好的,其目的是为了维护文学艺术的健康发展,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他所反对那些没有文学色彩的、“以概念代替了形象化的不能取得艺术的感动力的作品”,而并不反对抗战文学。胡风反驳说,他并没有忽视民族解放的“神圣的任务”。提出周扬不能抹杀他的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写作态度的主线,并举例说,他前不久写了《文学上的民族战争》的短文,在文中,他指出民族解放斗争是人民大众的生活要求,而人民大众的生活要求就是艺术的美学的基础,指明了在生死存亡的民族危机下面什么是文学上的能够抓住万千人民大众的心的主题,并且指明了革命的民族战争文学争得了一个新的纪录,要求一切进步的勇敢的作家们为保持并且追过这个纪录而奋斗。④至此,关于典型的论争告一段落。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胡风在典型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把握上有失偏颇,没有周扬那样准确。但他在典型创造的问题上阐述得比周扬更深入、更全面、更富有理论的洞察性。通过他们的论争,关于典型的几个学术上的理论就很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如:典型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统一,典型的艺术创造过程等问题。这对于我们加深对典型本质的理解和对典型艺术特征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也为后来的典型理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对我国文学史上典型理论的建设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周、胡之间关于典型的论争已经成为历史,作为历史中的人物,其是非功过留待我们后人去评说,相信后人自会给他们一个公允的评价。这场论争发生在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刚刚引入我国而自身典型理论还处于一片空白的草创阶段,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前人对刚刚引入的典型理论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误解是可以谅解的。而他们在学术上求真求是的勇气,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在面临民族危机的紧急关头,要求文学为抗战服务,其抗战热情也是可以理解的。
(责任编辑:艳红)
I025
A
1003—4145[2010]07—0142—04
2010-05-04
胡 灿(1974-),男,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2007级比较文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