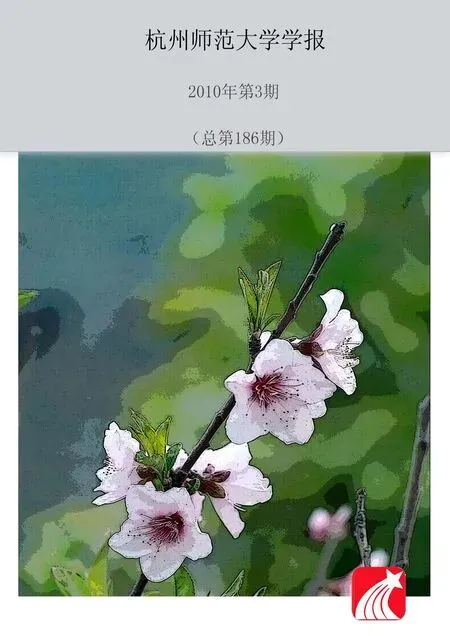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莽丛中》的女性主义解读
2010-04-11孙立春
孙立春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关于芥川龙之介的小说《莽丛中》,学界已有比较深入的研究。有学者从叙事学角度讨论小说叙述者的不可靠性,有学者注重分析凶杀案的真相,也有学者侧重从伦理角度探讨芥川对人性的剖析。本文以为,尽管小说是一个语言构建的迷宫,不同当事人叙述的故事完全不同,不同读者也会有不同的阅读体验,但其中一点是相对确定的:女主人公真砂形象并未发生根本变化,因为不同当事人的叙述受制于同一种话语机制。
小说中七位叙述者的叙述可分为两大部分:樵夫、云游僧、捕役和老妪属于局外旁证,他们的证言为杀人案件提供相关证据;强盗多襄丸、武士武弘及其妻子真砂为当事人,他们的叙述是小说的主体部分。从整体上看,七位叙述者的叙述内容客观性不尽相同。樵夫是最早发现尸体的证人,他交代案发地点和尸体情况,其叙述大体上是客观可信的;云游僧叙述案发前武士夫妇的情况,交代自己对武弘夫妇的印象;捕役叙述逮捕多襄丸时的情况,认为多襄丸是个“好色之徒”;老妪谈话的主观性最强,因为死者是其女婿,女儿又生死未卜,所以她在接受讯问时边诉边哭;四位旁证叙述内容的主观性越来越强。三位当事人的叙述主要反映他们不同心理:多襄丸内心充满欲望,真砂内心充满悔恨,武弘心中则燃烧着怨恨的怒火。三位当事人陷于强烈的情绪中,而对于谁杀死武弘这一事实,却有诸多自相矛盾之处。
一
多襄丸是个敢爱敢恨、爽直痛快的强盗。他承认自己杀死了武弘,却采用一套意味深长的叙述方式交代杀人动机的:
正巧一阵风吹过,掀起竹笠上的面纱,一眼瞟见那小娘儿的姿容……觉得她美得好似天仙。顿时打定主意,即使要杀她男人,老子也非把她弄到手不可。
反正得把女人抢到手,那男的就非杀不可。
只要能把那小娘儿抢到手,不杀她男人也没什么。
用不着杀那男人,也能把她小媳妇弄到手。[1](P.124)
多襄丸的叙述透露出两个信息。其一,他在窥见真砂美貌之后,才萌生强奸真砂的邪念。其言外之意是说,他强奸是有特殊原因的,是因为真砂长得太美,所以他才迫不得已动了凡心。这是一种典型的“女人祸水”论。其二,他杀人同样也是有原因的。多襄丸承认在杀武弘时曾犹豫过,甚至退一步认为不杀也行,但最终还是杀了武弘。“我凝目望着她的脸庞,刹那间,主意已定:不杀他男人,誓不离开此地。”[1](P.126)多襄丸叙述案件的过程中,有一个潜在话语逻辑:就是杀人也不是他的错,错误完全在真砂这边,之所以要强奸真砂是因为她漂亮,之所以要杀死武弘也是因为她漂亮。归根结底,他是要一步步地把犯罪的责任推到真砂身上。然而,他无论怎样,都无法改变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真砂始终是受害者而不是侵害者,而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
福柯认为,影响、控制话语运动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不可分的,权力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3](P.38)多襄丸叙述话语的背后掩藏着一种等级秩序。首先,多襄丸不是自己在说话,而是代表了整个父权制社会在说话。尽管在不同时代和不同文化中,男性也遭受压迫,但他们是由于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的成员而受压迫,而并非由于是男性而受压迫。女性则不同,除了因为属于某个阶级或阶层等原因之外,还仅仅因为身为女性而受压迫。多襄丸对真砂的暴行反映了女性在父权社会的境遇。其次,多襄丸在叙述时自觉地维护男性特权。在男权的社会天平上,男性永远处于优越地位,他们不仅掌握国家暴力机器,还牢牢控制着社会意识形态。女性则不仅无法主宰自身命运,甚至不得不以男性话语为话语,从而失去言说的权利。多襄丸利用男权话语进行叙述,实际是利用说话机会再次行使男性特权。他试图将自己装扮、美化起来,然而真砂的遭遇却戳破了所有的谎言。
二
如果说多襄丸是男性霸权意识的体现者,那么武弘则是父权社会秩序的自觉维护者。小说关于武弘的描述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小说通过被害人真砂的感觉,交代丈夫武弘对她失身后的态度;二是作品借女巫之口表达武弘对真砂的立场。首先,妻子真砂失身后,丈夫武弘的表情立刻发生了变化:
我看见丈夫眼里,闪着无法形容的光芒。……他那灼灼的目光,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有对我的轻蔑,真个是冰寒雪冷呀!……他的眼神同方才一样,丝毫没有改变。依然是那么冰寒雪冷的,轻蔑之中又加上憎恶的神色。[1](P.127)
接下来,小说通过女巫之口,进一步叙述武弘对真砂的态度。真砂受辱后仿佛变成另一个人,对奸污自己的强盗百依百顺。在叙述者的层层描述中,小说似乎要揭示女人多变这一事实。更让人震惊的是,武弘借助女巫之口反复强调,真砂多次要求强盗杀死自己。原本是一对情意绵绵的恩爱夫妻,在妻子失身之后却变成仇敌。武弘对真砂的冷漠和反感,揭示了其男性逻格斯中心主义意识。
在多襄丸眼里,真砂是容貌美丽的女子,以致他愿意为她犯罪;在武弘眼里,真砂不仅是令人厌恶的色情女郎,甚至还是怂恿强盗杀害丈夫的魔鬼。多襄丸和武弘对真砂的态度,恰好反映了父权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总是扮演着双重角色。“她既是男人的天使,又是男人的恶魔;既给男人带来欢乐与满足,又使男人产生厌恶及恐惧。天使/恶魔的二重性否定女性的人性,直接服务于男性的‘性权术’。”[4](P.53)这样看来,作为丈夫的武弘与强盗并无不同,无论强盗多襄丸还是武士武弘,他们在叙述时都是操着同一种话语——男权话语。从这个意义上看,与其说武弘是在维护自身利益,不如说他在维护父权制社会赋予男性的特权。他们对真砂的种种行为并无多少本质不同,都代表着来自男权社会的压迫。
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妻子真砂被强盗奸污时,丈夫武弘本人也在现场,被绑在树上。毋庸置疑,不能拯救妻子不是他的过错,但作为极具尊严感的武士,他在妻子受辱时并没有激烈反抗,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感觉,并未尽到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事后他不仅丝毫不为自身行为感到羞愧,还将所有责任都推到妻子身上。
与武士武弘相似,多襄丸也在美化自己的暴行。他将自己描述成颇具英雄气质的强盗,不仅具有骑士风度,似乎还具有“良好”的行为准则。比如在决定杀死武弘时,他宣称不用卑鄙的手段,于是放开武弘,让他和自己用刀决斗。多襄丸杀死武弘后,还敬佩他是能与自己交手到二十回合以上的人。多襄丸在美化自己的同时,将奸污真砂这一原则性罪行轻轻带过。多襄丸的叙述实际反映出男权社会道德观的一个死角:男人的英雄主义和骑士风度,对女性来讲不仅不是救赎,相反还可能是对女性权利的践踏和蹂躏。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的特有产物,不仅无法保护女性的人身安全,甚至还压抑和挤兑女性的生存空间。小说无意之中揭示出武士道的虚伪本质。
三
在真砂面前,强盗多襄丸与丈夫武弘是整个父权制社会的代表,他们共同形成强势的男性丛林,让生活在其中的真砂感到压抑、窒息。作为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女性,真砂一直处于绝望的境地。由于长期置身于男权社会,她无法走出布满陷阱的男性丛林。在父权至上的社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被玩弄和被鄙视的厄运。我们可以发现真砂至少遭受三种不同类型的压迫和戕害。
首先,真砂直接受到多襄丸的身体侵害。多襄丸窥见真砂美貌之后,强行与其发生肉体关系,给真砂的身心造成了巨大伤害。多襄丸在这里成为上帝、父亲、法权社会的符号,他对真砂的暴行反映出整个男权社会对女性的钳制和损害。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与女性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动宾关系,男性是“看”或“做”的主体,而女性往往是“看”或“做”的对象。女性作为一种宾格,俨然成为男性的附属品,是一种被消费和被玩弄的“他者”,其存在的价值之一就是满足男性的“偷窥欲”和“发泄欲”。真砂作为一个美丽的女性形象,其美丽只有在男性的注视下才有价值。她在多襄丸看来不过是个性感尤物,是一个可以实施暴行的载体,而不是一个有着情感和思想的鲜活生命。因此从某种程度来讲,多襄丸对真砂的强奸可以视为父权制社会对女性他者的一次全面进攻,他们不仅要满足自己的“偷窥欲”,还要进一步满足自己的“发泄欲”。真砂像父权制社会的无数女性一样,不知不觉地跌入父权制社会为其设计的陷阱之中。
其次,真砂还受到丈夫武弘的精神压迫。如果说强盗对真砂的伤害主要在身体的话,那么武弘对真砂的伤害则主要在精神。妻子真砂被玷污以后,她跑到丈夫武弘那里寻求帮助。因为强奸的事实已经成立,所以这时候真砂所寻求的主要是精神上的支持,甚至可以说是希望得到丈夫的谅解和宽恕,结果她“看见丈夫眼里,闪着无法形容的光芒。……他嘴里说不出话,可是他的心思,全在那一瞥的眼神里传达了出来。他那灼灼的目光,既不是愤怒,也不是悲哀——只有对我的轻蔑,真个是冰寒雪冷呀”真砂由于不堪精神重负而昏厥过去。她醒来以后,情况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尽管真砂也认为自己是受害者,但她并没有把责任归咎于侵害者一方,相反从文中可以看出,真砂的自我责备要多于对多襄丸的憎恨。真砂由于自己失贞而背负着沉重的精神包袱,她的遭遇反映了男权社会中女性的普遍境遇。在父权制社会,丈夫在妻子那里拥有至上的特权,性特权是丈夫对妻子的重要权力,只要他想要,随时都可以提取兑现。这一特权只是其个人的不动产,而婚姻之外的其他男人则不能染指这一特权。真砂没有能维护丈夫的特权,感到自己失职,亏欠丈夫,由此引发了精神上的压迫。从本质上看,真砂之所以没有取得丈夫的谅解和支持,就因为丈夫武弘和强盗多襄丸一样,都是父权制社会的代表。作为一名深受父权制戕害的女性,试图从丈夫那里取得精神上的支持是很不现实的。
再次,从真砂受辱后的内心独白看,她还显然受到父权制社会的话语制约。真砂未能捍卫自己的贞操,她时时感到无脸做人:“这么苟活人世,实在没脸见人。我这个不争气的女人,恐怕连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都不肯度化的。我这个杀夫的女人呀,我这个强盗糟蹋过的女人呀,究竟该怎么办才好啊!”[1](P.126)
可以看出,真砂之所以痛苦不堪是由于她生活在父权制社会的话语机制中,而贞操观则是父权制社会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念。这种观念认为,妻子必须为丈夫保持贞操,否则就是不贞、淫荡和堕落。失贞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不仅给女方自己,更会给其丈夫带来莫大的耻辱。不管失贞是缘于何种原因,都不值得辩护,更不值得提倡。为了维护自己的贞操和更好地忠实于丈夫,妻子可以牺牲生命来捍卫贞操,只有这样的妻子才是女人们学习的榜样。真砂没有拼死捍卫自己的贞操,她违背了父权制社会的游戏规则,注定要成为整个社会唾弃的对象。贞操观的本质是男性中心主义的产物,它总是为女性规定了许多义务,而忽视了女性的性别权利。男性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出各种各样的伦理规约,不断地用这些规约约束女性。女性实际上生活在男性社会为其编制的鸟笼中,成为被观赏的美丽的“金丝鸟”,成为处于劣势他者地位的第二性。从根本上说,包括受害者真砂在内,三位当事人的话语是一样的,都是父权制社会流行的话语。多襄丸在奸污真砂后,又以父权话语恐吓她说:“你既失了身,和你丈夫之间,恐怕就破镜难圆了。”[1](P.128)而真砂作为被损害、被侮辱的女性,只能接受这样的话语,并把它作为自我评价的标准。真砂由于缺失女性话语权,所以不仅缺少衡量自我的尺度,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表达体验和解释世界。由于笼罩在男权话语规约之下,真砂与其他亿万女性一样处于沉默状态,只能把男权话语作为自己的话语。
男权话语的核心是维护男性权力,对于女性来说,男权话语恰好成了一柄双刃剑。也就是说,受害者真砂无论怎样都摆脱不了尴尬状况,一方面她生活于父权制社会秩序之中,无时无刻不受男权话语的训导和规约,这种话语规定了她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模式,也强加给她以责任和身份;另一方面,她一旦认同男权社会的角色定位,接受男权社会赋予的责任和义务,必然就会失去自身的利益。尤其值得庆幸的是,真砂并未因羞辱而自寻短见,她认为自己没有勇气自尽。其实,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真砂作为一名受害者都是无辜的,她只是没有自觉地顺从父权制社会的规范。范静遐认为:“两位男性经历者对真砂的看法一致。结合真砂的叙述,我们会发现其中一个心理事实,就是妻子在被侮辱后,不管是被丈夫的鄙视憎恶的眼神所激怒也好,还是因为受到强盗甜言蜜语的诱惑也好,妻子都有杀死丈夫的心理事实。”[5](P.136)然而在本文看来,真砂有杀死丈夫的念头,倒可以完全用另一种原因来解释。那就是她不堪忍受男权社会的压制而产生的本能反抗。这不仅是对男性霸权和话语霸权的抗争,也是对男权话语的精神突围。
由此可见,小说《莽丛中》反映了女性在当时社会的真实境遇。在父权制话语规约下,真砂处于非常尴尬的两难境地:如果认同男权社会的道德规范,则意味着自我和权利的丧失;如果违背男权社会的期待和法权,她势必沦为品行不端和道德败坏的人。小说最终表明,女性只有打破男权神话并建立自己的话语,才能不丧失性别属性和生存权利,才不会成为男权社会的玩偶和工具,她们的悲剧才不会继续上演。
[1]高慧勤,魏大海.芥川龙之介全集:第2卷[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5.
[2]罗婷,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和中国[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3]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4]张岩冰.女性主义文论[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
[5]范静遐.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和伦理阅读[J].理论月刊,200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