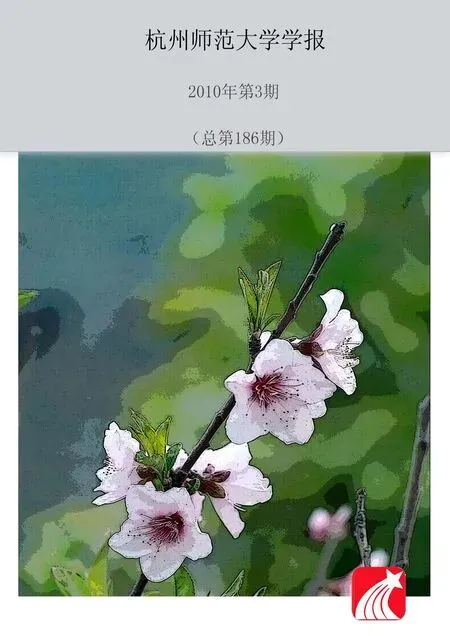一个概念与一种文学史图景
——读吴秀明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
2010-04-11俞洁
俞 洁
(浙江传媒学院 影视艺术学院,浙江 杭州 310018)
就中国现当代文学而言,“重写文学史”的呼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渐趋高潮。如果从1917年开始算起,中国现当代文学走过的历程迄今其实也还不满百年。但时间上的短暂并不能化约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复杂性。由于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诸如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共和国成立、“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等一系列重大的历史事件,而这一系列事件又构筑起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整个中华文明处于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之中。因此,从一开始,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语境就落在了由民族、政治、文化、经济等诸多因素交织而成的网络之中,其关系错综复杂;而作为大学教育体制中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其成立,在一开始,显然也有赖于主流意识形态的促成。正是这样,如何处理文学与政治、文化、经济之间的关系,乃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一大问题。80年代以后学界关于“重写文学史”的讨论,其表现于学科层面的致力点,固然是要将文学史从政治意识形态的控制或影响中解脱出来,从而使文学史叙述建立在其自身的轨道、范畴之内;但另一方面,隐藏于背后的另一大原因也在于,借助于文学史的梳理来清理发生“文化大革命”一类社会事件的思想基础。正是这样,20世纪80年代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的一个重点,是将其起点还原到了五四时期思想启蒙的语境之中。
将文学从政治的附庸中解脱出来,这样的学术取向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来说,无疑具有一种独立的姿态。这样的姿态有助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真正挺立,但在具体文学现象的研究或史的勾勒中,假如仅仅满足于以“启蒙主义话语去翻覆了革命史的话语,我们所做的只是‘调换/颠倒’了一种意识形态的凭借”,而缺少一种“内化的批评”,“缺少内化环节的批判,往往会追认既有的话语,用距离话语的远近来对某个对象进行批判,而无法阻止自己倾斜于这种暴力性”。[1]这样的学术警惕提醒我们,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将近百年之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还需要作更进一步的“内化的批判”。这意味着,对文学作品的评判与文学史的建构,以及与之相关的文学史教学,都需要超越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需要将自己的研究立场从“一元化地回收到位于对象对立面的意识形态中(在同为意识形态这一点上,其实并不两样)”[1]摆脱出来,而从由政治、文化、经济等全息的文学史语境出发,在文学本身所处的场域中来加以研究。从这样的学术立场出发,吴秀明教授的近著《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2]从生态学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无疑是一项极富价值的学术工作。
作者在这本著作中所借重的“生态场”概念,最早属于生态学范畴,由英国生态学家坦斯勒提出。“生态场主张把整个自然都纳入一个大系统中,研究整个自然系统内所有现象和所有能量的流动及与生物特别是与人的互动关系及其规律。”[2](P.333)但作者在书中无意纠缠于“生态场”的概念内涵及其演变等诸多问题,而是直入主题地将“生态场”理解为一个相对宽泛的学术领域,并在此基础上将文学生态学研究分为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生态文学与文学生态研究。作者认为,文学与生态的关系是多方面的,可作多维立体的研究。“文学生态研究”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研究,但却“从一个独到的角度对当代文学或文化现象作了概括和透视,并因此不仅赋予当代文学新的内涵,而且也为其分析研究提供新的参照和评价标准”。[2](P.346)这一研究取向的价值在于可以“摆脱以往人文与科学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为当下文学创作和研究寻找新的突破点,提供一种新的视角、方法和途径”。[2](P.329)在这样的研究设计中,文学生态研究所致力的,恰恰就是一种全息文学语境的还原与考察。就是说,对文学现象的考察,乃至于文学史的建构,都要求我们摈弃一种先验的价值立场,排除一种一元化的逻辑思维方式,在一个相对开放的场域中,综合考察与此一文学现象共存的多种社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这样一种研究立场的确立基于以下观察。在作者看来,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生态环境“殊为复杂且相当严酷”。在现代文学阶段,“它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动荡的战争中度过的,血和火的恶劣环境不仅规约了它的题材、主题,而且也深刻地制约着作者的思维理念”;在当代文学阶段,“由于相当长时期受‘左’倾文艺思想的指导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文化大批判、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使政治上‘解放’了的现当代文学在为政治服务之时逐渐丧失了学科属性特点”;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市场经济的魔力也使它在获得自由的同时又陷于另一种不自由,从整体上被日趋边缘化了”。[2](P.2)基于这样一种状况,对文学对象的“内化批判”,就不能单从文本出发作出结论,而需要在文本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影响文学创作的诸多外部力量——如政治、经济、文化霸权等等。即是说,导致文学生态异常“严酷”的诸多因素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等,不但不应被摒弃在研究对象之外;相反,想要深入理解文学对象本身的形成与价值,就必须综合地考察文学与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避免相互之间以一种二分的方式作对立的观察。
以“十七年”文学的研究为例。新时期以来,人们对政治意识形态浓厚的“十七年”文学的合法性提出了质疑,甚至否定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以为文学脱离政治就“纯粹”了,就是“回到文学自身”。作者认为这种“非政治化”的倾向其实是对文学现象的简单化处理,因为“当代文学即使在政治化的时代,往往也会与社会的主流观念形成一种矛盾碰撞的张力,而对原有的僵硬的思维理念有所僭越”,“倘若我们以意识形态为由,对以往政治化时代的文学采取一概贬斥的态度,就有失简单,也不利于当代文学学科建设及其有关历史经验的总结”。[2](P.57)这样的观点是中肯的。事实上,假如我们对“十七年”时期作家与作品之间的关系略作考察,就会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作家本人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召唤下,努力想要写出为政治服务的作品,但这些作品中有相当的部分,最后却也还都逃脱不了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批判的命运。在这样的错位中,我们其实正可以看到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张力与角逐,从而修正之前文学史所描述的,政治对于文学的单向度的作用;而假如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些错位的存在,对“十七年”文学的研究,无疑将丰富起来。这就是说,从“生态场”的角度进入文学研究,我们的研究对象就不会仅仅局限于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或文艺思潮之上,而会把研究的目光投射到整个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空间。在文学生态视野下,“我们可知文学生态系统中的各个主体因素,它们各自都有独立意志和自觉的能动性,但又各自受着自身生态环境的制约,彼此形成或协调或冲突或磨合的复杂关系,并由这些关系决定着生态系统的最终效应”。[2](P.348)
在这本著作中,作者对这样的研究理念作了很好的实践。全书主要分上下两编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上编为“文学史论与学科建设”,从全球化语境、历史与现实境遇、整体性格与矛盾性特征、文学史编写等方面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作者对现当代许多文学现象(包括海外汉学研究、诺贝尔文学奖、文学史编撰等等)做出了全面而中肯的评价;下编为“生态场域与生态文学”,立足当下文学生态现状及其生态文学热潮,并借鉴“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位”等生态学的基本原理,从文学现状、文化领导权、经典重构、生态文学等方面探讨中国现当代文学所处的生态场域和生存状态。这样一种框架设计的目的在于,“试图通过这样两个不同的视角,触摸在全球化(特别是西方化)文化生态场域中现当代文学背后丰富复杂的内涵,把握文学与政治、经济、哲学、历史、教育、伦理、道德之间排往迎拒的关联,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实和未来的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启迪”。[2](P.3)通过这样一些论题的研究,文学生态研究的指向在实践的层面得以展开,它们不但让我们更为深切地理解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多重面影,同时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更为丰富的文学史图景。
在2002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3]中,吴秀明教授即将“客观写真”作为这部文学史教材的编写宗旨,采用“你说、我说、他说、大家说”的多元视角,将同一段文学事件、同一部作品在不同历史时期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的评论进行归纳,强化编写的文献性和客观性。这种兼容并蓄的开放式的文学史编写方式,其实已经涉及“文学生态研究”,其理念与实践都为这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的撰写奠定了基础;而这部著作的出版,则可以认为是对《写真》编写体例的一次理论化提升。或者说,前者是史料的准备与积累,是多重声音的提供;而这一部著作,则着重阐释看取史料的眼光,是这多重声音的串联与解读。这两者,原是二合一的工作,即只有将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才能够真正避免一种单一化的研究立场,而深入到文学对象的内部,作一种更为丰富的“内化的”批判。从这一层面来说,这部著作对研究者来说,其价值恐怕更在于方法论意义上的启示。
[1]坂井洋史.关于“后启蒙”时期现代文学研究的思考[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41.
[2]吴秀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与生态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吴秀明.中国当代文学史写真[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