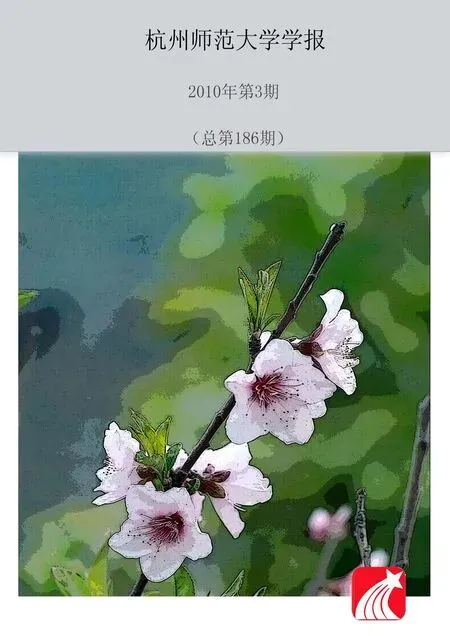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学说
2010-11-22闵家胤
闵家胤
(中国社会科学院 哲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20世纪世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发生了一系列转向,如语言转向、解释转向、后现代转向,直至文化转向。我们确实迎来了一个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也是一个研究文化的时代。
英国伯明翰大学于1964年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人类学家R.威廉斯在该中心对文化做专门的研究,他在《文化与社会,1780—1950》一书中指出,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上半叶,有五个单词——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class(阶级)、 art(艺术)和 culture(文化)在英语中变成了常用词。他认为“文化可能是上面提到的所有词汇中最引人注目的”。[1](P.18)在做了几十年研究之后,他又发现:“英语中有两三个最为难解的词,culture即是其中之一。”[2]可能是知难而退吧,《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10卷)和《西方大观念》(第1-2卷)之类大型工具书,都没有“文化”和“文明”的单列词条。
为了适应国际文化竞争,中国学术界有必要建立自己的文化学和文化哲学。
首先应对“文化”和“文明”这两个基本概念做出区分和定义。
欧美文化学学者对“culture”的定义做过精细的统计研究,发现有160多个定义。从词源学上讲,英文词“culture”是从法文移植来的,而法文词“culture”又来自拉丁文“cultura”。现在能查到的最早使用“cultura”这个词的是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前106-前43),他讲过一个拉丁文的论点“cultura anima philosophia est”,译成中文是“文化是心灵的哲学或修养”。[3]他意识到:文化产生和存在于人的心灵。“culture”的本义则是耕种,法国人安托万·菲雷蒂埃1690年编撰的《通用辞典》这样定义“culture”:“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1](P.5)由此可知,文化的起源是农业劳动知识的积累,特别是用文字记录下来的知识;而在此之前,在采集-狩猎社会,人类靠天吃饭,生产技能靠演示和口口相授,无法用文字记录知识。
近代,文化人类学家们最早致力于文化和文明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家泰勒在1871年写的《原始文化》一书中,将“文化”与“文明”两个概念混同,并定义说:“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和习惯的复杂整体。”[4]这个定义是有代表性的,因为欧美学术界后来涌现的160多个定义大类于此:要么“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要么把“文化”定义为平列的同样含糊的概念“整体”“总和”“总成绩”“模式”“方式”“样式”等等。
逻辑学上标准的定义方法是种加属差定义。据此,我们要尖锐地提出问题:为什么300多年以来,始终不能给“文化”下一个标准的种加属差定义呢,这究竟是为什么?
从人类知识体系的角度可以这样回答:直到20世纪末叶,人类知识体系有多方面的缺失,这些缺失决定了人们不可能给“文化”下一个种加属差定义。概括地说,这些缺失包括缺少本体论的相应范畴,缺少恰当的社会系统模型,缺少社会系统内部的通讯系统模型,缺少对“文化”和“文明”进行联系和区别的科学认识。
首先来谈本体论的缺失。自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在17世纪用拉丁文 “Cogito,ergosum”提出“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之后,整个西方哲学来了个“认识论转向”;本体论研究不是被根本否定、就是被撇在一边。然而,实际上人类知识体系是不能没有本体论承诺的。后来,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本体论问题,可是错误地借用笛卡尔讨论认识论的“主体-客体”二元框架来讨论本体论问题,结果得出“存在”和“意识”或“物质”和“精神”的二元论本体论,甚或得出更偏执的物质一元论或精神一元论。在这种一元或二元的哲学本体论框架中,哪里会有“文化”的位置,哪里会有“文化”所属的范畴即它的上位概念呢?
因此,在本体论问题上,我们应当纠正西方哲学家们的错误,跳出笛卡尔主客两分的框架,回归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进化多元论框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同时,20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相对论、量子力学、生物遗传基因(DNA)理论、大爆炸宇宙论和系统科学,改变了人类的认知图像,使我们有可能站在当代科学的宇宙广义进化的客观立场上,拉开科学认识必须要有的同被认识对象的距离,透视宇宙进化、银河系进化,太阳系进化、地球进化、生物进化和人类社会进化,得出“进化的多元论”:场→能量→物质→信息→意识,它们是依次进化出来的宇宙的五种元素,地球人类至少是生活在这五种元素的多元世界上;或者说,当代的科学思维和科学的哲学思维必得采用这样五个本体论范畴。[5]而用“奥卡姆剃刀”不可能剃掉其中任何一个范畴,也不可能归并其中任何两个范畴。
只要把“文化”放到进化的多元论的本体论框架中,原来一直缺失的“上位概念”或文化所属的本体论范畴就能被找到:“文化”属于“信息”这个种范畴,或者说“文化”的上位概念是“信息”。“文化”的本体论缺失因而得以消除。
社会系统的第一个模型、同时也是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模型,是马克思在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阐述历史唯物论原理时建立的模型。笔者在马克思模型的基础上,吸收系统哲学家E·拉兹洛在《进化——广义综合理论》一书中建立模型[6]的一个思想,把“文化信息库”(culture-information pool)放在中央位置;继而吸收钱学森社会系统模型[7]的一个思想,把“人”放在核心位置;进而把马克思模型中的“生产”分成“人的生产”、“物质产品生产”和“文化信息生产”三大块,由此建立了一个社会系统的新模型:[8]

图1 社会系统的新模型
按照这个新模型,笔者把社会系统定义为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自复制-自创新系统,人不断地从文化信息库中提取信息并进行人的、文化信息的和物质的生产和创新,从而实现系统的自复制-自创新,维持自身的存在和进化。从这个社会系统的新模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文化信息库”中的“文化”被安放在社会系统的中央位置;而文化的创造者“人”又被安放在核心位置,以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
通信系统的问题,则由当代信息-通信理论和分子遗传学为我们弥补了缺失。在信息论中,通信系统的最简模型为:

图2 最简通信系统模型
当代分子遗传学揭示了生物遗传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则。比照最简通信系统模型,可以把中心法则扩大、转换成生命的通信系统模型:

图3 生物遗传的通信系统模型
对“文化”和“文明”的区分。英文词“civilization”(文明)来自法文,法文来自拉丁文“civis”,拉丁文又来自希腊文“πολιτηs”,指生活在古希腊“城邦”中的“希腊族”人(“citizen”,公民),以别于生活在城邦之外的“蛮族”(barbarians)。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英国希腊学专家基托的《希腊人》,“城邦”的希腊文原词(πολιs )译为英语 “city-state”是不太好的译法。汉语随英语亦然,因为这个译法让人误以为“城邦”是个地理学概念,其实“城邦”是个社会学概念——城邦是当时的社会组织。亚里士多德的名言“人是政治动物”也是误译,正确译法应当是“人是生活在城邦中的动物”。
“城邦”是古希腊时代进化出来的基于血缘关系而又超出血缘关系的、由语言-文化关系构成的社会组织——社会系统。生活在这个社会组织中的是希腊族人,讲希腊语,有“共同的社会生活——婚姻关系、氏族祠坛、宗教仪式、社会文化生活”。[9](P.40)最后这一项很重要,包括政治、军事、道德、讲演、辩论、戏剧、体育和经济生活等。总之,生活在城邦中的citizen(公民)是接受希腊文化的文明人,生活在城邦之外的是没有接受希腊文化的barbarians(蛮族)。他们或是奴隶——俘虏来自外族人,或是移民——迁徙来的外族人;他们不会讲希腊语,只会像野兽一样bar bar(巴巴)地叫——至少希腊人听来如是,故名barbarians(蛮族)。[10]当时也有特许入籍(归化)的公民(ποιητοι πολιται),可直译为“制造成的公民”。[9](P.110)怎么制造呢?当然是用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制造。
“文明”一词在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中皆为Civilization。这个词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它是由法文Civil(英文Civis)一词演变来的。Civil一词原意是指在城邦中享有合法权利的公民。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把当时由封建习俗转向资产阶级化的演变称为Civilizer,它的原意为:“公民化过程”。到法国大革命时代,人们把体现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新的文化气象称为Civilization,即“公民化”的文化。它是西方公民社会中民主政治文化的一种新的气象和新的趋势。
在弥补了这四个缺失之后,我们就会明白:“文化”正是社会系统内部的“遗传基因”(DNA)!“文明”则是文化经过生产过程物化出来的“蛋白质”,或者说是各种各样由“文化蛋白质”组成的“文化表型”。“文化”同“文明”的关系恰好就是“基因型”(genotype) 同“基因表现型”(phenotype) 的关系。这样,我们就得到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的种加属差型定义: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遗传信息——社会-文化遗传基因,文明则是文化的社会表型。
论及二者的区别,可以直观地说,从人的头脑中出来、还可以回到自己或他人头脑中去的属于文化;而从人的头脑中产出的、通过劳动加工成为物品,因此再也不可能回到自己或他人的头脑中去的,则属于文明。文化是信息产品,由语言和文字编码,可以转录和翻译,并由文化遗传而永存;文明则是物质产品,不能转录和翻译,只能随时间衰败和瓦解。已经消失了的文明,其尚未完全瓦解的遗存,有时被考古学家们挖掘出来加以研究,以推断其中隐藏的文化。
这样,我们就找到了社会系统内社会-文化遗传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则:“文化→生产→文明”。我们称之为文化“中心法则”,是因为从我们建立的社会系统新模型看,尽管社会系统内有各个方向的信息流,并且都是双向互动的,可是“文化→生产→文明”是社会系统内主导的、最强大的和持续不断的信息流,它维系着文化的传承和社会的自复制。
我们进而尝试把“社会-文化遗传基因”的英文拼写Social-culture DNA缩写成S-cDNA。还可以把教育(education)缩写成S-eRNA,把科学缩写成S-sDNA,把技术缩写成S-tRNA,然后即可构制出“社会文化遗传信息流向的中心法则”之示意图:

图4 社会-文化遗传的通讯系统模型
社会-文化遗传的通信系统模型(图4)是普适性的,适用于各个时代的社会。我们进一步加上S-sDNA和S-tRNA,把它扩展成只适用于现代社会的“工业社会-文化遗传的通信系统模型”见图5:

图5 工业社会的社会-文化遗传的通讯系统模型
这样,“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价值所在就体现得非常清楚了。同时也直观地表明,在现代工业社会里,社会-文化遗传过程要比以往复杂得多。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展开了的文化定义: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的总和,是历代社会成员在生存和生产过程中心灵创造的积累,是社会的灵魂。其核心是所有成员共同的图腾、信仰、世界观、思维方式、价值和行为准则,其外围则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生活常识和生活技能。文化为社会系统个体的心灵结构和行为编码,为社会系统的结构和行为编码,以确保他们能在自然和社会环境中生存,并且通过生产不断复制和创造相应的文明表型。文化是社会系统内的最终决定因素,它最终决定社会系统的存在、停滞、变革和进化,决定历史。
我们把“文化”定义为“社会系统内的遗传基因”,“文明则是文化的社会表型”。由此,在现代社会中,文化决定文明是不言而喻的。我们又把社会系统定义为“在自然生态系统基础上进化出来的,由人组成的,并由人从文化信息库中提取信息进行人的、文化信息的和物质的生产之自复制-自创造系统”。按照这个定义,社会系统内的三种生产——人的生产、文化信息的生产和物质产品的生产,是社会系统内部的功能过程,既构成了文明,也构成了社会;既是文明的自复制-自创造,又是社会系统的自复制-自创造。换句话说,文明是社会系统的全部内涵,社会系统则是全部文明的外延,它们的所指是同一社会存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文明”等同于“社会”或“社会系统”。据此可以得出结论,既然文化决定文明,那么文化也决定社会;或者说,最终是文化在社会系统中起决定作用。
我们还可以用类比法论证这个命题。在金岳霖主编的《形式逻辑》教科书中,[11]关于类比法是这样写的:“我们观察到两个或两类事物在许多属性上都相同,便推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并将其图示为:
A与B有属性a1,a2,…,an
A有属性b
所以B也有属性b
中山大学林定夷近年研究类比法的一篇论文,[12]首先引英国贝弗里奇《科学研究的艺术》“类比是指事物关系之间的相似,而不是指事物本身之间的相似”之说,然后论证我国现行逻辑教科书的不足,最后得出结论:
类比是一种从特殊过渡到特殊的思维方式。它借助于对某一类对象的某种属性、关系的知识,通过比较它与另一类对象的某种相似,而达到对后者的某种未知属性和关系的推测性的理解和启发。
他给出了类比法的两个程式:程式甲和程式乙。将两个程式与本文的论证对照,笔者倾向于相信本文采用的类比法接近“程式乙”:
程式乙:已知A对象的属性a、b、c之间 有某种函数关系f(a,b,c)=0
预感到:B对象的属性a′、b′、c′在 数量关系上与a、b、c有些相似
猜测:a′、b′、c′之间存在同一形式的函数关系f(a′、b′、c′)= 0”。
笔者发现:在生命系统A中,DNA有本质属性a 和相关属性b、c、d、e、f、g,且DNA对其生命系统的表型有决定作用;在社会系统B中,S-cDNA有与a相近的本质属性a′,有与b、c、d、e、f、g相同或相近的相关属性b′、c′、d′、e′、f′、g′;于是可以推测S-cDNA对社会系统表型也有决定作用。
对最后这个论点,还可以用排除法证明,就是说用事实证明。例如,曾被认为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的强权政治、强大武力、强人意志在同先进文化的较量过程中,最终都是先进文化取得胜利。即便是经济决定论,分析到最后依然超不出文化最终决定论的表现形式。“人心向背”可以一时决定政权的更迭,可是唯有“文化”决定社会系统的演化,决定历史。把曾经和可能被视为社会系统中的决定因素的这五个因素都排除之后,剩下的“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却是不可能被排除和推翻的。
如继承古希腊文明的罗马,把欧洲古典文化推向新的高度。罗马三次被只学它的技术,特别是只学它的军事技术的蛮族打败。公元前390年高卢人,公元378年西哥特人,公元455年汪达尔人先后攻陷罗马。罗马遭到三次洗劫,帝国走向分裂和衰亡。然而,罗马依然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它的文化“充当从蝴蝶到蝴蝶之间的卵、幼虫和蛹体”,[13]在后世重放光芒,而那三个武力强大的蛮族则依然是消失得无影无踪。
同样的故事发生在中国。中国古代文化在宋朝达到高峰,可是宋朝在军事上非常软弱,被史家称为“无兵的文化”。在同强大的辽金和蒙元的长期对垒中,节节败北。最后宋朝灭亡了,汉人遭受蒙古人100年的奴役。然而,汉人是最后的胜利者,因为汉文化延续至今,而且还继续发扬光大,而蒙古人则如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所说,由于蒙元实行民族分治,拒绝接受汉族文化,结果他们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100年后被赶回草原还是什么样子。
强大武力斗不过文化,强权政治斗不过文化,强人意志依然斗不过文化!秦始皇留下千古伟业,可他焚书坑儒,彻底清除前朝及六国文化,这就做不到了,只留下千古骂名。再看,“文革”期间,林彪和“四人帮”一伙蒙骗几亿中国人,握几百万大军,指挥几千万红卫兵,要消灭所有封资修的黑货,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结果只疯狂了10年,就被扫进历史的垃圾箱了。正所谓,“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
至于“经济决定论”,我们承认和继承马克思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在图1“社会系统的新模型”中,“物质生产系统”仍然放在基础的位置,而包括生产、分配和消费的物质生产全过程就是“经济”。在图4“社会-文化遗传的通信系统模型”中,“生产”决定和制约整个“文明”,而“文明”即“社会”。笔者所做的补充是,在社会的“物质生产”之前总得有“人的生产”和“文化的生产”。如马克思自己所说,“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之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15]在图5“工业社会的社会-文化遗传的通信系统模型”中,本文所做的补充是,“生产”要有“技术”(S-tRNA),而“技术”源于“科学”(S-sRNA)。在工业和信息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决定“生产”,科学技术决定“经济”,当然现代科学技术文化最终决定了现代社会。
最后来谈“人心决定论”。中国的史家向来有“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的口头禅。那么,是否“人心”是社会系统的最终决定因素呢?首先,我们承认,“人”或者说“人心”,是社会系统中的原始变异点;人心变了,人心丧尽,一个政权肯定会灭亡。中国史家的断语是不错的。贾谊的《过秦论》就基于这个信条。1949年国民党人心丧尽而失政权,共产党人心所向而得政权。可是,它毕竟只决定政权的更迭,就是说只决定社会系统的一个方面、只决定一时一事。其次,“人心”是什么?这里谈论的“人心”决不是一团团的血肉,而是文化信息的接收器。绝大多数人要么接受传统文化,要么接受外来文化,要么接受新出现的流行文化——某种社会思潮,结果,具有共同文化取向的“人心”占到社会的大多数,就会形成推动社会变化和历史进程的力量。然而,“人心”毕竟只是社会-文化思潮的工具,而且经常是盲目的工具,例如外国有十字军、党卫军、塔利班,中国有义和团、红卫兵,他们都曾充当过某种文化-社会思潮的盲目工具。因此,最终还是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在背后决定着社会的变化。
因此, “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必须强调“最终”二字。在社会系统中,帝王的强人意志、专制的强权政治、蛮族的强大军力,都可以杀害文化人、暂时毁灭文化,都可以一时决定社会的兴衰存败,可是从长远来看,最终还是文化决定社会,文化决定社会的命运和社会的进化。经济固然是社会的基础,可是,在现代工业-信息社会,有比经济更基础的基础,那就是教育和文化;没有具有原创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教育和文化做基础的经济,就只能进行来料加工和组装,仅仅是世界工厂而已。人心向背固然可以决定政权的存亡更迭,可是人心不过是社会-文化思潮发挥最终决定作用的工具,而且往往是盲目的工具。
因此,我们观察全球社会,首先看到的是大国之间军事力量的竞争。可是,一位深刻的观察者应该在军事后面看到政治,在政治后面看到经济,在经济后面看到科技,在科技后面看到教育,在教育后面看到文明,在文明后面看到文化。在人类社会中最终是文化遗传基因(S-cDNA)的竞争,一如在生物界最终是生物遗传基因(DNA)的竞争。
将以上论述提高到抽象的理论上和科学的理性高度,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在 “社会系统的新模型”(图1)上,“人”被放在核心位置,环绕“人”的是“文化信息库”,可见“文化”也被安放在中央位置。那么,最后的结论为什么不表述为“人”或“人心”是社会系统的决定因素,而是说“文化”(S-cDNA)是社会系统中的决定因素呢?
历史哲学讲的“人心”是人脑-神经系统和心脏-血液循环系统耦合成的复杂系统的涌现,表现为自我意识,被称为“心灵”。人的心灵中的“意识”是宇宙进化和人超越其他生物特有的第五种元素,人的心灵具有获取环境信息和文化信息的能力,具有以灵感形式产生突变的能力,以此成为社会系统中的文化创新之源,文化反思之源,文化选择之源。
可是,尽管“人”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人的“心灵”作为认知主体具有创造文化的能力,有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能力,具有在多种文化当中做出选择的能力,可是作为社会-文化遗传基因的“文化”是前人“心灵”创造的积淀,是历史的遗产,是社会系统中最稳定的因素和最保守的势力。因此,任何人在进行文化反思、批判、创新和选择的时候,总是受到自己接受的文化遗传的支配,而他做出的反思、批判、创新和选择最终又融入文化传统继续支配自己,支配他人和支配后人。因此可以说,个人“心灵”是即时的文化,而“文化”又是历时的心灵。
这样一来,我们讨论的问题就变得更明晰和更尖锐了:人心创造文化,人心反思-批判文化,人心选择文化,而文化又遗传性地输入人心,控制人心,支配人心,社会系统的状态、结构和行为的演化就在文化和人心的相互作用中前进。可是,为什么说“文化(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呢?可以明确地说,在20世纪末完整的系统科学体系出现以前,任何人都无法解决和回答这个问题,而现在则可以。在哈肯的协同学中有一个“序参量和役使原理”,它科学地、严谨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许国志的《系统科学》这样概括上述原理:
在描述系统状态的众多变量中,有一个或几个变量,它在系统处于无序状态时,其值为零,随着系统由无序向有序转化,这类变量从零向正有限值变化或由小向大变化,我们可以用它来描述系统的有序程度,并称其为序参量(order parameter)。序参量与系统状态的其他变量相比,它随时间变化缓慢,有时也称其为慢变量,而其他状态变量数量多,随时间变化快,成为快变量。
在系统发生非平衡相变时,序参量的大小决定了系统有序程度的高低;它还起支配其他快变量变化的作用。序参量的变化情况不仅决定了系统相变的形式和特点,而且决定了其他快变量的变化情况,在这个意义上讲,序参量也可以称为命令参量。”我们知道,序参量的英文词是“order parameter”, 恰好即可以翻译成“序参量”,也可以翻译成“命令参量。
系统相变过程是一个由系统状态变量形成系统序参量,序参量又役使系统其他状态变量的过程。哈肯将相变过程中系统状态变量里序参量与其他快变量之间役使、服从关系称为役使原理。序参量确定以后,我们讨论系统的演化可以只研究序参量即可,序参量将整个系统的信息集中概括起来提供给我们,序参量给我们了解、认识系统提供了一把钥匙。[15]
社会系统无疑是最复杂的系统。在我们建立的“社会系统新模型”中,每一个子系统都可以看作是一个状态变量。在众多状态变量中,“文化”无疑是“整个系统的信息集成体”,无疑是慢变量,因而文化就是社会系统中的序参量或命令参量,而其他变量(包括人、物质产品生产、人的生产、文化信息生产和管理系统)都是快变量。众多快变量形成“文化”慢变量(即序参量),而文化作为社会系统中的序参量又反过来支配和役使众多快变量,所以文化(S-cDNA)就成为社会系统中的最终决定因素。
将“心灵”和“文化”两相比较,个人的心灵(即便是最伟大的心灵)不过是历史长夜中的流星,而文化则是无数流星汇成的照亮历史长夜的永恒之光。
倘若在笔者做了这么多论证之后,你对“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个命题仍旧有疑虑,那么就让笔者引导你想象地球-人类文明在未来发生的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地球-人类文明现在突然灭绝了,只留下残骸;二是在遥远的将来,在灭绝之前,人类成功地将自己的文明复制到一个类地行星上去了,让你看清“文化”是不是起“遗传密码”的作用。
我们知道,美欧已经发射伽利略探测器(Galileo Probe)寻找地外文明。设想在今后的某个时候,人类在遥远的宇宙空间找到了一颗类地行星,按其自然条件的基本数据,适合复制地球生物、人类和人类社会。可惜的是,那颗类地行星太远了,宇宙飞船要飞300年才能到达,人飞到那里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只能靠智能机器人携带克隆设备,携带地球动植物主要物种的DNA, 携带地球四个人种的DNA, 到那里去克隆。怎么复制那地外的第n+1个地球-人类社会呢?显然只须智能机器人携带一张芯片——五维记录,信息量是现有芯片的一万倍,上面转录有占人类社会文化遗传基因(S-cDNA)5%的功能基因。待新人类克隆出来之后,由智能机器人用那5% 的S-cDNA按图4和图5的程序教育,和他们一起学习、设计、建造和生产,地球Sn+1社会肯定就在遥远的类地行星上复制(翻译)出来了。
抽象地从理论上讲,笔者的意思是,如果我
们已经对地球上现有n个社会系统进行考察,证明“S-cDNA在社会系统中起最终决定作用”这个命题为真命题,而且以上又证明它对未来地球上或地外类地行星上的n+1个社会系统仍然是真命题,那么我就用绝对可靠的完全归纳法对这个命题做了最终证明。
这回,你信服了吧!
[1]维克多·埃尔.文化概念[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2]萧俊明.文化转向的由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
[3]D.Paul Schafer.The Cosmological Conceptfon of Culture[M].world culture project,Markham, Canada.1988.
[4]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99.
[5]闵家胤.进化的多元论——系统哲学的新体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71.
[6]E·拉兹洛.进化—广义综合理论[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8:103.
[7]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182.
[8]闵家胤.社会系统的新模型[J].系统科学学报,2006,(1).
[9]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10]H. D. F.基托.希腊人[M].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1.
[11]金岳霖.形式逻辑[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25.
[12]林定夷.科学逻辑与科学方法论[M].成都: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2003:245-258.
[13]汤因比(Toynbee,A.T.).文明经受着考验[M].沈辉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191.
[1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23,202.
[15]许国志,顾基发,车宏安.系统科学[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245-2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