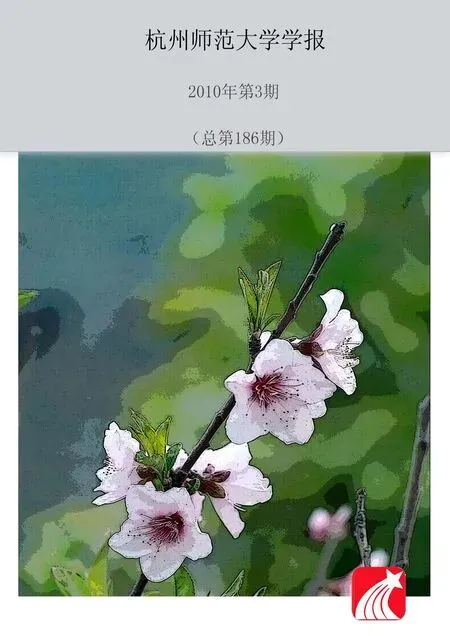走向平衡:卡莱尔文化观探幽
2010-04-11殷企平
殷企平
(杭州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浙江 杭州 310036)
假如一定要用一个单词来形容卡莱尔的文化观,那就应该用“平衡”(balance)一词。事实上,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在《文化与社会》(CultureandSociety,1958)一书中曾经多次用“平衡”来评价卡莱尔的思想精粹。不过,威廉斯又认为“平衡”通常不属于卡莱尔的思想范畴:“我们想到卡莱尔时,通常不会联想到平衡的观念。然而,这篇论文(笔者按:指《时代的特征》一文)中有真正的平衡:既有洞见,又有决断;两者达到的优美统一,如今已非常罕见。”[2](P.75)相比之下,倒是我国青年学者何艾莉的下述观点更为贴切:卡莱尔为治病救世“开具的各类药方都遵循了平衡这一主导思想”。[3](P.1)应该说,平衡的观念不仅体现于卡莱尔开具的各类药方,而且体现于他的各种论述;不仅贯穿于《时代的特征》,而且贯穿于他的整个创作生涯,因而是他文化思想的灵魂。
本文拟在细读卡莱尔有关作品的基础上,探讨平衡观念在卡莱尔文化思想中的位置。
一 精神与物质的平衡
卡莱尔是在对工业主义的批判中提出并完善自己的文化观的。如威廉斯所说,“在卡莱尔那里,把文化看作一个民族的总体生活方式的观念明显地得到了新的增强。这种文化观是他抨击工业主义的基础:一个社会若要名副其实,维系它各个组成部分的就应该远远不止是经济纽带,应该远远超越那种以现金支付为唯一联结的经济关系”。[2](P.83)威廉斯此处点明了卡莱尔从事文化批评的原因和目的:他身处一个精神与物质失衡的社会,一方面是高速发展的工业和科技,另一方面则是信仰缺失、道德沦丧和两极分化;如果不解决这一问题,整个社会将名存实亡,因为人类社会不可能仅仅靠经济纽带来维系。换言之,卡莱尔意在改造以“现金联结”(cash-nexus)为特征的社会。“现金联结”和“工业主义”都是卡莱尔首创的术语,前者指涉“由自由放任、竞争供求关系的哲学来说明”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4](PP.54-55)后者的意思与之紧密相连:发展工业本来无可厚非,但是一旦上升到哲学层面,成为一种主义,就会导致“现金联结”,也就是导致物质与精神的失衡。
针对这种失衡状况,卡莱尔使用了“文化”这一术语。尽管这一术语不是他的首创,但他用文化概念来与现金联结、工业主义和机械主义抗衡的最早的、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因而是约翰逊所说的“19世纪文学知识分子”中最杰出的代表:“19世纪,文化概念大体属于文学知识分子的研究领域。当时对英国社会的不满、抗议和批判主要来自他们,并形成了一种社会思想传统,而文化是他们用来表示这一重要传统的术语。”[5](P.1)当然,卡莱尔不仅使用了“文化”,而且设定了“现金联结”等许多术语。对此威廉斯有过中肯的评论:“他设定这些术语,是为了恢复平衡。”[2](P.75)令人费解的是,威廉斯虽然大段大段地引用了卡莱尔的有关论述,但这些引文中没有一处直接出现过“文化”一词。事实上,仅在《拼凑的裁缝》一书中,卡莱尔就多处使用过“文化”一词,如“我们伟大的商业和高贵的宪法给所有的英国文化和活动打上了政治烙印,或者说急功近利的烙印,因而阻碍了思想的自由飞翔”。[6](P.5)卡莱尔此处说的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脱节、失衡的现象:维多利亚社会注重商业,注重宪法等外在机构和制度的建设,却折断了思想的翅膀,也就是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竟让文化也打上了急功近利的烙印——这种“文化”其实只是一种假文化或“反文化”,因而卡莱尔呼唤真正的文化,呼唤能确保精神和物质之间平衡的文化。
在卡莱尔看来,人类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的失衡,是“机械时代”的固有现象。他在《时代的特征》一文中首次用“机械时代”来命名那个时代的:“假如我们需要用单个形容词来概括我们这一时代的话,我们没法把它称为英雄的时代或虔诚时代,也没法把它称为哲思时代或道德时代,而只能首先称它为机械时代。无论就外部意义而言,还是就内部意义而言,它都是一个机械时代。”[7](P.100)下面这段话解释了“机械”的意思:“目前受机器主宰的不光有人类外部世界和物质世界,而且还有人类内部世界和精神世界……不光我们的行动方式,而且连我们的思维方式和情感方式都受同一种习惯的调控。不光人的手变得机械了,而且连人的脑袋和心灵都变得机械了。人们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失去了信心,对任何自然的力量失去了信心。他们希冀并为之奋斗的不是内在的完美,而是外在的组合和安排,是机构和法则,是这样或那样的机制。他们的所有努力、寄托和看法都围着机制转,都具有机械的性质。”[7](PP.101-103)此处,关于内在文明和外在文明——也就是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的失衡,以及这种失衡所具有的机械性质,卡莱尔已经说得非常透彻。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卡莱尔所说的外在文明不仅是经济建设,更重要的是诸如机构和法则之类的建立,也就是我们如今所说的法制建设。工业革命之后,欧洲各国开始流行这样一种观念:只要进行政治改革,并加强法制建设,一切社会矛盾就会迎刃而解。卡莱尔把这种观念的流行也看作“机械时代”的特征之一:
从一开始我们就能注意到,世人对纯粹的政治和法律上的安排表现出强烈的兴趣,这本身就是机械时代的特征。整个欧洲的不满都被引向了政法改革。从所有文明国家的深处,都传来了一个强烈的呼声,一个必须予以回应的呼声:让我们进行政改吧!良好的立法机构、适当的行政约束、明智的司法安排,构成了人类幸福的所有要素。……我们的幸福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更有甚者,我们的精神力量和尊严竟成了这些外部环境的产物……[7](P.106)
卡莱尔的这段论述非常重要,可惜它被引用的频率并不高,被接受的程度更不高。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法制文明只是物质文明,只代表外在的刚性力量,代替不了道德情操等柔性力量;若把人类的幸福只寄托于前者,而轻视后者的作用,那不啻严重失衡。在卡莱尔之前,还没有人能用如此犀利的语言,来阐明其间的利害得失。仅凭这一点,卡莱尔就足以彪炳青史。
Thermodynamic Analysis of Supercritical Working Fluid Brayton Cycle ZHENG Kaiyun(42)
须强调的是,卡莱尔并不反对外部文明或物质文明的建设。常常有人把他说成“道德主义者”,这种说法过于简单。卡莱尔注重道德不假,但是他并非唯道德论者。他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互补的社会:
人的这两类活动(笔者按:指人的内心活动和人在外部世界的活动)互相作用,互相依赖,其联系错综复杂,难解难分;要划定它们的界限,从本质上讲是不可能的。即便对最明智的人来说,它们的相对重要性也因时而异,因具体时代的特殊需求和特殊趋势而异。显而易见的是,我们只有使这两类活动协调无误,使两者都生机勃勃,才能找到正确的行动路线。对内在动力的不当培育,以及对外在动力的不当培育,都会产生危害;前者会导致懒散虚幻,导致不切实际的行为……后者虽然一时不容易暴露偏颇之处,甚至会带来许多可以触摸的短期利益,但是最终必然会摧毁道德力量,也就是摧毁一切力量的源头,因而比前者的危害有过之而无不及。[7](P.111)
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个重要观点:(1)内心世界和外部世界必须协调发展;(2)两者的重要性因时而异。这两个观点属于卡莱尔文化思想的核心部分。换言之,卡莱尔的文化思想是辩证的、反机械主义的——他关于道德力量的论述是最好的见证:虽然道德力量是一切力量之源,但是它的重要性仍然是相对的,是因时而异的。只有因时而异,才能在总体上获得平衡,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二 工作:通向平衡之路
卡莱尔的文化思想,不仅表现为对精神与物质失衡现象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寻求平衡之路的努力。
卡莱尔之所以向往平衡,是因为他相信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历史的发展应该像有机体生长的过程。他早年深受伯克和柯勒律治等人的影响,后者尊崇传统,强调社会的有机体特性,尤其强调“价值观和制度都不是在书斋里制造出来的,而是从源远流长的历史事物这一土壤中生长出来的”。[8](P.251)把社会看作有机体的观念,必然强调事物的整体性与和谐性,也就是平衡性,而机械主义则必然撕裂社会整体,破坏其和谐性与平衡性。如前一小节所示,由于机械主义施虐,卡莱尔所在的社会已经严重失衡,因此他要奋力寻找通向平衡的道路。
通向平衡的道路在哪里呢?
卡莱尔认为,工作是通向平衡之路。他在《过去与现在》一书中提出了“工作福音”一说,其矛头直指“现金福音”,或称“现金联结”,即用自由放任、竞争供求关系的哲学来说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哲学,而“这种哲学将成为一种拜物教,一种终极的世界福音;并作为一种信仰而甚嚣尘上,满足人们的虚荣之心——但这始终是一种不祥的信仰”“现金福音”之所以不祥,是因为它会造成前文所说的失衡现象。正因为如此,卡莱尔提出了与之针锋相对的“新福音”:“在这个世界上,最新的‘福音’是:了解你所要做的工作,并认真去做你所要做的工作。”[4](P.61)他还说:“有一种福音历史比其他任何福音更悠久,它还没有被人传播,它是不可言说的,但是,它却根深蒂固、万古长存。这种福音就是:工作,会给我们带来幸福安宁。”[4](P.67)这里所说的“幸福安宁”,不无平衡的意味。
确实,“工作”是卡莱尔文化思想的核心概念之一。布雷顿曾经对卡莱尔、康拉德和奥威尔笔下的“工作”与“劳动”这两个概念作过分析和梳理,并坦言他使用的“工作”概念与威廉斯《文化与社会》一书中的“文化”“几乎是同义词”。[9](P.21)布雷顿还说:“跟威廉斯一样,我相信关于工作的总体理论(他的总体理论是关于文化的)应该把握作为总体生活方式的工作与劳动(或文化与社会)之间的关系。”[9](P.21)布雷顿的这段话,至少用在卡莱尔身上是非常合适的——卡莱尔提出“工作福音”,是因为他发现人类的生活方式出现了问题。按照威廉斯在《关键词》(Keywords,1976)一书中的考证,“文化”一词最常用的意思是“一个民族、一个时期、一个群体乃至全人类的某种特定生活方式”。[10](P.90)从这一意义上说,卡莱尔对工作的关注,就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也就是对文化的关注。
把工作视为生活方式,以崇敬的态度对待它,这是19世纪兴起的一种新观念。*西方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着贬低工作的倾向。古希腊人一般把它跟奴隶联系在一起;古希伯来人和中世纪的基督徒大都把工作视为负担或惩罚——人为了赎原罪才工作。除卡莱尔以外,推动这一观念的有艾略特、罗斯金和莫里斯等小说家和文化批评家。例如,艾略特笔下的亚当就是“工作福音”的化身。他虽然也把工作当成谋生手段,但是更注重工作本身能够带来的愉悦、自豪感和满足感。他多次当着乡民们的面说:“不管我的报酬是多是少,只要我着手做一件工作,就要把它做好”在小说的尾声部分,我们仍然发现“工作始终是他的宗教的一部分”。[11](P.227,416)亚当这一形象的塑造,跟卡莱尔的影响不无关系。爱略特自己就曾经强调,她所处的“这个时代里出类拔萃或思想活跃的人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未受过卡莱尔作品的点化”;“假如卡莱尔从未出世,英国过去十至二十年中问世的任何一本书都会变样”。[12](P.344)也就是说,在19世纪传播“工作福音”的文人、学者中,卡莱尔是不容争议的第一人。
在卡莱尔所生活的时代,“工作福音”并非当时社会的主流话语。当时占据主流位置的是亚当·斯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等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些理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倾向于用抽象的概念和模式、可以量化的数据和指标来解释世界,并用单向度的经济/物质进步来衡量生活的质量。一言以蔽之,它们的共同支撑点是机械主义和工具理性。根据这些理论,工作只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或是社会创造财富的手段,而像亚当那样以工作为乐趣,则被视为非理性的。不仅工作只是手段,工作者也成了手段——亚当·斯密就是这样看的:他笔下的劳动者几乎全都是抽象的符号(也就是理性和感性失衡的产物),我们无法从中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和七情六欲。亚当·斯密为社会“进步”提供的“秘诀”也十分简单:只要“诉诸(人们的)自利之心”即可,因为带有市场特征的“交换倾向受到自利心的鼓励,并导致劳动分工”,而“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13](PP.5-15)假如亚当·斯密的理论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那它还有合理之处,然而它不幸从生产方式的指针,延伸为好几代人生活方式的指针,因而导致了前文所说的物质与精神失衡的现象。应当承认,亚当·斯密,以及后来的李嘉图和马尔萨斯,也都关心社会问题,但是他们有关社会的构想都明显地打上了机械思维的印记。恰如玛丽·普维所说,“马尔萨斯的追随者们一贯把社会看成一个身体,其健康虽然时常受到各种疾病的威胁,但是只要利用立法的手段,就能药到病除;李嘉图的弟子们则坚持认为,社会好比一架机器,即便出现了短暂的故障,只要加上一些‘调节器’,就能加以修复”。[14](P.132)按照这种思维逻辑,工作/劳动只是“调节器”,只跟经济利益挂钩,只跟工资、合同和劳动时间挂钩,而跟劳动者(也是“调节器”)的精神诉求无关。这种把工作局限于经济和物质领域的思维模式,必然导致一种畸形的、失衡的生活方式。
上述思维模式还导致了马克思当年批判的劳动异化,即主客体的分裂和倒置。劳动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变成一种异己的活动,这在卡莱尔的笔下时有揭露。他在许多著述中都猛烈抨击了劳动者被剥夺劳动果实(也就是劳动异化)的现象,并在《宪章主义》一文中发明了“英国状况问题”一语,用来指称英国工人阶级含冤受屈的种种惨状。[15](P.168)在这种异化背后,是以自由竞争为核心的、机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作怪,因此卡莱尔在《过去与现在》中强调,自由竞争已经导致如下怪现象:一方面是劳苦大众在“出口自己制造的机械,纺纱炼铁”,另一方面“棉布已价值两便士一码,甚至更低,衣不蔽体者触目皆是”。[4](PP.49-50)在《时代的特征》一文中,他还揭露了工人被机器奴役乃至驱赶(同样是劳动异化)的现象:“在各方面,活生生的工匠都被赶出他的作坊,让位给一个速度更快的、没有生命的工匠。梭子从织工的手指间掉落,落入到穿梭得更快的铁指中。”[16](PP.108)也就是说,作为主体的劳动者和他/她所处的客观世界之间的分裂已经日趋严重。
正是针对这样的异化现象,卡莱尔提出了他的“工作福音”。如布雷顿所说,卡莱尔跟马克思一样,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黑格尔的工作观。根据后者的观点,“工作不只是一种具体的经济活动,而是自我在精神的指引下塑造世界的方式:‘人’和世界的中介”。[9](PP.37-38)换言之,工作是连接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桥梁;人通过劳动,既改造了世界,也改造了自己,也就是使世界变得更加和谐、平衡。在《过去与现在》中,卡莱尔清楚地写道:“人正是通过工作来完善自己的。通过工作,龌龊的丛莽被清除了,取而代之的是肥沃的良田和雄伟的城市;而且,人自己也不复为丛莽,不复为龌龊的、不健康的沙漠。”[17](P.204)从这段话来看,布雷顿的观点是中肯的:卡莱尔确实跟马克思有十分相似之处,他俩都认为“工作开启了一个主客体互相改变的过程——主体改变了世界,世界也改变了主体。这一思想牢固地确立了历史在哲学中的地位”。[9](P.37)值得一提的是,卡莱尔经常被贴上“唯心主义者”和“神秘主义者”的标签,可是以上分析表明,他的工作观跟历史唯物主义观不无相通之处,至少他在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追寻着平衡。
在卡莱尔的平衡观中,工作和闲暇也是不可分割的。卡莱尔十分讨厌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即“人们工作,只是为了享受随后的闲暇”。[9](P.4)前文提到的那些政治经济学理论家们就十分热衷于这种观点,其指导思想是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主义。卡莱尔的“工作福音”跟这种观点形成了抗衡。前文提到,卡莱尔对工作的关注,就是对人类生活方式的关注。更确切地说,在卡莱尔眼里,工作就是生活方式。在《拼凑的裁缝》里,主人公托尔夫斯德吕克经历了千辛万苦,同时经历了一个从“持久的否定”向“持久的肯定”的转变过程,也就是找到了正确的生活方式。下面是他找到生活真谛后的一段表白:
我现在也可以对自己说:不再是一片混乱,而是一个世界,甚至是世界的近似物。创造!创造!……起来!起来!无论什么事,你的手发现要干,就要全力去做。今天你就要工作,因为夜晚到来了,那时候什么人都不能工作。[18](P.182)
在这段话中,工作、信仰和生活方式几乎是同一个概念。在这样的生活方式中,工作其实包括了闲暇,两者是互相交融的。这让人想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一段话:“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文艺批评,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评家。”*笔者根据原文对这段译文的个别文字作了更动。[19](P.27)卡莱尔的表述跟马恩的这段表述虽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把工作视为理想的生活方式,其要素仍然是本文始终强调的“平衡”:人只有在工作和闲暇互通的社会里生活,才能使自己的各项才能平衡地发展。
综上所述,平衡是通向卡莱尔学说的一把钥匙,是他文化观的核心。平衡牵引着他的思绪,激扬着他的文字。无论是针砭时弊,还是憧憬未来,他都遵循了平衡之道。在他描绘的文化图景中,精神和物质,主体和客体,都呈平衡之态。为实现平衡,他寄希望于工作。他呼唤平衡,为了他所生存的时代,更为了千秋万代。
[1]黄卓越.定义“文化”:前英国文化研究时期的表述[J].文化与诗学,2009,(1).
[2]Williams, Raymond.CultureandSociety[M]. London: Chatto & Windus,1959.
[3]何艾莉.寻求平衡[EB/OL].http://cdmd.cnki.com.cn/Article/CDMD-10335-2008088553.htm.
[4]托马斯·卡莱尔.文明的忧思[M].宁小银译.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5]Johnson, Lesley.TheCulturalCritics:FromMatthewArnoldtoRaymondWilliam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1979.
[6]Carlyle,Thomas.SartorResartus[M].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
[7]Carlyle,Thomas.TheCollectedWorksofThomasCarlyle,Vol.Ⅲ[M]. London: Chapman and Hall,1858.
[8]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9]Breton, Rob.GospelsandGrit:WorkandLabourinCarlyle,ConradandOrwell[M].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1965.
[10]Williams, Raymond.Keywords:AVocabularyofCultureandSociety[M]. Flamingo: Fontana Press,1983.
[11]Eliot, George.AdamBede[M]. Hertfortshire: Wordsworth Classics,1997.
[12]Eliot, George. “Thomas Carlyle”, inSelectedEssays,PoemsandOtherWritings, (ed.) A. S. Byatt and Nicholas Warren[M]. Harmondsworth: Penguin,1990.
[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原因和性质的研究[M].杨敬年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
[14]Poovey, Mary.MakingaSocialBody:BritishCulturalFormation, 1830-1864[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
[15]Carlyle,Thomas.‘Chartism’[A].EnglishandOtherCriticalEssays. London: J.M. Dent, 1950.
[16]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M].吴松江,张文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
[17]Carlyle,Thomas.PastandPresent[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1927.
[18]托马斯·卡莱尔.拼凑的裁缝[M].马秋武,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9]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