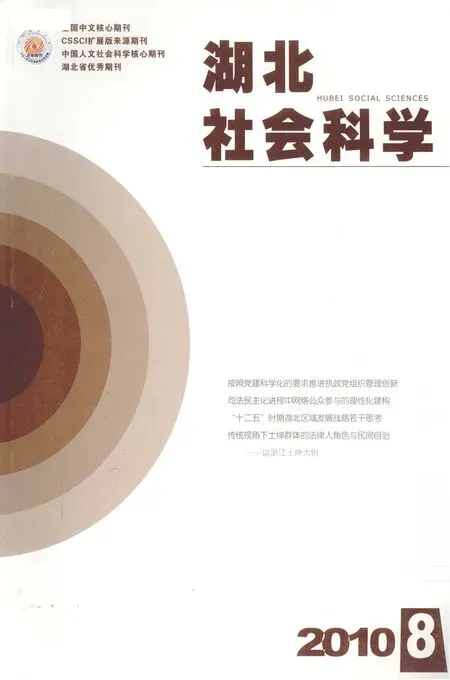孟荀人性论的再审视
2010-04-10谭绍江
谭绍江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孟荀人性论的再审视
谭绍江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论说”是先秦诸子为实现各自理想所采取的重要手段。论说主旨和所面对的论说对象的同异决定了诸子某些具体的思想内容的同异。孟荀二子在阐述人性论时,主旨同为实现儒家理想,所面对的对象也都包括了“在上者”和“庶民”两种对象。从这种视角出发,二子在人性论上的观点之同异可以被再解读。
孟子;荀子;人性论;在上者;庶民
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作为先秦时期两位儒学巨擘,二人迥异的观点差异带来了后世数千年的纷纭聚讼。笔者发现一个前人或有所忽略的问题,那就是,二子在进行立论之时,是如同今日文章一般,将所有观点统一地面对全体读者呢,还是每篇、每段论说都有各自不同的对象,按照对象的不同在进行分别的论说呢?这值得分析。
论说是先秦时代知识分子都致力从事的主要工作,孟、荀也不例外。他们在各自的年代围绕着能否实现儒家的理想主张,在不同的历史时空中进行了大量“论说”。从这种论说的角度出发,我们发现,孟、荀在许多理论的阐述上都是有着鲜明的“对象性”特点的。也即,对于同一个问题,二子文章是在面对不同言说对象进行不同的言说。虽要旨为一,但在具体论述、观点上有相应之差异。而再以此“论说对象”的特点出发,我们发现二子的关于“人性”的思想内容可以进行重新的解读。
二子在“人性”上的论说对象大体可以分成两个类型。一个是面对“在位者”“、在上者”或者“为君者”这样一些掌握权力者或者将要掌握权力者的论说;另一个则是面对庶民、众庶也即面对全体人群、一般人类的论说。按照这种论说对象的划分,二子在“人性论”上的观点有一番异同需要重新审视。
一
为达成自己的政治主张,孟、荀都孜孜奔走于各国诸侯之间,用具有说服力的观点对诸侯们进行劝导,以期见用,在其论说中就包含着“人性论”的内容。
先看孟子。他在与梁惠王对话时讲道“: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孟子·梁惠王章句上》)这里孟子的主旨不是在讨论“人性”,但是他言论中的内容却无疑正是将人性中所包含的某些内容透露了出来,也能窥见他对于人性的部分看法。他认为“士”与“民”在人性上是有区别的,这个区别也即能否保有“恒心”。朱熹注曰“: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士尝学问,知义理,故虽无常产而有常心。民则不能然矣。”[1](p203)也即,孟子认为于“民”而言,若无恒产常处困窘中,则人性中的“善心”并不能常驻。“善心”不常驻,则会作恶。因此,为君者必须把握“民”在“人性”上的这个特点,先解决庶民基本的生存需要问题,方能引导成善。“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章句上》)无疑,此处站在“民”的立场上,孟子认同了“人性”中作为自然欲望的内容。这与他的论说目的密切相关。此时面对掌握了实际政治权力的梁惠王这位“在上者”,他必须鲜明地指出这一点。只有将人的一般自然欲望都算作“人性”——而且对于“民”而言是必须首要满足的“人性”,才会让“在上者”去着手解决这些问题。这是他所极力推行的“仁政”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再看荀子。荀子之书,对话式较少,大部分都是直接论述的,所以他某些论说对象不能像孟子那样直接就知道,但是也并非就看不出来。从言论内容、态度以及所要达到的目的上仔细分析,大体可以窥见他论说时所面对的对象是什么样子的。围绕着他的主张,他的论说对象有分别。“与很多具有劝说倾向的著作不同,《荀子》有选择地设定说服对象。”[2](p17)他讲“性恶”的时候,对象就不是一般庶民百姓,而是“在上者”或者潜在的“在上者”。
我们来看他论述的逻辑以及最终之目的。他是从人的天生之性说起的。“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荀子·性恶》)他认为,能被称为“人性”的应该是天然而具有的,这种东西最直接就是人的自然欲望和人的天生能力。如“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煊,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荀子·性恶》)这是讲欲望。“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荀子·性恶》)这是讲天生的能力。对这种欲望和天生能力本身,他无意定其善恶。真正的“恶”来自对欲望的放纵。“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荀子·性恶》)王先谦注曰:“性,天生性也;顺是,顺其天性也。”[3](p434)显然,荀子不是直接将人性定义为“原罪”的“恶”,他是先承认了人具有“好利疾恶”、“耳目声色”这样一些“天生”的基本欲望,如果完全顺从、放纵下去就会演变成“恶”。
那么此时,他的论说对象是谁呢,是面向庶民吗?我们看他下面的说明:“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他此处是在对上述“性恶”现象提出的解决之道——“师法之化”、“礼义之道”。从上下文结合起来的倾向上看,在荀子的思维中,“师法”、“礼义”不可能是一般民众自己能具有的,而应该是来自庶民个体之外的力量,包括“圣人”、“圣王”。“问者曰:‘人之性恶,则礼义恶生?’应之曰:‘凡礼义者,是生于圣人之为,非故生于人之性也。’”《荀子·性恶》)这里就更进一步表明了这种态度,解决人性本身可能带来“恶”的弊端的方法之“礼义”,不在一般人自己那里,而在“圣人”。“圣人”应该是庶民还是在上者呢?“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这一段话讲得很清楚,靠“人”、靠庶民自己的话,则会在一连串“不能不”之后,必然”会达到“争则乱,乱则穷”的地步。真正在最后能起到解决问题作用的还是能“制”“礼义”的“先王”,他显然不是一般的庶民,而应该是能够引导、领导众人的“在上者”。他当然也讲到过“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荀子·礼论》),但他这么讲只是在强调“圣人”的来源问题,并不影响“圣人”在地位上应高于众人的判断。荀子在此处所强调的“性恶”,与其说是专论一般之人性,不如说是站在“在上者”的角度审视一般庶民的人性。对于要达到“治”的“在上者”而言,他应该明白,在普通庶民人性中最主要的部分是自然欲望,这是庶民自身无法控制的。如“在上者”不加以节制疏导,则后果便是恶”的流行。这样就为“在上者”从外在的路径通过“隆礼重法”的方法推行儒家的理想以引导与管理社会秩序[4](p89—94)找到了人性上的根据。
以上内容是孟荀二子在面对“在上者”时的“人性”论说,我们发现,二子共同点是都试图让“在上者”明白一个道理,即庶民人性中的自然欲望是需要重视的。二子差异在于孟子是要让“在上者”想法去满足庶民的基本欲望,荀子则让“在上者”想法去节制庶民欲望的过度。
二
再来看二子是如何面对另一种对象——庶民或说一般人群进行“人性”论说的。
孟子讲“性善”从人心中皆有之“端”说起。他认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仁”、“义”、“礼”、“智”四者之“端”。“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孟子·公孙丑章句上》),人若保持这四端不丧失,并将这“四端”不断培育、推广开去,便能成“善”乃至成“圣”。他强调,此乃人应具有之本性,是一种人“固有之”的能力,“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孟子·告子章句上》)这也就是他所谓“人性善”的基本涵义。那么,他讲“性善”是面向什么对象在进行的呢?从《孟子》文本本身来看,孟子讲“性善”有不同的场合,有时是独白,有时在和人辩论,有时是在向学生宣讲。但若进一步分析他之所以持“性善”之论的背后原因,我们可以确定他讲“性善”最主要面对的对象应是“庶民”或者说一般人群。孟子讲“性善”,最根本的原因是要上继子思《中庸》的主旨,为在一般人中挺立“君子”这个“道德主体”夯实先天的依据。[5](p5—12)同时,有些时候,他在激烈地强调“性善”还有更直接的动机。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桊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桊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桊,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孟子·告子章句上》)朱熹注曰:“言如此,则天下之人皆以仁义为害性而不肯为,是因子之言而为仁义之祸也。”[1](p308)显然,孟子此时讲“性善”的直接动机就是非常担心一旦告子将“人性”与“仁义”分开的理论被传播开去,会使得天下民众思想混乱而不肯再勉力行仁义,铸成巨祸。所以,他要竭力批驳告子,以正视听。由上可知,孟子讲“性善”是想告诉以庶民为主的天下人,一方面,大家都先天具有为善的能力,是性善之人;若是有人为恶,不是与生俱来的能力问题,而是自己将之丧失而不找寻的问题。另一方面,若是有人向大家宣扬人性不是“善”的理论,大家千万不能相信,因为那样会让大家迷失人生道路进而迷失社会的方向以致天下大乱。所以,无论孟子是要为人能挺立“道德主体”夯实先天依据,还是担忧“非性善论”的泛滥会使得天下人心错乱而带来社会动乱,他都是以全体人群或者说庶民为对象的。
荀子讲“人性”也有个面对庶民的论说问题。我们仔细审视荀子之文,就会发现,除了那些天生的自然欲望和能力之外,分明还有一部分内容也是人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比如,“义”和“辨”。“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生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荀子·王制》)“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荀子·非相》)“夫禽兽有父子而无父子之亲,有牝牡而无男女之别。故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荀子·非相》)上文中第一段中所论之“义”不仅属于“人性”,而且是人特有之性,因为因它才使人“最为天下贵”,优于其他非人类事物。第二、三段又进一步强调了“辨”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那么他这样讲人性的时候是在对谁讲呢?其实在他的言辞里面我们已经可以找到答案。他在性恶》中写道:“‘涂之人可以为禹。’曷谓也?曰:‘凡禹之所以为禹者,以其为仁义法正也。然则仁义法正有可能可知之理,然而涂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然则其可为禹明矣。’”
很明显,他说这么多关于在人性中具有的“最为天下贵”的特性,就是要讲给“涂之人”听的,也即面对最普通的大众,以庶民为主的天下人为对象。其目的就是要让大家拥有“为禹”的信心,勉励人行善。
将以上内容对比,我们同样发现,在面对庶民时,孟荀二子在“人性”内容的观点上也有极大的相类性。他们都积极强调人性中具有主动为善、进行道德理想追求的内容。不同的是,孟子讲“性善”的时候有意排斥其他人性成分,而荀子在讲人这种“仁义法正”之质具时,并不排斥其他的人性内容。
三
通过审视孟、荀二子在面对“在上者”和“庶民”时所进行的具体的“人性”观点论说,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新的结论:其一,孟、荀二子原来看似水火不容的两种“人性论”主张,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十分相同的内容。这种相同一方面体现在具有相同的推行儒家理想的主旨,他们都是想通过对社会中个体的良好培育推展到社会的整体和谐;另一方面,他们在思考如何去推行儒家主旨时所选取的角度也是相同的。他们都是选择面对“在上者”和“庶民”时进行不同的“人性”论说。并且,面对“在上者”时,都会强调“人性”中自然欲望的内容需要重视,面对“庶民”时,都会强调“人性”中道德能力的内容需要重视。其二,孟、荀二子的“人性论”都是多层次的。自然欲望与道德能力,起码这两种内容在他们的“人性论”观点里都有自己的位置。当然,对这两种内容的位置排布有所不同。一方面,各自有突出的重点,孟子当然突出了道德能力的内容,而荀子更强调自然欲望的内容。另一方面,在对待这两种内容的态度上有差异。孟子在强调一个内容的时候,会排斥另一个内容。例如,他在强调人的“道德能力”时候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孟子·尽心章句下》)他告诉大家,人性中有自然欲望,但是人的自然欲望在现实中会受到许多客观因素(所谓“命”)的制约,根本无法真正自主地追求,不是人性的本真,故而应将之排斥在“君子”所确认的“性”之外。荀子异于是,他讲两种内容时采取的是将二者合而言之的态度。上文已经提到过,荀子论“人性”时很注重“合”的问题,他在强调人比其他事物“贵”的根本原因是在于人有“义”时,也并不因此就把人性中与其他事物相同的那部分属性排斥掉。其三,二子论说“人性”时所选取的论说对象的重心不同是导致二子差异的主要原因。显然,孟子更为看重的是对庶民、普通大众的论说。从孟子的态度来看,他对自己通过说服“在上者”来推行“仁政”的现实可能性是有忧虑的。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章句下》)朱熹注曰:“言当此之时,而使我不遇于齐,是天未欲平治天下也。然天意未可知,而其具又在我,我何为不豫哉?然则孟子虽若有不豫然者,而实未尝不豫也。”[1](p240)孟子口中说的是乐观而无豫,其心中实忧。因此,通过“在上者”这条路径去推行“仁政”不是他真正的学术重心,其重心在于在当时复杂的生存状态下,为众庶找到一条反身向内、成己成人的道路,他希冀让所有人(尤其是生存状态不理想的人)通过心灵的修持而达到维系信念、保有信心的道路,保持住生活的希望。在个体成善的基础上,使得社会能真正和谐。所以他要强调“性善”的问题,强调“善端”的问题。
而荀子更看重的则是针对“在上者”的论说。对于通过“在上者”来推行儒家理想,“隆礼重法”,他有一定的信心,并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有较为全面的论证。所以他指责“思孟学派”时很大的原因是担心在面对“在上者”时过于强调人性中“性善”的东西不能达到说服的目的。他认为“思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其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案饰其辞而祗敬之曰:‘此真君子之言也’。”(《荀子·非十二子》)在这段话里面,他首先就指出孟子的错误在于“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也即对儒学如何通过“先王”这条路径的传播是弄错了的。结合前文的分析,荀子认为以“先王”立场推行儒学应该以“人性恶”为基础,否则,就不需要“先王”、“圣人”来特地引导了。而在下者的庶民们也就失去了“为学”的动力。“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荀子·性恶》)我们看到了荀子站在他的主要论说立场上体现出来的巨大忧虑与担心。这与孟子对告子的担心如出一辙。
总之,从“论说对象”这个视角进行简要关照,我们发现,孟、荀二子对人性的真正看法都是清醒而全面的,并非偏狭之论,且作为儒家,二子在人性论说的主旨上也是相同的。造成二子在某些具体观点的激烈冲突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的论说重心的差异。孟荀二子在“人性”论上的主张可以互为补充,我们不应对之过于对立地看,而应更多地采取综合的态度。
[1]朱熹.四书集注[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2]陈文洁.荀子的辩说[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
[3]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
[4]化涛.“隆礼重法”与王霸兼用——荀子政治思想研读[J].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7,(1).
[5]胡治洪.中庸新诠[J].齐鲁学刊,2007,(4).
[6]米继军.荀子“隆礼重法”观辨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3).
[7]陆建华.荀子礼法关系论[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2).
责任编辑 高思新
B222.5 B222.6
A
1003-8477(2010)06-0112-03
谭绍江(1981—),男,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