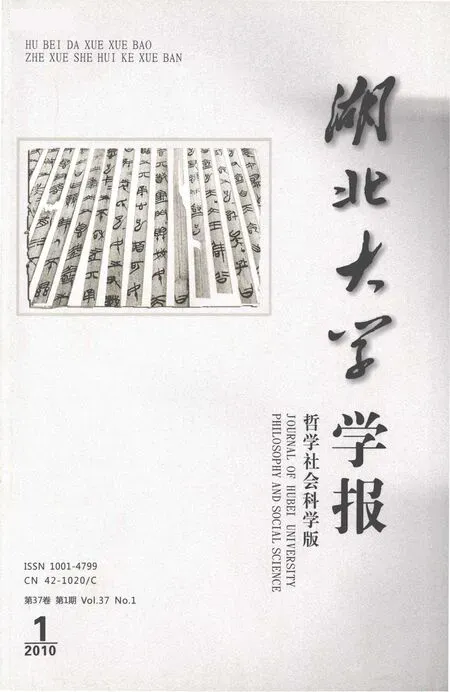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
2010-04-08彭雷霆
彭雷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
彭雷霆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072)
晚清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实为近代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官方统一名词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在这一机构出台的过程中,曾主管学部的张之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名词馆的筹设得其赞同,始能成事,而且其对新名词的政治考量使得名词馆的出台并不单只是为了统一名词,也暗含了借此纠正士风、严防邪说暴行的潜在目的。张之洞寄予名词馆的这一潜在目的,揭示了清政府积极介入名词审定的关注所在,即通过审定名词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遏制各种不利于清政府统治思想的传播,是清政府隐性国家控制的一次技术实践。
张之洞;编订名词馆;学部;审定名词
在近代的野史笔记中,湖南朱德裳在其《三十年闻见录》中留有这样一则关于张之洞的记载:
清自庚子后,以各国清议所在,仍下明诏废科举,设学堂。各省督抚以能派学生为有体面。张孝达(之洞)改定两湖功课,派遣学生动以百计。朝廷特派专员为留学生监督,汪伯棠最先。一时日本名词,终日在士大夫之口。孝达厌之,以为此日本土语也。当日本初译西籍,定名词时,亦复煞费苦心。大半取裁内典及中国《史》、《汉》诸书,非杜撰。如“禁产”、“准禁治产”之类,本于佛典;“能力”二字,本于《史记》,如此之比,不可胜数。至“宪法”二字,尤为古雅。中土初译西籍,谓为“万法一原”,意同而词累矣。今外务部行文中犹有“治外法权外”之语,日本人定为“治外法权”,岂不文从字顺耶?孝达在军机时,欲有以矫之,特设名词馆于学部,以严几道(复)为之长,改“原质”为“莫破”,理科书中所谓“含几原质”者,改为“几莫破”,一时传为笑柄。然西籍苟非由日本重译而来,此等笑话,不知多少。[1]66~67
朱德裳此则笔记虽为私家野乘,但透露信息却颇多,特别是明确提及了张之洞与晚清学部编订名词馆之间的关系,将编订名词馆的设立归之于张之洞想要纠正当时国人流行的“日本名词”。此一论断,粗粗看来似乎并不可信。因为张之洞在1909年10月4日即已病逝,而编订名词馆直到该年11月2日才得以正式成立。两者在时间上存在明显的差距。但值得注意的是,另一熟悉近代掌故的徐一士也曾指出:“学部之设名词馆,当亦(张)之洞之意。”[2]283若说单只朱德裳一人之言,还事有可疑,但同为当时人且被世人誉为“凡所著录,每一事必网罗旧闻以审其是;每一义必训察今昔以观其通。思维缜密,吐词矜慎”(徐一士:《一士类稿·孙思昉序》)的徐一士也持此说,则让人不得不正视此事,细究缘由。
朱德裳关于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的论述其实包含两层含义:一为编订名词馆的设立出自张之洞之意;二为张之洞设立编订名词馆的目的是为了纠正“日本名词”。今若要考究此事真伪,关键也在此两点。鉴于学界迄今为止对于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之间的关联仍无专文论及,笔者拟就此略加探讨,以求正于方家。
一
晚清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实为近代汉语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近代中国官方统一名词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在这一机构出台的过程中,曾主管学部的张之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编订名词馆隶属于学部,是继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所设文典处之后的另一个官方审定名词的专门机构,甚而被不少论者视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审定学术名词的统一机构”[3]363,“国内第一个审定科学技术术语的统一机构”[4]104。但学部在最初的行政架构中只有五司十二科三局两所,编订名词馆并没有包含在内。所谓“五司”是指学部下设的总务司、普通司、实业司、专门司、会计司,在各司下面又分别设置若干个科,共计十二科,以具体承担学部的各项事务。如总务司下就有机要科、案牍科和审定科。其中审定科的职责“掌审查教科图书,凡编译局之已经编辑者,详加审核颁行。并收管本部应用參考图书,编录各种学艺报章等事”。所谓“三局两所”是指学部所设立的编译图书局、京师督学局、学制调查局和高等教育会议所及教育研究所。后随着政局的变动及学部事务的增多,学部的行政架构虽也时有增改,但大体还是维持了这一“五司十二科三局两所”的框架。
从学部最初的行政架构及各司局的职能来看,显然编订术语、统一名词并不是学部成立时必需或急需处理的要务,因而自然也不可能为此设立一专门机构。但到了1909年,情况突变,该年4月18日学部向清政府提交了《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在该奏折陈列学部分年应办各事的清单中明确规定宣统元年(1909年)应“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择要先编以后按年接续)”,宣统二年(1910年)应“编辑各种辞典(以后逐年续编)”(《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学部官报》第85期)。这是学部首次在公文中正式提出要编订名词和编辑各种辞典。
同年5月,学部与素有译才之名的严复接洽,央其审定各科名词,并准其“自寻帮手”。但严复觉得“此乃极大工程之事”,自身精力又不及从前,加之“帮手”难寻,所以最初对于接此重任仍有顾虑,后来觉得“(学部)来意勤恳,不可推辞,刻已许之”[5]747。严复应承此事后,即于6月24日被任命为学部丞参上行走,开始做编订名词馆开馆前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聘请名词馆分纂。10月13日,严复“具正辞馆节略与学部”,也就是向学部提交了关于编订名词馆的计划书。半个月后,10月29日学部正式奏请开办编订名词馆,作为“编订各科名词、各种字典”的专门机构,并委派严复为总纂;此议迅速获清政府批准(《奏本部开办编订名词馆并遴派总纂折》,《学部官报》第105期)。四日后,编订名词馆正式开馆。
从编订名词馆设立的大致经过,我们可以发现,名词馆出台的关键即在于学部所提交的《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正是在此折中,学部才有了审定名词、编辑辞典的动议,而后才有了编订名词馆的设立。因而要寻求编订名词馆究竟是由谁人推动,可以从此折决议过程窥知一二。此时主持学部的主要为张之洞、荣庆、严修、宝熙四人,其中张之洞为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大臣,荣庆为学部尚书,严、宝二人分别为学部左、右侍郎。
按照学部最初的官制设计,学部的最高长官应为学部尚书,学部决策一般经由每周例会讨论而最终由学部尚书决定,参加讨论的包括学部尚书、侍郎、左右丞参及各司官员等,“有要事则开临时会议”[6]735。荣庆主持部务期间,因其人本为“伴食宰相”,对于新式教育了解有限,主要依靠下属官员严修、罗振玉等人来推展各项学部事务,所以对于每周例会讨论的议决模式大体遵行。早期学部的重要文件,也“多由罗振玉起草,张元济、李家驹、范源镰、陈宝泉①其时,罗振玉、张元济、李家驹、范源镰、陈宝泉都为学部职员。等参与意见,几经修改”,然后得荣庆同意,再决定奏发[7]186。后人在评价学部初立时,也常提及当时学部“一切政务俱出严修擘画”[8]106。但张之洞主管学部后,情况则又有不同。
首先是在官制上。1907年9月21日张之洞奉命以大学士管理学部事务,这实质上是“在学部尚书之上,又加一主管”[7]204,从而使得原以学部尚书作为最高首脑的学部科层体系受到另一重制肘。其次就个人个性论。张之洞少年及第,成名甚早,后又长期权掌一方,独当一面,故为人处事难免有些恃才傲物,更为强势。当时不少人就评价张之洞是“自负才地,多作度外之事,不屑拘守旧规,年愈迈而气愈骄”,且好“事事把持”[9]265,249。加上张之洞作为“当今第一通晓学务之人”,对于兴办教育素有主见,此次清政府命其入主学部也有借其能力“冀得纠正学术”的用意,所以张之洞兼管学部后,立即大权独揽,不但将原学部尚书荣庆几乎架空,而且在学部各项决策中更是独断专行。如学部奏设大学之议就是出自张之洞一己之言。据罗振玉记载:
文襄(张之洞)管部后,议奏设大学。侍郎严公(修)谓学子无入大学程度且无经费,持不可。文襄曰:“无经费我筹之,由高等卒业者升大学,无虞程度不足。”侍郎争之力,文襄怫然曰:“今日我为政,他日我蒙赏陀罗尼经,被时君主之可也。”乃奏设经法文格致农工商七科。[6]745
张之洞与严修此次争论,姑且不论对错是非,单就讨论过程中张之洞的言行态度,仅其“今日我为政,他日我蒙赏陀罗尼经,被时君主之可也”一语,就可想见张之洞主政之风格。张之洞在学部决策中对于时为学部左侍郎、仅在学部尚书之下的严修都如此不留情面地加以驳斥,使得其他人对于张之洞的主张即便有所异议也不敢置喙。张之洞如此做派,当然容易惹人非议,但张之洞此时是以枢臣而兼管学部,仕途资历远超学部众人,所以即便是满蒙权贵、时任学部尚书的荣庆也不敢逆张氏锋芒。张之洞更规定,“凡本部关于学务各折稿先由各堂阅看后”,然后由其斟酌改正,“始令缮折入奏”(《张相国慎重奏案》,《大公报》1908年5月10日)。
由此可知,张之洞入主学部后,学部决策是由其一人把持。直到张之洞病重,此一情况才有所改变。据严修日记,1909年7月20日张之洞因病请假,此后才无张之洞到部记载[7]232。因而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摺并单》起草之时,恰为张之洞主持学部期间。学部拟“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编辑各种辞典”,应是获得张之洞首肯,始能成事①《张文襄公奏疏未刊稿》第2函中即收有《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这也可印证该奏稿确经过张之洞之手,然后才上奏清廷。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上海书店2003年版,第152页。。
而就张之洞自身思想轨迹而论,其对名词审定的注意应早已有之。1901年,张之洞与刘坤一合办了江楚编译局。该局章程就曾指出“译书之弊,莫甚于名号之不一。同一物也,同一名也,此书与彼书异,一书之中前后又复互异,使阅者无所适从”,为革除此弊,计划“将人名、地名编为一表,而后按表以校,始能画一不讹”(《江宁江楚编译书局章程》,《东方杂志》1904年第9期)。1903年,张之洞与张百熙等人共同制定了《学务纲要》,在其中也有“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的规定。因而张之洞在入主学部之前,应对名词审定已有所认识。故而“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编辑各种辞典”这一决策要获得张之洞赞同并不困难。
事实上,还在编订名词馆成立之前,在张之洞主持之下的学部就已有过某些编订术语、统一名词的举措。1908年,学部审定科编撰了《物理学语汇》和《化学语汇》两书,由学部图书局公开发行。这两书以中、英、日对照的方式分别收录物理、化学学科术语近千条。这可视为学部推动名词统一的初步努力。但学部审定科主要的职责是负责“审查教科图书”,若再由其承担术语名词的审定统一工作,势必不堪重负。且“专科学术名词,非精其学者不能翻译”[10]173,仅靠学部的普通官员要完成学科术语的厘定,也势所不能。因而,学部要真正全面的审定名词就势必增设专门的机构。但要增设机构、扩编人员,这已非学部内部可以单独决定。因而要促使主管学部的张之洞下此决心,仍需一定机缘。
不过随后清政府公布的九年预备立宪清单,倒是为学部增设编订名词馆提供了一个契机。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公布了九年筹备清单,以对此后预备立宪作一整体规划与指导。在该清单中,学部第一年与第二年应做的事就是编辑、颁布国民必读课本与简易识字课本[11]61~62。清政府在公布这一清单后,为示慎重,特发上谕,强调清单所列筹备事宜“均属立宪国应有之要政”,各级官员“必须秉公认真次第推行”,以后每届六个月,各部衙门还必须“将筹办成绩胪列奏闻,并咨报宪政编查馆查核”[11]68。学部在接获这一上谕后,不敢怠慢,迅速着手国民必读课本与简易识字课本的编辑。正是在这一编辑过程中,学部发现“坊间所出”各国民必读课本与简易识字课本,弊端很多,其中包括“杂列名词,无复抉择”、“方言讹语,不便通行”等(《奏编辑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大概情形折》,《学部官报》第78期)。为纠正这些弊端,按时编辑、颁布普及全国的国学必读课本与简易识字课本,学部着手编订名词、统一术语的工作自然也就提上了日程。
1909年4月13日美国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拜访严修,向其提出了“学堂宜讲道德及各科名词宜划一”的建议,此点获得了严修的认同[7]228。有了明恩溥的提议、严修的认同,加上张之洞对名词审定本已留意,故而五日后,在学部提交的《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上就堂而皇之的出现了“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与“编辑各种辞典”的规定。
值得注意的是,还在该年4月8日,学部尚书荣庆就因风疾请假,直到当年8月才“强起视事”[12]684。故而从学部《分年筹备事宜折并单》提交的时间看,主导该奏折的只可能是管理学部事务大臣张之洞与学部左侍郎严修(学部右侍郎时为宝熙,但其在学部向无大的作为)。从这一角度而言,编订名词馆的正式开馆虽是张之洞逝后之事,但学部决定“编定各种学科中外名词对照表”与“编辑各种辞典”,并筹划编订名词馆,无疑是在张之洞主持学部期间就确定下来的,并在获得张之洞支持后,才得以推行。因而朱德裳、徐一士关于学部增设名词馆出自张之洞之意的说法,应有一定道理,但若说编订名词馆的设立完全出自张之洞个人之意,则稍有偏颇。严修在此当中,应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
关于编订名词馆设立的目的,按学部的公开说法是:“查各种名词不外文实两科,大致可区六门。……惟各种名词繁赜或辨义而识其指归,或因音而通其假借,将欲统一文典,昭示来兹,自应设立专局,遴选通才,以期集事”(《奏本部开办编订名词馆并遴派总纂折》,《学部官报》第105期)。换言之,这一机构出台的目的就是为了纠正术语、名词的混乱以“统一文典,昭示来兹”。对照前述名词馆设立的经过及当时出版界的状况,可以发现此一说法应为当时实情。
早在1902年,筹办京师大学堂的张百熙就注意到“中国译书近三十年,如外洋地理名物之类,往往不能审为一定之音,书作一定之字”。为将名词统一,“免淆耳目”,张氏提议“由京师译局定一凡例,列为定表,颁行各省,以后无论何处译出之书,即用表中所定名称”[10]55。基于张百熙的这一设想,京师大学堂在译学馆内设立了的文典处,计划搜集“已译书籍、字典,及本馆(译学馆)外国文教科译出之文字,或外来函告所及(的译词)”,编辑成册,经学务大臣鉴定后“颁发各处学堂及各办理交涉衙门以备应用。并当另印多册,以备学者购取”[10]173。不过从后来实施的情况看,文典处并无大的作为。以至数年后,名词混乱的现象依旧如故,甚而一些已在中国流传甚广的学科译名此时仍无法统一。如“化学”一词即为一例。以“化学”对译“chemistry”最早出现于王韬1855年的日记,稍后出版的《六合丛谈》也使用了这一译词。受此影响,“化学”一词逐渐流传开来。到20世纪初,此一译名应该说不仅已被在华的传教士所认定,而且也被国人所认可。如1904年,作为益智书会译名统一的最终成果《术语辞汇》(Technical terms:English and Chinese)就是将“chemistry”译为“化学”。而1902年由清政府颁布的《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也将“化学”列为正式的大学课程,这就表明官方对于“化学”译名也已基本认定。但是后来担任名词馆分纂的曾宗巩于1906年翻译出版的一本化学教科书却堂而皇之的命名为《质学课本》,以“物质学”(简称“质学”)来指称“chemistry”。更耐人寻味的是,该书是由学部编译图书馆出版发行,由京师官书局承印。由此可见,当时的学科术语远远谈不上统一。
在此背景下,学部要按时编订出普及全国的国民必读课本、简易识字课本及其他部定教科书,统一名词,特别是统一教科书中的名词,已刻不容缓。编订名词馆也由此得以设立,“统一文典,昭示来兹”也成为了编订名词馆设立的主要目的。
但编订名词馆的出台是否仅是为了“统一文典,昭示来兹”呢?若联系当时张之洞入主学部后的系列举动,则可发现学部增设名词馆“统一文典”的背后还另有因由。
庚子事变后,清政府为维持自身的统治,被迫宣布推行新政,尔后又下诏“仿行宪政”。在这推行新政与宪政的过程中,兴办新式教育都被清政府视为其中重要的一环。但事与愿违,新式教育的兴办不仅不能遏制革命思潮四处流传,反而致使各处学潮不断,不少学界中人更成了革命的急先锋。在此局面下,如何挽回人心、扭转学界的革命之风成为清政府,特别是主管学务的学部急需解决的问题。
张之洞入主学部期间,恰值革命风潮日益高涨,因而“谨邪说暴行之大防……务期士风之丕变”[13]335,阻止革命思想的流传、平息学生中暗流涌动的革命运动成为其主持部务首要考虑之事。其具体举措就包括设立存古学堂、奖励出身等。而增设名词馆“统一文典”其实也可视为这一系列举措之一。因为在张之洞看来,新名词的流行泛滥是助长“邪说暴行”的因素之一,而“统一文典”正可纠正此种弊端。
张之洞对新名词的负面观感由来已久。如前所述,还在1903年,由张之洞、张百熙等人共同制定的《学务纲要》中即有“戒袭用外国无谓名词,以存国文端士风”的规定。张之洞等人在当时已注意到“近日少年习气,每喜于文字间袭用外国名词谚语”,这些“外国名词谚语”或“固欠雅驯”、或“虽皆中国所习见,而取义与中国旧解迥然不同,迂曲难晓”、或“意虽可解,然并非必需此字”,而“大凡文字务求怪异之人,必系邪僻之士。文体既坏,士风因之”,所以若任由此等“外国名词谚语”流行,必“将中国文法字义进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正是基于此点判断,张之洞等人要求“此后官私文牍一切著述,均宜留心检点”,“如课本日记考试文卷内有此等字样,定从摈斥”。当然,张之洞等人也知道在当时提倡新学、兴办新式教育的背景下,完全禁止新名词并不可行,因而在反对“外国无谓名词”的前提下,对于创制新名词也提出了自己的标准,认为“除化学家制造家,及一切专门之学,考有新物新法,因创为新字,自应各从其本字外,凡通用名词自不宜剿袭掺杂”,而且所制新词要特别注意“雅驯”,并举日本为例,声称“日本通人所有著述文辞,凡用汉文者,皆极雅驯,仍系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从未阑入此等字样”[14]53。《学务纲要》中厘定新词的标准也被同年所设的文典处所继承。文典处的章程也认为“外国文字数十百倍于中国,且时有增益,中文势不敷用,应博搜古词古义以备审用;若犹不足,再议变通之法”[11]173。换言之,文典处译词的首选为“古词古义”。
尽管有了官方的明令禁止,并刻意提倡“雅驯”的新词,但张之洞所反对的新名词却愈禁愈多,难于遏制。到了其入主学部前夕,据其自承,已是“至于论说文章、寻常简牍,类皆捐弃雅故,专用新词”,如此以来,“正学既衰,人伦亦废。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则不啻有洪水猛兽之忧”[13]304。直接将新名词泛滥的危害同国家危亡联系到了一起。此论粗看貌似牵强,有危言耸听的嫌疑,但却点明了清政府警惕新名词流行的实质,即在于其对清王朝统治的危害,而非只是对中国学术风俗的冲击。正如王国维所言:“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5]387反之亦然,新言语输入的同时,也伴随着新思想的输入。紧随在这些不“雅驯”的新名词后面的就包括了革命、民主等危险的政治理念。从事西学翻译,喜“自立新名”的严复也曾指出:“今新学中所最足令人芒背者,莫若利权、人权、女权等名词。以所译与西文本义,全行乖张,而起诸不靖思想故也。”[16]1055可见在时人眼中,“新名词”与“起诸不靖思想”确存在某种联系。张之洞对于此点显然早已洞若观火,因而提倡“取材于中国经史子集之内”的“雅驯”的译词。
由上可知,张之洞反对新名词的出发点其实有二:一为国家计;一为世道计。为国家计,新名词的泛滥“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新名词的流行“将中国文法字义进行改变。恐中国之学术风教,亦将随之俱亡”。因而无论是为“国家”,还是为“世道”,张之洞都势必反对新名词。这也吻合了张之洞向来的“儒臣”理念,既考虑国家存亡,又看重名教兴衰。
当时清政府内部反对新名词的,也非张之洞一人,如端方、王先谦、叶德辉、定成、张人骏等人都曾不同程度地表示过对新名词的反对。甚至在主持推广新式教育的学部当中,反对新名词者也大有人在。学部参事官罗振玉就曾批评他所校阅的留学生国文试卷,“几无一卷通顺,满纸膨胀、运动等新名词,阅之令人作呕”。按说王先谦、叶德辉、定成、张人骏等旧学中人,反对新名词还不难理解,但端方、罗振玉,作为提倡新学、有过出洋经历者,却也不约而同的反对新名词,实在令人愕然。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反对新名词的根源,应大致与张之洞所想类似,或为国担忧,或虑旧学延续。前述罗振玉之所以批评新名词,就是担心“新学未兴,旧学已替”,国学危亡实在堪虑[6]741。张之洞入主学部后,其对新名词的负面观感一如其旧,1908年初明令学部各司“嗣后无论何项文牍,均宜用纯粹中文,毋得抄袭沿用外人名词,以存国粹”(《张中堂禁用新名词》,《盛京日报》,1908年2月1日)。当然要彻底根除新名词的负面效用,仅靠禁止还只是“治标”之策,要“治本”的话,最直接的就是通过审定名词、统一术语来过滤那些不“雅驯”的新名词,另立一套“雅驯”的名词取而代之。顺此逻辑,增设编订名词馆的潜藏目的也就呼之欲出了。
另可作为旁证的是,在编订名词馆最初筹划时,其拟定的名称应为“正辞馆”而非后来的“编订名词馆”。这“正辞”二字正好暗含了学部设立名词馆的真正主旨所在。不过也许因为此一名称过于显露了清政府的本意,故而最终定名时并没有沿用前说而是取名为“编订名词馆”。尽管有此曲折,但主持名词馆的严复对此显然已心领神会。其在1911年为《普通百科新大词典》写序时,即有所表露,认为:“顷年以来,朝廷锐意改弦,以图自振,朝暮条教,皆殊旧观,闻见盱眙,莫知的义。其尤害者,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诐遁邪淫。然则名词之弗甄,其中于人事者,非细故也。”[17]277新名词能“生心害政,诐遁邪淫”,当然“非细故也”。革命党人章太炎对此也有所觉察,在讥讽民国建立后对一些言辞也大加禁忌时,即以“破文碎词,以为历禁如此,是即清之名词馆乎”相比拟[18]574。
由此可见,学部奏设编订名词馆的目的并不单纯,所宣称的“统一文典,昭示来兹”只不过仅是表象而已,其本心所在还是企图通过审定名词,清除那些可以使人“起诸不靖思想”的新名词,以维护清王朝的旧有统治,维系中国传统的“学术风教”。而在当时新名词与“日本名词”几乎互为表里的情况下(1905年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曾描述过新名词进入中国的情况:“十年以前,西洋学术之输入限于形而下之方面,故虽有新字新语,于文学上尚未有显著之影响也。数年以来,形上之学渐入中国;而又有一日本焉,为之中间驿骑。于是日本所造译西语之汉文,以混混之势而侵入我国之文学界。”可见1895年为一关键点,在此以前,日译新名词传入中国的并不多,而自此以后,日本译词日益流行,到了20世纪初已逐渐占据了新名词的绝大多数,以致形成了“混混之势”。故而当时所言新名词几可等同于“日本名词”),学部针对新名词的审定自然很容易被外界视为是对“日本名词”的纠正,徐凌霄就认为编订名词馆就是为了“矫正东洋译名的粗陋”[19]397。因而朱德裳所言名词馆是张之洞为纠正“日本名词”而设,并非无因。
综上所述,编订名词馆的出台既是当时译名混乱的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是近代中国语言演变的内在需要,有其出现的合理性。在这一机构出台的过程中,张之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不仅名词馆的增设是得其赞同,始能成事,而且其对新名词的政治考量也使得名词馆审定名词的工作在“统一文典”之外暗含了借此纠正士风、严防邪说暴行的潜在目的。而张之洞寄予名词馆的这一潜在目的,正揭示了清政府积极介入名词审定的关注所在,即通过审定名词来加强对民众思想的控制,遏制各种不利于清政府统治思想的传播。从此点而言,编订名词馆的设立又是清政府隐性国家控制的一次技术实践。朱德裳对于张之洞与编订名词馆关联的描述,虽为局外人之言,但却大致符合了当时的实情。
[1]朱德裳.三十年闻见录[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徐一士.文病偶述[M]//长河流月——《逸经》散文随笔选萃.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3]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
[4]范祥涛.科学翻译影响下的文化变迁[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5]严复.严复集:第三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罗振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二[M].台北:大通书局有限公司,1989.
[7]严修,高凌雯,严仁曾.严修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90.
[8]王芸生.严修与学制改革[M]//文史资料选辑:第87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
[9]胡思敬.国闻备乘[M]//近代稗海:第一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10]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一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
[1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卞孝萱,唐文权.辛亥人物碑传集[M].北京:团结出版社,1991.
[13]张之洞.张之洞全集:第四册[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8.
[14]陈学恂.清代后期教育论著选:下[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
[15]王国维.论新学语之输入[M]//王国维论学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16]严复.严复集:第四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7]严复.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章太炎.参议员论[M]//汤志钧.章太炎政论选集: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
[19]徐凌宵.古城返照记:上[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2.
K25
A
1001-4799(2010)01-0097-06
2009-11-15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资助项目:07JZD0040
彭雷霆(1981-),男,湖南衡阳人,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