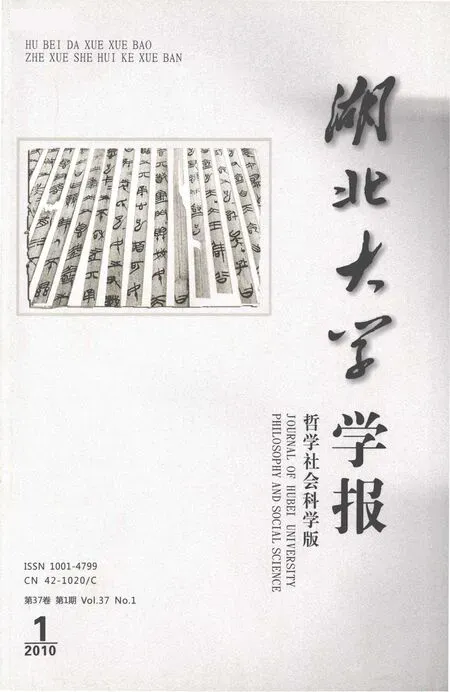楚蛮与早期楚文化
2010-04-08刘玉堂尹弘兵
刘玉堂,尹弘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楚蛮与早期楚文化
刘玉堂,尹弘兵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湖北武汉430077)
楚蛮是商周时代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为古三苗的遗裔,又称“荆蛮”,文献中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三苗衰微之后,其遗裔散居于江汉地区。楚蛮在商代后期已较为强大,与华夏集团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楚成王时,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其余脉蛮子国为楚昭王所灭,此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商代的楚蛮居住在汉东和鄂豫陕交界地区,周代的楚蛮居住在汉水中游地区。楚蛮与楚国有区别: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楚蛮和楚国公族族源不同;初期的楚国很小而楚蛮分布广泛;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楚国始封时就在楚蛮之地,熊渠以后楚国逐步融合楚蛮。早期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很难区分,早期楚文化是江汉土著民族与周代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楚蛮当是其中的主体部分。
楚国;楚蛮;源流;地域;早期楚文化
楚蛮又称荆蛮,为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中与中原联系较为紧密的一部分。《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可见熊绎受封立国之前,楚蛮即已存在,而楚国之得名,也当因楚蛮而来,何介钧说:“不是因为封了楚子,丹阳一带才被称之为楚,而是因为丹阳一带世为楚蛮所居,所封子国因袭该地民族(或地域)名称,取名为楚。”[1]12这是楚国与楚蛮之间的因果关系。可知熊绎以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又荆、楚古通用,传世文献中,则多荆蛮之称。楚蛮与早期楚国有极密切的关系,二者几乎不可分,将楚蛮与楚国的关系清理出来,对于早期楚文化的探讨有着重要意义
一、楚蛮的源流
传说时代,南方地区的居民是苗蛮集团,又称三苗或有苗。三苗的年代,大致与古史传说中尧、舜、禹的年代相当,尧的时代三苗已存在,则其上限或更早于唐尧。
三苗居地大体在长江中游地区,其具体范围,吴起说是“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战国策》卷22《魏策一》“魏武侯与诸大夫浮于西河”章)。据徐旭生先生考证,彭蠡、洞庭即今鄱阳湖和洞庭湖,文山不知其所在,衡山则有争议,但可以肯定不是今湖南省南部的衡山,可能在江北,总的来说,三苗的范围在今湖北、湖南、江西一带,西面和南面的界限,文献无征,东面的界限,今江西的大部分地区仍当属于苗蛮,其北界较为明确,大约在河南西部熊耳、外方、伏牛诸山脉间,具体而言,东以大别山脉为界邻于东夷集团,西则北越南阳一带,侵入外方、伏牛山脉间,北邻于华夏集团[2]65~67,75~76。徐先生考定的这一区域大体与考古学上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分布范围相当。
在古史传说中,尧、舜、禹所领导的北方华夏集团与南方的三苗集团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争,尧曾与三苗“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则“窜三苗于三危”、“分北三苗”,舜晚年时还曾亲驾“南征三苗”,结果“道死苍梧”,到了禹时,战争更加激烈,最后禹利用三苗出现内乱、遭逢天灾之机大举进攻,取得决定性胜利。禹与三苗的战争,《墨子》卷5《非攻下》有详细记述:“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龙生於庙,犬哭乎市,夏冰,地坼及泉,五谷变化,民乃大振。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四电诱祗,有神人面鸟身,若瑾以侍,搤矢有苗之祥,苗师大乱,后乃遂几。禹既已克有苗,焉磨为山川,别物上下,卿制大极,而神民不违,天下乃静。则此禹之所以征有苗也。”在禹的进攻下,“苗师大乱,后乃遂几”,《说文》:“几,微也,殆也。”三苗从此衰微,不再见于文献。
三苗衰微之后,“三苗”、“有苗”、“苗民”等称呼消失不见,可知三苗作为一个族群已经瓦解,但三苗的遗裔当仍在江汉地区生息繁衍。到了商代,他们发展成人数众多、有一定势力的集团,但这一集团在整个商周时期,并没有象以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居民,文化上也较为落后。这些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在文献中称为荆蛮,最早出现于夏末商初。今本《竹书纪年》:“(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帝癸即夏桀,可见夏末商初时荆蛮已出现。《越绝书·吴内传》则谓:“汤行仁义,敬鬼神,天下皆一心归之。当是时,荆伯未从也,汤于是乃饰牺牛以事,荆伯乃愧然曰:‘失事圣人礼’。乃委其诚心,此谓汤献牛荆之伯也。”这两条文献虽然年代较晚,但至少可以说明在后人的记忆中,荆蛮于夏商之际时已存在。
商代后期亦有荆蛮,今本《竹书纪年》:“(武丁)三十二年,伐鬼方,次于荆”。武丁伐荆一事,又见于《诗经·商颂·殷武》:“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殷武即殷王武丁,是商人赞颂武丁功绩的诗篇,从《殷武》所载来看,荆蛮在商汤之时已臣服于商,此亦商初时已有荆蛮之证,但后来商朝失去了对荆蛮的控制,至武丁时,遂出兵征伐荆蛮。这两条文献互证,可知商代后期时荆蛮已较为强大,居于南方、占地广泛。
西汉贾捐之亦曾述及商周王朝与荆蛮的关系:“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而颂声作。”(《汉书》卷64《贾捐之传》)贾捐之之言,亦反映出在中原文献的视野中,荆蛮是商周时期的南方居民。
荆蛮的地域,大抵为原三苗之居,出现年代则在三苗解体之后,后世荆、楚通用,因此荆蛮即楚蛮。对楚蛮(荆蛮)的族源,学者有较一致的看法,均认为楚蛮为古三苗之后:张正明主编的《楚文化志》谓“所谓楚蛮,即楚地的蛮族,其主体是三苗的遗裔”[3]5;张正明著《楚史》同此说,亦谓楚蛮的主体应是传说时代“三苗”的遗裔[4]52;伍新福认为商周时期的荆蛮是原三苗的后裔,“他们经过数百年的较为和平的发展后,势力又强盛起来,同中原华夏族发生接触和冲突,中原人就不再把他们叫着‘三苗’、‘有苗’,而以地命名,称之为荆蛮。其实,他们就是三苗的后裔”[5];刘玉堂认为禹征三苗之后,“以三苗遗部为主体的‘荆’或‘荆蛮’成为江汉地区的主要民族”[6]。按学者认定楚蛮或荆蛮为古三苗之后,除了居地相同、时代相接外,也因苗与蛮实为一义,苗、蛮二字属阴阳对转。徐旭生先生说:“这个集团,古人有时叫它作蛮,有时叫它作苗,我们感觉不到这两个名词中间有什么分别,所以就综括两名词,叫它作苗蛮。”[2]65石宗仁则从民族学和语言学角度论证,Mao(或Mu)—髦—蛮—模—猫—苗均为同音异译,至今中部苗族犹以猫(Mao)或模(Mu)即蛮为自称[7],故荆蛮、三苗、苗族实为同一族群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称谓[8]。可知楚蛮为古三苗的遗裔,文献中又称为荆蛮或荆、蛮荆,三苗灭亡后在南方形成一个分布较广的民族,其族源属南方的苗蛮集团,与华夏集团有别。但由于禹征三苗和商汤、武丁征荆,楚蛮与华夏集团当有较多的交往,在文化面貌上可能与中原较为接近。
楚蛮(荆蛮)在周代亦屡见于文献。西周初年周封熊绎于楚蛮,周昭王曾大举南征荆蛮,《吕氏春秋·季夏纪》云:“周昭王亲将征荆蛮。”①按今本《吕氏春秋》荆下无蛮字,此据《左传》僖公五年孔颖达《正义》引补。周夷王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曾一度强大,称雄江汉,并封其三子为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周厉王时,又有“召穆公帅师追荆蛮,至于洛”(今本《竹书纪年》厉王十四年)。西周末年,郑桓公与史伯议东迁,“当成周者,南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可知西周末年荆蛮分布于成周以南。今本《竹书纪年》:“(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此事又见于《诗经·小雅·采芑》:“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戎车啴啴,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狁,蛮荆来威。”至齐桓公时,“周室微,唯齐、楚、秦、晋为疆。晋初与会,献公死,国内乱。秦穆公辟远,不与中国会盟。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史记》卷32《齐太公世家》)。所谓“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当是指楚蛮主体被楚国兼并,此后楚蛮作为一个族群不再存在。
楚成王之后,楚蛮余脉仍有活动。《左传》文公十六年载庸国率群蛮叛楚,庸国所率之群蛮,应为楚蛮。群蛮又见于《左传》哀公十七年楚大夫子谷之言:“观丁父,鄀俘也,武王以为军率,是以克州、蓼,服随、唐,大启群蛮。”子谷所叙为楚武王时之事,则观丁父所启之“群蛮”,可能亦是楚蛮。文公十六年后文献中再无群蛮活动之记载,应是楚国加强了对群蛮的统治,将楚蛮完全融合。
《左传》哀公四年又记有楚昭王灭蛮子国、俘蛮子赤之事,按蛮子国在汝水上游地区,具体地点在汝水以南、今河南临汝至汝阳一带[9]272,已脱出楚蛮的范围,但《春秋》哀公四年“晋人执蛮子赤归于楚”句下杜预注:“赤本属楚,故言归。”故蛮子国虽位于汝水上游,但有可能原属楚蛮之一,后退至汝水上游独立建国。蛮氏又见于南宋郑樵《通志·氏族略》,有“瞒氏”和“蛮氏”。“瞒氏”条:“《风俗通》云,荆蛮之后。本姓蛮,音讹遂为‘瞒氏’。《左传》有司徒瞒成。”“蛮氏”条:“芈姓,荆之后,因氏焉。”可见蛮、瞒本同氏,后分为两支,据《风俗通》,这两支蛮氏为楚蛮之后裔。当然,郑樵言蛮氏为芈姓有误,当因楚蛮尽入楚国,故后世误以蛮氏为芈姓,或楚蛮之后冒楚之姓,这应当是楚国与楚蛮融合的后果之一。楚灭蛮子国后,楚境内再无蛮族活动的记录,蛮子国成为楚蛮之绝响。
二、楚蛮的地域
(一)商代及周初楚蛮地域
商代楚蛮地域,据今本《竹书纪年》,夏桀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征荆,荆降。”有洛为古族名,《逸周书·史记解》:“昔者有洛氏宫室无常,池囿广大,工功日进,以后更前,民不得休。农失其时,饥馑无食,成汤伐之,有洛以亡。”张华《博物志》卷十亦谓:“昔有洛氏……人民困匮,商伐之,有洛氏以亡。”有洛氏之族,当在洛水流域,《尚书·五子之歌》:“太康尸位以逸豫,灭厥德,黎民咸贰。乃盘游无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书序》云:“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传:“太康五弟与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可知有洛当在洛水流域。而商师征有洛之后再征荆,则此荆必近洛水,又荆蛮(楚蛮)为古三苗的后裔,则荆蛮之地,应在古三苗的分布范围之内,据徐旭生先生所考,苗蛮集团的北界,在今河南西部南阳以北、熊耳、伏牛、外方诸山脉间,正与洛水流域相邻。从自然地理来看,熊耳、伏牛、外方山脉以北,为伊水、洛水流域,以南即丹淅水、唐白河流域,而丹淅水、唐白河流域正好在苗蛮集团的分布区内。由此可见,商师所征之荆蛮,当在伏牛、熊耳、外方山脉以南,以今丹江库区为核心的鄂豫陕交界地区。此处还可补充一条旁证,据石泉先生考证,内乡(按内乡在淅水以东不远处)附近,有最古的荆山[10]208。由此可知,今鄂豫陕地区,应为当时楚蛮(荆蛮)的分布地区之一。
又据《商颂·殷武》和今本《竹书纪年》,武丁曾伐荆楚,甲骨文中亦有武丁南征的记载:
乙末[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
乙末卜,贞:立事[于南],右比我,[中]比舆(举),左比[曾]。十二月。
这两条甲骨文均属武丁时代,“立”,即莅;事,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戎事。“立事于南”,是说商王武丁亲临南方,指挥战争。我、曾、举均为商代方国,据考证,曾在今湖北、枣阳、随县、京山到河南西南的新野这一范围内,举在汉东举水流域[11],我的地望不可考,当与曾、举相邻。“比”则有联合、配合之义[12],这两条卜辞是说:商王武丁亲帅右、中、左三军,在我、举、曾三个方国的配合下征伐荆楚。举、曾两国均在汉东地区,则武丁所征之荆楚当去举、曾之地不远。武丁伐荆楚,或与商代楚蛮的兴起及盘龙城的废弃有关。盘龙城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上下层之间,废弃于二里岗上层二期晚段,则其始建年代相当于商王中丁在位或稍早的公元前1450年左右,废弃于盘庚迁殷前的公元前1300年之前[13],盘龙城的性质,现一般认为是商人在南方的军事据点。考《殷本纪》:“自中丁以来,废嫡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代立,比九世乱,于是诸侯莫朝。”“九世之乱”期间,商的势力处于退缩中,可能商朝在此期间失去对荆蛮的控制,而盘龙城之废弃,或与此背景有关联。至盘庚迁殷之后,商朝国力复振,极力对外反击,尤其是武丁在位期间,大征四方,武丁征荆蛮一事或在此背景下发生。由此推测,汉东地区在商代亦应为楚蛮分布地区。
(二)周代的楚蛮地域
商周鼎革之后,人文地理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周人在立国初期,就开始经营南方,徐中舒先生谓:“周人自大王居歧以后,即以经营南土为其一贯之国策。”[14]688《太保玉戈》记载周王令太保召公省视南土,沿汉水南下,召集江汉地区的诸侯朝见周王。郑玄《毛诗谱》亦谓:“至纣,又命文王典治南国江、汉、汝旁之诸侯。”可见江汉地区在商末周初时就已成为周人的势力范围。
《左传》昭公九年记詹桓伯辞晋之言,述及周初时的政治地理格局:“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詹桓伯所言周之南土,巴国于春秋时屡见于《左传》,与楚国曾有密切的关系,童书业先生据《左传》考订其地望应在今陕西东南境、大巴山以北[15]243,244,石泉先生结合文献及考古材料,考证先秦时巴国在今陕东南、汉水中上游的安康一带[16]14,近年来汉水中游陕南城固一带出土较多商周时期巴式青铜器,可见商周时的巴国当在此地[17]10~20。濮,是一个古老的部族,曾参与武王伐纣之役,为“牧誓八国”之一,但濮并不是一个邦国,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权,故《牧誓》称之为“濮人”,直到春秋时期,濮还处在各自“离居”的状态,因此又被称为“百濮”。濮之地望,孔传:“庸、濮在江汉之南。”孔颖达《正义》亦引《左传》文公十八年伐楚之役论证之。石泉先生则认为,春秋时期的古麇国、楚麇邑地在今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西北岸地,与之相邻近的百濮,其地当在今枣阳市境桐柏、大洪两山间的山区丘陵地带[16]10~11。段渝则据“百濮离居”认为百濮居地当不限于一处,而是在西周时代的南土有广泛的分布,襄阳以西到竹山以南和襄阳以东汉水东北岸及滚河下游一带,均为西周时代百濮离居之地[18]。顾颉刚先生则认为濮在武当、荆、巫诸山脉中[19]31。虽然对濮的具体定位还有一些困难,各家的说法不一,但西周春秋时的濮,大体当在今襄樊附近地区,就区域而言,可以认为上述各家的意见是基本一致的。邓即今襄樊邓城遗址,楚在丹淅之会。可见鄂豫陕交界地区在西周初年即已成为周朝的势力范围。周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又成为“汉阳诸姬”所在。
鄂豫陕交界地区和汉东地区,在商代均为楚蛮分布之地,商周之际当亦大抵如是。但由于周人对南土的经营,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周初时,首先是汉水以北成了周朝的南土,昭王南征以后,汉东地区也成“汉阳诸姬”所在。于是商代及周初时的楚蛮居地,多为周人所占。但楚蛮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终西周一世,楚蛮颇为活跃,可见楚蛮应是转移到周人势力所不及之地,开始了新的发展。
西周晚期时楚蛮地域,可从熊渠的活动中约略窥知,《楚世家》:“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勾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其征伐范围及三子封地,皆为“江上楚蛮之地”,可见西周晚期的楚蛮,地在“江汉间”,或“江上”之地。以上诸地点,庸国,见于《左传》文公十六年,杜预注:“庸,今上庸县,属楚之小国。”唐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房州竹山县,本汉上庸县,古之庸国。昔周武王伐纣,庸蛮在焉。”日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今湖北郧阳府竹山县,古庸国。”可见古庸国应在今湖北竹山县。杨粤之地,唐代学者已不知其所在,只能笼统地说:“地名也。”现代学者试图加以解释,段渝从声音相通出发,谓汉代以前,於、雩、于、越诸字本可互用,从於之字,多有阴郁、淤塞之意。释越为於中,地在今内乡、邓县与襄樊之间[20]。顾铁符认为杨越与扬州有关[21]108,何浩《楚灭国研究》、张正明《楚文化史》、罗运环《楚国八百年》、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等则认为杨粤即杨越,与杨水有关,乃杨水附近的越人。这些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以前我们也曾认为,杨粤即杨越,但叶植指出,杨粤当是一个具体地名而非地名兼族名,杨越作地名兼族名讲时,一般是指笼统区域概念兼笼统的族名概念,在此概念上,《史记》均作杨越而不作杨粤,另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江、汉、沮、漳之地并不是越文化的分布地区,春秋中晚期以后尤其是楚灭越后,才有少量的越文化因素进入楚核心区。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非是既作族名又作地名的杨越,而只能是汉水中游的一个具体地名[22]399~401。叶说有理有据,信而可从。因此熊渠所伐之杨粤,似与杨越无关。
我们或可从熊渠征伐所及之地与熊渠三子的封地之间的关系来推定杨粤之地,从《楚世家》所叙来看,熊渠所征之地与其三子的封地应有联系。熊渠中子红为鄂王,当即熊渠所征之鄂地。长子康为勾亶王,《集解》引张莹曰:“今江陵也。”但未知何据,现代学者认为勾亶与庸国有关,赵逵夫就认为句亶之地当近庸,非在江陵[23]。黄锡全赞同赵逵夫的意见,肯定句亶之地绝非在江陵,并从文字学的角度来加以论证:句字无义,古地名冠以“句”字之例在古籍中常见,如句容、句注等,句亶之“句”当同此例,亶从旦声,《世本》作袒,句亶、句袒当即离“庸”不远的“句澨”,亶、袒、澨上古读音是很接近的,音近可以假借,故“句澨”又可作“句亶”、“句袒”,这是因音近而出现的不同写法,故“句亶”即是离庸不远的“句澨”,“句澨”作地名可能是取义迂曲的水堤边,具体地点在“庸”之东北,汉水南岸,东离丹水入汉处不远[24]。叶植也认为勾亶即《左传》文公十一年“楚师次于勾澨”之“勾澨”,地在汉水中上游南岸,今丹江口市西北至郧县一带[22]404。段渝认为勾亶即巫诞,今竹山一带,其地跨有今堵河中游两岸,正在熊渠所伐的庸地范围内。另据《世本》,熊渠长子康原作庸,康、庸形近,或许就是因为封于庸地之故。因此句亶即巫诞,熊渠伐庸后将其地封以长子康、立其为王[18]。以上赵、黄、叶、段诸说相距不远,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论证句亶不当为江陵,而是“句澨”,尤其是诸家之说均以为勾亶与庸国有关,地当在庸国境内,应是可取的。
由此看来,熊渠长子为勾亶王,当与熊渠所征伐之庸地有关,中子红为鄂王,当与鄂地有关,则熊渠少子所封之越章王,应与熊渠所征之杨粤有关。越章之地,学者多以为即吴师入郢时所经过的豫章。豫章所在,《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汉东江北地名。”孔颖达《正义》:“《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名,在江南。此在江北者。《土地名》云:‘定二年,吴人伐楚师于豫章,吴人见舟于豫章,而潜师于巢,共军楚师于豫章。又伯举之役,吴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与楚师夹汉,此皆在江北淮南。盖后徙在江南之豫章。’”然这个江北淮南之说亦未能实指,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试图划定其范围,谓江西之九江、饶州,江北之安庆府,直到颖、毫、庐、寿、光、黄,“皆为楚之豫章地”。这样,自江南至淮北,皆属豫章,但从《左传》及《史记》有关豫章的叙述来看,豫章当是一个具体的地名,至多是一个小区域,不可能是一个如此大范围的地区。另一说则定豫章在今安陆的章山,此说始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大清一统志》即采此说,今人何光岳则认为:“故越章王的地望确定在安陆之章山、章水一带是无疑了。”[25]罗运环亦谓越章在今云梦一带的可能性比较大[26]107。石泉先生则通过对吴师入郢的行军路线及军事地理形势的考证与分析,认为吴师与楚师夹汉之豫章,当在汉水中游附近,亦即《水经注》卷31《淯水篇》所记淯水下游(今白河)左(东)岸、近汉水之豫章大陂一带[10]191,360。叶植则认为杨粤即陽穴,楊、瑒、煬皆从易得声,上古音、形、义皆完全相同,为同一字,偏旁系后加,粤(越)与穴上古亦存在通假关系,杨粤即麇子国之国都陽穴[22]401~402,404,陽穴见于《左传》文公十一年:“潘崇复伐麇,至于陽穴。”按麇子国为百濮首领,《左传》文公十六年:“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选,将伐楚。”麇国及陽穴地望,传统说法认为在今湖北郧县西,不确,据石泉先生考订,麇国当在雍澨东北不远处,邻近吴楚之战的主战场柏举,地当在随枣走廊西口外,今滚河西入唐白河后的唐白河下游东岸[10]388,389。按杜预注《左传》时已不知麇国及陽穴地望,石泉先生所考订之麇国、锡穴和越章(豫章)、百濮地望,与叶说主张杨粤即阳穴及《左传》所记麇率百濮叛楚正可互证,从地理体系的角度来看,上述诸地点相互之间可紧密吻合。可见越章地望当依石说,在唐白河入汉处,麇国及其国都陽穴、还有与麇关系密切的百濮,虽然可能有迁徙,但大体上应在这一地区。据考古调查,今襄阳县黄龙镇高明村附近,有一西周时期的古城址,今名楚王城,年代为西周中晚期,此地位于唐白河入汉水处以东不远,正在石泉先生考订的越章范围内,或即熊渠少子执疵所封之越章,附近地区应即熊渠所伐之杨粤。
鄂,是熊渠远征所达的最远点。鄂地自古即有东鄂和西鄂两说,东鄂在今鄂州,西鄂在今南阳北。熊渠所伐之鄂,是东鄂还是西鄂,学术界有不同看法。从鄂的起源来看,西鄂起源甚早,商代时已有鄂侯,商末鄂侯与西伯昌、九侯并称三公,据徐少华考订,商代鄂国原在黄河以北的沁水流域,其地望大致不出今沁阳县城或略偏南一带,西周时迁至南阳盆地,鄂国进入南阳盆地的时间,上限在成王初年,不迟于西周早中期的昭穆之际,鄂已立国于南阳盆地[9]。而东鄂之名,最早见于屈原《九章·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王逸注:“鄂渚,地名。”渚为水中的小块陆地,洪兴祖补注:“鄂州,武昌县地是也。”可见东鄂之名出现,有可能迟至战国晚期。张正明虽主东鄂说,但认为“东鄂和西鄂不是并世共存而是异时相承的”[4]45,此言颇有见地,从目前材料来看,西周时期,只有西鄂而无东鄂。另从考古学的角度考察,今鄂东南一带的西周时期考古学文化面貌,迵异于以鬲、盂、豆、罐为主要特征的早期楚文化遗存,据分析,此类遗存可能与杨越有关[27],可见西周时期,鄂东南一带应为越人所居,未见有与楚文化或早期楚文化相关的考古学遗存,因此现在看来,我们认为熊渠足迹应未至鄂东南。直到春秋中期以后,楚人才开始进入鄂东地区。又鄂地见于《鄂君启节》,陈伟认为舟节铭文“自鄂市,逾由”一句中“由”即“育”,“油水”即“淯水”,即今天南阳盆地的白河,并进而论定《鄂君启节》中的“鄂”为南阳盆地的“西鄂”[28]。综合以上分析,熊渠征伐所及之鄂,应以西鄂的可能性为大。
由此看来,熊渠时代的“江汉间”或“江上楚蛮之地”,均在汉水中游一带。据石泉先生考证,江并非长江的专称,先秦时期,汉水亦称江[10],因此“江上楚蛮之地”的江上,当指汉水。赵逵夫先生亦谓:“先秦时代常常江汉连称,是古人亦以汉属南方。司马迁不知三王的封地究竟在何处,故以‘江上楚蛮之地’一语概言之。他又说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可见在司马迁的概念中,‘楚蛮之地’也包括汉水流域在内。”[23]故西周晚期时当有较多的楚蛮生活在汉水中游两岸,他们未受周朝的统治,而熊渠时的楚国亦当在此间。
三、楚蛮、楚国与早期楚文化
由以上梳理可知,楚蛮(或荆蛮)在商周时代与中原王朝交往较多,是中原政治与文化势力的边缘部分,与中原王朝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来说对中原王朝表示臣服,受中原王朝统治,但叛服无常,又往往成为中原王朝的征伐对象,属于中原王朝疆域中不太稳定的边缘区。在文化上受中原文化较大的影响,虽然可能有自身的特色,但属于中原文化体系,是中原文化的边缘组成部分。由此似可推测,楚蛮当为南方居民中与中原关系较为紧密、联系较多,在政治、文化上受中原影响较深的一部分,在地理上亦应较邻近中原。楚国则始自熊绎,楚蛮与楚国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其区别主要在于:
1.熊绎受封之前,只有楚蛮而无楚国。
商代时,楚蛮已在南方有广泛的分布,商周时代楚蛮相当活跃,与中原王朝有较为复杂的关系,一般臣服于中原王朝,但因叛服无常,又常遭中原王朝的攻击。而夏商鼎革之际,祝融八姓因与商王朝的密切关系,在商人伐夏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受到商人的重大打击,可能因此之故,芈姓一族在商代悄无声息,居地不明,世系不清,未知身在何处,到商末才有鬻熊出现在历史上。可见商代之时,芈、楚二分,芈指季连一族,楚指楚蛮,二者并无瓜葛。
2.楚蛮与楚国公族族源不同。
楚蛮的族源属南方苗蛮系统,为古三苗的后裔,而楚国公族的族源属中原华夏系统,是声名显赫的祝融后裔。二者出现的时代也不同,楚蛮始见于夏商之际,楚公族为芈姓,始于季连,而季连的年代当在夏代之前。
3.楚蛮与楚国大小不同。
初期的楚国很小,楚国初封时是“封以子男之田”,其封地大小,诸书皆言仅五十里,《史记》卷47《孔子世家》载楚令尹子西曰:“且楚之祖封于周,号为子男五十里”,卷14《十二诸侯年表》则称:“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至春秋早期,楚地尚“土不过同”(方百里为一同)。而楚蛮早在商代时在南方就有广泛的分布,是南方土著居民中数量较多、分布较广的一支。
4.与周的关系不同。
楚是周朝的封国,而楚蛮则往往成为周朝的征伐对象,周昭王曾大举南征荆蛮。
但楚蛮与楚国又有极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甚至密切到二者难以区分的程度。楚国初封时就是在“楚蛮之地”,到西周晚期时,熊渠统治下的楚国“甚得江汉间民和”,其活动范围“皆在江上楚蛮之地”,从熊渠自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来看,此时楚人当已植根于江汉蛮夷之中,与楚蛮初步融为一体。到春秋早期时,“楚成王初收荆蛮有之,夷狄自置”。此后随着楚国的发展,楚蛮完全融入楚国,成为楚国下层民众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主体。而楚国之所以能在春秋时期迅速崛起,被时人目为“天方授楚”,当是楚国在长期经营的基础上将楚蛮、濮等江汉蛮族整合成为楚国的有机组成部分,使得楚国迅速摆脱了部落国家的狭隘性质,成为具有地域性质的新型国家,从而具备了强大的实力,令周朝诸侯望而生畏。
由此看来,由于芈姓楚国长期与楚蛮共处,双方当在文化上较为接近。至迟西周晚期熊渠的时代,楚国与楚蛮已初步融为一体,此时的楚国与楚蛮在文化上可能已很难区分。楚国统治楚蛮,属于那种“从深化人民出去,跑到浅化人民中间去作首领”[2]75。由古今中外的例证来看,凡少数的“深化人民”统治多数的“浅化人民”而建国者,虽然少数的“深化人民”在政治上起着主导作用,但在生活习俗上都不可避免地要被多数的“浅化人民”所同化。芈姓部族虽然在商末周初时主动接受周文化,但其建国于楚蛮之地,不可避免地要受楚蛮影响,西周晚期时又主动与楚蛮打成一片,则楚国在文化上当会受到楚蛮的影响。诚如徐旭生先生所说:“祝融由于到苗蛮集团中做首领,苗蛮自然受他的影响,而他及他的后人的风俗习惯大部分也要同化于苗蛮,也是一种不可免的情形。”[2]751①按:徐先生此处之祝融,实指楚、蛮芈、夔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楚文化应是楚蛮及其它江汉土著民族和包括楚国在内的南土诸国共同创造的文化,楚蛮则可能是创造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体族群之一,而楚国则是这一考古学文化的主要继承者。
[本文得到湖北省文物局南水北调工程丹江口库区文物保护科研课题“早期楚文化生成环境研究”(合同编号NK 10)资助,特此说明。]
[1]何介钧.关于楚蛮和楚族族源的断想[M]//楚文化研究论集:第三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
[2]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3] 张正明.楚文化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4] 张正明.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5]伍新福.荆蛮、楚人与苗族关系新探[J].求索,1988,(4).
[6]刘玉堂.夏商王朝对江汉地区的镇抚[J].江汉考古,2001,(1).
[7]石宗仁.苗族自称与荆地蛮夷、熊绎之关系[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3).
[8]石宗仁.苗族与楚国关系新论[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4,(6).
[9]徐少华.周代南土历史地理与文化[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4.
[10]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
[11]江鸿.盘龙城与商朝的南土[J].文物,1976,(2).
[12]林沄.甲骨文中的商代方国联盟[M]//古文字研究:第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1.
[13]徐少华.从盘龙城遗址看商文化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发展[J].江汉考古,2003,(1).
[14]徐中舒.殷周之际史迹之检讨[M]//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8.
[15]童书业.童书业历史地理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4.
[16]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续集[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
[17]彭万廷,冯万林,等.巴蜀文化源流[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3.
[18]段渝.西周时代楚国疆域的几个问题[J].中国史研究,1997,(4).
[19] 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0]段渝.楚熊渠所伐庸、杨粤、鄂的地理位置[M]//历史地理:第8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
[21]顾铁符.楚国民族述略[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22]叶植.试论楚熊渠称王事所涉及到的历史地望问题[M]//楚文化研究论集:第四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23]赵逵夫.屈氏先世与句亶王熊佰庸[M]//文史:第二十五辑.北京:中华书局,1985.
[24] 黄锡全.楚地“句亶”、“越章”新探[J].人文杂志,1991,(2).
[25]何光岳.“越章”考[J].江汉论坛,1984,(10).
[26]罗运环.楚国八百年[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
[27]刘玉堂.杨越与楚国[J].江汉论坛:《楚学论丛》专刊,1990,(9).
[28]陈伟.《鄂君启节》之“鄂”地探讨[J].江汉考古,1986,(2).
K29
A
1001-4799(2010)01-0001-07
2009-10-28
刘玉堂(1965-),男,湖北大悟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楚史研究;尹弘兵(1967-),男,湖北天门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楚文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邓建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