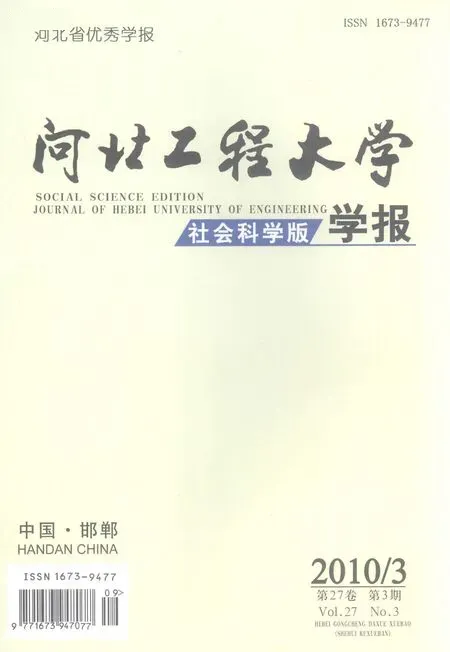论科举制度舞弊与防治的本质及现实启示
——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视角
2010-04-07刘超
刘 超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论科举制度舞弊与防治的本质及现实启示
——以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双重视角
刘 超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河北石家庄 050000)
科举制度从创制起就充满了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如果对这一斗争千余年的演化做一个简单的历时性梳理,并以共时特征为视角挖掘其中的历史性和遗传性制约因素,可探究其本质并从其现实性、变异性中获取现代考试制度防治舞弊的重要现实启示。
科举;考试;舞弊;启示
从隋唐创立至清末废止,科举制度一刻也没有停止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因此其发展史在相当意义上也可视为舞弊与反舞弊的斗争史,在综合其中舞弊与防治的共时性特征,寻求科举考试制度与现代考试制度相关因素彼此之间的映射关系后,可以求得现代考试制度防治舞弊的现实启示。
一、历时性和共时性视角下的科举考试舞弊与防治
由于中举带来的巨大经济和社会效应,科举考试制度自产生之日起就不断受到舞弊的冲击,科场舞弊屡禁不止,舞弊手段层出不穷,举子们丑态百出;而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为了保证科举考试顺利施行,各朝代不间断地制定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和措施,反舞弊的手段和力度日益加大。纵观这种过程性绵延,可发现双方变化趋势的特点:科场舞弊及防治并没有凝固不变,而是一个变动不拘的历时性动态进程,舞弊手段越来越隐蔽而防治手段也越来越精致,二者进行着一种“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艰苦殊绝的搏斗。
以历代最为盛行的挟带舞弊为例,唐时举子们的挟带舞弊充其量不过是怀挟“书策”、“书文”,把所备书籍文章较为随意地置于随身穿的衣服里带入科场而已;到宋代就发展成为将经文抄写在内衣中以求躲过搜检;至明时举子们则需要煞费心机将必考经文以尽可能小的字体抄在薄纸上,或卷入笔管、或藏入砚底、或封入蜡芯才有可能躲过搜检;而到了科举末期的清代,欲行挟带舞弊的举子们已经无所不用其极,从特制的夹层衣帽靴、夹层笔砚和食物乃至一切考试用具,甚至利用身体器官进行挟带。挟带手段的持续发展,导致防治措施不断升级。随着挟带舞弊手段的日益“高明”,统治者不仅制定了相应的法规,采用了严格的考场搜检制度并加大了搜检力度,而且处罚措施也逐渐严厉,在唐代对挟带舞弊仅处以停试一至二科的处罚[1],至清时对舞弊的惩罚已发展到处以极刑、亲属连坐。
在科举考试舞弊与防治千余年变迁的过程中,双方各自呈现出纷繁斑驳的发展特点,舞弊者挖空心思的舞弊方法好像水银泻地一样无孔不入,而科场关防则力图做到密不透风、滴水不漏。这种二元矛盾看似随机地发生于无序的状态中,基本模式为舞弊一方形成对考试的冲击进而引起防治手段的相应变迁。但是,在任选一个时间点作为共时结构研究的平面择取点后,我们可以从二者外在形式的变化中发现静态的内在性结构冲突,即不为外在时空分割的内在质性:科举考试舞弊与防治共时平面展开的对抗性二元矛盾在并未改变,双方不断涌现出的新形态实质上是矛盾内在质性外在表现形式的过程性变化,是处于历时过程中舞弊与防治各自要素的重新构造,千余年的交锋史则可看成是二元矛盾诸因素交互作用的“过程性绵延”。舞弊与防治千年斗争史不过是矛盾双方围绕着破坏和维护秩序的关节各自嬗递、斗争的过程。
二、科举考试舞弊与防治的本质——对公平制度的维护
既然从共时性视角看考试舞弊与防治是一种内在性结构冲突,那么产生这一矛盾并推动矛盾发展的根源何在?笔者在探究科举时代舞弊与防治措施的特点时发现,舞弊者固然无所不用其极,而统治者除了采用各种有形的措施外,还试图施加一种无形的精神压力来制约科场舞弊的发生。以明时科举考场的布置为例,各省科举考试的场所——贡院,无一例外都是当地最宏伟、庄严、肃穆的建筑,统治者试图利用深邃复杂的格局和中正崇高的建筑风格体现出一种形而上的至公用心,让举子们感受到公平的压力:建筑格局的设计是开放式的,主考官对举子考生居高临下的格局,突出主考官对举子的“俯视”,用压抑的视觉冲突施加一种公平公正的气氛,其意主在营造一种浩然正气,用一种精神压力约束舞弊发生的可能性。这从一个层面说明了在封建社会历史环境和社会条件中,科举制度已经达到一个极高的地位并成为社会凝结的中心,这迫使舞弊与矛盾双方不断整合,以至出现了一种固有的、稳定的、重复出现的对抗关系,进而体现出一种必然性。而这种必然性恰好显示出矛盾的本质——舞弊与防治双方对科举制度公平理念的破坏和维护。
从制度本身看,相比于前朝的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科举考试制度最大的优势在于打破了世势二家对吏选的垄断,其选拔机制立足于可操作的客观标准,让举子们在科场这一空间内尽施所能。“一切以呈文为去留之标准”俨然就是古代的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尽管在“天下之大公”和“天下至公”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背后,隐藏着封建统治者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深远考虑,但科举制度既迎合了绝大多数举子对公平的渴望和意愿,也是封建社会罕有的公平精神的一种社会展现。因此科举考试制度的任何一级考试,都会成为这一群体中优秀、顶尖人才的汇集,各地举子齐汇考场,实际上相当于一次人才大阅兵。此种盛况,“不仅政府与社会常得声气相通,即全国各区域,东北至西南,西北至东南,皆得有一种相接触相融洽之机会,不仅于政治上增添其向心力,更于文化上增添其调协力。”[2](P293)此时每一场考试都是统治者展示其国力鼎盛、人心向上的大好时机,这种盛况,既得到统治者的认可和支持,又受到百姓的接受和赞同,其管理必须加以高度重视。而科场内举子的互通性、民众的关注性以及考试的受关注程度,在客观上也要求统治阶级必须以一种至公的态度加以对待。此外,科举制度作为封建统治者选拔优秀行政人员,借以提高封建统治行政效能和绩效的制度,一方面通过选择有利于维护封建统治的考试内容,将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有效灌输到应举者的头脑或思想中;另一方面以强有力的组织测度对举子们的德、学、才、识进行甄别,选拔出符合封建统治需要的合格行政人才,使封建社会人才得到有效配置,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目的。它实际上是一项划分“治人者”与“治于人者”的重要制度,无论从治人者的长治久安出发,还是治于人者的人心向背来说,都需要对科场舞弊予以高度重视。这在客观上迫使统治者们必须不断巩固和完善舞弊防治的措施,提高惩处力度使科举制度更好地维护统治阶级的统治。
对统治者而言,尽管绝大多数举子都会名落孙山,但他们只能怪学识不够或运气不佳,而相信程序是平等的。统治阶级实际上围绕科举制度创造着一种生活方式和信念——利用公平竞争让举子们获得一种满足感,此时科举制度实质上成为一种带有奴役性力量的协调工具,统治者以经济利益为驱动目的把封建社会精英约束在考试制度上,依此获得社会精英对国家意志的认同,使社会精英归顺甚至依赖封建统治。这在主观意识形态领域也迫使统治者采取严厉手段维护考试的公平性,可见,无论是客观形势还是主管设想,都要求科举制度体现出“至公”。
而对举子们来说,利益显在使科举制度拥有了巨大的魔力,一旦中举及第便可迅速提高社会地位,获得通过一般途径难以取得的诸多政治和经济利益,这时科举考试上升为一种获取社会资源或地位的手段,推动着举子们铤而走险进行舞弊,“前赴后继”地千方百计打破公平秩序,从而使得考试舞弊从偶然状态成为经常状态。在政治设想和社会现实强烈反差面前,我们不难理解科举考试舞弊与防治的本质及其推动二元矛盾不断发展的根源所在。
三、现实借鉴
从共时性角度看,科举制度虽于清末废止,但舞弊与防治基本的关系结构与现代考试制度并无本质区别,一些重要的考试要素在二者之间仍可以找到相对应的层级、位置:“至公”仍是设置和施行考试制度的首要目标;考试制度仍拥有巨大的社会权重;人情、关系、面子、权力、金钱或人际关系仍干扰着考试的秩序;夹带、替考、抄袭等舞弊手段仍以相同的形态复活于现代社会;科举考试所实行的闭卷、密封、监考、回避、入闱、复查至今仍为现代考试所沿用。只是现代考试制度已经不可能也不会象科举制度那样成为应试者唯一的梦,但它仍关乎应试者拥有、享受各种社会资源的机会,是社会进行利益分配的一条重要途径和手段,其作为维护和体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秩序的调节阀作用依旧存在并在某些领域显得更为重要。一些大的国家级、大规模的选拔性考试,如高校招生、干部升迁、人员聘任、资格准入还承担着维护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的责任,如不能有效地维护良好的考试风气,很容易产生尖锐、剧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同时,作为一种制度,考试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综合效益,满足国家、社会、个人等多方面需要。这同样需要考试制度完成强化其活动的有序性、规范性来实现自身的功能,尽全力提供平等参与的机会,使人们能尽可能平等地享受程序公平,进而通过树立良好的考试风气,对社会价值取向起到良好的导引作用,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承担起更多保障和建设公平正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提高对考试舞弊危害性的重视程度,加强考试管理的严密化、严格化,是现代考试制度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
另一方面,如果从历时性的角度观照这对矛盾,科举防治舞弊除了注重法规建设外,还形成了与法规相配套的技术措施,在主考官选拔、考场的布置监督、考试内容、形式与阅卷评分等各个环节都发明和采用了各种措施,籍此维护科举制度的良性发展。如不如此则千年科举积弊甚深,“盖不有此严刑峻法,恐弊端更甚,不克维持至清末。”[3](P371)而处于更高级社会经济结构中对抗性矛盾已发生了显著的变化,随着考试制度在社会中的地位日益重要,舞弊内容被不断赋予新质从而发生新的震荡和变迁,其内部诸构成要素的状态及社会对考试的认识等外部条件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从而导致了矛盾双方的发展、格局、态势又有了新的重要变化。这都推动着考试舞弊的蔓延和扩展,并呈现出一种旧痼新疾相加的趋势,比如随着考试使用范畴越来越广,考试在现代社会影响力已经被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考试制度已经成为社会进行静态结构分层和动态人员流动的重要手段,人们逐渐把考试视为一个具有特殊性质和功能的工具,这种在经济利益推动下产生的舞弊动因使得考试舞弊难以根除。与此同时,信息传播技术与舞弊的融合为舞弊加速发展提供了客观的物质基础并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使考试舞弊长期得不到有效地遏制,而现有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心理并未真正认识到舞弊的危害性而难以形成强有力的纪律约束和自我约束。这说明现阶段不论是主观促发因素还是客观制约因素都对考试舞弊防治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亟需社会、考试制度和个人正确认识舞弊对考试良性发展的制约性及其对社会发展的深层撞击和影响,采用持久的、大力度的措施来协同应对。当然,在现代文明社会中不能采取野蛮措施来防治舞弊,而是需要我们借鉴科举时代舞弊防治的经验和教训,从知识、技能乃至道德、规范等角度关注考试制度各种人文显性的发展趋势,在他律和自律两个方面依靠道德和法律互摄整合而形成的综合效能,转变“见招拆招”的被动解决办法,有力应对考试舞弊随社会发展而变化的新情况。
[1]肖祖法.大规模选拔性教育考试作弊问题研究 [D].福建:厦门大学,2002.
[2]钱穆.国史新论 [M].北京:三联书店,2001.
[3]谢青,汤德用.中国考试制度史 [M].合肥:黄山书社,1995.
The exam ination system of corruption,the essence of control and the reality revelation——an double visual angle of diachron ism and synchron icity
L IU Chao
(From Hebe Education and Examination College,Shijiazhuang 050000,China)
Examination system is full of corruption to against corruption since being created,if heckle this more than thousands of years’struggle of evolution to be a s imple nature,which need to dig for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historic and hereditary factors use the synchronic character as visual angle,can seek the essence of reality,and achieve important reality revelation ofmodern examination system prevent corruption through reality and variability
imperial examination;test;corruption;revelation
K207
A
1673-9477(2010)03-0099-03
2010-09-12
刘超 (1975—),男,甘肃天水人,副研究员,哲学硕士,主要从事考试哲学、非学历证书考试研究。
[责任编辑:王云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