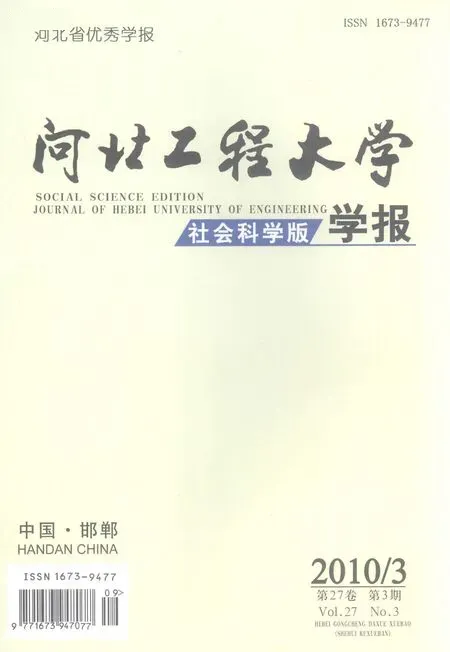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2010-04-07王晓文
王晓文
(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山东济南 250021)
论现代边地小说的文化价值
王晓文
(山东省委党校文史教研部,山东济南 250021)
边地小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独特的文学样式,自身蕴含着特有的文化价值。但是,长期以来边地小说的价值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掘,一直处在一种遮蔽状态。因此,论文秉持生态文学观,运用对话理论,从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的互动来剖析边地小说存在的文化和文学意义,由此体现出多元民族文化形态互补的重要性。
对话;交融;边地文化;汉儒文化
对话而非对抗这是进行文化交流最合理的方式,也是获取双方信任与理解的最佳前提。“对话一定不能够被视为一种说服的开场白。我们也不应当将对话作为解释我们自身立场或表白我们自己信仰的机会。毋宁说,对话是扩展我们的视野,深化我们自我反思以及开拓我们文化意识的机会。对话的本质特征是一种倾听的艺术。并且,只有通过面对面的互动,我们才能够作为合作伙伴开始相互理解,以便容忍、认可、尊重、欣赏并庆祝差异。”[1]而且“在文化全部实有之中,我们不可有意或无意把我们认为‘好的’或‘要得的’看作是文化;而把我们认为‘不好’或‘要不得的’看作不是文化,而只是‘历史中的偶然’。”[2](P17)因此,边地文化与中原汉儒文化也需要在相互包容中获得最佳的交流效果。
一
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来看,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北方诸非汉民族在历史长河里一次又一次大规模的进入中原农业地区而不断为汉族输入了新的血液,使汉族壮大起来,同时又为后来的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多元因素。这些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3](P20-21)而且“中国历史上,正统的王朝都是建立在农耕基础上的王朝 ,如夏、商、周、秦、汉、六朝、隋、唐、宋、明、清。即使是北朝及五代时期的诸政权、元朝、清朝的建立与游牧民族有关,但其政权的基础仍然是农耕”。[4](P13)这不但从自然生态的角度阐释了农耕文化重要性,还表明了中原文化的主导位置。因为农耕文化的主要存在地就是中原地区。“在我国历史上,统一不能从血统着手而要看文化高低。文化低的服从文化高的,次等文化服从高等文化,而文化最高的是汉人中的士族。要统一汉人莫过于推崇士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行汉化,在与南朝争取文化正统地位上,做得相当成功。”[5](P230-234)边地少数民族统治者要想统一整个中国必须要承认汉儒文化的正统地位,才能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所以,在历史上,少数民族文化有意识的吸收接纳汉儒文化。汉儒文化也为边地输入成熟的文化理念,影响着边地文学的发展。“历朝采用的中央集权制使得‘中央——四方’这一政治地理观念延续下来,这就影响了文学。与都市政治相对的则是边陲政治。边陲政治是产生边塞传说与边塞诗歌的温床,像李广难封,汉妾辞宫的传说,像‘日光寒兮草短,月色苦兮霜白’之类的描述,则透视出边陲政治那邈远厚重的历史文化氛围。与都市文学相比较,边塞文学肩负着正义与苦难,所以总是以苦涩为多,但这种苦涩也仍然具有永恒的魅力,它虽然粗粝,依然豪放,即使荒寒,总有春温。”[6](P161)
边地文化的混杂性与现实功用性使得这种文化缺少中原汉儒文化的理性与严谨。而且由于这种文化的内在结构成分的不稳定,使得其内在构成与外在表现形式上都呈现出发散的文化特性。这样就使得它的活力因素相较中原汉儒文化来说更多一些表现也更突出一些。自由、活泼、放达成为此种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因此,这种文化对于人性的约束相对宽松,允许较为自由的宣泄人性的本能冲动,认同更接近于自然化的人类生活方式。它不像汉儒文化那样经过了五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历程已经形成了超成熟稳定的体系,具有强大的控制与约束能力。边地文化对人的控制并不严密。即使像周文笔下的川康边地那些“实力派”人物也只是依靠着蛮强之力来压制别人,并不能像汉儒文化一样从精神上扼杀人。所以,边地文化孕育出来的边地人虽然粗野但是朴质。自然而生、自然而长的生存状态造就出一群相对自由的生命形态。从文化的辐射力来看,汉儒文化覆盖了几乎整个中原文化区域,成为封建帝国意识形态的基础。它突出强调一种理性的人生追求,特别是对士大夫阶层要求他们修身养性、克己复礼、中庸处世。对于社会下层民众,虽然没有那么严格的儒家礼教修身要求,但是这些思想也渗透进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这样整个中原文化区就在汉儒文化的操作机制中运转。而且汉儒文化的过度理性还极大束缚了人性的自由发挥与生命潜能的充分释放,使得中原文学中出现大量的性格扭曲变形的人物。以至于鲁迅尖锐地指出中国四千年的历史是“吃人”的历史。这种文化形态在无形中淹没了很多无辜的生命。像鲁迅作品中的祥林嫂、魏连殳、子君;巴金描写的牢笼般的大家族中诸多年轻人的生命等都是被这种文化给“吃掉”的。就连端木蕻良笔下的边地草原由于受到汉儒文化的影响较深,其游牧文化的特征也渐渐消退。边地小说中少不了穷困潦倒的底层人的形象,但是这些人物在精神内涵上却比较自由。所以,一些被中原文化排挤出去的“可怜人”往往会选择边地作为避难所。艾芜的《南行记》中那些生活的流浪者就是典型的例子。这种不同民族之间人口的流动与迁徙,促使文化的互动也频繁起来,各种文化交混在一起形成一种杂交文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这种互动对中国文化母体来说是有益的。“中原文化要维持它的权威性、维持它的官方地位,它在不断的论证和发展过程中,自己变得严密了,同时也变得模式化了、变得僵化了。这个时候,少数民族的文化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不同的文明板块结合部特有的开放性,就可能给中原地区输进一些新鲜的甚至异质的、不同于原来的文明的新因素。”[7](P20)由此看来,各种文化形态的对话与融合大大有利中国文化的再造与重生。边地文化中包含少数民族文化的成分,而且少数民族文化的因素可能要超过汉儒文化的比重。而且边地文化空间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相比汉儒文化,少数民族文化就长期处在一种边缘状态。当然,这并非表明边地文化等同于少数民族文化,而是说边地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有文化共性。二者都具有自由活泼的特质。边地文化既可以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比照也可以与中原汉儒文化互为参照。这样,中国多元文化的碰撞、交流直至融合的文化发展过程,可以产生更多新质文化因素从而激发母体文化的活力,使我们的文化更具有竞争实力。
二
文学作为反映特定文化的叙事载体既能抽象的体现作家的文化理想也能具象的表现文化的细节。因此,研究边地小说的意义,一方面在于通过具体小说来呈现边地文化,另一方面也将中国作家的边地空间体验挖掘出来。中国不缺少边地,也不缺少表现边地的文学作品。若要将文化中国完整的呈现出来就需要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进行有效的对话。在双方互动中才能发现我们的主流文化存在哪些问题,才能够不断的补充新质活力因素。回到文学这个主题上来说,古往今来那些文学审美价值较高的作品往往都是多种文化因素交织碰撞的产物。四大文学名著之首的《红楼梦》至今仍然是中国文学的骄傲。现代文学中,沈从文的《边城》、《长河》,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马子华的《他的子民们》等都是现代文学丰美的收获。除了对话,包容也很关键。如果当初中原文坛拒不接受沈从文那些异族风情的边地小说的话,城里人是不会知道中国版图上有湘西这个地方,也不会领略到湘西多民族混居的风俗人情,更不会欣赏到《边城》这样的经典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也就缺少了一个拥有独特人文思想的优秀作家。当年若不是鲁迅的提携,巴人的大力肯定,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不会直立起来。它仍会沉寂在塞北,伴随着岁月的流失而荒芜衰老。蹇先艾的川黔边地的原始与压抑的乡村景象,如果不是鲁迅的慧眼识珠,也只能沉默在崇山峻岭封闭的贵州边地。周文描写川康边地同样也是得到鲁迅的首肯后才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农村工厂的题材自然重要,但当中国每个角落都陷入破产的现在,别的题材也还是很需要的。”[8](P423-424)因此,主流作家的认可与鼓励是边地作品涌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当然,如果上述这些作家没有主动走出“边地”的包围,感受中原文化的魅力并主动接受现代文化的洗礼,相信中国现代文学会单一、沉闷很多。“多民族文化融合所产生的综合功能,由于各种文化基因嵌入的位置、配比、深度等等的差异,就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文化范式。因此,如果我们以文化范式的角度来研究文学的话,那么民族之间的胡化、汉化的问题就很值得注意。”[9](P24)汉化、胡化的相互交流融合就是进行文化对话后的结果。
谈到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就是以汉儒文化为主体的文化,而其他文化样态则都是边缘文化或者说次要文化。但是,在少数民族聚居区,汉族则被看作为“少数民族”,汉儒文化也不再是主导文化,而转换为次要文化。在这种情况下,汉儒文化往往会失去自身的特征而被少数民族文化所收编。在边地文化空间,汉儒文化不再是具有强势特征的中心文化而是与少数民族文化混杂在一起而出现。这种状况在边地小说中是通过不同的社会阶层所持有的思想鲜明体现出来的。蹇先艾的《到镇溪去》中的那个年轻能干的寡妇春云酒店女老板——王大嫂,如果按照场上老者们的意思应该赶紧嫁人,以免“破坏风化”。这无疑是汉儒人伦道德的体现,而一般的村民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们从王大嫂自身的利益出发,认为她没必要再为亡夫守孝而应该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两种文化在边地空间中产生了交锋。交锋的结果从小说的叙事中可以看出,应该是边地文化占据了主导。王大嫂并没有像一般中原农村的女性一样被强行嫁人,而是自由的选择自己的意中人。因此,中心与边缘的也是相对而言的。中心的存在是因为有了边缘的衬托,而边缘的活力却是中心存在必不可少的动力源泉。中心与边缘在某种条件下会相互转化。但是中心的确立是必要的,中心过多容易造成文化失重。
三
不同文化之间允许善意的对抗,甚至是偏激的矫正,但是多元文化的平等交流是最重要的。在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中,“边地文明往往带有原始性,同时又是几个文明板块之间交叉的地方,几个文明的接合部,所以它的文明带有原始性,带有流动性,带有吸收外来的开放性,不断地给中原文明输入一种新气息。”[9](P44)从文学审美上看,边地文化空间的构成使得作家可以依托这些空间来表达非同寻常的人生体验与生存感觉。这样就在主流中原文学之外增添“另类人生”的文学想象,使中国现代文学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时代与民族特色。通过有效的对话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从中获得文化和文学发展的培养液。在《阿黑小史》中沈从文借边地油坊的“昨天”和“今天”的变化,揭示出历史时空的转变。时隔 6年在《边城》中,他又预言了边城的“明天”。沉迷在母族文化的过往记忆中,他将“时间”拉长,让“空间 ”静止。“今天 ”、“明天 ”和“昨天”的命运既是边地人生的写照,也是乡土中国的命运。周文在《白森镇·后记》中写道:“这个中篇,和在三个月前写的一个长篇《烟苗季》的题材,都是取于十年前我在一个边地所看见的一些生活和人物,边荒的情形究竟多少不同于内地,而且在这个不断发展和变动的社会中。”[10](P719)边地是作者所熟悉并产生深刻人生体验的地方,边地与内地在社会的发展变动中存在着不同之处,这些都成为作者创作的动因,也是剖析边地小说文化及文学意义的着手处。“鲁迅特别反感‘中国的精神文明主宰全世界的伟论’为洋人的枪炮击碎后,又臆想以此‘开化’苗瑶一类的大汉族的自卑、自大;更愤慨统治者对新疆回民、广西瑶民等少数民族‘南征北剿’、‘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一类的‘王化’。他向中国大声喊出了孔孟之道的本质;并宁取边缘化的立场,自我放逐于汉儒文化中心。”[11](P171)鲁迅先生自我放逐于汉儒文化边缘的态度表明他可贵的生态文化观。这种对少数民族文化的包容、借鉴、赏识的大文化观使得鲁迅不但在创作上给了边地作家借鉴模仿的范式,而且这种文化认同也给边地作家极大的精神鼓舞,使他们所持的“边缘化”理念得到了中心的呼应,使他们能够进入以汉儒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圈的视线中。边缘“是在同一时代背景下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区域、民族、社会体系、知识体系之间,从隔阂到同化过程中人格的裂变与转型特征,这是一种空间性、地域性文化冲突的产物。”[12](P48)根据这个定义,可以看出边缘与中心的关系既相互冲突也相互转化。因此,文化之间的隔膜不但会造成文化保守还会形成社会的动荡,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对话是非常必要的。提出“边地”这个文化概念,就是为了在文化生态学意义上凸现出“文化边地”的审美价值,发掘出以往被文学史所忽略的边地文学。这些边地文学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乡村文学。它是从更细化的角度来呈现“中国”的全貌,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学和多民族文学混杂的问题。而且从生态文化学的角度来看,边地小说的研究有助于较为深入的发掘中国文学的“边地”空间,以便在理论和创作上加强这个薄弱的环节,为中国文学的整体提升提供借鉴。边地并非只是满眼荒凉、一派萧条的边僻之地,如果“进入”它的深处,会发现这里蕴藏着无限的生机和活力。而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交融互渗往往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历史上,每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其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从而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13](P147)边地文化由于其驳杂的文化组成因而形成立体交叉的文化结构。它既带有少数民族文化的活力也渗透进汉儒文化的基因,还有自身在历史演变过程中形成的边地特质。边地小说承载了边地文化的精神内涵,作家的文学想象与人生体验成为记录边地发展的最佳载体。
边地小说带着边地独有的气质从“边缘”走向“中心”,为描绘中国现代文学的生态全景增添一份亮色。正是因为边地文化的开放野性的特质才让我们认识到中原汉儒文化的滞重保守的另一面,正是因为边地小说的粗粝瑰奇才使中国现代文学更加丰富多彩。边地文化与中原文化在相互碰撞交织中丰盈着中国文化母体,使其呈现出勃勃的文化活力。
[1]杜维明.儒家传统与文明对话 [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
[2]殷海光.殷海光文集 (第三卷)[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
[3]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20—21.
[4]王玉德.生态视野的中华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A].引自张全明,王玉德.生态环境与区域文化史研究 [C].北京:崇文书局,2005.
[5]万绳楠.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M].黄山书社,1987.
[6]覃召文,刘晟.中国文学的政治情结 [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7]杨义.通向大文学观“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8]《周文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
[9]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 [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10]周文.在白森镇·后记[A].引自中国新文学大系 [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4.
[11]张直心.边地梦寻——一种边缘文化经验与文化记忆的勘探[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2]叶南客.边缘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13]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
The cultural valve of modern r imland novel
WANG Xiao-wen
(The Department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Party School of Shandong Province,Jinan 250021,China)
The rimland novel as the unique literature style of China modern literature,contains the unique cultural value.But the value of rimland novel has not been well-explored.Therefore,this paper based on Eco-literature implications are revealed through the interaction be tween rimland and Han cultures,which shape the complementary importance.
dialog;blending;rimland culture;Chinese meek culture
I207.4
A
1673-9477(2010)03-0085-03
2010-03-25
王晓文 (1979-),女,山东临沂人,文学博士 讲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批评及文化产业。
[责任编辑:王云江 ]